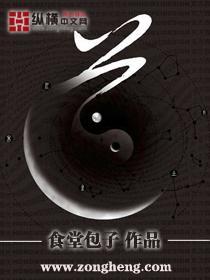第5章 章節
器坊的門口陰森森的。那是建于前朝的一片老宅,陽光下只見灰塵飛舞,裏面黑乎乎的,什麽也看不清。銅的鏽味從裏面發散出來,映得人須眉皆碧。
可宗令白無心看這一切。他的心比天高,一心盯的只有向上的去處。
他身處的那塊地方地處天門街人群的邊緣,人本就少。這時更顯得他們一幹人白衣鹄立,與世不諧。
卻奴心中卻更急切:他知道師傅在找什麽,可如果連師傅都找不到,那就更別提他了!
他看着師傅那一身白衣在這擾擾紅塵中就這麽站着,卻在這一向他敬為離群超卓的身姿裏讀出種說不出的凄惶來。
他隐隐聽說過:宗令白為了一心清寧,很少去聽雜樂。可今日他被迫出來,面對的就是這些雜樂。師傅沒有望向這木樓——賀昆侖的琵琶,那該是師傅不喜歡的吧?可師傅所敬仰的……
卻奴的目光忽下意識的反師傅之道而行之,“向下”地望去。
然後,他吃了一驚,在天門街那麽熱鬧的人群底下,原來,還有這麽多;
——只見一地的灰塵中,有張惶的小孩兒,行乞的癱子,沒有主的狗,泥濘的鄉下人的鞋子,不知為何蹲下來、也許腹痛的人們、還有他們頭頂的汗滴;暗中扣着的手,暗中行竊的手,暗中撓癢的手;可憐巴巴的地攤與守攤兒的老人,地攤兒出奇的荒冷,老人無助地在人群随時要踩踏來的腳下維護着……
……那些快樂下各呈形态的腳:疲乏的、雀躍的、張惶的、支着拐的;麻鞋、布鞋、軟靴、官靴、圓履、方履;各式各樣的鞋面,專門洗淨了才出門的,上面卻踏着別人的腳印兒;還有幹果皮,包幹貨的紙……
可他的眼睛忽然一跳,因為望到那古銅器坊的廊檐底下。
——那兒有一口大鍋。
好黑好大的一口鍋,凹得像沒有光的夜一樣。
銅器坊邊本伸出好寬寬的一道廊檐。廊柱年深月久了,都被雨水浸成了黑色。那口鍋正支在廊檐底下。鍋裏面的鐵黑黑的,火在鍋下面燒,鍋裏正貼着一種還是戰禍時代流傳下來的餅食。
——那叫“姜石餅”,可這時,還有會誰吃這個?
那個攤子生意不旺,跟那餅一樣缺油少鹽的,全沒有一絲蔥花的爆香。
Advertisement
卻有一人在鍋邊不遠處卧着。地上該有塵土,可他全然不避。他身上的衣衫看不出什麽顏色來,略略顯得有一點髒相。今日滿街的人都在興奮緊張着,只有他、看起來那麽落拓頹唐。
因為師傅的白衣,卻奴忽注意起與之全然相反的一切來。
他不由自主地向那個卧着的人望去。滿街的人都立着,面對那場熱鬧,翹着首、踮着腳、還唯恐不及地望着。
——可他為什麽……
卻奴忽很感興趣地觀察起那個委身于地的人。
其實他先前已看到過那個人,卻沒怎麽注意。
今日所有的人都像洗淨了才出來的,只有他挾着一身的風塵。
那像是平日冷漠的娘偶爾高興時給他說起的一些故事和那些故事裏的人:那些人的風塵之味已鏽進了骨裏,他們走過所有的苦難與紛擾的世事,抹不去眼底的烽煙,烤不幹身上的風雨,抖不落過往的塵埃。卻常常、在人所怯縮人所茍安處不肯怯縮茍安着,在盡可放松的時日裏不可放松着……
……那個人盡管姿式疲憊,卻意态舒徐。
這時那人忽擡了下眼,卻奴就見他似有意似無意地瞟了師傅一眼。
相離這麽遠,他不可能看清那人的眼神。可這一眼還是讓他覺得,那一瞟、讓那人的身姿洩出了一種不同于俗的寂寞和一點蒼涼已極的譏诮來。
就是這一眼,跟一把細火似的把卻奴的整個心都點燃了。
他曾努力幻想過真的見到那個人時會是什麽樣子,可無論怎樣的設想在此時看來都已荒唐,反而他這時的姿态讓卻奴覺得無比的真實。
頭頂上賀昆侖的琵琶已彈入佳處,那流宕的快樂似一根無形的線把街上所有的人都串在了一起。
——可他、不在其中。
——仿佛一只鳥……早已鑽出了自己羽翅的牢籠。
街上人影幢幢的,琵琶在響,陽光在人臉上噼叭地打着,到處揚溢着塵土的腥味。
可這一切,似乎都從那個人身上透體而過。
卻奴在心底忽像聽到了“滴”的一聲。
——這一聲滴在了賀昆侖那繁音驟響的琵琶聲上,仿佛從遙遠的世界裏傳來,在遙遠的山洞裏,那兒有石鐘乳滴下,石筍在時間裏靜靜地長,可這一聲突然“滴”過,像這繁華世界裏劃過了一聲與之全不相容的……
——萬載空青。
木樓底下忽然一陣騷動。
卻奴位置高,原較衆人看得清。
只見天門街的人群忽然亂了,十幾個健漢正從街西湧出,他們人人肩上都頂了個高數丈尋的巨橦。
所謂巨橦,也就是雜耍人專用的木杆,其粗細輕重視雜耍人的功夫而定。
那十幾人頂着的巨橦上還纏絲繪彩,如同十幾根炫目的彩柱。露出木頭的地方就露出雕刻,沒有雕刻的地方都用彩綢纏住。他們一路走來,卻全不消停,只見那十幾個人個個全不靠手,那粗達碗許、重逾百斤的橦柱就被他們不停地由肩傳到頭頂,再由頭頂傳到背上,甚或額上、下巴上都可做為那巨橦的生根之地,再左右肩交換着……岌岌可危,卻又穩如磐石。
每當他們一動,旁邊人就會爆出一片驚吓,那是怕被砸着、不由發出的一片驚呼。
那聲音即害怕又飽含着一種刺激的快樂。亂叫聲中,人群已被這十幾個健漢劈得分開。旁觀者腳步個個步履趑趄,慌不疊地避讓。可那十數根橦杆、卻只是筆直朝上地豎立着,紋風不動。
長安人本已見多雜耍,卻少見過如此多的好手聚在一起,而且動作還如此整齊劃一着。
人人避閃間,只見他們已走到距東市賀昆侖那木樓百餘步處。
他們忽停下身,頂着橦的額頭用力一抖,十幾根粗壯的脖子青筋一暴,汗水甩下,那些橦柱就穩穩地落在了他們的肩頭。
這批人一共十二個,立在那裏,有十一個圍成了一個圓圈,圓圈中心還站着一人,這人頂的橦卻又較其它人為粗。
那些巨橦根根筆直朝上,高兩丈許。衆人一時還沒弄明白他們在耍什麽花樣,就見有一個小兒已走到圓圈中心,背着一張網。他忽從中心那大漢的腿上直攀到他肩頂,然後雙手一合,就抱着那橦杆飛竄而上,轉眼之間,已達杆頂。
衆人才叫了一聲好,就見那小童捏着一根亮閃閃的羊腸線,又自背上掣出那張網,那網也是羊腸線織就的,銀光閃閃,孔若魚鱗。然後只見他将那張網結在橦頂上,然後雙腿蜷屈,倒挂在竿上,竟向另一根橦杆上躍去。
人群一聲驚呼,他卻已穩穩地抱住,在那竿頂上又結住網的一角,接着就在那十餘根橦間跳躍,姿式驚險,還牽着那面網,卻分毫不亂。
沒一會兒,那小孩兒就在那十二根橦柱頂上結好了那張銀亮的網。
那網在十二個壯漢與十二根巨橦的映襯下輕柔如無物,銀閃閃的仿佛一場輕華的夢。
網一結迄,那小兒就已滑溜而下,一鑽不見了。
人群中乖覺地已叫了起來:“好啊,西市打擂臺的來了!”
衆人笑叫道:“有趣,有趣!”
卻有人高呼道:“琵琶,我們只要聽琵琶!”
——大家都在猜西市這回會弄出什麽花巧來與東市鬥。
剛才他們被賀昆侖的絕技已逗弄得萬衆一心:此時只要看西市能找來什麽好手,能把賀昆侖那天下第一的琵琶壓下去!
叫嚷聲中,只見街西又穩穩地走出了兩個人。這兩人也都是壯健小夥兒,卻不頂橦,倆人兒合夥兒架着一架雲梯。那雲梯直豎,中間纏着軟索,同樣纏絲繪彩,竿子卻是兩根紫竹。他們走到憑空搭起的網邊上就停了下來。
然後,只見一個女郎在他們身後袅袅娜娜地走出,不發一語,擡步即起,緣着那梯上軟索拾級而上。
她素襟窄袖,身上并無多餘裝飾,梯子兩側卻彩帶飄飄,随風招搖。衆人還沒看清她臉,就已為她這踏絲步雲的風姿傾倒。
那女郎也着實輕盈,雙腳如履平地,全不用手扶那梯子,像乘着一條絲織的天梯般憑空飛渡,直向那橦頂的網上行去。
那女郎手裏挾着一個素囊,直到她登至那張網上,才沖衆人略微颔首一笑,就此跽坐于網。
——這橦竿當然沒有賀昆侖所坐的東市木樓搭建得高,那女郎自有一種不倨不傲的風度,直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