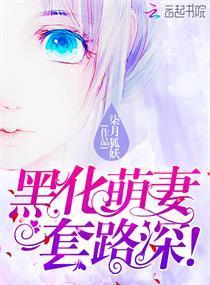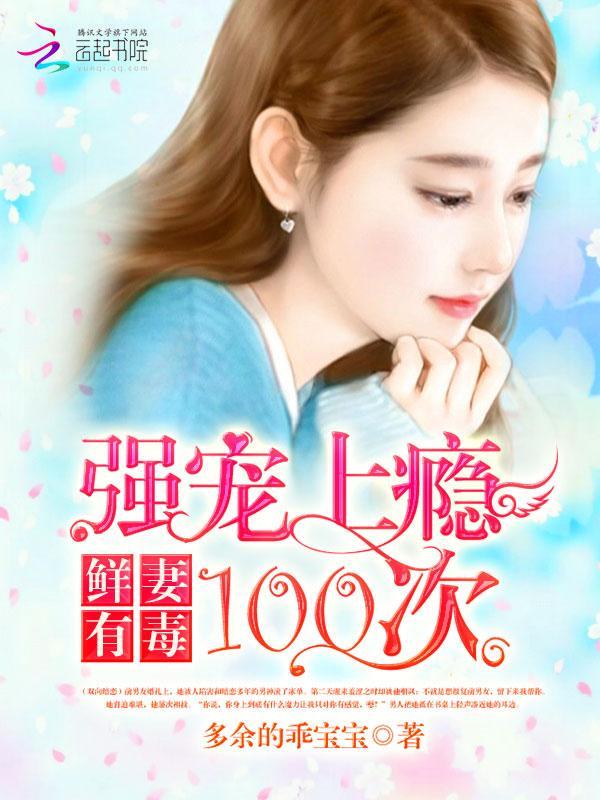第13章 新紙廠開工
? 吃過早飯,李代聰便急匆匆奔紙廠而去。
今天是新紙廠開工的日子。他作為土生土長的第一位抄紙師傅,那種神聖的責任感與自豪,使他的腳步變得格外的輕快。
時間已是農歷四月。群峰吐翠,山花爛漫,生機盎然。門外的燈杆坪,右邊的李大墳園,樹木的新葉在暖暖的微風中搖曳;房屋邊、地坎上,三三兩兩的李樹梨樹,花謝果出,頂在枝頭;地裏的油菜已是菜莢,蒜苗變成了蒜頭,播下的瓜果,已發芽生長,牽枝伸蔓。濕潤的空氣,混和着淡淡的土香,撲面而來。
他走下左邊一個小坡,經過杜文龍的門外,直到公房的曬谷坪。放眼看去,輕霧之中,天馬山那高大巍峨的馬頭,許許如生的馬鞍,圓圓的屁股以及長長的尾巴清晰可見。彎彎的蒲江河靜靜地抱着一片灰白,一片碧綠,一片亮光從曬谷坪腳下的樹蔭裏流去。黃沙壩裏已經是一派春播春種的繁忙景象。
過了公房,跨過一條小溪,就是他老丈人王國光的家。看到老丈人的房子,他心中總會湧起一種莫名的滋味,也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老婆來。新婚之夜的震憾,還時時襲擊着他的心。這種震憾,每每帶給他的,是無盡的快樂……
王國成已經在門外了。
他們到達紙廠的時候,還沒有人。他們來到漚着的麻堆邊,一股帶着濃厚石灰味的微微的熱氣拂着他們的臉。李代聰伸手拉出一匹麻來揉了揉,正合适。他們來到廠房裏,做着開工前的各種準備。
廠房是全木架,四坡頂,小青瓦。四面沒有牆壁,也沒有圍欄。中間地面上安裝着一副平碾:一個中間稍高,四周稍低,周邊上翹的青石拼就的大石盤,盤上鑿有鋸齒樣的斜紋;中心矗着一個大木柱;一根湯碗大小的硬木拖着圓柱形的碾砣,一頭穿在大木柱上,另一頭套着一副枷端。廠房的兩頭,檐口邊上各有一口大石缸,一個大木架。
李代聰看了看水缸,摸了摸木架滾筒,搖了搖套着枷端的碾砣,臉上露出滿意的微笑,他自言自語地說道:“這杜如泉還不枉自是木匠的兒子哈!”
杜文龍來了,王國林來了,劉顯文來了,李代聰的老爹李世民來了,王國君也來了。
這是中隊上的一件大事情,中隊上大大小小的領導,還有一些看新鮮稀奇的男男女女也來了。跳得特別歡的,是一群小孩子,盡管他們并不知道大人們在幹什麽。
招娣也來了。她站在人群中,看着李代聰把冒着熱氣的竹麻從麻堆裏掏下來,拿背篼背到廠房裏,倒進碾子裏,鋪勻了,然後牽來一頭大牯牛,套上,一聲吆喝,牛拉着大石滾子吱吱呀呀地轉起圈圈來。伴随着牛蹄子的踏踏聲,碾子架架的吱吱聲,石滾子的轟轟聲,竹麻很快就變成了麻渣,麻渣很快就變成了麻漿。她心裏那個味啊,那就是甜唏唏,麻酥酥,喜滋滋的。
說來也真是怪。自從她嫁給李代聰後,以前的那些毛病真的就都沒有了。一切的一切與個正常的女人沒有兩樣,還顯出更多的羞怯與妩媚來。這使李代聰心中那快沉重的大石頭一下子落了地,生活也更加地充滿了溫情與希望。
李代聰和王國成時不時地抓起正在碾碎的竹麻,捏一捏,揉一揉,判斷着柔軟細膩的程度。當太陽從柴桑嘴上照着紙廠的時候,第一碾紙漿碾成了。
李代聰拿了一只大鐵皮撮箕,把碾好的麻漿從碾盤裏撮起來,倒進裝滿水的大缸裏。他左腳站在缸邊,右腳放在順缸的那根木頭上——這是最便于用力的姿勢——左手握着竹棍的中間,右手握着竹棍的上頭,在水缸中來回攪動。從內側輕輕地推過去,然後用力從外側飛快地劃過來,再推過去,再劃過來,水缸裏便顯出類似橢圓的軌跡,發出“嗬”——“嘩”——“嗬”——“嘩”的聲音。在這“嗬”“嘩”“嗬”“嘩”之間,竹麻砣砣漸漸變成了竹麻漿漿。
缸子前面的坡坎上已經聚集了好幾個人,有王海華、杜如泉、蔡金良這些小夥子,還有鄒雲英翠翠等大姑娘小媳婦,正看着李代聰的動作,聽着他摻漿的嗬嘩聲。
Advertisement
“大姑爺,你那個好學不?”王海華問道。按輩份,他應該叫李代聰姑父。
“好學,”李代聰說。
“拿給我告一盤(試試)!”
“來哇”,李代聰将竹棍遞給王海華。
王海華學着李代聰的樣子,用勁摻攪起來。可他一用力,便推劃出一片片大水花,飛濺出去,濺得圍觀的人們一身一臉,引得衆人一陣陣哄笑。他自己的衣服袖子也潑濕了一大片。他連攪了幾次,依然是水花飛濺。“棰子喽,大姑爺,我看你摻咋就一點水花都沒得呢?”
“你不慌噻,慢慢來嘛,你看哈,這樣……這樣……,這不就行了?”李代聰接過竹棍,給他示範了動作要領。他接過來又劃了幾下,水花依然飛濺。他把竹棍向缸裏一甩,“難毬得整,老子才不學哦!”
“哈哈哈哈,你娃要學會,天上都會掉銀子下來!”杜如泉笑道。
“老子才不學,老子這一輩子都不學,毬大爺才學你這些!”王海華罵罵咧咧地甩手走了。衆人便暴發出嘻嘻哈哈的笑聲。
王國君看了王海華一眼,笑了笑,沒有說話。
李代聰依舊攪拌他的紙漿。在他的均勻而有力的嗬嘩聲中,一大缸紙漿被攪得又細又勻。他把水放滿,再攪攪,取來架子,鋪上簾子,右手提着右邊的提把,左手拇指壓着廉邊,其他手指勾着廉架,輕輕在缸裏一舀,然後左手擡高,右手慢慢提起,水向右邊輸盡,廉子上就粘上了一層姜黃的嫩皮,他提起廉子對着光亮看看,厚薄均勻,透光一致,沒有圪塔。他臉上現出滿意的神色。
“嗬”——“嘩”——“嗬”——“嘩”的聲音,也從王國成那邊傳了過來。
“可以了。”他對着杜文龍和劉顯文說。他提起廉子,翻轉過來,将廉子的邊挨緊兩根豎着的木條,放在厚木板上,拿手在上面細細的抹了抹,然後揭開廉子,姜黃的均勻的現在還不能稱為紙的東些就貼在了厚木板上。
他反複地重複着動作,那厚木板上姜黃的均勻的還不能稱為紙的整齊劃一的東西,變得越來越高,越來越厚,變成墩子了。到天色暗下來的時候,已有一尺多高了。他搬起一塊同樣厚而平整的木板,放在墩子上,向下壓了壓,再在上面放兩塊石頭,就收工了。
到第二天下午,墩子足有三尺高了,一缸子的紙漿也舀完。他在墩子上蓋上那塊厚木板,在木板上放兩塊木墩子,扛起那根硬木大杠,一頭塞進立柱的橫枋下,另一頭用大繩子将它與滾筒套在一起。他拿來雕杠穿進滾筒的圓洞裏,向下一壓,紙墩裏的水就被擠壓出來了。
當大繩收緊到一定程度時,他解開繩索,加上一兩塊木墩,再如法炮制,紙墩裏的水就被擠得越來越少了。如此幾次,滾筒再也轉不動了。那紙墩,則由姜黃色,變成了淡黃色。
他松開了大繩,扛開了擡杠,拿開了木墩,揭開木板,把紙墩翻起來。啊,這是他在中隊紙廠裏舀出的第一個紙墩!也是他跟着紙匠跑以來的第一個由他自己親手舀出來的紙墩!在這個中隊上,也只有他和王國成才能夠舀出來。他的心中,充滿了成功的快樂,不免有些自得起來。
他拿來一根背辮子,套在紙墩上,背起來,大步向他老丈人王國光家走去。他老丈人家,除老丈人老丈母外,就只有一個小姨妹了。人口少,房子多,三個人住着一個大四合院。中隊上商量,就把揭紙晾紙的場所定在他家裏,并派人四處尋找了很多細長的杉木,剝了皮,曬幹,作為晾紙的晾杆放在了屋裏。
李代聰背着紙墩來到老丈人家裏時,天已黑盡了。小姨子已經把晚飯做好了。叫他吃飯,他也沒推辭。就着炒雞蛋,陪老丈人喝了兩杯,然後回家去了。
早晨,天還沒亮,招娣就把一碗熱氣騰騰的荷包蛋端到了他的床前。“代聰哥,快起來。”他坐起來,披上衣服,招娣就把碗遞到了他手裏。他拿起調羹,舀了一塊蛋放進嘴裏,一股甜密從喉嚨飛快地浸進了他的心裏。他擡頭望望招娣,正微笑着看着他。
“甜不?”她問。
“甜。來,我們一起吃。”他舀起一快,遞到招娣嘴邊。
“我不吃,你吃。”招娣說。
“來,聽話。”
招娣滿臉幸福地湊過來,他把一大塊雞蛋放進她的嘴裏,看着她慢慢吃下去。他會心地笑了……
他穿好衣服,走出房門,在早已燒好熱水的鍋裏舀了一盆水,洗了臉。招娣已經把飯菜端上桌了。他吃了一碗飯,跟他父母說了一聲,“阿伯阿媽,我去出工了哈。”出了龍門,徑直朝他老丈人家走去。
他老丈人王國光已是三代單傳,上輩人十分看待,從小就吃得好穿得好耍得好,二十七八了還沒有做過什麽象樣的活路。讀了不少的書,也算是一個小知識分子。但是,生性就不好善樂施,有時候也耍點自己的小聰明。當然也不欺軟怕惡,只願意過自己的小日子,似乎對一切的事情都不管不顧不聞不問。解放前是這樣解放後也是這樣。他的一生生有三個子女,大女兒就是李代聰的老婆招娣,兒子在去年死了。三女兒還小,也就十四五歲。
他那個小舅子都十七八歲了,在蒲江中學都讀到高中二年級了,成績也很優秀。誰知道得了一種什麽病,在華西醫院住了一個多月,好了,回來繼續讀書。不久後病又返了。再去住院以後被抱回來的就只是一個骨灰盒。這使他老丈人一家人悲痛萬分。一片高大明亮而充滿甜蜜希望的天空,瞬時間跨蹋了,全家都被昏暗籠罩着。大年三十,他老丈人買了幾張白紙,自編自寫整了許多對聯,滿屋子都貼上,以此來悼念愛子,喧洩他對生活的追求向往失望無奈與凄涼。這讓看到的人們無不哀嘆,也生出諸多的同情來。這次他老丈人同意把中隊的晾紙場放在他的家裏,很有些出乎人們的意外。但反過來一想,也就不難知道原委了。
李代聰把安放紙墩的架子擺好,把紙墩抱起來放在上面。作好各種準備之後,開始了他揭紙的工作。他把紙從紙墩上一張張揭下來,整齊地貼放到旁邊斜着的木板上。那個揭紙的動作,從一只手啓一只角,到另一只手啓下另一只角,再到兩手拉着紙的一頭從上到下揭下來,再整齊地貼到另一個木板上去,優美而娴熟,似乎是在舞蹈。
貼到一定的厚度時,便将它們提下來,按相應厚度一疊一疊地晾曬在晾杆上。揭完一個紙墩,也需要兩天時間。揭完後,再去舀墩子,背回來揭,揭完了再舀。這麽循環往複,兩三個月下來,王國光四合院廊檐上旮旮角角都晾滿了。
李代聰把晾幹的紙取下來,按八十張一疊,或者一百張一疊,數出來,把兩頭向中間一交,就是一刀紙。二十刀紙捆在一起,就是一捆,兩捆就是一擔。打谷子前,李代民就捆起了十來擔紙。中隊上安排人背到公社供銷社去,第一次就買了三百多快錢。
幹部們笑了,社員們笑了,李代聰還有他老婆王招娣就笑得更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