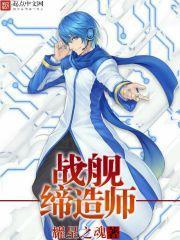第54章 遺言
小新街也在珠江北岸,和花園酒店不過20分鐘車程,說是街,其實是個社區,崔景樓就在小新街社區裏的一條小路上,開了一家老城區裏常見的廣式茶樓,樓下待客,樓上住人,每日裏人來人往,嘈雜喧鬧。
為了盡量不打擾生意,也不被打擾,譚宗明把會面安排在了午後兩點,生意最清淡的時候。之前去永州和張北,兩人都是輕車簡從,這次譚宗明傷勢嚴重,不得不帶了一群人,但到了茶樓外面,他還是把他們都留在車裏,和汪曼春低調地進了茶樓。
因為樓梯狹窄,譚宗明又拄着拐,他們在茶樓一層的包廂裏落座。茶樓簡陋親民,說是包廂,不過是屏風隔出的一個小角落,一碟榴蓮酥,一碟越南春卷,兩碗紅豆牛奶龜苓膏,廣式下午茶冒着獨特的香氣,屏風外面傳來咿咿呀呀的粵曲背景音。
只比崔孺鏡早出生五分鐘的崔景樓,看上去比妹妹足足大上十歲。和崔孺鏡一樣,他長着酷似明臺的鷹鈎鼻,而因為性別相同,那張臉就更像是一個老了以後的明臺,只是目光不再清澈,肩背不再挺拔,若說崔孺鏡還帶着明鏡那樣矜持高傲的風度,六十多年廣州市井的生活,崔景樓身上早已沒有半分明家的清貴氣息。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姓崔,以為自己沒名沒姓,被爸媽——其實是我的養父母——扔在廟門口,我當了五年小和尚,解放後誠叔才找到我,告訴我生父生母的身份,原來我爸爸犧牲時情況比較危險,很多地下黨都緊急撤離了,誠叔沒來得及接我,我就跟養父母失散了。誠叔解放後跑遍了京津河北山東,好容易才找到我。我們先去了永州,他受我爸爸的囑托,在潇水邊給一位叫于曼麗的姑娘立了個衣冠冢,然後又南下廣州找我外公。沒想到程家早就離開大陸,我們無依無靠,就想回永州,至少碼市鄉還能接收。
“可是那時誠叔身體已經不行了,他的舊傷一直沒好,為了找我整整奔波了一年,離開廣州沒多久就再也走不動了,每天大口大口地咳血,我們只能又回到廣州。我在一個小餐館做學徒,誠叔領一點救濟,就這樣勉強維持生活……”
譚宗明問,“明誠叔公是傷殘軍人,沒有特殊照顧嗎?”
崔景樓搖頭,“他的接收地是永州,要領津貼就得回永州去領。”
汪曼春默然,譚宗明又問,“後來你們一直沒回過上海?”
“沒有,誠叔到去世都沒離開過廣州一步。”
汪曼春問,“他……他和您提過明家嗎?”
崔景樓悠然嘆道,“提,怎麽不提,他跟我說最多的就是明家。明家有大姐,大哥,還有個最調皮不聽話的小少爺,他說我淘氣的樣子,和我爸爸小時候一模一樣……他說當年的上海灘,明家有財有勢,大富大貴,可為了抗戰的勝利,為了新中國,這個家庭犧牲了整整一代人……”
汪曼春心中一恸,何止是犧牲了一代人,明家連後代都只能更名換姓,流散四方,互不相識,無法團圓。有財有勢,大富大貴的明家,已經從上海灘,從中國歷史中永遠地消失了。
“誠叔說明家有三個孩子,我,孺鏡,還有明樓伯父的孩子譚正,孺鏡不在大陸,我是找不到她了,譚正我一定得找到他。可誠叔去世的時候我才十四歲,吃飽飯都不容易,哪有本事去找人?我一個人到處打散工,好不容易攢了錢,還要娶妻生子,等孩子長大成人,自己也老了。”
崔孺鏡是無心,崔景樓是無力,譚正有心有力,卻完全沒有頭緒。明家的三個後人就這樣天涯海角,彼此失散在茫茫人海中。
“九三年,突然有人從香港過來找到我,說是我妹妹孺鏡派來的。孺鏡把我們接到香港團聚,我和妹妹不到周歲分開,再見面,都已經五十一歲了。孺鏡問我願不願意定居香港,我在廣州住了一輩子,不想走,她就給了我一筆錢,幫我弄了這個茶樓,你們不要看這門面小,珠江北岸的地價可貴呢!”
Advertisement
老人略有些倔強的語氣,把汪曼春和譚宗明都逗笑了。茶樓确實不大,陳設雖然翻修過,店堂布置和牆上的例牌都還是十多年前的樣式。見兩人打量店鋪,崔景樓又道,“你們都見過孺鏡,她不太好相處,可對我還是不錯,一直想幫我擴建茶樓,我不要,我文化不高,也沒什麽本事,做這間小店剛剛好,再大我也做不來,白白浪費她的錢。反正我有吃有穿,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孺鏡的錢也是何家的,我跟她從小不在一處長大,老了也是她先找到我,我哪好意思總要她來贊助?各人有各人的路,沒病沒災平平順順就好了,我沒有那麽高要求。”
老人絮絮叨叨說了一通,又把手機裏一張全家福翻出來給譚汪二人看,“這是我兒子媳婦,今年都是四十六,這是我女兒女婿,剛過四十,這是我孫子,快考大學了,這是外孫,剛過完十二歲生日。這是我老伴,今天不在,社區有個什麽歌唱比賽,跟她那些手帕交去比賽了……”
和崔孺鏡那冷寂的深宅大院一比,這滿滿當當的全家福裏蘊含着多麽醇厚喜慶的煙火氣。
這是明家最清貧的一支後人,也是明家最熱鬧的一支後人。
汪曼春不由朝譚宗明望去,轉過臉的剎那,才發現他也正好在看她。兩個人目光相碰,都像觸了電似的迅速分開。不是不能對視,只是彼此都能從對方眼中讀出不約而同的羨慕和感慨。
崔景樓一雙老眼瞧着兩人之間轉瞬即逝的火花,摸摸下巴笑道,“我知道宗明是譚正弟弟的孩子,但不知樊小姐是什麽輩分,該怎麽稱呼?”
汪曼春正要開口,譚宗明先回答,“小美祖上姓汪,是明家世交,論輩分算我妹妹。”
呵,姓汪,妹妹。
沒想到崔景樓知道汪家,“汪家有個女孩兒叫汪曼春,和明樓伯父是……是什麽來着?什麽梅什麽竹的……”
汪曼春心頭一震,萬萬沒想到,她還能從這個遠離明家七十年的老人口中聽到自己的名字。“青梅竹馬。”她以微微顫抖的聲音提示他。
“對,青梅竹馬,誠叔就是這麽說的。”
“關于汪曼春,他,他還說什麽了?”
崔景樓笑了,“沒有了,他只說過汪家小姐很漂亮,和明樓伯父的感情很深,就這些。”
汪曼春幾乎要落下淚來。
無論出于什麽原因,他自己一廂情願的理解也好,對明樓內心的參透也罷,無論如何,明誠抹去了樓春那段孽緣中,所有黑暗醜惡的部分,在他留給明家兒女的往事裏,就只有一段愛情最初也最單純的剪影。
“那麽……明誠先生有沒有提過,他們在南京獄中的經歷?……”汪曼春鼓起勇氣,問出此行她最想知道的問題。
“有。可是……”崔景樓長長地嘆息,“他和明樓伯父一起被抓,徐恩曾勸降他們,還拿了報紙給他們看,上面有中央大學教授譚百年原是共.黨分子,投誠國民政府的新聞……”
汪曼春脫口而出,“那是給中.共看的!”
“是啊,誠叔說,徐恩曾逼明樓伯父,反正你也回不去中.共了,不如跟我們走吧,只要你真心歸降,你在我們這裏原來怎麽樣,就還怎麽樣,甚至還能更進一步……明樓伯父拒絕了,他們就用刑,各種大刑,把明樓伯父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就只剩一口氣還在……”
汪曼春的手在桌下攥成了拳頭。
“誠叔說,他們怕明樓伯父自殺,連牢飯都用木碗盛,用手抓着吃,牢房四面都拿棉布包着,明樓伯父跟他們說,不用操心了,他不會自殺的,他要看着這個政府倒臺,看着人民的政權勝利……誠叔說,就連典獄長都說,沒啃過這麽硬的骨頭……”
汪曼春別過臉,她要的真相太殘酷,要用很大的意志力才能鎮定地聽下去。
一只手伸過來,在她握緊的拳頭上安撫地拍了拍,她轉回臉,譚宗明正關切地望着她。
“我沒事。”她笑笑,把手收回來,放回桌面,“後來呢?”
“他們把明樓伯父和誠叔,還有其他幾個被捕的地下黨關在江東門,一直關到四九年四月,解放軍已經打到長江北岸,馬上就要渡江了,準備逃亡的南京政府才将其中的要犯全部槍決,準備槍決其他人的時候,犯人發起了暴動,誠叔僥幸逃出來。他說,明樓伯父是聽着渡江戰役的炮聲走向刑場的,他死得其所,死而無憾。”
汪曼春低頭,漸漸湧起的霧氣模糊了她的眼睛。
“明樓伯父還被逼寫過一張自白書,雖然收走了,誠叔後來默出來了。我拿給你們看。”
汪曼春和譚宗明都是一驚,沒想到,他們還能看到明樓的遺書,雖然,只是經了明誠之手的複制品。
透明細薄的塑料文件袋,被壓得平平整整的陳年毛邊紙,棕黃的粗糙的紋理上,流轉着明誠病弱但依舊風骨嶙峋的筆跡。
“我姓明,名樓,字閣遠,祖籍蘇州,生于上海,我最大的心願,就是活在陽光下,我想讓這裏所有人都知道,我明樓是一個抗日者,是一個軍人,是一個中.共.黨.員。我沒有辜負這座城市,我生于斯長于斯,将來也要埋骨于此,我唯一辜負的就是明家,辜負了大姐和小弟。然而我們上戰場,不是為了求死,是為了求生,求家園與民族的生,為了求生而死,我明樓含笑九泉。”
作者有話要說:
明樓的自白書其實就是一封遺書,應該怎麽寫,我拟過很多文字,最後都棄用了,你們看到的,是明長官在僞裝者中的臺詞,以及顧長官在戰長沙中的臺詞。
致敬山影和正午陽光,以及所有為我們奉獻了好劇的演職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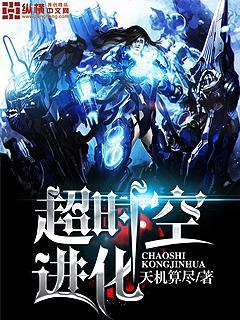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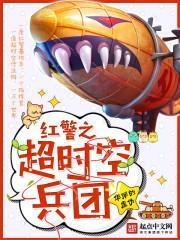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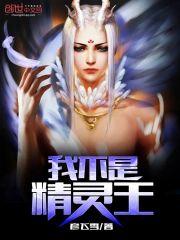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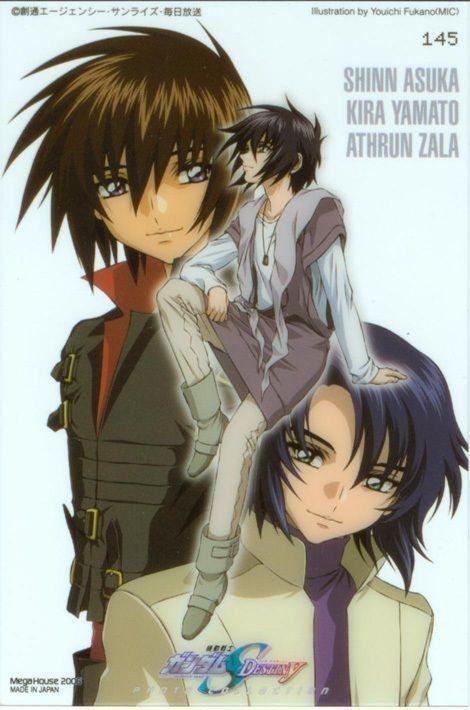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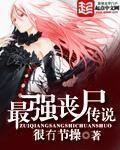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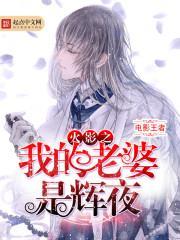



![[神夏+HP]以探案之名](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32779.jpg)
![[綜武俠]俠客們的反穿日常](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2907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