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江華
上海到永州每周只一三五有直達航班,譚宗明和汪曼春都不想等到周一,于是趕在農歷正月十二星期五,登上了飛往零陵機場的飛機。
永州位于湖南南部,潇湘二水彙合之處,下轄兩區九縣,而其中和廣東廣西兩省接壤的正是永州唯一的瑤族聚居地——江華瑤族自治縣,這也是汪曼春推測的,于姓湘繡商人最有可能的家鄉。事關家族秘辛,譚宗明輕裝簡行,沒帶任何随從,和汪曼春在永州市區休整一夜,次日便租車沿着國道207開往江華。
車出零陵區,一路南下的同時也逆着潇水溯流而上。秀麗潇水便如多情的湘女,時而緊貼公路相伴,時而隐入山野丘陵,蜿蜒逶迤,若即若離。湘地崎岖,臨水的地方,公路在上碧波在下,岸邊半人高的白茅,一人高的野蕉,經冬不落迎春又綠,幾株散生的早櫻正是花期,粉白花瓣落入潇水,打着旋兒随波而去。不臨水的路段,車窗外掠過一片片茶園、果園,和尚未春播,還□□着新鮮泥土的稻田,間或又有些旱地裏高高立着的闊葉,一枝一枝,宛若小傘。
“那是荷花嗎,怎麽沒長在水裏?”汪曼春好奇地問。
“那是芋頭……”譚宗明忍笑回答。
“好吧,沒見過。”
譚宗明本以為她只是五谷不分,後來發現她竟然對路上跑的拖拉機,田邊的微型水力發電機甚至種草莓的塑料大棚都觀察得津津有味,不禁大為好奇,“難道你讀的是私塾?”私塾也不至于教出這麽不接地氣的學生。
汪曼春讪讪一笑,微露窘色。離開魔都的水泥森林與複雜人際,她周身的漠然疏離消散不少,這段渺茫旅程開始時的沉重,也在青山綠水的早春鄉間慢慢淡去。在國道邊一處小飯館旁停下來抽煙時,她甚至在他耳邊悄悄吐槽,“大庭廣衆,這也太不雅了……”
譚宗明順着她目光一看,玻璃門上四個大字:“打胎補氣”。
這是三十一歲的樊勝美?真想敲開她那顆漂亮的小腦袋看看裏面裝的都是什麽……
國道路況不佳,車子快到江華時被碎石塊紮漏了胎,前不着村後不着店,譚宗明只能自己下來換胎。湖南二月的寒風裏,他扳螺絲扳得渾身冒熱氣。好容易扳松了螺絲,輪胎卻怎麽都卸不下來,踹兩腳,還是卸不下來。他蹲在車邊叫,“小樊!小樊!”
汪曼春提着保溫瓶從車後轉出來,“熱水。”
譚宗明詫異,“你怎麽知道我要這個?”
“胎卸不下來,熱水澆一澆,熱脹冷縮。”汪曼春學他剛才的眼神,“誰還沒換過幾個胎。”
譚宗明又對她刮目相看了。這女孩子是學什麽長大的?她不是沒駕照麽?
澆完水靜待一分鐘,壞胎順利卸下。譚宗明換完胎,就着保溫瓶裏剩的水洗手。汪曼春握着瓶子低頭給他倒水,額頂幾縷毛茸茸的碎發在風裏晃悠,勾起他一點壞心,“小樊啊——”
Advertisement
“嗯?”汪曼春毫無防備地擡頭,瞬間被他滿手水彈了一臉……
“譚宗明!”汪曼春想都沒想,反手就把瓶裏剩下的最後一點水涓滴不剩,全潑在了譚宗明臉上。
可憐的譚老板二次被潑……
“樊勝美!”
“幹什麽?!”
“我們來談談利息……”
汪曼春拔腿跑了,譚宗明叉腰站着,提着竹籃頂着竹匾的瑤族老鄉從車邊經過,露着滿口白牙大聲地唱着山歌,“舀水行路有高低,一心送妹洗臉的。妹洗一帕哥一帕,別人笑我倆夫妻……”
車入江華縣城,譚宗明和事先托關系輾轉聯系上的一位縣政府公務員接上頭,在這位公務員的協助下找到了縣政府檔案室負責人。時值周末,譚宗明攜汪曼春親自到對方家中拜訪,奉上重禮,再輔以一系列慷慨陳述深情剖白,終于勸得對方同意第二天上檔案室幫他們查找資料。
正月十四星期日,縣政府檔案室,木架輕移,塵埃泛起,故紙堆中譚宗明看到了如下一行記錄:
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一日原中央情報部上海站明誠領人民幣伍拾萬圓大米四十斤布三十尺縣政府往碼市鄉車票一張
以及指示碼市鄉政府接收、安排明誠的介紹信底聯一封。整條記錄末尾還有明誠的親筆簽字,工整清秀,嚴謹有度,只是筆端微微顫抖,不知是心緒不寧還是手勁不足,看在譚宗明眼裏,有種令人心驚的緊張與壓抑。
“碼市鄉就是現在的碼市鎮,離咱們縣政府大概九十公裏。”檔案室負責人友情提醒。
于是譚汪兩人又驅車直奔碼市鎮,鎮上沒有像樣的檔案館,六十年前的記錄蕩然無存,所幸譚宗明口才、人脈與金錢開道,還是找來了一位□□前曾在鎮政府工作過的退休老幹部。
“這麽久的事情啊,我看你們只能找盤乙姑問問了。”
“盤乙姑是誰?”
“老人家剛解放時就在鄉裏打雜,她都不知道的事,咱們鎮上可就沒人能知道啦!”老幹部捋着胡子指路,“盤乙姑老了就回寨子住了,你們去邬石沖找她吧。”
當譚宗明把跋山涉水還挂了彩的破SUV停在邬石沖盤乙姑老太太的吊腳樓下時,已是正月十四晚上七點多了。
八十一歲的瑤族老太太盤着灰白發辮,纏着青绉紗,蓋着織錦頭帕,一邊給他們斟香茶,一邊操着濃重的高山瑤口音悠然回憶,“明誠啊……”
譚宗明端着茶凝神聆聽,汪曼春則整個人都朝盤乙姑挪了過去。
“我不記得這個名字了。不過那時候,真有個軍官到鄉裏來,問我一個做湘繡生意的老板葬在哪。我也不知道啊,他就走了,聽說去潇水邊上立了個衣冠冢,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他後來去哪了?”
“不知道,立完就走了,再沒見過。”
“他給誰立的衣冠冢?”
“不知道,好像是個女的,不知道是不是他老婆。”
譚宗明看了一眼汪曼春,“明誠一直沒結婚。”
“那那個墳現在在哪兒呢?”
“早就推平啦!八幾年修小水電,潇水邊那些沒人管的野墳全都推平喽!”
“當時是誰跟您說他去立衣冠冢的?”
“我一個遠方兄弟,在潇水上打漁的,你們也不用問他,他□□時就死啦!”
“盤奶奶您再好好想想,那個軍官,還有什麽特別的地方?”
“特別的啊……他身體很不好,腿有毛病,一直拄拐,眼睛也不好,還老咳嗽,咳得驚天動地的,真怕他把肺都咳出來……”
汪曼春面露狐疑,“這麽多年的事,您怎麽能記這麽清楚的?”
老奶奶核桃似的臉上現出幾分赧色來,“哎呀……你們不知道……咱們碼市那幾年,總共就接收過那麽一個部隊下來嘛!再說……那個軍官啊長得真好看……我那時十五歲,可從來沒見過那麽好看的小哥哥……偏偏一身的病這不好那不好的,多可惜啊……”
譚宗明想得更多,“明誠級別不低,他就自己一個來嗎?鄉裏沒有人陪着?”
盤奶奶搖頭,“我可不知道他什麽級別,我還以為他是個兵呢,也沒有挂勳章嘛,是一個人來的……不不不,好像……好像還帶着個小娃……”
“小娃?”譚汪兩人一齊叫出來。
“嗯,一個小娃,遠遠站着等他,我也看不仔細……”
“男孩女孩?多大了?叫什麽名字?”
一連串的問題,盤乙姑的回答全都是不知道,不記得了。譚宗明無法強求,對一個年過八旬的老人,六十多年前的事早已淡若雲煙,能回憶起這麽多細節,已是拜明誠強大的個人存在感所賜,若換成個面貌普通的人,他能得到的信息恐怕根本是零。
一切線索在1950年秋天的碼市鄉戛然而止,除了一個意外出現的孩子。能“遠遠站着等他”,這孩子絕對不會是戰後出生,而譚宗明百分百确定,明誠直到被捕都不曾婚娶,何來一個這麽大的孩子?
“這孩子……會不會是爺爺的?”譚宗明謹慎地問汪曼春。
“怎麽可能?!”
說實話譚宗明對明樓娶妻之前的生活完全不了解,父親譚正出生時爺爺已經年過四十,在這之前就不可能有過什麽經歷?汪曼春卻一口咬定,“絕對不可能。”
好吧,不是就不是吧,天知道她哪來的信念如此堅定。那麽明誠到底從哪兒撿的這麽個孩子?又或者他自己無家可歸,所以收養了同病相憐的戰争孤兒?可他腿不好眼睛不好肺不好,一副殘軀又如何承擔起下一代的生活?明明有願意接收他的碼市鄉,他又為什麽帶着孩子飄然遠走?
盤乙姑小小的吊腳樓上,譚宗明和汪曼春面面相觑。再追問下去似乎也問不出什麽了,可千裏迢迢奔波到這遠山瑤寨,要就此罷休,又都有點不甘心。窗外夜色正濃,不知何時下起了淅淅瀝瀝的山雨,落在池塘,屋檐和野蕉葉上,發出低徊綿密的聲音。盤乙姑從火塘邊站起來,摸摸窗下堆到半人高的禮盒,轉身說,“下雨啦,走夜路不安全,你們就在我這裏住下吧,不嫌棄的話,老婆子給你們做點吃的,也不能讓你們兩個娃娃白跑一趟。”
作者有話要說:
別怪我讓劇情在該緊張的時候反而變慢,因為作者想讓汪處和老譚在如畫風景裏好好發展下奸(劃掉)感情……
最後還得再啰嗦一句,正如前面已經說過的,本文的設定,只有譚宗明長得像明樓,而趙啓平長得不像明誠,關媽媽長得不像明鏡,樊勝美哥哥長得不像梁處,應勤長得不像日本兵,2102的女鄰居長得不像朱徽茵,關關的同事長得也不像阿香……不然wuli汪處分分鐘精神崩潰O(∩_∩)O
快留評吧留評吧留評吧留評吧留評吧啦啦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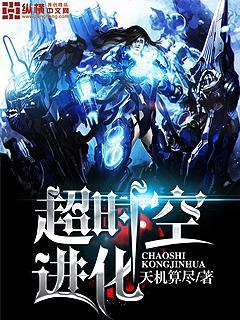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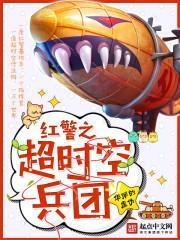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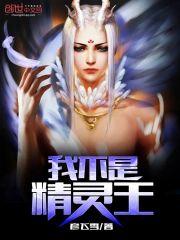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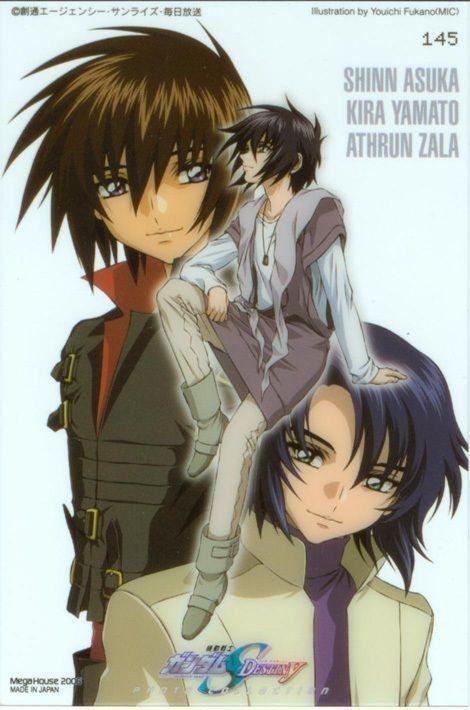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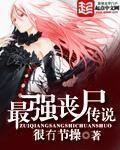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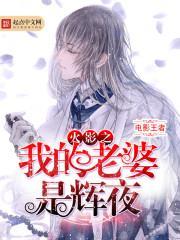
![[神夏+HP]以探案之名](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32779.jpg)


![[綜武俠]俠客們的反穿日常](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2907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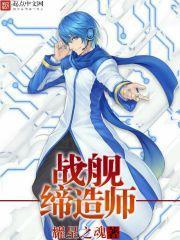
![[綜]我的家人](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3374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