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長安
這般癡纏歪鬧,稍微讓皇帝消除了些戒心。
皇帝又緩緩地搖了搖頭,道:“你總是這樣……罷了,到裏間來陪阿耶下下棋罷。”言罷舉步便朝殿裏走去。太平應了聲是,跟在他身後三步遠的地方。
忽然間皇帝問她:“是阿娘讓你來的?”
太平一怔,下意識道:“是……也不是。”
皇帝搖頭失笑,但卻未曾多說什麽,而是與太平一起慢慢地往裏邊走。太平一面琢磨着父親的真正意思,一面陪着他說些笑話來聽。皇帝今日的心情似乎是很好,不但同她說了許多平時不會說的話,而且還偶爾提到了一些行宮裏的事情。
可以看出來,他這些日子在行宮裏過得不甚如意。
其一自然有太宗皇帝的緣故,其二自然是他的身子一日比一日差了。前些天武後言稱要扶太子登基,這消息他也有耳聞,但細細想來,卻又不大願意了。再加上太宗又……
他們一路走,一路地說着些閑話。後來大約是太平哄得他開心了,面上的愁雲盡皆散了去,連帶着語氣也微微地有些松快。等轉過長廊時,他的心情便又恢複了過來。
再加上太平着實是太了解他了,知道應該如何勸說,才能讓父親心情舒暢。因此到後來,他幹脆笑道,索性讓太平留在這裏陪着他,晚些再回長安成罷。
因為太宗皇帝歸來而導致的那一絲陰影,似乎也悄然散去了。
太平知道父親的心結,因此便故意沒有提大明宮裏的事情,更沒有提長安城的事情,所做的一切僅僅是讓父親感到愉悅且安心罷了。
又過了些天,甚至連太宗陛下也以為,讓太平留在這裏陪着父親,是上上之選。
太平在祖父跟前,從來都是不敢造次的。不管祖父是否遮掩過自己的身份。到後來,皇帝很享受這種女兒在其中斡旋的感覺,有些不願意讓太平回長安了。
自然武後原先的提議,也便成了無可無不可。
這種古怪且又平和的關系僅僅維持了兩個月的時間,便被長安城的一個消息打破了。
太子,登基。
Advertisement
這件事情本就是衆人默認的,因此登基不過是件順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太子登基之後,長安城裏的書信便像雪片一樣飛來。有擔憂太後擅權的,有抱怨新皇行事荒誕的,也有言稱新皇不足,請太上皇回長安主持大局的。皇帝陛下自然是沒有回去,回去的是太宗。
太平揣着明白裝糊塗,在行宮裏留了一日又一日,平時偶爾給薛紹寫兩封家書。至于朝堂上的事情,她一件都沒有插手。太宗陛下與武後兩個肯定有自己的一套,她此時再要貿然插手,便完蛋了。
因此這段時日,太平唯一做的一件事情,便是設法逗父親開心。
大約是太宗陛下留下來的陰影實在是太嚴重了罷。他一走,皇帝陛下便恢複了一大半。
再加上太平是故意要彩衣娛親……哦不,是裝癡扮傻哄父親開心的,因此太宗陛下留下的另一半陰霾,很快便煙消雲散了。過了一些時日,皇帝陛下便提出要回長安。
他在行宮裏住了一個夏天加一個秋天還有一個冬天,實在是快要長出蘑菇來了。
要不是後來太宗陛下來到行宮,他本該在兩個月前便回去的。
是以第二年春天,太平陪父親回到了長安城。
長安城比起先前并無太大變化,除了變得熙熙攘攘一些之外,幾與前世一般無二。不過又過了些日子,她便聽聞前些日子新皇與太後鬧得有些不愉快,連範陽王都攪合進來了。
又過了些時日,她的父親便言稱長安城裏過得不大自在,要去洛陽。
甫一回長安便要去洛陽,顯然是有些不對勁了。
又或是……她父親看出些什麽來了。
太平又試着在宮裏打聽了些時日,便聽聞太上皇離開之前,曾和武後詳細地談過兩回。沒有人知道他們具體說了些什麽,但聽說那一日過後,太上皇是鐵青着臉色離開的,太後的臉色亦不算太好。再加上皇帝在政事上頻頻出錯,朝堂上的怨言和為皇帝說話的聲音對半開,這趟水就變得更渾了。
太上皇離開的第二日,範陽王反了。
這事兒原本與他沒有關系,但是重生的武後,很巧妙地又走了第二步棋。
她知道上一世提議出兵反武的人範陽王,因此重生之後,她又很巧妙地擺了範陽王一道,讓範陽王在朝堂怨憤四起、太宗陛下左右為難、天平已不再向太子傾斜的時候,讓他提前幹了那件事兒。
如此一來,整個局面就全都變了。
太平聽聞此事時,驚得出了一身的冷汗。
但是恰好那幾天突厥人又開始不安分了,她便再一次去了北疆。因為前兩次她都走得很順利的緣故,這回武後并未阻攔她。因此她很順利地便出了長安城。
但在出長安城北上之後,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濟州刺史府裏放了一把火。
那些來往的信件、聯絡、出兵的條條框框,全都被燒得幹幹淨淨了。
一點兒都不剩下。
直到這時,武後才給她來了一封信,問她到底是何意。
諸王的書信往來,在這個世上,唯有武後、太平與薛紹三個人知道。但是這些天薛紹一直留在長安城裏,連城門都不曾出過;武後自己自然不可能去燒信;因此唯一一個燒信的,便只能是太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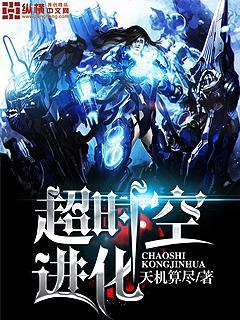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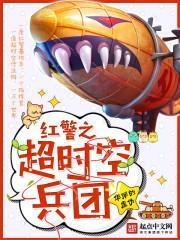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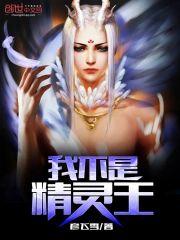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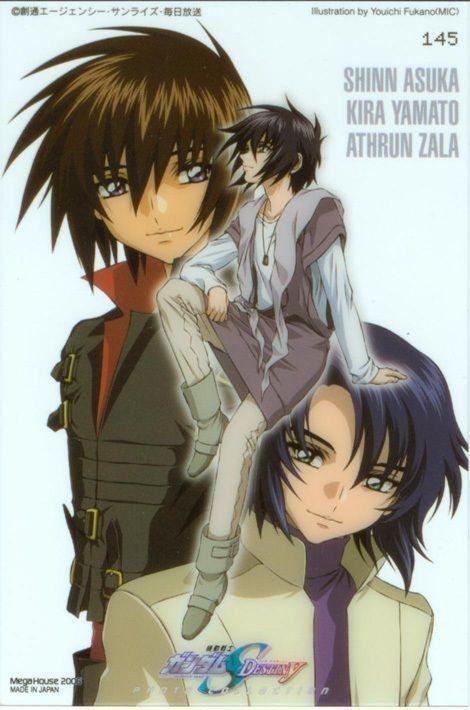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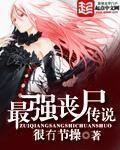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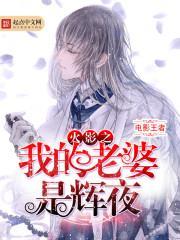

![[神夏+HP]以探案之名](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32779.jpg)

![[綜武俠]俠客們的反穿日常](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2907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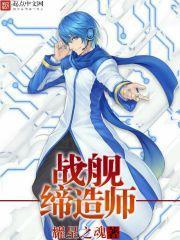
![[綜]我的家人](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3374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