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end
但那時太平不在長安,故而武後于她無法。
如此兜兜轉轉又是半年有餘,太平一直留在北疆未歸,長安城裏亦有些暗流洶湧。待到她終于回歸長安時,半座長安城都被噤了聲。太宗陛下歸來的消息已傳遍整個朝堂,但信與不信的人,卻是對半開;太後與皇帝分庭抗禮,而先前起兵的諸王,也多半被拘在了大理寺。
那些被焚毀的書信,将昔日諸王與外界的消息盡皆斬斷。
她聽聞武後曾想借此事,重提前世的一類神碑檄文,但卻被壓了下去。
她的父親留在洛陽一直未歸,皇帝每日坐在皇位上如坐針氈;現如今皇帝就是一枚制衡的棋子,要是擁戴他的人多了,武後便會設法讓他做些荒唐的事情出來;要是有人想要廢了皇帝的位置(例如太宗皇帝曾因氣急,動過廢立的念頭),那她便站在皇帝的那一邊,助他坐穩皇位。
但在暗地裏,不管是武後還是身為郡王之子的太宗陛下,都在暗自交鋒。
因此武後需要皇帝站在臺前,充作自己的擋箭牌。
不管是好,是壞,全憑武後的一個念頭。
她又從上官婉兒那裏,聽到了太宗皇帝曾試圖做過的許多事情,但無一例外地,都被或多或少地阻攔了一些。因為太宗皇帝的身份有些尴尬,他明面上新安郡王之子,是一個早已被邊緣化的宗室,再加上前些日子範陽王腦子一抽,出兵了,便又讓武後捏住了一個把柄。一個宗室的把柄。
皇帝非傀儡而形同傀儡,太後非稱制而形同稱制,郡王之子非東宮,而形同東宮。
現如今的長安城,已形成了這樣古怪的三角之勢。
至于太上皇本人……他留在洛陽城裏修身養性,除了偶爾見見宰相,看看已批好的折子之外,便再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
但是又聽說,他在去洛陽的前一日,曾經指着武後,氣得渾身顫抖。
當天武後與他都說了些什麽,大約早已經無從得知了。但現如今的長安城,分庭抗禮之勢看起來相當穩固,但又相當脆弱,似乎一個不察,便能打破這樣脆弱的态勢。
但是後來,皇帝忽然下了一道旨意:
封太平公主為超一品公主,再加封邑五千,增號鎮國。
Advertisement
此事一出,衆皆嘩然。
太平的封號和封邑,其實在第二次回長安之後,便已經被提過一回了。但那時太後與其他人的争端尚未擺到臺面上,因此不甚激烈。這回公主的封號一加,難免便會讓人想入非非。
公主所站的位置,到底是皇帝,還是太後,還是現如今炙手可熱的新安郡王之子,實在是太讓人遐想,也太讓人感到……不安了。
再加上太平公主回宮的那一日,便同武後吵了一架(因為當初太平燒信之事),這樣的舉動落在有心人眼裏,便又是一樁不可言說的站隊之舉。
大多數人都以為,公主這回理當站在皇帝或是新安郡王之子的那一邊,起碼在衆人眼裏看來,公主理當如此。
但出乎衆人意料的是,公主自從和武後吵過一架後,便将自己關在了公主府裏。足不出戶。
公主有自己的眼睛,也有自己的耳朵,對外界的消息一概都很清楚。
但她現如今的态度卻是,足不出戶,顯然不管是太後還是皇帝,她都不願意插手。
這種平靜且詭谲的氛圍持續了小半年,直到有一天,洛陽城裏傳來了太上皇病重的消息。
公主第二日便去了洛陽,帶着她的驸馬,還有剛剛出世的孩子。
長安城裏依然維持着詭谲的平靜,但暗地裏的交鋒,卻一點兒都不見少。
太宗皇帝盡管有着天然的優勢,但奈何他的現實身份所限,并非所有人都願意相信他。
而武後……
她知道未來将會發生什麽。雖然現在已經有了些許改變,但大部分的事情,卻都在安安穩穩地循着前世的軌跡行進。尤其是在重生一世之後,她對朝中的大臣,可以說是了如指掌。
兩相碰撞之下,居然是誰都奈何不了誰。
又過了些時日,太上皇病體加重的消息傳來,皇帝、太後、宰相,還有留在長安城的宗室,三品以上的官員們,大多都一同去了洛陽,預備見太上皇的最後一面了。
誰都沒有想到,太上皇臨終前誰都沒有見,而是與新安郡王之子,促膝長談了整整一個下午。
直到太上皇臨終前,都是看着自己的侄孫,也是自己的父親,阖眼離去的。
太上皇故去的第二日,宮裏便發生了一場兵變……唔,是一場小範圍的兵變。
誰都不知道那場兵變到底持續了多長的時間,但兵變過後,卻有人拿出了一張遺诏。
诏書上寫着:将新安郡王之子過繼給皇帝為嗣子,位主東宮。
衆皆嘩然。
太平曾以為,此事是太宗皇帝的手筆。
但在新太子入主東宮的第二日,她才聽到武後輕描淡寫道:“那件事情,是我派人做的。”
十分幹脆地将太宗皇帝捆在了自己的戰車上,不管太宗皇帝到底想要扶持那位大王上位,都要歇火。因為現在太宗皇帝是李顯的嗣子,未來的皇帝,他沒有理由自己扶持一個新皇,去篡奪自己未來的皇位。
不得不說,武後的這一手,實在是很高明。
這樣一來,即便太宗皇帝對她再是不滿,也只能站在她這一邊。
至于“太子為何不廢掉皇帝自己上位”?……
因為現在太子只有十五歲,要是想廢掉盛年的皇帝自己上位,別說是太後不允,換了朝中的任何一個人(尤其是宰相),都不會允許的。
先前太宗皇帝想要廢立,也僅僅是提出“廢立”,也有大半原因在于此。
如此相安無事地過了六年之後,矛盾再一次被挑了起來。
這回是真真切切地有人想要廢立,廢掉李顯,改立太子。
但是……
這六年來皇帝陛下在太後的扶持下兢兢業業,半點差錯也無。
太後需要皇帝荒唐的時候,皇帝便荒唐;
現在太後不需要皇帝荒唐了,皇帝便不荒唐了。
雖然人人都知道皇帝僅僅算得上是半塊擋箭牌,背後多半是太子和太後在較量,但幾乎無人敢參合進來。而且這些年,就連皇帝親封的鎮國公主,也僅僅是偶爾出來打個圓場,将矛盾全都壓在水面之下,表面上看起來,依然是一如既往地風平浪靜。
而且鎮國公主身負北疆,功勳赫赫,無人膽敢指摘半句。
即便是東宮太子,也僅僅嘆了一句“她實在是很小心”而已。
而太後……
公主這些年來,倒有大半時間,是在給太後收拾西面和北面的爛攤子。
因為自從太後取代了皇帝之後,諸州、道、府,倒是無甚大礙了,但是邊地卻……
噓。
太後的壞話,是萬萬不能言說的。
不過雖然太平費盡心思,将那些矛盾都壓在了水面之下,但水面下的交鋒卻一點兒都不曾減少過。這些微小的矛盾積累到了某一日,終于爆發。
太子二十五歲那年,兵變,奪位,封皇帝為太上皇,太後為太皇太後,暫居洛陽。
說是“暫居”,但其實……無異于軟禁。
宮中兵變時剛好碰上吐蕃入隴右,也是吐蕃國的最後一次垂死掙紮。太平帶着人去隴右了,回長安時才發現有些不對。等聽完事情的經過時,不免有些感慨和唏噓。
她像前些年一樣,去洛陽陪自己的母親住了一段時日。
但在她離去之後,她的母親卻自盡了。
不知緣由,事出倉促也很突然。
随之便與高宗皇帝合葬,功過不論,亦不知緣由。
想必在太宗皇帝眼裏,這是最合适的去處了罷。
從那一年起,新皇便再也沒有束縛。
前世想做的,未完成的,甚至連從來不曾想過的……
一件一件地,在數十年的時間裏,全都做完了。
至于太平自己……
她的原話是:唯此盛世,敢不從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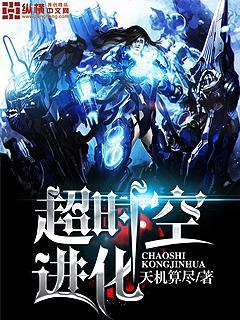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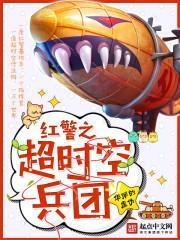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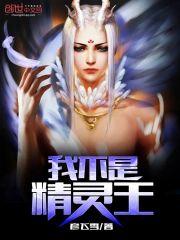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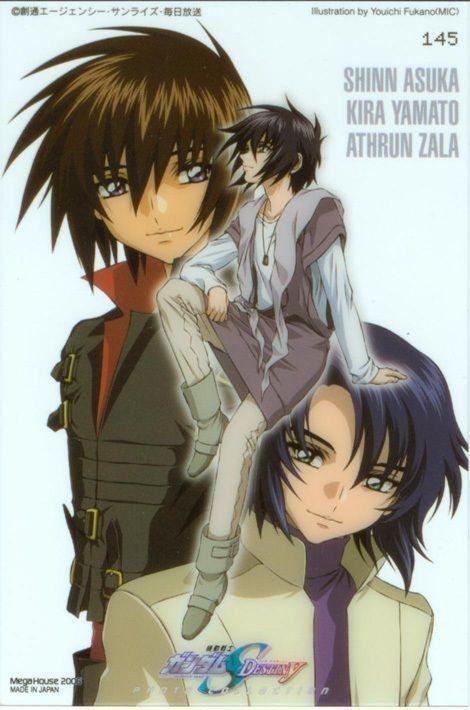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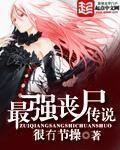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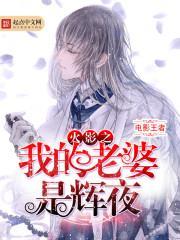

![[神夏+HP]以探案之名](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32779.jpg)

![[綜武俠]俠客們的反穿日常](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2907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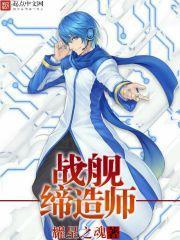
![[綜]我的家人](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3374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