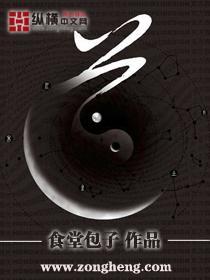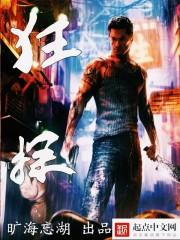第39章 (6)
了個濕帕子在臉上輕輕一拭,拭過的面容在燭光下就顯出種別樣的風致炫燦。只聽她輕輕吩咐道:“水荇兒,點燭、上香。”
座中人都一愕,連水荇也一愕。她一向聽小姐的話,當下拿了一雙在金陵城帶來的燙金紅燭,那燭上有巧手匠人細雕的龍鳳呈祥圖樣。她輕手輕腳地又點起了一束香,靜靜插在月佬像前的那個香爐上。一股優檀的香氣就在這久無煙火的偏殿裏彌漫開來。蕭如不看衆人,自顧自定定地看着那個月佬——縱是你千萬恩惠贈我以紅線,我以萬千柔情将之系于彼此的腳腕,看來今日還是牽不來那個人了。
但牽不來又何妨?——她一揚眉。我又不是不能将自己嫁與那要紅線。
她的笑容裏隐露出一絲絕愛與自傷,她從懷中取出了一根紅绫,就這麽披在了頸上。那紅色中一點慘淡的喜意交映在她的淡黃衫兒與揉藍裙子上,顯出一種縱全身披紅也沒有的百年靜美。她輕輕遙對着那月佬像弓腰一拜,然後再拜、三拜,将自己懷中的大紅帖子供在了案上。
她來時原有準備,将另一個袁辰龍墨筆親書的帖子也同時供上,那是她平時留心,留下了袁辰龍一向積下的字紙,依着他的字跡把他的庚辰親手描在那個空紅喜帖上的。
——百年倥偬,輕身一躍,就是無人接抱,她也要躍入其中了。只聽她忽回身叫道:“小舍兒。”
米俨卻就在不遠的耳室中。他為避九姓中人,一直不曾出來。這下他聞聲疑惑而來。只聽蕭如笑道:“今天是我許身與你們袁大哥的日子。他有事不能前來,你好歹算是男方人,就在這兒站一站吧。”
米俨怔住,萬沒料到蕭如前來順風渡口原來所來就是為此。
然後就聽蕭如婉轉輕吟般地道:“他就是來了,還不知許不許我如此一嫁呢。但這一生,差不多的都順着他了,這事、且由我自作主張一回——我把他生生拉郎配了吧。”
她口氣中宛如輕嘆。
米俨的眼中忽然冒淚。他是個堅強的小夥兒,這一生少有流淚,可這一刻,卻覺:大哥、轅門,負這個如姊是何等之深!
蕭如已在蒲團前低身跪下,用盡全部身心的,一拜、再拜、三拜。只見她在身側的蒲團上,放了一把精巧佩刀。可能就是那把佩刀,才讓方才驚覺過來的九姓中人沒有貿然上前。
那是袁辰龍送與蕭如的佩刀,很小巧,從得贈之日起她就一直未曾離身的。
擡起頭,蕭如的目光中有如煙水迷漫。只聽她輕輕道:“此日結缡,兩心不移。辰龍,我也就不多言了。你也未來,但就這樣了,也就這樣了。”
身邊那個啞聲女子忽然暴怒起來,尖笑道:“我說如妹,真沒見你這麽賤的。你就差抱着只大紅公雞拜堂了。你是失心瘋還是花癡了?那袁大有什麽好?值得你這麽給九姓中人丢臉。”
蕭如身子輕輕一顫。她不願在此時反望那刻薄女子的臉,只淡淡道:“這是我的事。我愛佩刀,不愛公雞。那公雞,還是你留着吧。”
Advertisement
米俨一怒,卻不好發作。那女子猶待開言,卻聽大殿深處忽傳來聲音。那是一聲大喝,只聽那人大喝一聲道:“滾!”
這一“滾”字發在那啞聲女子就待開聲反譏之時。她被那人一語壓住,心中登時煩惡大起,萬般難受,氣血一時倒轉,直攻心脈。
那女子捂着胸口痛道:“誰?”
那人不答,只是再次暴喝了聲:“滾!”
座中九姓中已有人驚道:“錢老龍!是錢綱錢老龍!”
殿內深處之人已嘿然笑道:“不錯,正是我錢綱。別等我出手趕你們這群兔崽子。一個個都給我乖乖地滾!”
他為人狂悍。就是九姓族人,一言不合,他也會将之痛毆的。加之他一身功夫極高,在九姓中已無人能出其右——他本不獨為九姓之冠,在江湖中也允稱為一等一的絕頂好手。那石、柴、王、孟之輩人人色變,臉上陰晴不定。忽齊齊忿哼了一聲,棄座而去,有人口裏猶低聲道:“賤人,賤人,你不如也反出九姓一門吧!”
那錢老龍見人人都走了,才走進這前殿來,嘿嘿道:“小蕭兒,別理他們,今日是你的好日子,我也沒什麽禮。他們都是些兔崽子,你別在意。你這婚事,別人不認,我錢老龍認!如果今後有誰多嘴,叫他們找我說話去!”
說完,他已大笑騰身而去。
殿中一時靜極——都走了,該走的都走了。
連水荇兒與米俨也被蕭如遣走了。殿中只剩下她一個人。
這是她一個人的花燭之夜。她靜靜坐着,雙目空睜,直到三更。
三更一過,就算明天了。明天,她已是袁辰龍的妻子。
梁上忽有聲音輕響,像是那人故意發出來的。
蕭如擡目向梁,她已是袁辰龍的妻了,他的事她自當代為處理。
只聽她擡頭道:“庾先生?”
梁上那人帶笑答道:“不錯,正是庾某。”
“蕭女史,庾某這廂有禮了。”
說着,那人輕輕落下,身上不染一絲梁上微塵。
此刻天上,參星已杳,商星未出。淮上當有一人正自中宵舉盞。他在想什麽?只見他舊白的衣倚側在淮上的風中。他的雙目舉望天宇——在參與商的間隔迢遞之間,庾不信是否該已與蕭如面見了……?
第五部 秣陵冬
引 子
秣陵的冬是冷寂的。哪怕是初冬,哪怕還沒有一場雪。玄武湖上沒有一絲縠紋的波面冷映着岸邊的衰柳枯楊,鏡子般地反襯着這城中猶不甘卸落的粉黛鉛華。在一些冷眼人看來,怎麽也有一二會心之處吧?
這個城市據說是有着一些王氣的。所謂“鐘阜龍蟠、石頭虎距”,那是三國時一代賢相諸葛亮的話。戰國時,楚威王滅越國,也是覺得這裏樹木蔥郁、山勢峥崚、隐有王氣,所以在獅子山之北埋金塊以鎮之,又于清涼山建城,取名金陵;其後,秦置郡縣,呼為“秣陵”;東吳時稱“建業”;至東晉時則稱“建康”、“江寧”;唐一度呼為“白下”;到宋時則又名之為“昇州”。
只是小小兩個字的變化,壓入《地理志》中還不足薄薄一頁吧?但其間之歌哭交接,繁華相替,卻怕是一千冊一萬卷也說不盡,道不完的。
多年以後,有了那麽一首歌。歌名已經含糊,歌中卻有一句這麽唱道:“……歷史的一頁尚未寫盡,硯上的筆早已凝幹……說什麽死生契闊,說什麽歲歲年年……那紅底金字的愛……”
對,——“那紅底金字的愛……”——就那麽被壓成薄薄的一頁——就那麽沉入這簡短的兩個字的地名的變遷嗎?
總有人不甘于那些人世中這所有的情癡怨戀、掙紮折挫就那麽被歷史壓薄成無奈的。
于是又有了一個作者,耗上些心血,呵一口氣,噴向硯上那早已凝幹的筆。那硯中冰凝的墨水在這一呵之間似乎就又有一脈脈、一縷縷不曾完全死去的生意慢慢浸潤開來,潤在了濫觞自宋時的紙上,化為一個個橫豎聳亂的字跡,試着再次氤氲起那個逝去的年代中秣陵的冬、與一些不甘就此沉淪的“紅底金字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