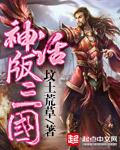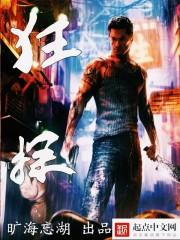第36章 官渡,(1)
〔這是一場生死之戰,處于弱勢的曹操努力改變着不利的局面,支撐他的是心中的信念。面對異常強大的對手,他甚至産生了動搖。奇跡在最後一刻發生了,一份情報、一場大火最終改變了這一切。〕
【一、龍蛇之年】
建安五年(200年)是農歷庚辰年,也是龍年;次年是辛巳年,也是蛇年。按照五行學的說法,每遇龍蛇之年就會對聖人不利。這件事一般人也不會放在心上,因為除了天子,大家都不算聖人,不用操這份心。
但是有個人比較在意,雖然他沒把自己當成聖人看待,但總覺得在這一年裏會發生些什麽,這個人就是名動天下的大學士鄭玄。
在建安初年獻帝征召天下名士時,農業部部長(大司農卿)一職本來是特意留給他的,只是到現在他也沒來上任。
鄭玄最後一次應召還是何進當大将軍時,何進失敗後,鄭玄回到家鄉青州刺史部的北海國隐居,同時聚衆講學,研究經術,著書立說。他的名氣實在太大了,從四面八方投到門下的有一千多人,日後有名氣的學生有趙商、崔琰、公孫方、王基、國淵、郗慮等人。
袁紹占據冀州并控制青州的部分地區後,鄭玄的老家成了“袁統區”。袁紹經常把鄭玄拉來參加聚會,出席各種活動,為自己撐門面。
在何進時期鄭玄就認識袁紹,對于這個比他小得多的政壇名人他并沒有太多好感,但出于無奈,他也不敢駁袁紹的面子。
在一次聚會上,大家聽說天下最知名的學者鄭玄将要出席,一些自認為肚子裏有點學問的人不禁躍躍欲試,精心準備了一些問題,想為難鄭玄一下,順便讓自己出名。沒有想到,鄭玄對所有問題都對答如流,知識之淵博、思路之敏捷讓人嘆為觀止,大家無不折服。
整天迎來送往、勾心鬥角,只是抽空看兩眼書,也敢叫板整天鑽在書堆裏只是偶爾出來喝回酒的鄭老師?鄭玄給大家上了一課。
袁紹以冀州牧的名義推薦鄭玄為茂才,并表奏他為左中郎将。袁紹的想法有點幼稚,如果鄭玄接受,袁紹就成了鄭玄政治上的恩主,這雖然是別人巴不得的好事,但對鄭玄不好使。在此之前,被鄭玄拒絕過的類似薦舉已多達十三次。
随後,獻帝的诏書到達北海國,獻帝還派來一輛專車,接鄭玄到許縣就任。鄭玄這次答應了,但動身不久,就感到身體不舒服,未及上任便請求告老還鄉。鄭玄雖然沒有正式就任大司農,但後世一般稱他為鄭司農。鄭玄就是一個專心學問和教育事業的知識分子,無奈名聲太大,想安安靜靜地讀書過清淨的日子也不容易做到。
不僅朝廷和袁紹這樣的人對鄭玄尊崇備至,就連黃巾軍聽到鄭玄的名字也甚為禮遇。據《後漢書鄭玄傳》記載,鄭玄有一次半路上遇到很多黃巾軍,他們聽說是鄭玄,磕頭便拜,并且相約不進鄭玄的老家高密縣(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誰說知識不是力量?
建安五年(200年)鄭玄七十四歲,在當時這已是絕對的高齡,他感覺身體越來越不适。這年春天,鄭玄夢見了孔子,在夢裏還跟他說了話。對五行學、易學深有研究的鄭玄把這個夢與龍蛇之年聯系在一起,總覺得這個夢預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心裏悶悶不樂。
正在這時,青州刺史袁譚親自來到高密縣,要接他到邺縣去,鄭玄以為袁紹又讓他陪酒吃飯,有點不想去,但小袁的态度很堅決,不去不行。鄭玄只得收拾行李,随袁譚出發。
一行人走到元城縣(今河北大名)時,鄭玄的身體實在不行了,病情加重,只得停在那裏。到了夏天,鄭玄逝世,臨死之前,他還抱病專心注釋《周易》。
在鄭玄的很多學生看來,他們的老師就是當代孔子,而鄭玄也無愧于這個光榮稱號,他一生潛心學問,不參與世事紛争,是一個純粹的學者。
這次袁紹明知鄭玄身體情況不允許,仍然執意要他來,目的是讓他随軍。此時的袁紹,已決定發起對曹操的全面進攻,為此他進行了精心準備,除動員所部幾乎所有精銳部隊傾巢出動外,還做了大量思想輿論發動工作,征鄭玄随軍也是其中之一。
袁紹對這一仗志在必得,随他一同出征的還有大量圖書典籍,其中不乏關于典章制度方面的資料,顯示出袁紹不僅着眼于這一仗能否打贏,而且已經開始考慮打贏之後的事。
袁紹原本規劃打敗曹操之後,他就立即接管朝廷,如果獻帝肯合作,就還讓他當這個傀儡皇帝,如果不願意合作,就另立其他人。
袁紹讓大筆杆子陳琳撰寫了一份檄文,向各郡縣發布。在動手之前先動口,大造輿論,歷來都是這個套路。
這份檄文約一千三百字,陳琳下了很大功夫,痛揭曹操的黑史,從曹操的爺爺曹騰開始寫起,羅列了曹操的數條罪狀:
一、曹操的祖父故中常侍曹騰與左、徐璜等宦官均屬妖孽,禍害百姓。曹操的父親曹嵩是乞丐家的養子,大權在握後經常幹貪贓枉法的事。至于曹操本人,是典型的“贅閹遺醜”,無才無德,而且好興兵作亂。
二、曹操幾次陷入危機,都是袁紹出手相助,但曹操不思報答,反而趁機發展勢力,攻擊袁紹。
三、曹操喜歡亂殺人,原九江太守邊讓是天下知名之士,因為不阿附曹操,被他殺害,士林無不憤怒。
四、獻帝東歸時,袁紹自己受制于公孫瓒無法脫身,派從事中郎徐勳前往曹操處傳達命令,讓他保護銮駕,修繕郊廟,但曹操卻趁機專制朝政,令百僚鉗口,公卿以下都成了擺設。
五、故太尉楊彪享有極高的威望,曹操因為個人恩怨,随意治罪,根本不顧憲章。議郎趙彥忠谏直言,引起曹操反感,擅自将其殺害,也不向天子報告。
六、曹操設置發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官職,專門幹盜墓的勾當。
七、曹操統治殘暴,兖州、豫州百姓無不怨聲載道,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沒有超過曹操的。
八、袁紹與公孫瓒交戰,公孫瓒被圍一年多,曹操趁其未破,偷偷地寫信給公孫瓒,想與他勾結,共同謀害袁紹。
檄文是專門為讨伐造勢用的,把敵人有多壞就說多壞。袁紹曾經被公孫瓒的檄文罵過,對照一下,就會發現陳琳的這篇檄文寫得更有氣勢,殺傷力也更強。
這篇檄文沒有空洞的口號,而是将論點與論據結合起來,說得有理有據,同時大肆爆料,專抖曹操的黑史。
文中所言曹操殺邊讓、徐勳傳達袁紹命令、曹操設盜墓機構、曹操秘密聯絡公孫瓒等事,是別的史料中未見或少見的,一種可能是袁紹無中生有,颠倒黑白,另一種可能是确有其事,不過經過後世史家的删改,已不多見于史料。
無論真假,這些材料經過陳琳這個大筆杆子的加工,曹操的黑史立即傳布四方,在當時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曹操後來常被人诟病,很多素材也來自這裏。
文中把曹操稱為“贅閹遺醜”,雖屬人身攻擊,不值得提倡,但也成了一句很著名的話,這種把曹操一家三代人合在一起攻擊的罵街作風,經過陳琳的文字包裝,倒也顯得文采飛揚,很有氣勢。
曹操也看到了這篇文章,當時他正為眼前的戰事傷神,偏頭疼的毛病又犯了,看了老朋友陳琳寫的痛罵自己的文章,腦袋居然一下子不疼了。
【二、左翼争奪戰】
在說袁、曹對峙中路的情況之前,先看看左翼和右翼。在右翼,也就是兖州、青州、徐州方向,曹軍采取了攻勢,從建安四年(199年)下半年開始,曹操授意臧霸集中孫觀、吳敦、尹禮等部的人馬,從徐州北部的琅邪國境向袁紹占領的齊國、北海國、東安國等發起進攻,使袁紹不得不分出重兵由長子袁譚率領守衛青州。
兖州是曹操的老根據地,有程昱等人在此據守,曹操心裏稍稍安下心來。關中、河東郡一帶是此次戰役的左翼,那裏情況複雜,雖然有鐘繇坐鎮,但曹操心裏還是沒底。
袁紹左翼的總指揮是他偏愛的小兒子袁尚,協助他的是袁紹的外甥高幹以及河東郡太守郭援。南匈奴人一直與袁家關系很好,在剿滅公孫瓒的戰鬥中出了大力,如今南匈奴在平陽(今山西臨汾)起兵,公開響應袁紹。
平陽與關中近在咫尺,鐘繇率部渡過黃河,将平陽城圍了起來,但是兵力有限,未能将其攻克。正在這時,傳來郭援率軍南下的消息。面對敵我實力懸殊的态勢,很多人建議從平陽撤軍。
鐘繇說:“郭援與關中諸将暗中相通,關中諸将之所以還沒有反叛,原因是還想觀望一下。如果現在撤走,就是示弱于人,此為未戰而先自敗。”鐘繇認為,郭援剛愎好勝,喜歡輕軍冒進,一定可以找到戰勝他的機會。于是,曹軍繼續圍住平陽,迎戰郭援。
鐘繇并不是盲目樂觀,他有秘密武器對付袁軍。
鐘繇的秘密武器是馬騰和韓遂。
當時關中諸将裏勢力最大的當屬馬騰和韓遂兩支,他們各擁強兵坐觀天下之變。袁紹也派了使者前來聯絡他們(發使西與關中諸将合從),但馬騰和韓遂對于該站在哪一邊,仍然舉棋不定。
鐘繇以司隸校尉的身份坐鎮關中,他積極争取各派勢力的支持,取得了不少成績,但馬騰和韓遂十分強大,得不到他們真心支持,關中的事情仍然不好辦。
鐘繇分別給馬騰、韓遂寫了封信,陳述利害,要求他們站在朝廷一邊。信寫好了,鐘繇想找個有膽識有能力,又有口才的人前去,他想到了新豐縣令張既。張既果然不負重望,把這項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張既字德容,關中地區左馮翊郡高陵縣人。年輕時為郡吏,工作很有能力,得到大家的好評,曹操擔任司空後,征辟他到司空府工作,還沒有去鐘繇就來了。鐘繇發現張既是個人才,向曹操請求把他留下來并舉薦為茂才,任命他擔任新豐縣令。張既頗有實幹能力,在年終考核時業績位居三輔地區各縣第一名。
張既說服了馬騰、韓遂,最後他們不僅同意站在曹軍一邊,而且還願意将兒子送到曹操處為人質,以示誠心。馬騰和韓遂所率的涼州軍名滿天下,僅就戰略作用而言他們的影響力十分巨大,在這個意義上說,張既此行居功甚偉。
張既是如何說服馬騰和韓遂的,史料記載不詳。但是在司馬彪所著《戰略》一書中,有傅幹勸說馬騰的記載,說馬騰等人最終站在曹操一邊,扶風郡太守傅幹立下大功。據《戰略》說,袁紹的使者也曾到達馬騰那裏,馬騰等人已經暗地裏答應袁紹(陰許之)。傅幹知道後趕緊來勸馬騰,傅幹說:
“古人雲‘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這就是順道呀。袁氏背王命,驅使匈奴人進犯中原,他本人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強,其實已失天下人心,這就是逆德呀。如今将軍您表面上站在有道者一邊,但卻不盡力,暗地裏坐觀成敗,陰懷兩端,恐怕等成敗确定之後,曹公必然會奉辭責罪,将軍您也得落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馬騰一聽果然害怕了(騰懼)。傅幹進一步說:“智者善于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陳兵河東,将軍引兵讨伐郭援,當有勝算,将軍此舉如同斷袁氏之臂,可以解曹公之急,事後曹公必重謝将軍!”馬騰認為這個建議很好,表示接受,派遣兒子馬超率精兵一萬多人,支援鐘繇,韓遂也派兵參戰,統一由馬超指揮。
傅幹字彥材,又字別成,出身于著名的涼州北地郡傅氏家族,其父傅燮是桓靈之際的名臣,受宦官排擠出任涼州刺史部漢陽郡太守,戰死于叛軍之中,被朝廷追封為壯節侯,當時傅幹年僅十三歲。傅幹日後成為曹操的重要參謀,他的兒子傅玄更是了不起,是曹魏時期的名臣和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
鐘繇得到涼州勁旅的支援後,實力大增,他讓人不要聲張,誘使郭援率軍輕進。郭援不知道對手的力量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仍然不把鐘繇放在眼裏,快速向平陽推進。
平陽的外圍是汾水,郭援抵達後下令渡河,剛渡到一半,鐘繇、馬超的聯軍立即發起攻擊,袁軍大敗,馬超手下的部将龐德親自斬殺了郭援。鐘繇趁勝追擊,大破南匈奴人。
這是一場關鍵性的戰鬥,戰前西線的總體形勢是袁強曹弱。戰後,雙方處于均勢,鐘繇雖然還沒有能力進攻袁紹的并州,但打掉郭援之後,袁軍也沒有能力進一步攻擊長安和洛陽,保證了曹軍左翼的安全。
此戰也是二十四歲的馬超第一次獨立帶兵作戰。
馬超字孟起,是馬騰之子,也是韓遂的幹兒子,馬騰死後其部由馬超率領。
平陽之戰穩定了關中形勢,使涼州刺史韋端也決定站在曹操一邊。為了慎重,韋端派手下的從事楊阜前往許縣,名義上向獻帝朝奉,實際是觀察虛實。
楊阜字義山,涼州刺史部天水郡冀縣人,《魏略》說他很有才幹。楊阜到了許縣,被天子拜為安定郡政府秘書長(長史)。楊阜回來後對韋端說:“袁紹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現在雖強,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人雖少但兵卻精,手下人各盡其力,必能成大事。”韋端聽後堅定了站在曹操一邊的想法。
後來,朝廷征韋端為交通部部長(太仆),涼州刺史一職由韋端的兒子韋康接任,楊阜任韋康的別駕。曹操當丞相後,征楊阜為丞相府參謀,後來又回到涼州任職,是曹魏在涼州地區的重臣。
東邊有臧霸,西邊有鐘繇,曹操保證了兩翼不失,可以在中路放手一搏了。
【三、斬顏良,誅文醜】
袁紹的大本營邺縣和曹操的大本營許縣直線距離約五百裏,中間隔着黃河、汴水等河流,沿線有黎陽、白馬、延津、官渡等戰略要地,這裏是袁曹決戰的中線,也是決定最終成敗的戰場。
為了迎擊袁紹的進攻,曹操布下了三道防線:第一道防線是黎陽(今河南浚縣),這裏在黃河北岸;第二道防線是黃河南岸的白馬(今河南滑縣)、延津(今河南延津);第三道防線是官渡。
決戰之前,曹操派一小部分人馬進駐黎陽,不求與袁軍交戰,只起到監視敵軍、配合南岸行動的目的。他還命令于禁率兩千人駐守延津,命令東郡太守劉延駐守白馬,将其餘主力布防在官渡一帶。
面對十多萬袁軍的進攻,曹操擺出了多梯次的縱深防禦體系,而不是将主力分布于黃河一線死守,之所以這樣安排,實在是因為自己的力量不足,難以在正面數百裏的黃河沿線分兵把守。
第二道防線的作用是遲滞袁軍的進攻,消耗袁軍的有生力量,挫其銳氣,然後在第三道防線與袁軍展開決戰。
但這樣的軍事部署也冒了很大風險,因為官渡是許縣的最後一道屏障,在前兩條防線被敵軍攻破之後,已經退無可退,必須在這裏取勝,否則就徹底失敗。
建安五年(200年)二月,袁紹親率大軍由邺縣南下,兵指黎陽,随行的還有劉備。曹軍未作抵抗,迅速撤到黃河以南。
黎陽自古即是黃河北岸的重要戰略要地,是進行渡河作戰的基地,歷來都有許多大戰在這裏發生。曹軍無意在黎陽與袁紹作戰,因為在這裏自己的部隊難以接續,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有被敵軍全殲的危險。
袁紹占領黎陽後,派部将顏良為先遣部隊,渡河攻擊南岸的軍事要地白馬。這項決定卻遭到了沮授的反對。
沮授勸袁紹說:“顏良這個人生性褊狹,雖然骁勇,但不能獨立擔當大任。”袁紹不聽。
顏良的情況不詳,但卻很有威名,當時在軍中的地位和名望遠遠超過關羽、張飛等人。袁紹曾經對沮授很倚重,幾乎言聽計從,但這次卻不接受沮授的建議。結果,事實證明沮授是正确的。
對于袁紹的這次南征,內部有一定分歧,以田豐、沮授為代表的本土派表示反對,矛盾一度公開化。臨行前,袁紹将持強烈反對意見的田豐下獄。
沮授在袁紹手下以奮威将軍的名義任監軍,權力很大。在郭圖等人的建議下,袁紹将沮授監軍之權一分為三,分別由沮授、郭圖和老将淳于瓊擔任。
據《獻帝傳》說,袁紹出發前,沮授把本族的人招到一塊,把家財分了分,對他們說:“勢如果在,則威無不加,勢如果不在,則不能保一身,悲哀呀!”他有一個族弟說:“曹操怎麽能是袁公的對手,您何必擔憂?”沮授說:“以曹操的明略,加以挾天子以為後盾,我們又剛剛打敗公孫瓒,士兵疲弊,主将驕縱,成敗已經很明顯了。”
大軍還未行動,沮授已經到處散播“亡國論”,袁紹一定有所察覺,沮授在冀州的影響力讓袁紹不至于立即發難,但對沮授的信任大為降低。所以,當沮授對重要的人事安排再指手畫腳時,袁紹出于對沮授的反感,想都沒想就駁回了。
建安五年(200年)四月,顏良率部渡過黃河,直指白馬。
曹操決定親自北上,解救白馬之圍。這時候,荀攸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袁紹兵多勢盛,不宜強攻,只能智取。荀攸建議先置白馬于不顧,主力開赴延津,這裏是黃河上最重要的渡口之一,給袁軍一種曹軍要從這裏渡河包抄黎陽的架勢,誘使袁軍主力向延津對岸一帶轉移,袁軍被調動後,再迅速轉進白馬。
這個建議的冒險性有兩個方面,一是袁紹看破曹軍的企圖,不分兵西進;二是袁軍雖然分兵,但他們兵力足夠多,既能迎擊延津之敵,又能加強白馬的攻勢。這兩種情況的結果都一樣:白馬丢失,曹軍大敗。
曹操認真考慮了荀攸的建議,他認為在敵強我弱的現實情況下,荀攸的建議值得嘗試,于是放棄親自馳援白馬的方案,轉而進軍延津。袁紹果然中招,将進攻白馬的一部分主力調往延津。
曹操看計策成功,便以張遼為主将組成一支輕騎兵,以閃電之勢急馳白馬。張遼領命,并請求讓關羽同行,曹操同意了。
關羽投降曹操後,與張遼、徐晃二人志趣相投,關系很好。他們三個人都是從敵方陣營歸降的,也許因為有共同的經歷,更容易談得來。曹操很欣賞關羽(壯羽為人),但是發現關羽好像沒有久留的打算,就讓張遼去摸摸關羽的底。
張遼說明意圖,關羽嘆道:“我知道曹公厚待我,然而我受劉将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能背叛他。我不會永遠留在這裏,但我會報答曹公以後再走。”張遼把關羽的話如實轉告曹操,曹操沒有生氣,反而覺得關羽很有義氣。
據《傅子》一書說,關羽對張遼講了那一番話後,張遼心裏犯了嘀咕,原話轉告,怕曹操生氣殺了關羽,不如實轉告,又覺得對不起曹操對自己的信任。最後張遼還是如實說了。
在白馬前線的顏良,一直以為主戰場在百餘裏之外的延津,沒有想到突然有一支勁旅向自己殺來,倉促應戰,結果打了敗仗。此戰關羽立下大功,親斬敵方主将顏良。
關羽力斬顏良,兌現了當初的承諾,曹操預感到關羽有可能走,立即對關羽給予厚賞,想留住他。但關羽去意已定,他把曹操賞賜給自己的東西全部封存起來,留下一封信,離開曹營找劉備去了。曹操手下人想追趕,曹操說:“他也是各為其主,不要追了。”
關羽在後世很受追捧,被稱為武聖,其實不是因為他的勇猛,而是由于他的為人做事。關羽的為人在此事上表現得很突出:不為利所動,所有的事都以義為先,做事很講究,即使離開,也讓人挑不出理來。
劉備此時已投靠袁紹,關羽剛殺了人家的大将,袁紹那邊恐怕正給顏良開追悼會呢,關羽偏偏敢在此時投奔。這就是關羽,心裏只想着義,其它的一概不多想。袁紹對跑過來的關羽既恨又愛,最後還是沒說什麽。
在關羽重新回到劉備身邊之前,一直在公孫瓒手下效力、公孫瓒失敗後下落不明的趙雲聽說劉備在袁紹這裏,也專程來投奔。劉備客居在袁紹這裏,手下的主要武将張飛、關羽、趙雲總算聚齊了。
曹操雖然解了白馬之圍,但自知袁紹的大軍随後便到,于是決定從白馬撤軍。袁紹果然指揮主力渡河,對此沮授又表示了不同看法。
據《獻帝傳》記載,沮授建議不管白馬,拿下已經唾手可得的延津,憑借這裏的渡口優勢,将主力源源不斷運過黃河,之後鞏固延津,使其作為一個戰略支撐點,進可以直取許縣,退可以從容撤回黃河以北。
沮授的話袁紹特別不愛聽,在袁紹看來此行壓根沒有戰敗撤回這樣的選項。同時,首戰即在白馬挫敗讓袁紹大失面子,在哪裏跌倒就要從哪裏爬起來,袁紹非拿下白馬找回面子不可。
沮授站在黃河邊上嘆息說:“黃河啊黃河,我知道這一去就回不來了(悠悠黃河,吾其不反乎)!”于是以身體原因請辭。袁紹很生氣,把沮授所部交由郭圖來統率。
曹操料定袁紹會命主力來攻白馬,他下令白馬軍民全部随軍撤離,但向哪個方向撤退卻讓他頗費思量。
白馬屬兖州刺史部的東郡,沿黃河向東不遠就是另一個軍事要地濮陽,此時還在曹軍手中。再往東就是曹操在兖州刺史部的中心城市鄄城。
防守鄄城的是程昱,手下只有七百人。為了保證中路的安全,曹軍分散在各地的人馬已經盡可能地都抽調到中線。戰役開始前,曹操想給鄄城增派兩千人,程昱不同意,他說:“袁紹有十萬之衆,自以為所向無敵。現在看到鄄城的兵少,必然輕易不來進攻。如果增加人馬,他們就會認為不能不攻。”
程昱建議不要管鄄城,曹操接受了這個建議。袁紹聽說鄄城沒有多少人馬,果然放棄對這裏的進攻。事後曹操對程昱的膽識和準确判斷大加贊賞,曾經對賈诩說:“程昱的膽識真勝過古人!”
程昱的建議似乎沒錯,從保全鄄城來看,示弱也是一種戰術,類似于空城計,鄄城得以保全,多虧了沒有增兵。
但從全局戰略考慮,袁紹如果分兵來攻鄄城,也會減輕中路主戰場的壓力,通常攻城的一方會數倍于守城的一方,袁紹不攻鄄城,更可以集中優勢兵力決戰主戰場,程昱的想法也算有得有失吧。
現在,鑒于東部防守的薄弱,曹操不可能向東撤退,但也不能輕易撤往官渡的第三道防線,所以曹操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沿黃河向西撤,并且帶上白馬的所有辎重和百姓。
沿黃河向西就是延津,這裏剛被袁紹占領,曹操向西撤退,出乎袁紹的意料。袁紹此時的戰略應該是棄曹操于不顧,直接向南進攻,這裏才是中心戰場。但袁紹急于找曹操本人打一仗,找回失去的面子,于是将已渡過黃河的主力部隊分為兩隊,一部分由郭圖率領守白馬,一部人由文醜、劉備率領順着曹軍撤退的方向追擊。
袁軍追到延津之南,在這裏遇到了曹操親自率領的部隊。此時袁軍的兵力大約有五六千人,而曹操只有六百人,形勢十分危險。但即便是這樣,曹操仍然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
《三國志武帝紀》對此戰的記載是:曹操已經紮了營,聽說袁軍殺來,讓人登上高處偵察。不一會偵察員報告:“敵兵來了,大概有五六百人!”曹操沒有動。過了一會兒,偵察兵又報告:“騎兵更多了,步兵不計其數。”曹操說:“別再說了!”
面對十倍于己的敵人,曹操沒有下令撤退,反而下達了一道奇怪的命令,他讓大家出營解鞍下馬,同時把從白馬帶來的辎重擺在道路上。随行的将領們都認為敵人騎兵多,不如退到營寨裏堅守,待援軍到來。
曹操把目光移向他的副參謀長荀攸,荀攸微微一笑說:“這正可以作為誘餌,怎麽能撤呢?”荀攸說出了曹操心裏的秘密。
敵兵眼看快到了,諸将都說該上馬了,曹操說:“別急。”又過了一會兒,敵人的騎兵越來越多,看到路上的辎重,有一部分人開始忙着清理這些戰利品。曹操說:“可以了!”
曹軍全部上馬,縱兵殺出,袁軍沒有防備,大敗。
此戰文醜被殺,沒有戰死的也全部成了俘虜。
上述記載似乎有些可疑。此戰的結果沒有疑問,文醜被殺,袁軍再次受到重創,但僅以區區六百人一舉打敗五六千人,并斬敵方主将于陣前,則讓人不解。
表面看是曹操以辎重為誘餌,先使敵軍大亂再趁亂出擊所以取勝,但這只是一個方面,它改變不了敵我兵力懸殊的事實。即使敵兵開始有些慌亂,但對一支訓練有素的勁旅而言,臨陣應變是基本能力,他們很快便可以組織起有效反擊,到那時兵力衆寡才是勝負的決定因素。
袁軍是追擊而來,人數還在不斷增加,也許五六千人并不是它的全部,曹軍的六百人退到營寨裏打敗敵人的幾次進攻尚可以理解,将敵兵全殲,并将沒有打死的敵兵全部俘虜那就不可思議了。
遍翻史書,對這個問題都沒有詳解。分析一下,有幾個問題需要注意:一是曹操為什麽非要向已被敵兵占領的延津撤退?二是為什麽曹操身邊只有六百人?三是随曹操撤退的辎重都在,而老百姓上哪裏去了?
如果把這些問題聯在一起考慮,似乎可以看出曹操撤向延津是一個精心構思的計劃,帶上辎重和老百姓也是特意的安排,袁軍看到辎重停下來搶占而沒有提防後面的曹軍,是因為辎重裏混着大量老百姓,場面很混亂,像是趕大集。做誘餌的不僅是這些辎重,還有老百姓。曹操向延津撤退的路上,應該有時間進行兵力部署,調集周圍的部隊向預設的戰場機動轉移。曹軍趁袁軍搶占辎重突然發起進攻時,投入的兵力絕不是六百人,而要多得多,如果短時間內能全殲袁軍,人數至少比袁軍還要多。
《三國志武帝紀》等相關史料之所以沒有這些方面的詳細記載,是因為它不便回答随軍行進的老百姓在此戰中的作用,所以炮制出六百人全殲五六千人、臨陣斬殺名将文醜的神話。
當然曹操此計有很大的風險,那就是袁紹變得聰明起來,他不向西追,而直接進軍正前方的官渡。但曹操對袁紹太了解了,他們自青年時代便相識、相惜,如今在戰場上相見,曹操知道袁紹首戰挫敗後急于報複的心情,所以只帶六百人親自當誘餌,把袁軍主力吸引到延津一帶,集中優勢兵力迅速将其殲滅。
顏良、文醜都是名将,短短幾天內被曹軍打敗并斬殺,極大地鼓舞了曹軍士氣,也深深震撼了袁軍士兵。
袁紹被激怒了,他親率大軍渡河,前鋒推進到陽武(今河南原陽東南),曹操率主力由第二道防線南撤,退守官渡。
【四、曹仁的閃電戰】
自戰國以來,黃河和淮河兩大流域之間不斷開挖了幾條人工運河,最後形成以鴻溝、汴渠、狼蕩渠等為主組成的運河體系,将南北水域連接在一起,一千多年間成了溝通南北經濟和人員往來的水路交通要道。
這條水路兩岸很繁華,在全國經濟、文化以及軍事方面的重要性遠遠超過現在。其中的鴻溝大約成西北-東南方向,當年楚漢相争時曾以這條河為界,東西兩邊分別為項羽和劉邦占有,故而留下了“楚河漢界”的典故。
邺縣直達許縣這條通道與鴻溝的交彙處,是一個重要的渡口,名為官渡,此地位于今河南省中牟縣境內,是由華北南下中原腹地進而到達華中的必經要地。
連失兩陣的袁紹不聽沮授等人的建議,揮師南下,力圖尋找曹軍主力與之決戰。他們很快推進到鴻溝附近,在官渡與曹軍形成了對峙。
對曹操來說,雖然連殺袁紹兩員大将,但戰争總體态勢仍未改變,前兩道防線雖然遲滞了袁軍的進攻,連贏兩陣振奮了官兵的士氣,但對于許縣這最後一道戰略屏障,他只能死守,已無路可走。
在力量懸殊的形勢面前,一部分人産生了動搖,還有一小部分人甚至暗中與袁紹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