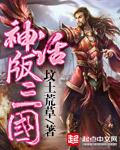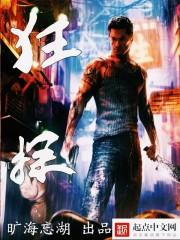第34章 (2)
,他一定在回味着呂布臨死前的那句話:“大耳兒最不可相信!”
按照曹操的想法,他現在就要提兵殺回徐州去,把劉備抓住,把下邳奪回來。但如今許縣的情況已經不容樂觀,袁紹的軍隊正在黃河北岸集結,更要命的是,還有情報顯示遠在江東的孫策也在積極調動軍隊,有北上的意圖。
還有近在咫只的張繡,随時有聯合劉表進擾的可能。公孫瓒、呂布、袁術三大集團相繼滅亡之後,天下表面看來暫無大事,但陰雲密布,預示着一場更大的風暴就要到來。
在這種情況下,曹操不能親自遠征劉備。經過考慮,他派劉岱、王忠二人率軍進攻下邳。
這是一個奇怪的決定,因為劉岱、王忠二人并不在曹軍一流将領的行列。《魏武故事》說這個劉岱字公山,是曹操的沛國老鄉,擔任曹操司空府的秘書長(長史),他與已故兖州刺史劉岱同名。《魏略》說王忠是扶風郡人,逃荒到了荊州一帶,聚衆襲擊劉表的部下婁子伯後投奔曹操,曹操任命他為中郎将。
史書對王忠還有一個恐怖的記錄:他吃過人。曹丕當了皇帝後,王忠有一次随駕出行,曹丕想跟他開開玩笑,就讓随行的藝人(俳)找了些墳地裏的骷髅,挂在王忠的馬鞍上,進行取樂。
如果遠征劉備,至少也要派曹仁、曹洪或者夏侯淵、于禁這些人去吧,劉岱和王忠根本不是劉備對手。《獻帝春秋》稱,劉備輕易便打敗了劉岱、王忠,還教訓他們道:“像你們這樣的,來上幾十個、上百個又能把我怎麽樣?就是曹操親自來,結果也未可知!”
劉備說完這些豪言壯語,留下關羽守下邳,自己回到小沛。《三國志》說關羽被任命為下邳國相(領太守事),《魏書》說關羽為徐州刺史(領徐州)。此前,關羽在劉備手下有記載的職務是獨立團團長(別部司馬),大約相當于上校。投降曹操後被任命為中郎将,相當于準将一級,現在一躍成為州郡大員,看來還是獨立發展進步得快。
劉備在小沛一邊派孫乾聯絡袁紹,給自己準備退路。一邊策反徐州、兖州一帶曹操陣營的人,杜氏的前夫秦宜祿就是這時候被張飛策反的。
劉備還把策反工作的重點放在了“泰山幫”身上。這些人不是曹操的嫡系,劉備與他們以前也有交往,策反相對容易。雖然臧霸等大多數人沒有跟劉備走,但劉備也取得了巨大收獲,“泰山幫”裏的二號人物昌造反了。史書上說,昌造反之後,附近的很多郡縣都積極響應,聚合起數萬人。
這時已經到了建安五年(200年)初,官渡之戰的序戰已經打響了。
面對徐州出現的緊張形勢,曹操決定親征徐州。對此,曹操的大多數參謀和部将都表示反對,擔心曹軍主力遠征徐州後袁紹趁機南下,許縣就危險了。
曹操說:“劉備是天下豪傑,現在不打敗他,日後必是大患。袁紹雖然有大志,但他優柔寡斷,不會立即采取行動。”
曹操的想法得到郭嘉的支持,他認為只要此次行動速度快,就一定能做到兩頭都不耽誤。曹操妥善安排了許縣及以北地區的防禦,親率大軍火速進兵,直撲徐州。
劉備沒有料到,在曹操即将與袁紹展開大決戰的前夕還有精力照顧他一下,聽說曹操親率大軍殺來,簡直不敢相信,他自知不是對手,率數十騎逃往青州,投奔袁譚去了。
曹操先後占領了下邳和小沛,俘虜了關羽以及劉備的家眷。
劉備跟劉邦有一拼,打起仗來經常跑路,一跑路就把家眷弄丢。在劉備的一生中,這樣的經歷前面有過,以後還會有。
青州刺史袁譚聽說劉備來了,趕緊率軍迎接,袁譚把劉備接到青州刺史部平原郡。劉備曾在這裏工作過四年左右,也算是故地重游了,只是身邊少了愛将和家眷,心裏一定會覺得凄涼。
袁譚派人将此事報告給袁紹。袁紹剛剛經過一系列的內部讨論和謀劃,決定全面發起征讨曹操的決戰。聽說劉備來投奔,覺得這是一個好兆頭。在袁紹的眼裏,呂布、袁術不在了,豫州、徐州一帶數劉備還算是個有分量的人物,有一定的利用價值。
袁紹派人專程到平原郡迎接劉備,劉備一行快到邺縣時,袁紹更是給足了劉備面子,親自出邺縣二百裏迎接。
【五、張繡意外之降】
曹操打跑了劉備,也不敢在徐州多停留,立即率大軍回防。對于徐州他這次不敢怠慢,把剛剛被任命為冀州牧的董昭調過來,改任徐州牧,替他主持徐州方面的事務。
在處理危機、果斷應對突發事件方面,董昭有過人之處,他也是曹操可以完全信任的人,現在的徐州由董昭來主持再合适不過了。
曹操嘴上說袁紹優柔寡斷,但心裏無時無刻不充滿了擔心。袁紹雖然不足成大事,但他手下難保不會冒出幾個明白人,如果把袁紹點撥醒了,後果不堪設想。
其實,曹操的擔心一點都不多餘。據《三國志》記載,就在曹軍閃擊徐州的同時,袁紹的主要謀士之一田豐就跑去力勸袁紹抓住機會襲擊許縣。但是袁紹沒有采納,對田豐的建議他沒有說不好,也沒有說好,就是沒有行動。他的理由很奇怪,他說兒子有病,等等看(紹辭以子疾)。
袁紹一共有幾個兒子,具體人數不詳,但至少有三個,除擔任青州刺史的袁譚外,次子叫袁熙,三子叫袁尚。本來袁譚應該是繼承人,但袁尚長得最好看(貌美),袁紹和正妻劉氏都喜歡三子袁尚,所以袁家的繼承人問題一直沒有明确下來。
袁紹消滅公孫瓒後,任命這三個兒子以及外甥高幹各負責一州,袁譚為青州刺史,袁熙為幽州刺史,袁尚為兖州刺史,高幹為并州刺史。袁紹的想法是,給這幾個孩子提供一個平等的機會,看看他們的才能誰更強。
此舉明擺着是要推翻袁譚嫡長子的地位,為立袁尚做鋪墊。對此,大部分人都表示反對,沮授說:“一個兔子跑到街上,就會有許多人追他,有一個人把它捕住了,想逮它的人就會住手,因為這只兔子已經有主人了。希望您能看一看前人失敗的教訓,想一想逐兔分定的含義。”但是袁紹不聽,沮授大失所望,說:“大禍就要從這裏開始了(禍其始此乎)!”
沮授為什麽會危言聳聽?因為在一般人的心裏,嫡長子繼承制是亂不得的,不管老大多麽笨、多麽傻,都輕易不能另立他人,否則就會引起混亂。這種混亂,如果放在普通百姓家裏,頂多也就是摔幾個碗、砸幾口鍋的事,但在君王和諸侯家裏,就足以引起時局的動蕩。
袁紹事實上已經是一方諸侯,因而他的家事已不再是普通的家事,而與這幾個州、數百萬人口的前途命運息息相關,所以沮授才會那麽着急。可惜的是,袁紹看不到這一點,還以為家事就是自己家的事,與別人無關。
袁紹打破常規的舉動果然在部下中造成了混亂,審配、逢紀等人看到袁紹偏愛袁尚,開始聚攏到袁尚周圍,而辛評、郭圖支持袁譚。袁紹陣營裏形成了不同的派系。
一個集團裏這樣的派系一旦形成,就會把派系的利益淩駕于集團整體利益之上,不惜犧牲集團的利益以換取少數人的利益,歷史上很多有前途的集團都是這樣走向覆滅的。
田豐建議袁紹抓住機會南下,這雖然是一個高明的謀略,但沒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袁紹又以兒子有病為借口把田豐的建議擱置了。田豐很生氣,他用手杖敲着地說:“這麽好的機會,卻因為小兒子生病而失去了,真可惜呀!”
上面是《三國志》的記載,在其它史書中還有完全不同的描述。
《獻帝紀》一書稱,袁紹很快發起了向南面的進攻,在出師前袁紹集團內部還進行了一次激烈讨論。袁紹的主要謀士旗幟鮮明地分成了鷹派與鴿派兩個陣營,鴿派的首領正是上面積極請戰的田豐。
《獻帝紀》稱沮授和田豐都反對袁紹出兵,他們認為連年征戰,百姓已經苦不堪言,現在應該發展生産,積蓄力量,可以用三年時間而不是妄圖通過一場戰争來打垮敵人(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
他們的看法遭到鷹派代表人物審配、郭圖等人的反對,鷹派認為現在正是最佳的戰略機遇,機會稍縱即逝,不能慢慢拖着,應該一舉擊敗曹操,否則等曹操勢力更加壯大收拾他就難了。
沮授反駁道:“救亂誅暴是義兵,恃衆憑強是驕兵,驕傲的軍隊最先失敗。曹操迎奉天子,定都許縣,現在率兵攻打他是為不義。曹操推行法令,訓練軍隊,情況跟公孫瓒完全不一樣。現在發動沒有理由的戰争,而放棄最安全可靠的策略,我真感到擔心。”
沮授搬出了戰争的正義與非正義論題,其實扯得有點遠了,聽起來冠冕堂皇,但在現實局面下卻顯得蒼白空洞。沮授和田豐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想法,他們代表的是冀州本土人士普遍的觀點,本土派都不希望打,就像當年兖州人不支持曹操打徐州一樣。而審配、郭圖這些外來戶普遍贊成打,他們心裏默念的就是打回老家去。
袁紹也是一個外來戶,他傾向于鷹派的觀點。更重要的是公孫瓒滅亡後,他心裏統一天下的想法越來越強烈,甚至有點等不及了。
袁紹接受了鷹派的建議,不僅迅速組成了南下兵團,向黃河一帶開進,而且還做了很多戰争準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連續派出多路使者,拉攏同盟軍。
袁紹拉攏的重點對象是張繡、劉表和孫策,他想建立一個統一戰線,給曹操搞出一個包圍圈。
袁紹的這個戰略雖然不能說一點成效都沒有,但基本上都失敗了。
袁紹派往南陽郡的使者最先到達,他們見到了張繡,陳述了袁紹的主張。袁紹深知賈诩在張繡面前的分量,所以專門給賈诩寫了信,派使者暗中去做賈诩的工作(袁紹遣人招繡,并與賈诩書結援)。
張繡看到袁曹大戰一觸即發的形勢,也許他想都不用想就會站在袁紹這一邊,因為他與曹操之間是敵人,且曹操也視他為不共戴天的敵人。袁紹的使者說明來意,張繡當場就準備答應。這時,賈诩說話了。
賈诩當着張繡的面對袁紹的使者說:“請回去轉告袁本初,兄弟尚不能相容,又怎麽能容天下人呢?”
張繡聞言大吃一驚,問賈诩說:“這話怎麽說呀!”
打發走袁紹的使者,張繡問賈诩:“既然這樣了,下一步該怎麽辦?”
賈诩說:“不如投降曹操。”
張繡又吃了一驚,說:“袁紹強大曹操弱小,我們又與曹操互為敵人,怎麽能歸順他呢?”
賈诩說出了其中的理由。他說:“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這是第一條理由;袁紹強大,我們弱小,在這種情況下歸順他,必然不會重視我們,曹操弱小,得到我們必然欣喜,這是第二條理由;有霸王之志的人,肯定會把個人恩怨放在一邊,而讓普天之下都知道他的寬容,這是第三條理由。希望将軍不要再遲疑!”
經過賈诩一分析,張繡認為也有道理,于是率所部投降了曹操。
張繡投降曹操是一個非常大膽的決定,曹操只有如賈诩分析的那樣,是一個胸懷遠大志向、把個人恩怨抛于腦後的人,他對這項決定才不會後悔。張繡投降袁紹,基本上不用擔什麽風險,而投降曹操,則面臨着生死考驗。
所幸的是,一向料事如神的賈诩在這個重大問題上依舊保持了他的一貫正确,曹操聽說張繡投降自己,驚訝之餘,頓時感到欣喜若狂。
這時候,曹操已經移師到官渡前線,張繡攜賈诩到前線面見曹操,曹操拉着張繡的手不放,這個人曾經差點要了他的命,而且還欠他一個兒子、一個侄子加一員愛将的命,是一個他做夢都想誅滅的敵人。現在卻站在了他的面前,只要他願意,可以輕而易舉地完成複仇的想法,但現在所有的仇恨頃刻間土崩瓦解,因為他真的很高興。
曹操設宴款待張繡和賈诩,拜張繡為揚武将軍,封列侯,将張繡帶來的人馬就地編入官渡前線兵團。為了打消張繡的顧慮,他還主動提出兩家結為兒女親家,讓自己的兒子曹均娶張繡的女兒為妻。
曹均是周姬所生,後來過繼給曹操之弟曹彬,曹丕當皇帝後封這個弟弟為安公。
對于賈诩,曹操更喜歡。雖然這是一個可怕的對手,讓自己連吃了三次苦頭,但今天終于得到了他,曹操有如獲至寶的感覺。曹操拉着賈诩的手說:“是先生您讓我在天下人面前增添了信譽呀!”
曹操以獻帝的名義封賈诩為都亭侯,給他安排的職務更高,委任他為執金吾,這是部長級的高官,負責宮外的安全保衛工作。當然這是個虛職,曹操不會讓賈诩跑到許縣給劉協站崗去,委任賈诩一個很高的榮譽性職務,目的是先把他從張繡身邊挖過來,他要把賈诩留在自己身邊。
董昭改任徐州牧後,冀州牧一職空缺,曹操于是任命賈诩為冀州牧。這雖然也不是一個實職,但在一般人心目中州牧屬于“封疆大吏”,地位很高。
曹操不費一兵一卒,居然解決了懸在心頭很久的難題,對南邊的形勢,他可以松口氣了。
【六、劉表不可告人的想法】
袁紹在聯絡張繡的同時,也派人來到襄陽見劉表,希望結成同盟共同對付曹操(紹遣人求助)。
劉表口頭上答應袁紹,但未做實際行動。在袁曹争鋒中,劉表只打算坐山觀虎鬥,保存實力,以觀天下之變。
目前,足以與袁紹、曹操集團實力匹敵的,也就是劉表了,無論地盤之大還是人馬之衆,劉表都是當時天下的第三號人物,他的态度自然會影響到即将開始的大決戰的勝負。
對于劉表不介入的策略,他的部下有人提出不同意見。
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都勸劉表說:“豪傑并争,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軍。将軍若欲有所作為,可以乘此機會崛起;如果不然,也應該選擇其中的一方給予支持(固将擇所從)。将軍擁有十萬之衆,怎麽能坐而觀望呢?”
韓嵩等人進一步分析說,如果對袁紹和曹操都不支持也不反對,實際上在他們那裏都不會落好(兩怨必集于将軍),以劉表目前的狀況,想中立那是不可能的。韓嵩、劉先以及劉表最重要的部屬之一蒯越都勸劉表站在曹操一邊。
他們認為曹操這個人相對賢明,天下賢俊紛紛歸順,在決戰中有可能戰勝袁紹。如果現在不聯合曹操,将來等他戰勝了袁紹,必然舉兵南下荊州,到那時恐怕就無法抵擋了。他們提出了一個大膽建議:“不如率全部荊州歸降曹操(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操必然厚待将軍,那樣以來可以長享福祚,垂之後嗣,這才是萬全之策!”
劉表手下的大多數人也都支持曹操,這讓劉表頗為猶豫(表狐疑),他決定派韓嵩到曹操那裏走一趟,觀察虛實後再作決定。
這樣,大約在建安五年(200年)初,劉表的使者韓嵩一行來到官渡前線見曹操,受到曹操的熱情接待。韓嵩此行對曹操和曹軍都有了更深的印象,又到許縣拜見了天子。在曹操的授意下,獻帝拜韓嵩為侍中,韓嵩大概不願意接受,表示想回荊州,獻帝又改任他為荊州刺史部零陵郡太守。
這番好意沒想到給韓嵩幫了倒忙。韓嵩回到襄陽,向劉表彙報所見所聞,對曹操大加贊揚,并勸說劉表送兒子到許縣作人質,以證明自己的誠意,這引起了劉表的懷疑。
在一次有數百名部屬參加的會議上,劉表召見韓嵩,盛怒之下,拿出天子所賜的符節,意思是想斬殺韓嵩。大家都很緊張,勸韓嵩趕緊賠罪,韓嵩動都不動。大家對劉表苦苦相勸,就連劉表寵愛的妻子蔡氏也出來說情,劉表盤問了與韓嵩随行的人,沒有發現韓嵩有什麽不妥的行為,這才饒過韓嵩一死,把他關了起來。
韓嵩事件平息,勸劉表投靠曹操的建議沒人再敢提起,劉表繼續他原先制定的策略,對袁紹那邊盡量敷衍,對曹操不和不戰,保持他的中立。
劉表突然問罪于韓嵩,表面看來是他的疑心病犯了,看到韓嵩不加掩飾地稱贊曹操,加之他接受了獻帝的任命,心裏很不痛快,所以發難。陳壽評論這件事時也認為,劉表雖外貌儒雅,但內心多疑忌,像這樣的事很多(皆此類也)。
但實際上也許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作為舉足輕重的一方諸侯,劉表一開始的想法就是坐山觀虎鬥,誰都不支持,誰也不反對。因為,投降曹操或袁紹,對于蒯越、韓嵩等人來說是無所謂的事,但對劉表來說差別就大了。
自己當老板掙的再少也是老板,給別人打工掙得再多也是個打工仔,劉表不糊塗。若幹年後孫權也面臨了同樣的問題,孫權手下大多數人也如韓嵩、蒯越一樣主張投降,而孫權寧可冒滅亡的危險也不願意投降,道理是一樣的。
劉表想中立,但韓嵩、劉先、蒯越等人都勸他投降曹操,也許勸他的人還有不少,尤其是蒯越這樣的地方實力派,他的意見劉表不能置之不理。無奈之下,他派韓嵩到曹操那裏走一趟,說是考察情況,實際上是做給主降派們看的。
韓嵩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回來對曹操一陣猛捧,這給了劉表問罪于他的一個口實。劉表問罪韓嵩可以把他叫到辦公室裏來談話,也可以把他交給有關部門審查,完全沒有必要當着手下數百人的面進行。劉表此舉,正是明告那些有同樣想法的人閉嘴。
這樣看來,劉表做事也挺有手段,對于投降派,孫權氣得拔劍剁桌子,劉表只需不露聲色地召集大家開個會,也達到了他想要的效果,可見其城府更深。
但是不久之後,劉表遇到了麻煩,荊州的後院突然出了事。劉表的長沙郡太守張羨在孫堅舊部桓階的策動下反叛,周圍的零陵郡、桂陽郡、武陵郡紛紛響應,荊州的南方四郡眼看要獨立。
桓階字伯緒,長沙郡臨湘縣(今湖南長沙)人,孫堅當長沙郡太守時很賞識他,舉薦他為孝廉。後來孫堅死于襄陽城外,別人都不敢表示什麽,他冒死為孫堅發喪,劉表感其義氣,沒有為難他。
桓階後來跟張羨關系很好,張羨是南陽郡人,《英雄記》說他在南方四郡一帶很得人心,但他性格倔強,劉表不太喜歡他,對他也不夠尊重(不甚禮也)。
袁曹相持于官渡,桓階勸說張羨不如抓住機會投降曹操,“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張羨表示同意,于是聯絡周圍的另三個郡同時舉兵抗拒劉表,派出使者去見曹操。
曹操簡直不能相信天底下還有這樣的好事,如此一來,等于給劉表的脊背上頂了一把刀,荊州方向更沒有問題了。
劉表急攻張羨,後來張羨病死,桓階逃匿,南方四郡之叛平息。
再後來,曹操南下荊州,他找到了桓階,當得知他策動張羨有功時,就把他留在自己身邊任職。曹操當丞相後,桓階擔任過丞相府辦公室主任(丞相主簿)。曹丕稱帝後,桓階升任尚書令,成為曹魏的重臣,于曹丕在位時病逝。
南方四郡叛亂雖然被劉表平息了,但此舉牽制了劉表的行動,讓他在袁曹對峙時無暇顧及北方之事。
袁紹寄予厚望的兩路盟軍,一路投靠了曹操,一路态度消極,只想中立,且又自顧不暇。袁紹渴望給曹操來一個大包圍,這個計劃看來要歇菜了。
袁紹派出來的使者其實遠不止這兩路。袁紹給自己老家同時也是曹操大後方的汝南郡也派出了使者,拉攏的對象是李通。
袁紹給李通開出了很高的價碼,任命李通為征南将軍,刻好了印章,準備了绶帶,由使者帶給李通。曹操給李通的軍銜僅是裨将軍,職務僅是汝南郡的陽安都尉。袁紹給的是大軍區司令,李通現在擔任的是地區公安局局長,雙方相差何止三級?
面對袁紹的厚禮,李通卻堅定地站在曹操的一邊。但是,李通的親戚以及手下很多人都主張投靠袁紹,他們看到袁紹勢力強大,擔心曹操沒有多少勝算。
不光是袁紹,劉表也派人來招降李通,但都被李通一一拒絕。李通的親戚和手下人都很生氣,苦口婆心地勸他,李通手按着劍,厲聲道:“曹公是明哲之人,必定會贏得天下。袁紹雖然表面強盛,而能力有限,最終一定會成為曹公的俘虜。我意已決,至死都不會改變(吾以死不貳)!”李通殺了袁紹派來的使者,把使者首級以及袁紹給他的征南将軍印绶呈報給曹操。
汝南郡是袁紹的老家,袁氏在這一帶很有影響力,聽說袁紹就要殺回來,社會上謠言亂飛,人心浮動。趙俨在汝南郡當朗陵縣長,和李通很要好,遇事常一塊兒商量。趙俨對李通說:“現在形勢很嚴峻,人心惶惶,征戶調一事如果照常進行的話,會不會激起叛亂?”
李通也看到了這個問題,但他有顧慮:“曹公與袁紹相持甚急,正是因為有的郡縣準備叛亂,所以如果我們不送戶調的話,會不會有人說我們也在觀望?”
趙俨說:“你考慮的也不是沒有道理,但事情應該分清輕重。現在還是應該暫時不征,我替你去解釋。”趙俨給荀寫信,說明了情況。荀立即轉報了曹操,曹操下令不僅暫停征調,還把前面征收的發還縣民,上下皆大歡喜。
在李通、趙俨等人的努力下,汝南郡的形勢慢慢穩定,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曹操的後顧之憂。
之外,袁紹還向青州的臧霸以及關中諸将也派出了使者,但收效都不大。臧霸的态度很堅決,全力支持曹操,“泰山幫”裏除了昌以外都站在了曹操一邊,他們集中精兵,布防在青州一線,防止袁軍從東面包抄徐州和兖州。關中地區的大小割據勢力在鐘繇和衛觊等人的努力下,要麽表态支持曹操,要麽保持中立。
【七、孫策意外之死】
但是,袁紹并沒有完全失望。
還有一路人馬,袁紹本來沒有抱太大希望,他或許也派了使者去聯絡,但沒有這方面的記載。這路人馬很強大,袁紹只希望他不投靠曹操就行,但沒有想到的是,他卻主動向許縣殺來了。他就是孫策。
孫策在江東發展得很快,先後把劉繇、王朗、華歆等朝廷委任的郡太守打敗,又收拾了境內的嚴白虎、白朗等匪寇,占據了揚州六郡中的江南四郡。
對于孫策的崛起,曹操感到了威脅。據《吳歷》記載,曹操聽說孫策平定了江東,曾經多次說過一句話:“猘兒難與争鋒也。”《說文解字》說“猘”的意思是狂犬,曹操說這話并無貶意,是說這個勇猛的小子。
為了安撫孫策,曹操除了以獻帝的名義授以孫策官職、封侯外,還把一個侄女許配給孫策的弟弟孫匡,又為自己的兒子曹彰娶了孫堅侄子、孫策堂兄孫贲的女兒,對孫策的另外兩個弟弟孫權和孫翊,都按照朝廷制度進行征辟,又讓揚州刺史嚴象舉孫權為茂才。
孫策表面上擁戴許縣朝廷,但還是一心想着擴充實力。他趁袁術稱帝後牆倒衆人推之際主動向江北出擊,占了江北的不少地盤,接收了袁術許多舊部。僅在突襲廬江太守劉勳的皖城之戰中,他就收編了袁術的舊部以及僞朝廷的百工、樂手等三萬多人,其中有相當多的水軍,袁術和劉勳的老婆孩子也成了他的俘虜。
皖城之戰孫策的另一大收獲是得到了本地美女大喬。大喬名字不詳,她的父親人稱喬公(不是與曹操關系密切的前司徒梁國人橋玄),她有一個妹妹人稱小喬,二喬是出名的美女(皆國色也)。孫策自納大喬,把小喬許配給自己的好朋友兼部将周瑜。
劉勳敗走投奔曹操後,孫策在江北的勢力得到了更大發展,他任命李術為廬江郡太守,利用從劉勳那裏俘獲的水軍,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了長江上游劉表的勢力範圍,在這裏駐紮的是劉表的部将黃祖。
對孫策而言,黃祖還有另一重身份:殺父仇人。
當年在襄陽城外的岘山,正是黃祖所部将孫堅射殺。無論出于擴充地盤的需要,還是出于報殺父之仇的想法,孫策都将下一個攻擊對象鎖定在黃祖身上。孫策任命周瑜為江夏郡太守,這個職務黃祖正在擔任,雖然地盤還在人家手裏,孫策已經志在必得了。
劉表見黃祖有危險,立即派侄子劉虎以及部将韓率五千長矛軍來支援,但他們不是孫策的對手。據孫策呈報給許縣朝廷的戰報稱,此戰俘獲黃祖的親屬七人,斬殺劉虎、韓以下二萬餘人,另有一萬多人溺水身亡,繳獲各類船只六千餘艘,孫策取得大勝。
幹寶的《搜神記》裏記載了一個傳說:在孫策此次西征的隊伍裏還有一個身份特殊的人,他是名字叫于吉,就是那個著名的道士。關于他的故事很多,在許多書籍裏,于吉都是個無所不能、呼風喚雨的人物。
于吉在江東一帶的活動有很多記載,歷史上應該确有其人,從各種記載來推測,他應該是某個民間宗教團體的領袖,影響很大,這樣的人鬧不好就成了又一個張角,所以為統治者所忌憚。
《搜神記》說,此次出征期間遇到大旱,于吉不知因為什麽事得罪了孫策,孫策命人把于吉抓了起來,五花大綁,扔在大太陽地裏讓他祈雨,如果能祈來雨就可活命,否則就殺頭,這是公孫瓒曾經給劉虞弄的待遇。但于吉比劉虞牛,一會兒便雲氣上蒸,再過一會兒大雨降了下來,溪澗盈溢。将士們都很高興,以為于吉必然沒事了,都去向他祝賀。孫策更不能容忍,于是把于吉殺了。
關于于吉之死,也有另外一些說法。畢竟《搜神記》嚴格來說不是史書,所記內容真實性很差。但于吉之死與孫策之死有些關聯,所以姑且引述。
孫策取得西征黃祖的大勝,這時已經是建安五年(200年),曹操與袁紹開始對峙于官渡。
對于形勢的判斷,孫策跟劉表的想法不一樣,他認為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想趁曹軍主力北上對抗袁紹之機,對許縣發動突然襲擊。
孫策的這個想法如果付諸實施,以後的歷史會是什麽樣将很難說。但是,也可能是曹操的命大,也可能是孫氏家族陷入了一種神秘的不可知的魔咒中,孫策的軍事部署都已經完成了,即将從背後向曹操發起攻擊之時,孫策居然離奇地死了,死法跟他的父親孫堅差不多:路上遭人暗算,中箭不治身亡。
這件事的确很離奇,純屬偶然事件,卻足以改變歷史的進程。
據《江表傳》記載,孫策在襲擊許縣前,想對曹操的部将廣陵郡太守陳登先發起攻擊,解除右翼的威脅。陳登留在徐州是曹操為對付袁術和孫策布下的一手棋,他沒有辜負曹操的期望,發展勢頭很猛,不僅在江北一帶給孫策造成威脅,而且還聯絡江東的嚴白虎,準備随時給孫策以重擊。
孫策不敢輕敵,他親自率軍征讨陳登,進軍到丹徒,在這裏等待運送軍糧,想等軍糧運到後再向陳登發起總攻。孫策喜歡打獵,在等待的幾天空閑時間裏,他只帶着幾個随從就外出打獵去了。
對于孫策喜歡輕出微行這種冒險行為,他手下的名士虞翻曾經規勸過他,孫策嘴上表示接受,但總難改老毛病,這一回果然出事了。
孫策領人追鹿,他騎的是好馬(所乘馬精駿),手下人的馬追不上。孫策一個人在前面跑,突然從林中冒出來三個人。
孫策厲聲問道:“你們是什麽人?”
這幾個人回答:“我們是韓當将軍的士兵,在此射鹿。”
孫策說:“韓将軍手下的士兵我都認識,從沒有見過你們!”
孫策意識到有危險,取弓便射,其中一個人應弦而倒。剩下兩個人害怕了,舉弓向孫策對射,結果有一箭射中了孫策的面頰。孫策手下人随後趕到,把他們全殺了。
事後得知,這幾個人是前吳郡太守許貢的舊部。許貢的身份跟劉繇、王朗等人差不多,是朝廷任命的郡太守,也是孫策打擊的對象。相對于劉繇等人來說,許貢沒有什麽實力,一度依附于劉繇。
孫策消滅了劉繇、王朗等異已勢力後,許貢內心不滿,他多次向朝廷秘密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