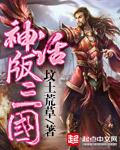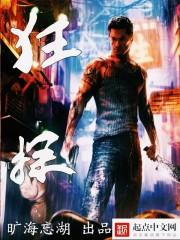第28章 (2)
在曹操幾乎走投無路的時候,是他出手相救,才化解了曹操的危機。自己騰不出手來去迎接天子,曹操去了應該算是自己派去的,曹操理應向自己彙報彙報情況吧。袁紹在邺縣等着曹操彙報工作,曹操沒有來,也沒有派個人來,卻等來了獻帝措辭嚴厲的一封诏書,把袁紹臭罵一頓,袁紹的肺都快氣炸了。
這件事《三國志》裏沒寫,僅記錄在《後漢書》中,說獻帝到許縣後,給袁紹下了一封诏書,責備他雖然地廣兵多,但只顧培植自己的勢力,擅自征伐,不來勤王(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讨伐)。
诏書雖然是以獻帝名義下達的,但幕後指使一定是曹操這小子,這不是公然以下犯上嗎?地廣兵多的又不是我一個,有幾個勤王去了?曹操自己不也到處讨伐別人嗎?為什麽只點名批評我呢?袁紹實在想不通。
袁紹覺得既然是天子的诏書也不能不有所回應,他認真地給獻帝上了一份書,這份文件挺長,全文也收錄在《後漢書》中,一看就是下了不少功夫寫的,可能出自大筆杆子陳琳之手。這份上書的開頭部分尤其精彩,袁紹寫道:
“我以前聽說有了蒙冤之人上天會五月降霜,又聽說悲聲痛哭可以讓城牆崩塌,每當看到這些我都認為是真的,但跟現在的情況一比,才知道那些都是假的,為何這麽說?我為國家做了那麽多事,搭上了整個家族的性命,一片忠心卻換來了如此罪過,怎不讓人日夜哀嘆、心腸裂斷、眼裏哭出血來(晝夜長吟,剖肝泣血)?但即使這樣,也沒有見城塌霜降來應驗,可見原來那些傳聞都是假的。”
這段話中心意思就一個:冤!然後袁紹從自己參加工作開始說起,說他如何跟張讓等宦官作鬥争,在何進被殺後如何力挽狂瀾,如何不畏董卓的強暴,後來如何在孟津休整兵馬,領導反董大業。袁紹一再申明的是,自己對帝室一直忠心不二,一直以來都在做着匡扶漢室的努力,絲毫不敢懈怠。
這封長篇上書裏除了袁紹不停地訴委屈之外,還透露了一些有趣的信息。一個是說曹操到兖州的活動是袁紹指派的(以議郎曹操權領兖州牧),而且說,曹操幾次都快要死了,是袁紹救了他(曹操當死數矣,我辄救存之)。這些或許符合事實,但卻對曹操有些不利,這也就是為什麽除《後漢書》以外的其它史書都未記載這件事,也沒有收錄袁紹這份上書的原因。
另一個是,袁紹也順便解釋了他跟袁術翻臉的原因,在袁紹看來他跟袁術不合完全是由一個人引起的,這個人就是朝廷特使馬日。當初朝廷派馬日和趙歧出使關東,馬日到了袁術那裏,由于他處事不當、偏聽偏信,使得他們兄弟倆成為仇敵。
袁紹說的後一件事十分強辭奪理,但此時馬日剛剛去世,把責任推給死人,反正也無法查證。袁紹想說的是,他很忠誠,很努力,很正直,所以很無辜,很委屈。
袁紹的上書送到許縣,他心裏的氣還沒有散完,又來了一件事把袁紹心頭的怒火徹底逗了起來:袁紹接到诏書,朝廷任命他為太尉。
太尉名列三公,以袁紹的年齡和資歷能擔任太尉一職無疑是件榮耀的事,數十年來,三公已經快要成了袁家的專利,從他父輩往上數,四代人一共出了五位三公。而他這輩人裏還沒人有這個榮耀,如今能當上三公,且是朝廷正式任命而非自己“表奏”的,在家族的三公榜上再續一筆,那将是多麽值得驕傲的事。
可是,袁紹一打聽,得知曹操擔任的是大将軍,高興勁一下子沒有了,袁紹認為,曹操既然是大将軍,他這個太尉也就一錢不值了。
大将軍位在三公之上,是文武百官的首領,在設大将軍的情況下,三公的地位就矮了一截。尤其是太尉,在三公裏分管軍事,與大将軍的職權重疊,更是形同上下級關系。
如果接受太尉的任命,就承認自己甘居曹操之下,這怎麽可以?
袁紹的不滿也有些道理,即使是現在,無論袁紹還是其他人,都會認為曹操只不過是袁紹陣營中的一員,袁紹是上級,曹操是下級,現在居然掉轉過來了。袁紹想,即使自己肯接受,手下這些人會怎麽想,這不是鼓勵大家以下犯上嗎?
《後漢書袁紹傳》說,袁紹上表天子不接受這項任命。《後漢書陳紀傳》進一步補充說,袁紹不僅沒有接受太尉的任命,而且讓位給陳紀。陳紀自然不敢接受,他此時被朝廷任命為外交部部長(大鴻胪卿)。陳紀,著名的穎川郡陳氏家族成員,他的兒子陳群日後成為曹魏陣營裏的名臣。袁紹不接受太尉的任命,這成為一件棘手的事。曹操這才發現,在處理這個問題上他考慮得有些不周。
原本他以為,袁紹無論擔任什麽職務都是名義上的,沒有實質意義,對袁紹來說,太尉已經是很不錯的安排了,他沒費一兵一卒就白得了這個職務,應該滿意。沒有想到,袁紹絲毫不領情,雙方的隔閡反而因此進一步加深了。
曹操早就明白他跟袁紹遲早會有一場決戰,但不是現在。不僅如此,袁紹還是他要利用的力量,跟袁紹過早攤牌,那是極不明智的做法,曹操越想越後悔。
他決定辭去大将軍一職,讓給袁紹,自己擔任司空。
這是很傷威望的事,換成別人,寧可錯下去也不會輕易低頭,但曹操是個務實的人,他寧願損失一些個人威望,也要把與袁紹的同盟關系繼續維持下來。
這項任命很快以獻帝诏書的形式下達,曹操辭去大将軍,改任司空一職。可是,袁紹那邊卻毫無反應,接到诏書後,如果接受,應該立即上書謝恩;如果不接受,也應該有所表示呀。曹操明白,袁紹面子上還有些下不來。
過了年,他想派個有分量的人到邺縣走一趟,幫袁紹找回面子,讓他消消氣,把大将軍的任命接下來。曹操想了想,覺得孔融最合适。
孔融的名氣沒有問題,目前擔任部長級的将作大匠一職,地位也沒有問題。曹操讓孔融走一趟,還有一個原因,想通過這件事讓他們緩合一下矛盾。
一年多前,孔融還是袁紹的敵人,他跟袁紹的長子袁譚都擔任青州刺史一職,袁譚攻擊孔融,打了大半年。孔融到了許縣後,心裏常常不踏實,總怕曹操哪一天受袁紹之命找他的麻煩。孔融剛一聽說曹操讓自己出這趟差,脊背上直冒涼氣,莫非姓曹的這小子真要把我支到袁紹那裏挨收拾?但孔融是個極聰明的人,經過簡單地分析他很快明白了曹操的用意,曹操想收拾他不會等到現在,曹操是想幫他的忙。
孔融很感激,盡管他以後成了反曹鬥士,但在建安初年他跟曹操的合作還算不錯。孔融接受派遣,于建安二年(197年)三月來到邺縣,宣布朝廷對袁紹大将軍的任命。
獻帝不僅拜袁紹為大将軍,而且封他為邺侯,這是一個縣侯,較袁紹此前的伉鄉侯高一級,還賜給袁紹天子的節钺,以及只有天子才能擁有的虎贲衛士百名。這還不算,獻帝還給了袁紹一個新的行政職務:督四州事。這四個州指的是冀州、青州、幽州和并州。
獻帝下達這項任命時一定沒有查閱過近幾年的皇家檔案,也許皇家檔案已經全丢在逃亡路上了,總之這項任命很有問題,因為幾年前獻帝也曾頒發過同樣的任命,就連所督的這四個州也絲毫不差,不過那是頒給另外一個人的,公孫瓒。
公孫瓒那邊沒有免職,這邊又重新任命了新人,如果不是技術性錯誤,那就只有一個解釋:讓舊人和新人相鬥。
這可能是曹操故意安排的,當年“三人小組”能想出來的主意,曹操更不在話下,袁紹和公孫瓒已經勢如水火,給他們加把柴,讓火燒得更猛些。
失去大将軍職務的曹操也沒有什麽實質性損失,官位是死的,規定是活的,他擔任了司空一職,同時代理車騎将軍,還順便搞了一次職務改革,規定司空在三公中地位最高,是朝官的首領(百官總已以聽),仍然把政權和軍權牢牢掌握在手中。
【五、“曹統區”掀起大生産運動】
解決了朝廷的人事安排問題,暫時平息了袁紹的不滿,曹操還有一系列挑戰需要面對,最突出的問題來自于經濟方面。
曹操離開兖州大本營,出于戰略考慮将新首都定在許縣,在後勤保障方面就要承擔很大的壓力。近一兩年來,曹操采納毛等人的建議,在兖州一帶積極發展生産,基本保障了自身的糧食供應問題,從而讓自己處處居于主動。
但是,曹操在許縣一帶基礎還不很紮實,許縣以及周邊的穎川郡、汝南郡雖然曾經是重要的農業區,但這些年來遭受戰争的影響也最深,黃巾軍在這裏勢力很大,有大量人口流失到了南面的荊州地區。
朝廷正常運轉需要大量糧食、布匹等物資,軍隊也需要後勤保障,這些物資如果都依賴兖州供應,浪費會很大,兖州那邊也難以為繼。
拿軍糧運輸來說,就是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從兖州運到許縣來必須組織大量人力參與運輸,還要考慮運輸隊伍途中的物資消耗,往往運一車糧食,至少還得再準備一車糧食供人們路上吃,另外,沿途安全又難以保證,這個辦法基本上不可行。
許縣的糧食供應問題必須立足于就地解決。曾在東郡任東阿縣令的棗祗和夏侯的副将韓浩同時向曹操建議,通過在許縣周邊一帶進行屯田的措施解決目前的燃眉之急。
棗祗是穎川郡本地人,家住陽翟縣,跟郭嘉同縣。曹操在東郡時,棗祗在東郡下面的東阿當縣令,張邈、陳宮之叛,兖州近八十個縣裏只有棗祗的東阿縣等三個縣沒有叛變,為曹操反敗為勝立下了大功。棗祗這時也随曹操來到許縣,有的史料稱他此時擔任獻帝近衛部隊的指揮官(羽林監)。
韓浩一直擔任夏侯的副手,當年夏侯被人劫持,韓浩臨危不亂,将夏侯解救出來,曹操事後對他進行了表揚。
棗祗、韓浩建議曹操效仿漢初以來的經驗,把流民組織起來,開展農業生産,開展大規模的屯田。
屯田作為制度其起源可考的是漢文帝時期。據《漢書晁錯傳》記載,著名改革家晁錯分析了秦朝守塞北失敗的教訓,認為單純以戍卒守邊的制度有很大毛病,必須實行“且屯且守”的制度,把屯田與戍邊結合起來。于是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漢文帝下令在邊郡屯田,這比漢武帝時經濟專家桑弘羊建議屯田西域還要早得多。
不過,晁錯和桑弘羊所推行的屯田都與國防建設有關,屬于半軍半民性質,許縣的情況與那時有很大不同,能不能參照前人的辦法推行,在當時還存在着争論。
反對屯田的人也不少,據《三國志司馬朗傳》等史籍記載,對于曹軍收複的大量無主土地,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應該賞給有功之人,有人甚至提出恢複古代的井田制,大力推行土地私有化。實行屯田實際上就是土地“國有化”,由于反對的人不少,曹操也不得不有所考慮。曹操讓棗祗找荀等人商議,荀支持屯田。在當時特殊的情況下,只有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才能度過危機。
經過內部讨論并逐步統一了思想後,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頒布《置屯田令》,從定國安邦的戰略高度,充分肯定了秦皇漢武獎勵耕戰,實行屯田的歷史經驗,闡述了屯田積谷的重要意義,下令開始屯田,标志着這項“戰時經濟政策”正式實施。
從建安元年到魏元帝鹹熙元年(264年),這項制度推行了七十年,可以說它伴随着曹魏帝國的興衰始終,成為曹魏勢力崛起的經濟基礎。
屯田首先在許縣附近試點,具體做法是,把已經找不到主人的土地收歸國有,然後把喪失土地的流民組織起來,由國家提供耕牛、農具、種子,收成由國家和農民按比例分成。
當時能集中起來的土地很多,流民也很多,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都不發愁,屯田很容易就搞了起來。
農業工作本應由九卿之一的大司農卿管理,為了加大推行力度,曹操決定親自抓這件事。在許縣試點期間,他任命棗祗為屯田都尉,任命自己的堂妹夫任峻為典農中郎将,管理具體的屯田事務,直接向自己負責。
也就是說,曹魏早期的屯田工作由司空府直接主導,由下面特設的屯田官來具體負責。這種制度一直保持了很多年。到曹魏時期,随着屯田規模越來越大,這項工作轉到了尚書臺管理,屯田官的職務和品級也逐漸固定下來,成為與地方行政官員并行的一個系列。
屯田剛開始推行的時候也遇到過一些挫折,據《三國志袁渙傳》記載,屯田剛開,被組織起來的農民還不太适應,他們經常逃亡。對此,袁渙建議曹操,農民都有安土重遷的傳統,不能一下子改變,必須因勢利導,要讓他們自願,不能強迫他們在土地上耕種(宜順其意,樂之乃取)。曹操采納了他的建議,情況這才有了好轉。
這麽好的政策為什麽農民不願意接受呢?原因是租稅太重。
過去農民給地主扛長活,交租的标準一般是收成的一半,即五五分成。曹魏搞屯田,政府扮演了地主的角色,收租也按這個比例。如果農民連耕牛一塊租,交租的比例就要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如此一來,大家的積極性自然不高。
漢代農業稅的比例大部分時候是三十稅一,即百分之三點三,現在屯田農民的稅務負擔是此前朝廷标準的十來倍。在農業生産技術落後、生産效率不高的情況下,這麽重的稅率,農民生活之艱辛可想而知。
但不這樣又不行,軍事鬥争每天都需要巨大的開支保障,曹魏所能聚集的財富十分有限,屯田這一塊相對較有保障,課以重稅既是循前朝慣例,也有不得已之處。
不過,曹操還是盡可能予以改進,包括合理安置勞力、分配生産資料、取消屯田戶的徭役等,保證屯田制的健康發展。對于屯田以外的普通農戶,曹操下令重新清查戶籍和財産,據此确定繳納賦稅的額度。
這有點像劃分成分,又像是核定收入申報納稅。據《魏略》記載,這項工作在“曹統區”全面鋪開,包括曹操本人在內都要評定“成分”,然後決定納稅标準。曹操家鄉的谯縣令給曹操、曹洪二人評為同一等級,曹操還說:“我家哪裏有子廉(曹洪的字)家富有呀!”
建安元年許縣屯田開始試點,次年就獲得了好收成,積餘糧達百萬斛。取得這樣的大豐收,除了新的農業政策發揮作用之外,據《齊民要術》一書介紹,還跟一種糧食品種的大面積推廣分不開。這不是新品種,它的名字叫“稗谷”,其實就是一種雜草,它不怕旱澇,容易生長,在《齊民要術》和《汜勝之書》這兩部古代最有名的農業著作裏,對它都有詳細介紹。
這種雜草也結穗,只是穗比較小,一般的作物出糧率可能在百分之六七十,這種作物只有百分之三四十,而且吃起來味道也不怎麽樣。但是這種作物有一個明顯優勢,那就是産量特別高。
一般糧食作物畝産約為七斛,按照百分之六七十的出糧率,實得糧食大約四斛左右;種稗谷一畝可收獲二三十斛,即使按照百分之三四十的出糧率,實得糧食也達到近十斛。
據《齊民要術》記載,曹操下令種植這種作物,“頃收二千斛”,即一百畝地收獲二千斛稗谷,糧食單産大增。《汜勝之書》還說,用糞便拌種子産量還會更高,不知道曹操讓人試過沒有。這種糧食口味雖然不佳,但作為戰馬的飼料應該沒有問題。種這種糧食,灑把種子在地裏就能長,不用管澆水除蟲的事,不耽誤軍事訓練,确實不錯。
曹魏屯田的規模很大,“曹統區”最興盛的時候曾控制或部分控制了十二個州,有九十一個郡國,大約七百三十個縣,而留下屯田記載的州就有十一個,郡國有二十八個。當然,實際情況肯定比這個還要多。
除了早期的民屯,建安末年又發展出軍屯,在“曹統區”的腹地以民屯為主,在與敵人接壤的地區大興軍屯,平時耕作,戰時打仗,亦兵亦民,在發展經濟、守土護邊方面成效顯著。曹操實行優先發展農業的政策,也培養了一批“農業幹部”,先後在曹魏“農業系統”擔任各級領導職務的有棗、任峻、國淵、袁渙、韓浩、裴潛、杜畿、呂虔、衛觊、蘇則、張既、鄭渾、徐邈、盧毓、嚴匡、杜松、弁揖、王、毛曾、倉慈、李勝、石苞等人,可以說燦若星河。“傷殘軍人”盲夏侯是這項工作的積極倡導者,多年後,他在淮南一帶搞軍屯,組織軍民修水庫,還親自參加勞動,擔土修壩。
【六、天才美少年】
現在,來說說曹操的家事。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将天子迎接到許縣,實現了自己事業上最重要的轉折。有了相對穩定的根據地後,他把家眷都接到了許縣。
曹操的正妻丁氏,年齡不詳,沒有生育子女;之後又娶了劉氏,生下長子曹昂,此年十九歲;曹操的第三任妻子,也是他最喜歡的女人卞氏小曹操五歲,本年三十七歲;據史料記載可知,曹操這個時候至少還有一個姓環的夫人和一個姓孫的夫人。
曹操的長女也是劉氏所生,以後她被封為清河長公主,後來嫁給了夏侯的兒子夏侯。
卞氏先後生了四個兒子,按長幼順序即曹丕、曹彰、曹植和曹熊。建安元年,曹丕十歲,曹植五歲,曹彰年齡不詳,介于曹丕和曹植之間,曹熊有可能還未出生。
除了曹昂、曹丕、曹彰、曹植這四個兒子,在去年即興平二年(195年),孫夫人還為曹操生下一子,名叫曹彪;今年,環夫人又為曹操生下了一個兒子,取名曹沖。
曹操一生,先後有二十五個兒子,女兒數目不詳,可考的除長女清河公主外,還有安陽公主、金鄉公主、高城公主以及曹憲、曹節、曹華等。安陽公主後來嫁給了荀的長子荀恽,曹憲、曹節、曹華三姐妹十九年後同時嫁給了漢獻帝劉協。
曹操一家如今人丁特別興旺,兒女們不僅人數衆多,而且其中還不乏出類拔萃者。他們之中日後不僅湧現出曹丕、曹植這樣的文學家,也有曹沖這樣的天才神童,還有像曹彰那樣能帶兵打仗的軍事人才。
這與曹操重視對他們的教育有關。在曹丕的回憶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曹操很懂得“教育要從娃娃抓起”的道理,在子女四五歲時就開始對他們進行各種教育,不僅有傳統的儒學、文學教育,他還特別重視騎馬、射箭、技擊這些實用型軍體活動,尤其對曹家的男孩子來說,他訓練起來更是嚴格,長子曹昂十幾歲時便被編到野戰部隊裏接受實戰鍛煉。
在曹操心目中,曹家的子孫們應該能文能武,個個成為精英。
在歷史上,名氣最大的是曹丕、曹植、曹沖等兄弟幾個,除此之外,在曹操的兒子中還有一個絲毫不遜色,成就更是不得了的人物,他就是建安初年來到曹家的何晏。
何晏不姓曹,因為他不是曹操的親兒子,而是養子。
何晏的父親叫何鹹,事跡無考,但何鹹的父親何進不同凡響。何晏就是已故大将軍何進的親孫子。
七年前,何進以外戚身份謀除宦官,結果反被宦官所殺,結束了一個時代。何進被殺時,何進的弟弟何苗也被殺,雖然沒有關于何氏一家被滅族的記載,但這個南陽屠戶出身的家族頃刻間土崩瓦解是掩蓋不了的事實。
當時的天子雖然是何進的外甥劉辯,但在随後的政治鬥争中,董卓支持劉協上臺,廢掉了劉辯,殺死了劉辯的母親何太後,按照政治鬥争的慣例,在何太後被殺的同時,何氏一族更是兇多吉少。所以有人推斷,何晏的父親何鹹大概死在這個時候,他死時未必看到了他的這個兒子,何晏有可能是何鹹的遺腹子,一般認為他生于那場大動亂的次年,即初平元年(190年)。
樹倒猢孫散,何鹹死後,他的妻子尹氏不知流落到了哪裏,但可以推斷的是,建安初年,曹操擔任司空後,她不知何故竟然來到了許縣,因為有資料顯示曹操此時正式納其為妻。
按照規範的稱呼,曹操的正妻只有丁氏一人,其他人都應該稱妾。尹氏是如何進入曹家的也已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認的是,她不是一個人來的,還帶着六七歲的兒子何晏。
何晏到了曹家後,衆人發現這個孩子很惹人喜愛,尤其是曹操,愛得不行,甚至超過了自己的親生兒子曹丕、曹植諸兄弟。何晏讨人喜歡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長得可愛,另一個是特別聰明。《世說新語》說何晏是個美男子(美姿儀),想必小時候也是個英俊少年。曹操自己長得不行,受他的基因影響,曹丕、曹植衆位兄弟長相上估計比較一般,曹彰生下來更是一頭黃毛,被曹操稱為“黃須兒”。在這個環境中,英俊少年何晏一定比較耀眼。
除此之外,何晏很小便展露出過人的才能,《太平禦覽》裏引用一本叫《何晏別傳》的書裏稱,曹操讀兵書時,遇到未解之處,試着問何晏,何晏小小年紀居然能分析得頭頭是道(分散所疑,無不冰釋)。
曹操對這個孩子簡直喜歡得不行,他想讓何晏幹脆改姓曹。哪知何晏根本不幹,他在地上畫了個圈兒,自己待在裏面誰叫都不肯出來,大家問他為什麽,何晏答道:“這裏是何家的房子(此何氏廬也)。”曹操知道了,就不再提改姓這件事。
姓沒有改成,但曹操還是喜歡何晏。吃的、用的、穿的都與曹丕兄弟們沒有任何區別,《魏略》一書說,曹丕看到這種情況特別不舒服(特憎之),每次見到何晏不叫名字,而是喚他為“假子”。
在曹操生前,何晏一直很受寵愛,後來曹操還把自己的女兒金鄉公主嫁給了何晏,何晏既是曹操的養子,又成了曹操的女婿。
何晏的岳母、金鄉公主的母親姓杜,其經歷與何晏母親尹氏很相似,杜夫人前夫是呂布手下的将領,名叫秦宜祿,杜氏在被俘後改嫁了曹操。除了金鄉公主,杜夫人還有一個兒子叫秦朗,是秦宜祿之子,像何晏一樣,秦朗也随母親一塊兒來到了曹家,成為曹操的養子。杜氏這段改嫁經歷充滿了戲劇性,後面還會提到。
随着何晏慢慢長大,他長得越來越白,這個白,既不是李白的白,也不是白居易的白,人家是真的白,是特別白、超級白,沒有抹粉就好像抹了粉似的,大家給他起了個外號,叫“粉面郎君”。曹丕的長子曹睿生于建安九年(204年),應該比何晏小十四五歲,曹睿當了皇帝後,何晏應該快四十歲了,他不太相信這個叔叔(或者叫姨父,金鄉公主是曹睿的親姨)會有那麽白,他懷疑何晏是抹了粉,于是想了一個辦法,要親自驗證一下“粉面郎君”的真假。
有一天,曹睿請何叔叔請飯,特意吃火鍋(肉絲湯餅),本來火鍋就熱,火還一邊烤着,不多時何晏就開始冒汗了,不時撩起衣襟擦汗。曹睿在一旁仔細觀察,發現何叔叔臉上一點搽過粉的痕跡都沒有,有點失望地說:“看來真是個粉面郎君呀!”
何晏為什麽這麽白呢?原因大概有兩個:一是人家何家的基因就是這樣的,要不然他的姨奶何皇後能受寵于靈帝劉宏嗎?另一個原因是何晏長年堅持服藥,這個白是一種藥物反應。
何晏服的藥名叫“五石散”,是以五種石頭為主要原料調制的藥物,這五種石頭是石鐘乳、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石硫磺,将這幾種原料調制在一起配制成藥的方法已經失傳。何晏吃了之後,估計效果不錯,同時期的大醫學家、針灸的發明人皇甫谧就曾經說,是何晏開始吃這種藥的,吃了之後,心神開朗,體力轉強。
對于魏晉史素有研究的魯迅先生曾說,“五石散”是一種毒藥,是何晏吃開了頭。何晏有錢,他吃起來,大家也都跟着吃。魯迅先生送給何晏一個“封號”:吃藥的祖師爺。
這些東西吃了真能強身健體、延年益壽嗎?實在不太清楚,但是應該會有一些立竿見影的效果,不然不會有那麽多人效仿。吃這種藥或許跟吃興奮劑一樣,有的人甚至認為跟吸毒差不多。
何晏長年服藥,他的臉色跟這個有很大關系,其實是一種病态。
何晏的名氣不完全是因為他的臉白,也不完全是因為他會吃藥,魯迅先生還送給何晏另外一個“封號”:玄談的祖師爺,何晏的名氣是從這裏來的。
魏晉以後,産生了一個新的哲學門派:玄學。何晏就是玄學公認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他還有王弼、夏侯玄、鐘會、荀粲等人。王弼是王粲的族孫,夏侯玄是夏侯淵的族孫,鐘會是鐘繇的兒子,荀粲是荀的兒子。這幾位有一個共同身份:高幹子弟。
他們的父輩和祖輩在前面抛頭顱、灑熱血地打江山,他們在後方沒有什麽事幹,于是經常搞聚會,吃吃喝喝搞得多了也很無聊,于是決定每次确定個題目大家辯論,有點像大專辯論會。他們辯論的題目常常讓人感覺浮虛而玄遠,如聖人有情無情、本末有無、聲無哀樂、言意的關系等,都是些玄而又玄的東西。辯得多了,影響也越來越大,終于辯出了名堂。
談玄慢慢成為一種新的風氣,到魏末晉初時逐漸演變成為新的社會潮流,那個時候的小資們通常都有一個好口才,這都是在辯論會上練出來的。
何晏的事以後還要講到。建安初年的許縣,随着何晏住進了曹家,曹操兒女們越來越多,曹家也更加熱鬧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