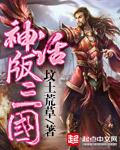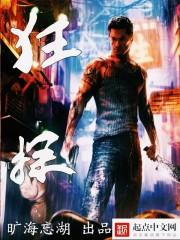第24章 (2)
将軍。”
孫策聽了,如夢方醒,激動不已。
在這個規劃中,張告訴孫策不要在袁術這邊耽誤時間了,應該及時向長江以南發展。揚州刺史部有六個郡,其中江北有兩個郡,分別是廬江郡和九江郡;江南有四郡,分別是丹陽郡、吳郡、會稽郡和豫章郡。袁術移師壽春後,江北的兩個郡已經基本為其掌握,而江南的四個郡,則基本上不在袁術掌握之中。
江南四郡的郡守或實際控制者分別為吳景、劉繇、王朗和諸葛玄。吳景和諸葛玄名義上屬于袁術,但吳景是孫策的舅舅,加上都尉孫贲是孫策的堂兄,丹陽郡具有很大的獨立性;袁術表諸葛玄為豫章郡太守,但豫章郡形勢很混亂,各種勢力都想染指,諸葛玄到任未能控制局面,袁術失去了對豫章郡的控制。剩下的吳郡實際控制者劉繇,原為揚州刺史,袁術來壽春後把他趕到了江南,可以看做是袁紹在袁術身後布下的一顆子,袁術必欲除之而後快;會稽郡太守王朗,原是陶謙的屬下,是長安朝廷正式任命的太守,政治傾向不明朗,還算不上袁術陣營裏的人。
江南四郡此時正是一團亂,袁術想一口吞下,無奈力不從心,其他勢力相距較遠,鞭長莫及。所以,張勸孫策南渡長江,以丹陽郡為基地,統一江南,之後虎視荊、揚,成為一方霸主。孫策認為有理,就跑到壽春,見着袁術,想要回父親孫堅留下來的子弟兵,之後渡江南下。
據《江表傳》記載,袁術很欣賞孫堅的這個兒子,但“不肯還其父兵”。孫策找得多了,袁術就出了個主意,說丹陽郡是出精兵的地方,你的舅舅在那裏當太守,你不如到丹陽郡去募兵。孫策無奈,渡江去了丹陽郡,在舅舅吳景的幫助下,很快募得幾百人,但是到泾縣(今安徽泾縣)時,遭到當地土匪祖郎的襲擊,隊伍被打散,孫策險些喪命。泾縣,就是後來皖南事變的發生地,看來這裏林深樹密,地勢險峻,自古以來行軍至此就很容易遭遇埋伏。
孫策募兵無果,又回到壽春,隔三岔五去找袁術要他爹留下的隊伍。袁術煩了,就把孫堅當年隊伍裏還沒有被拆散的一千多人還給了孫策。這支隊伍人數雖然不多,但是其中包括韓當、程普、黃蓋、朱治等人,對孫策的意義非同一般。
袁術把人給孫策也是有條件的,他讓孫策幫助自己平定九江郡,答應事後任命孫策為九江郡太守,孫策給袁術出了力,但到頭來袁術卻任命陳紀為九江郡太守。袁術又讓孫策幫他平定廬江郡,并且特別說明,上次食言是自己的不對,這回一定任命孫策為廬江郡太守。孫策又幫助袁術平定了廬江郡,但袁術像是得了失憶症,再也不記得當初說過的話,任命劉勳為廬江郡太守。這個劉勳,就是曹操早年的那個好朋友,後來他也歸附了曹操。
攤上這種朝三暮四、毫無信譽可言的領導,孫策真的覺得很受傷,也很無奈,他決心離開袁術,按照張的建議到江南發展。
孫策告訴袁術:“我願意到江南去,協助舅舅吳景平定江南各郡,到時候至少可以為您募得三萬甲士,助您完成匡輔漢室的大業。”袁術一聽大為高興,批準了孫策提出的行動計劃。大約在興平二年(195年)初,也就是曹操二次征徐州回師與呂布苦戰的時候,孫策渡過長江,開始了自己的拓疆之旅。
長江流到安徽境內時有一段向東北方向斜流,古人習慣以此段為标準确定東西和左右。把今天安徽省蕪湖市以下的長江下游南岸地區,即蘇南、浙江北部、皖南部分地區以及今江西的贛東北稱做江東。司馬遷《史記》中就有“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幹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同時,古人以東為左,以西為右,江東又稱為江左,江西則稱為江右。
孫策的開拓江東之戰打得激烈壯闊,在程普等宿将以及周瑜、張、張昭等人的幫助下,依靠舅舅吳景、堂兄孫贲等人的鼎立支持,打死了劉繇,趕跑了王朗,打退了陳登、劉勳等人的進攻,清剿了境內的嚴白虎、鄒他、錢桐、王晟、許貢等土匪,收服了華歆、虞翻、太史慈、祖郎等人,僅用了三四年時間,就基本上擁有了江南四郡。
關于這段歷史,與以後敘事有關的還将補述,此處只作簡單交待。
孫策的崛起是漢末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孫策靠着自己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個人號召力,趁着其他割據勢力無力插手江東之機,迅速平定了丹陽郡、吳郡、會稽郡的大部以及豫章郡的一部,擁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事實上脫離了袁術的控制,成為上升最快的割據力量。
孫策的崛起短時期內對曹操是有利的,孫策漸漸脫離袁術的控制,為曹操下一步戰略布局提供了新思路。面對袁術這個敵人,曹操可以通過拉攏孫策來牽制袁術。
從長遠來說,孫策及他的繼任者孫權,最終将成為曹操最可怕的對手之一。
【五、劉璋:生性軟弱反而占便宜】
興平元年(194年),在西南方的益州刺史部發生一件大事,益州牧劉焉死了。
劉焉就是那個提出“刺史改州牧”建議的人,這項政治改革被朝廷采納後,他又是首批被任命的州牧之一,靈帝中平五年(188年),他來到益州上任。
跟着劉焉一塊來益州的,還有他的心腹智囊、星象學家董扶,以及趙韪、吳壹等人。他們一行人打算從荊州溯長江而上到達益州,但到了州界一打聽,把他們吓了一跳:益州境內的農民起義鬧得正厲害,就靠他們這幾個文官,貿然前去必定是送死。
前面說過,益州的民風向來剽悍,充滿反抗精神。前益州刺史儉貪婪殘暴,激起了馬相、趙抵等人領導的農民起義,他們也打着黃巾軍的旗號,殺死了儉,後來馬相幹脆自己稱帝,隊伍發展到十幾萬人。
劉焉等人徘徊不前,不知道該進還是該退。正在心灰意冷之際,好運氣來了,從益州傳來消息,馬相等人被鎮壓下去,益州基本上平定了。立下這件大功的,是益州刺史部前從事賈龍。賈龍的角色,有點像陳宮、麋竺,是本地人,也是實力派,他們的政治傾向足以影響本地的局勢。賈龍平定益州後,聽說上級派來的新領導被困在州界,趕緊派人前來迎接。
這樣,劉焉揀了個大便宜,沒有費勁就得到了益州。他把州治遷到綿竹,開始了對益州的治理。劉焉這個人,應該說還是有些本事的,在擺平本土派與外來派之間的矛盾上,可以看出他頗有些手段。
當時益州的政治格局分為兩大派,一派是賈龍這樣的本土人士,在鎮壓馬相起義中立下大功,本應得到回報;另一派是董扶、趙韪這樣的外來戶,根基尚淺,但占據高位。
劉焉本人也是外來戶,當時還有大量湧入益州避難的從關中、荊州地區來的人,劉焉從他們中選拔出一支隊伍,稱為“東州兵”,是外來派的嫡系力量。
劉焉本來還不能跟本土派撕破臉,後來由于有東州兵撐腰,他決定先發制人。靈帝初平二年(191年),劉焉找了個借口殺了本土派重要成員王鹹、李權等十餘人,逼得賈龍、任岐等本土派人士起兵反抗,其實劉焉早有準備,不僅調動了東州兵,而且引進了羌族雇傭軍,很快便将賈龍、任岐殺了,本土勢力受到打擊,劉焉在益州的地位得以鞏固。
但這是威權之下的表面現象,益州本土勢力的生命力依然頑強,他們暫時雖然屈服,來日還将爆發。到那時,益州的政治分野更加複雜,随着大量外地人口的湧入,除了本土人、外地人、東州派這些政治勢力之外,扶風集團在益州也悄然興起,大家各懷心事,有勁不往一處使,加上繼任者的軟弱,終于一步步把劉焉父子在益州經營的基業引向了滅亡。
在處理益州內部政治矛盾上,劉焉雖然手段很強硬,但這種“硬着陸”的手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政治硬傷,也為日後留下隐患。
劉焉平定益州後的另一個重大動作是與漢中割據勢力張魯集團的結合。
張魯和他的父親張衡、祖父張陵都是早期的道教領袖,經過他們祖孫三代人的努力,創建了一支叫“五鬥米教”的道教組織。到了張魯時,他自稱天師,以秦嶺以南的漢中地區作為根據地,通過傳教擴大勢力。
漢中郡屬益州刺史部,作為益州牧,劉焉有義務對張魯集團出兵鎮壓,但他卻采取了另一種策略:合作。
劉焉私自授予張魯一個督義司馬的官職,并且派司馬張修協助張魯攻擊自己的下屬、漢中郡太守蘇固,讓張魯占據了漢中。張魯在漢中郡站住腳以後,仍然大力推行道教主張,建立了一套政教合一的政權組織,名義上受劉焉節制,但是有很大的獨立性。
漢中郡是益州的北部屏障,要進入益州,必須先進入漢中,再越過數重極險要的關隘才能到達。關中和漢中之間是巍峨的秦嶺山脈,在高山峽谷間僅有數條險峻的小道可以通行,在最險要的地方,只能靠人工修築的棧道通過。
劉焉密令張魯燒掉秦嶺山中的那些棧道,切斷了益州北面的出入口。益州的東面是大巴山和長江三峽,南面是尚未開化的少數民族地區,西面是荒無人煙的高原,在這個四面封閉的世界裏,劉焉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覺。
劉焉挺感激董扶,當初就是他力勸自己來益州,看來這個地方真好,只要張魯替自己守好北大門,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讓劉焉對張魯放心的還有一個原因,它記錄在《後漢書》裏。據說張衡的妻子、張魯的母親很懂得養生,年齡已經挺大了但面容仍然像少女一樣(有少容),而且很會裝神弄鬼(兼挾鬼道),經常到劉焉家做客,一來二去就跟劉焉好上了。在劉焉眼裏,可能已經把張魯當成半個兒子看待了,所以更放心。
劉焉自己有四個兒子,分別是劉範、劉誕、劉瑁和劉璋。劉焉來益州上任時,身邊只帶着老三劉瑁,其他三個兒子都留在了洛陽。這估計是朝廷有意安排的,把劉焉的三個兒子留在洛陽也算是人質吧。
董卓以及以後的李、郭汜等人對劉家當人質的這哥幾個還不錯,讓老大劉範當了左中郎将,老二劉誕當治書禦史,老四劉璋當奉車都尉,基本上都屬于中高級領導幹部。
有一天,朝廷接到了密報,說劉焉在益州圖謀不軌,證據是他在益州制作了只有天子才能乘坐的輿車,并且多達千餘輛,這可是大逆不道之罪。
打這個小報告的人是劉表。劉表告狀信上有一句很意思的話,說劉焉現在就像當年子夏在西河教書時被人當做聖人孔子一樣(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子夏是孔子的弟子,他在西河教書的時候,由于處處擺的是老師孔子的譜,所以被人誤以為是孔子。
劉表向朝廷強烈暗示:劉焉想造反。
朝廷此時已遷到長安,獻帝劉協接到劉表的報告不能不管,就派劉焉的四兒子劉璋回到益州規勸老爸認清形勢、迷途知返。在劉焉三個兒子裏之所以選劉璋回去,一來因為他年齡最小,二來劉璋這個人性格軟弱,溫和寬厚,不具有攻擊性,未來對朝廷的危害最小。
可是,劉璋卻沒有完成任務,反而被老爸留了下來(焉遂留璋不還)。
興平元年(194年),益州發生了一件離奇的事情,一場莫名其妙的“天火”将綿竹城燒得面目全非,大批百姓的房屋被燒成廢墟,同時把劉焉暗地裏制作的輿車也全部燒毀,劉焉不得已,把治所遷到綿竹鄰近的成都。
劉焉是個特別迷信的人,他覺得這把火來路不明,非常不吉利,心情很沉重。就在這時,傳來他留在長安的兩個兒子劉範和劉誕因為參與了一場未遂政變而被殺的消息,劉焉痛不欲生(既痛其子,又感祆災),背上發毒瘡(癰疽)而死。
劉焉作為劉氏宗親成員,自身有一定能力,始終都在為一己之利而忙活,在後世落下個野心家的名聲。
劉焉死後,趙韪等實力派力推劉璋繼任。劉璋上面還有一個哥哥叫劉瑁也在成都,但趙韪等人一致支持劉璋,有分析認為,這是緣于劉璋的性格,由于他為人溫和、軟弱,反而被實力派們相中。在此後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劉璋一直統治着益州。
【六、劉表在搞什麽】
安南将軍、荊州牧劉表告了劉焉的黑狀,他之所以敢這麽做,是因為他自認為自己在這方面沒有問題,對朝廷忠心耿耿,按時派人朝貢,從沒有非分之心。
事實也确是如此。雖然都姓劉,劉表比劉焉的野心小得多。劉表只想當他的荊州牧,既不想招惹誰,更不想篡位當天子,劉表不是野心家。
但是,他的這種立意自守、無四方之志的性格,在當下的亂世中,注定會以失敗告終。弱肉強食,适者生存,你不想吃掉別人,結果就是你被別人吃掉。
不過,現在還是劉表事業上最輝煌的時期,因為他待的荊州這個地方實在太好了,占盡了天時和地利。
岘山之役,勁敵孫堅意外喪命,讓劉表度過了最大的危機,袁術不久又撤離了魯陽,劉表身邊的威脅全部解除。
中原地區連年戰亂,形成多次難民潮,為了躲避戰亂,中原地區的人開始向邊境地區大規模遷移,主要的目的地,一個是遼東地區,一個是益州,還有就是荊州和江東。當然,也有一小部分逃到了更遠的交州,即今日的兩廣、越南一帶。
在這些地方中,逃到荊州的人最多,因為相對而言這裏與內地的交通最便利,而且劉表主政以後,荊州很少再起大規模的戰事,相對安寧。
荊州氣候适宜農業發展,物産豐富,經濟發達,也吸引大量逃難的人來此定居,其中包括大批的士人、官吏。
人力資源是重要的生産力因素,也是國力、軍力的重要體現,沒用幾年時間,劉表就發展成為“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裏,帶甲十餘萬”的割據勢力,在當時,其綜合實力僅次于袁紹集團。
如果把“治世能臣”的稱號給劉表,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劉表在地方治理方面确實有一套,他來荊州之前,這裏是“人情好擾,加以四方震駭,寇賊相扇,處處糜沸”,經過他的治理,這裏變成了“萬裏肅清”之地,俨然是東漢帝國最後一片樂土。
據《後漢書》說,劉表在荊州的治理很有成效,做到了“沃野千裏,士民殷富”,官民們都很高興而且佩服(大小鹹悅而服之)。這應該不完全是溢美之詞。
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之後,劉表大抓教育事業和文化事業,他興建學校,援引名師,博求儒術,培養人才。當時洛陽殘敗,太學被廢,劉表在襄陽設立的官學,成為當時全國最好的學府,進一步吸引了各方有識之士和希望求學的人紛紛從各地遷往荊州,使荊州代替洛陽成為全國的學術中心,荊州學校的規模和制度遠遠超出郡國學校的範疇,不妨說是洛陽太學的南遷。
文化教育事業在荊州的大繁榮,催生出一個新的學派:荊州學派。其代表人物有宋衷(一名宋忠)、司馬徽、颍容等,使得帝國的文脈不至于因戰亂而中斷,成為動亂年代文化事業上碩果僅存的一朵奇葩。
這個時期來荊州避難的北方士人,較為知名的有徐庶、石韬、孟建、崔州平、王粲、和洽、杜襲、趙俨、裴潛、韓暨、司馬芝、繁欽、傅巽、邯鄲淳、司馬徽等人,其中有些人前文已有提及。王粲在老師蔡邕被殺後懷着悲憤之情來到荊州,他跟劉表是同鄉,他的爺爺王暢是劉表的老師,因為這層關系,王粲到了荊州以後很受重視,成為為數不多的在劉表手下任職的北方士人。
王粲确實很有才,劉表曾經打算把女兒嫁給他,但是王粲長得不怎麽樣,身材不高,還有點兒醜。劉表這個人是大高個兒,儀表堂堂,他很看重外表,所以這件事後來沒有成。
劉表用王粲,僅是把他當成“文學之士”看待,不讓他插手政務和軍事,這讓王粲很失望。王粲是個對事業充滿激情的人,一心想建功立業,在劉表手下寫寫文章,當個筆杆子,顯然不是他全部的人生志向,為此他挺郁悶。王粲的代表作《登樓賦》就是在這種心境下寫的。
和洽字陽士,跟袁紹是老鄉,袁紹派人到家鄉迎接士人時,來了不少人,但和洽看不上袁紹,托故沒來,去了荊州。他看到劉表也徒有虛名,也不肯出來做事,幹脆跑到更南邊的武陵郡去了。曹操奪取荊州後,和洽進入曹操的幕府,和毛一起,長期負責曹操集團的組織人事工作。
邯鄲淳字子叔,是著名黨人度尚的學生,當代最有名氣的書法家之一,此時也在荊州避難,建安十三年後他歸順了曹操,在曹丕、曹植争奪繼承權的鬥争中因為“站錯了隊”,結局有點坎坷。杜襲字子緒,颍川郡定陵縣人;繁欽字休伯,趙俨字伯然,他們都是杜襲的老鄉。三家人到了荊州以後關系很好,有飯一塊吃、有錢一塊花(通財同計,合為一家)。他們發現劉表不是他們心目中的“撥亂之主”,于是都跑到長沙郡去了。裴潛字文行,河東郡聞喜縣人;韓暨字公至,南陽郡人;司馬芝字子華,河內郡溫縣人,應該是司馬懿、司馬朗的同族。這三個人都跟王粲很要好,也都對劉表不看好,躲起來不出仕。以上這幾個人,後來都歸附了曹操,大多成為曹魏重要的地方行政官員。
傅巽字公悌,北地郡泥陽縣(今陝西耀縣一帶)人,是漢末著名的傅氏家族成員,這個家族以後出了個名人叫傅玄。
至于徐庶、石韬、孟建、崔州平等人,都是諸葛亮的好朋友。這個時候的諸葛亮随同叔父諸葛玄南下豫章郡就任,其後的情況,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種是陳壽所記,說諸葛玄到豫章郡上任,但是朝廷此時已派朱皓為豫章郡太守,諸葛玄只好改投好朋友劉表。
另一種說法來自于《獻帝春秋》一書,說諸葛玄已經到南昌上任了,這時朝廷委任的豫章郡太守朱皓也到了,朱皓向時任揚州刺史的劉繇搬來援兵,攻擊諸葛玄,諸葛玄退出南昌,到了西城,後來西城鬧民變,将諸葛玄殺了,首級被送往劉繇處。
不管怎麽說,諸葛玄的豫州之行以失敗而告終,諸葛亮及弟弟諸葛均,還有兩個姐姐輾轉來到了荊州,這時候他大概十六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