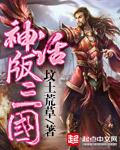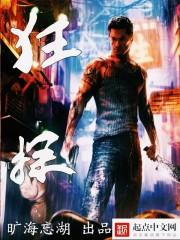第19章 (1)
〔為了保衛勝利果實,曹操打跑了袁術,打退了公孫瓒和陶謙,瓦解了故人的聯合軍事行動,顯示出高超的軍事指揮才能。但是,有幾股暗流已經在他身邊湧動,張邈、呂布、陳宮這些各懷心事的人,能做出什麽事來?〕
【一、敵人的聯合軍事行動】
初平四年(193年)年初,也就是馬日和趙歧出使關東前後,天下總體格局是南北對峙,以袁紹、袁術為核心,形成了兩大陣營。
除去盤踞在長安的涼州集團和偏安于益州的劉焉集團外,從北至南,劉虞、公孫瓒、袁紹、曹操、陶謙、袁術、劉表等實力派都牽涉到這兩個集團的對抗中,中間還穿插有黑山軍、河內郡的張楊、南匈奴于扶羅等勢力。
這兩大陣營大致劃分如下:袁紹陣營有袁紹、曹操、劉表、劉虞;袁術陣營有袁術、公孫瓒、陶謙,以及張楊、黑山軍、于扶羅等。至于孫策和劉備,這時候勢力還十分有限,分別附屬在公孫瓒和袁術之下。逃出長安的呂布,後來也加入其中,曾短暫依附于袁紹,更多情況下算是袁術陣營的人。
這種格局很有意思,用一句話總結就是“遠交近攻”,眼前的都是敵人,敵人的身後就是朋友,最終形成了夾擊和反夾擊的局面。以後,這種局面還會不斷變化,在打敗對方陣營裏的人後,同一陣營又開始厮殺。
現在,袁紹眼中的最大敵人是公孫瓒,而公孫瓒與袁術結盟,讓袁紹很惱火。待在南陽郡的袁術,在初平四年(193年)初突然向北運動,目标直指曹操的勢力範圍兖州。
關于袁術離開南陽郡另謀發展的原因,一種認為是袁術配合公孫瓒、陶謙的軍事行動,另一種認為是劉表給袁術施加了壓力。劉表不斷向北出擊,攻擊袁術的糧道,袁術在南陽郡發展困難。
這年春天,袁術親自帶兵進入陳留郡境內,陳留郡太守是張邈。說起來,僅在三四年前,袁紹、袁術、曹操、張邈都還是好朋友,在洛陽時常小聚。現在,卻要刀兵相見了。
在曹操擔任兖州牧之後,張邈的心态有了一些微妙變化,但支持曹操的立場總體上仍未改變。面對袁術這個不請自來的客人,他立即通報曹操,請求增援。
袁術開始行動後,黑山軍和于扶羅立即響應,在西北方的側翼給袁術助威。袁術的前鋒由劉詳率領,進駐到匡亭。
匡亭的位置,在陳留郡的平丘縣,這裏已深入陳留郡內一百多裏,再往前就是曹操的後方基地東郡了。曹操不敢大意,親自引兵迎戰。
荀等人分析,劉詳北上只是袁術的試探性進攻,可以先圍住匡亭不打,看袁術下一步的反應。曹操采納,将匡亭圍住,袁術果然率軍北上增援。
曹操在平丘、東昏一帶擺下陣式,就等袁軍開到。曹軍以逸待勞,袁軍北上的只是一部,實力稍遜一籌,結果大敗,袁術退到封丘。封丘離關東聯軍會盟的地方酸棗不遠,也在陳留郡境內,曹操揮軍追趕,将封丘圍住。
這是一個機會,因為袁軍主力部隊還未趕到,袁術又是孤軍冒進,如果曹軍行動迅速一點的話,有可能将封丘城圍死,袁術就走不了了。但那将是一件很棘手的事,無論殺掉袁術還是将他活捉,都不符合曹操目前的利益。曹操決定圍城的時候留下一個缺口(未合)。
袁術倒也識趣,知道這是老朋友誠心放自己一馬,于是順着缺口突圍逃走。他逃向的地方是襄邑,仍然在陳留郡的地盤上,曹操不能不管,又追到襄邑。
袁術未等曹軍開到,主動撤到襄邑附近的太壽,這時袁術的增援部隊也趕到了。一敗再敗,袁術顏面盡失,他想這回不能再跑了,必須打一仗贏回面子。但是,這只是他的願望而已。
圍攻太壽雖然不像前幾次那麽容易,但曹軍仍然取得了勝利,他們采取的辦法是掘開附近的渠道,用水灌城。袁術不敵,放棄太壽,逃到寧陵。襄邑、寧陵相距不遠,曹操曾在這一帶募兵,這裏是曹操事業的起點。曹操帶兵再次追擊,袁術這回幹脆向九江郡逃去。曹操五戰五勝,把袁術徹底從陳留郡趕了出去。雄心勃勃的袁術深受打擊,沒想到自己一向頗為自負,親自領兵打仗水平居然這麽差,如喪家之犬般一路逃命。從此之後,袁術心中的雄圖大志銳減,不再奢望吞并中原、虎步天下,能偏安于淮南一隅他已經相當知足了。
由匡亭到寧陵,曹操現身說法地給老朋友上了一堂軍事課,把袁術打服了。
其實,袁術敢于輕軍冒進,在于有公孫瓒和陶謙的配合,他們原計劃統一行動,從各個方向同時向曹操施壓。袁術一直逃到九江郡都還納悶:另外那兩個哥們幹嘛去了?
其實,公孫瓒和陶謙并沒有失約。公孫瓒一邊與與袁紹艱苦對抗,一面派他任命的兖州刺史單經和平原國相劉備配合袁術的行動。單經率部進駐平原國,劉備率關羽、張飛、趙雲等人進駐高唐縣,這裏在平原國境內,正好位于東郡的北部,其中高唐縣距東郡的東武陽、東阿等地已經不遠了。
據陳壽記載,陶謙也參加了這次聯合軍事行動,他進駐的地方是發幹。但如果對照着地圖看一下,這似乎又是不可能的。發幹縣屬東郡,距曹操的後方基地東武陽不過四五十裏路,陶謙能否将部隊布防到這麽縱深的地方另當別論,身為徐州刺史的陶謙能否離開徐州,越過多個敵占區,到千裏之外的發幹縣來,就首先是個疑問。
也許發幹縣确實有徐州的小股部隊,但不是陶謙本人率領。
陶謙如果配合袁術、公孫瓒聯合行動,可行的方案是攻擊徐州的北鄰,即兖州刺史部的泰山郡、任城國、東平國、山陽郡等地,給曹操制造麻煩。從後面的事态發展看,陶謙也确實這麽做了。
上述聯合軍事行動将使曹操北面、南面和東南面同時受敵,兖州将十分危險。但曹操輕易化解了這場危機,原因是:時間差。
聯合軍事行動之所以稱為聯合,必須在時間、地點上達到默契。北路的單經和劉備到達預定地點後,袁術的隊伍還在路上,這樣曹操在袁紹的支持下,很從容地先解決了北面之敵,他們主動出擊,将劉備和單經擊退。單經撤走,劉備退保平原國,公孫瓒方面首先退出聯合作戰。
曹操一路追擊袁術的時候,陶謙本可以幫忙,但一來路途有點遠,二來陶謙想保存實力,他抱着先看看再說的想法,想等曹操和袁術打上一陣再上前幫忙。讓陶謙吃驚的是,呼聲一向很高的袁術,軍事才能竟如此之差,被曹操一路打來,沒有任何招架之功,只有逃命的份兒。見此情景,陶謙放棄了增援行動。
這樣,三方聯合作戰計劃被曹操成功瓦解,打退了劉備、單經,打跑了袁術,剩下一個陶謙,那就好辦多了。
【二、轟動一時的血案】
初平四年(193年)夏天,曹操率軍到達定陶,這裏位于兖州刺史部濟陰郡的中部,是濟陰郡的治所。
在打退袁術的進攻之後,曹操順勢擴展了“曹統區”的範圍。現在整個兖州刺史部的形勢是:東郡、濟陰郡、山陽郡、任城國為曹操所直接控制,陳留郡太守張邈、泰山郡太守應劭作為曹操的屬下聽從他的調遣,濟北國、東平國處于和公孫瓒拉鋸狀态,雙方互有攻防。
曹操擔任兖州牧以後,把東郡太守一職交由夏侯來代理,駐守在黃河岸邊的戰略要地濮陽。曹操想讓隊伍集中起來休整一段時間,思考一下如何對付陶謙。相對于遠道而來的袁術,以及中間隔着袁紹的公孫瓒來說,對付眼前的陶謙更是當務之急。
而且,在逐漸鞏固了兖州後,下一步朝哪個方向發展也需要盡快決定下來。北邊是袁紹,往東以及東北方向目前是公孫瓒的地盤,不可能有發展的空間;往西是殘破不堪的司隸校尉部,人口大量外逃,稍大一點的城市都成了廢墟,又處在各種勢力的交彙處,別說不好占,就是占住了也沒法待;只有南邊以及東南方向的徐州适合于發展。在這個方向的敵人是陶謙。
陶謙是一個狡猾的人,在涼州一帶打過仗,能帶兵,有些謀略,手下也有一些人,經營徐州有幾年了,這樣的敵人不容易對付。雙方雖然還沒有正面交過手,但早已經在心中把對方當成了假想敵。
曹操盯着牆上的地圖,目光在兖州與徐州交錯的郡縣間游走。他的目光停在了徐州刺史部最北面的琅邪國附近,這裏是夫人卞氏的老家,它東鄰大海,遠離中原,是個避亂的好地方。突然,曹操想起了什麽,心裏一驚。
曹操突然想到,他的父親曹嵩等人此時正在那裏。
曹操在己吾起兵之後,除曹操的弟弟曹德外,曹氏以及夏侯氏兄弟們紛紛離開家鄉追随曹操去了,曹家在谯縣變得不安全。曹嵩經過考慮,決定找個地方避難,大約在一兩年前,在谯縣的曹家人都來到了琅邪國。
當時,從中原地區到這裏避難的人還不少。即便是現在,原屬琅邪國的山東省日照一帶仍然是河南、河北、安徽以及陝西人到海邊買房居住的首選之地。
曹嵩一行到這裏不是為了欣賞海景,而是來避難的。之所以選擇這裏,與卞氏的老家在這兒有一定關系,卞氏老家在開陽縣,是琅邪國的治所,曹家人來琅邪國應該住在開陽縣一帶。
與一般逃難的人家不同,曹家人非常富有,盡管刻意保持了低調,但從他們的吃穿住行以及随行帶來的衆多仆人等方面也能看得出來。
但此時琅邪國是陶謙的地盤,在開戰之前必須把家裏人從那兒接出來。琅邪國緊鄰兖州刺史部的泰山郡,曹操派人到琅邪國通知父親準備離開,同時命令泰山郡太守應劭派兵接應,把父親一行接到鄄城來。
但是,有人卻搶先了一步,把曹嵩等數十口人殺得一個不剩,制造了一起轟動一時的血案。關于這個案子,歷來有不同的說法,但都與陶謙有關,說是他派的人或者他手下人幹的。具體情節大致有以下不同版本:
據郭頒的《世語》一書說,陶謙派去的人撲了個空,曹嵩一行已離開了琅邪國。他們于是追趕,在泰山郡的華縣一帶追上。曹家人正在這裏等應劭來接應,還以為這是應劭的人,沒有防備,結果全部被殺。
《後漢書·應劭傳》與這個說法差不多,說曹嵩攜曹德等一行進入泰山郡,應劭派人已經接上了,但此時遭遇陶謙的突然襲擊,全家人被殺。
對此,同書中的《陶謙傳》進行了補充,說不是陶謙派人幹的,而是陶謙手下一個将領(未記載姓名),此時駐紮在距事發地華縣不遠的東海郡陰平,其手下士兵聽說曹家人很有錢,就在路上設伏,在華縣、費縣一帶把曹嵩等人殺了。
韋曜的《吳書》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陶謙聽說曹嵩想兒子,就派部将張帶領二百人護送。曹家人很有錢,光值錢的東西就裝了一百多車,張等人見財起了異心,在華縣、費縣一帶将曹嵩等人殺了,搶光了東西,跑到淮南去了。
上述各種記載中,《世語》寫得最細。說陶謙的人先把曹德殺了,曹嵩聽到外面有動靜,知道不妙就往後院跑,後院牆上有一道縫,他想從這裏鑽出去。跟他一塊兒跑的還有一個他最喜歡的妾,曹嵩想讓她先鑽,無奈這個妾長得太胖,鑽不過去,曹嵩沒辦法,只好跑到廁所裏躲起來,但被人發現,一行人全部被殺。
考察一下這些說法,《吳書》最不可靠,這部書一貫吹捧孫吳,對于曹操能貶則貶。按照他的說法,陶謙是個大好人,好心好意辦了個好事,曹操不僅不領情,事後還歸罪于他,實在冤枉。
《世語》的說法有點像傳奇故事,盡管細節很生動,卻不可靠,陶謙如果想殺曹嵩等人,恐怕早就動手了,琅邪國在他的地盤上,非等曹操來接人他才動手嗎?況且,把人殺得一個不剩不符合陶謙的利益,如果他真想跟曹操翻臉,把人控制起來作為人質也許更明智。
當這些不同的材料擺在司馬光面前時,經過慎重分析,他采用了《後漢書·陶謙傳》中的說法。《資治通鑒》是這樣記述這件事的:“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其子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迎之。嵩辎重百餘輛,陶謙別将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掩襲嵩于華、費間,殺之,并少子德。”應該說,這個說法比較合理。
不管怎樣,曹嵩、曹德等數十口全部被殺死在泰山郡華縣附近,沒有留下一個活口(否則也不至于有那麽多版本了),這已成為事實。與此有關聯的,一個是徐州刺史陶謙,他是重大的犯罪嫌疑人;另一個是泰山郡太守應劭,這個著名的學者、《風俗通義》的作者,害怕曹操連他一塊兒追究,幹脆棄官而逃,到邺縣找袁紹去了。
消息傳到兖州,還在定陶休整的曹操幾乎不敢相信,他簡直瘋狂了。
雖然父親對自己選擇的道路一向不看好,但作為自己事業上最大的支持者,父親一直對自己都盡可能地給予幫助。自己起兵以來,父親整天擔驚受怕,不敢待在谯縣,遠避琅邪國,如今又命喪他鄉,說起來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
由于曹家沒有一個人能夠活着回來,應劭又不知去向,對于整個事件的經過,曹操不是很清楚。但曹操不用太多思考,就得出結論:這件事只有一個人能做,也只有一個人敢做,那就是陶謙。
陶謙,我要讓你血債血償!
曹操迅速調整了計劃,命令部隊停止休整,全部進入戰備狀态。他要親自領兵殺往徐州,找陶謙報仇雪恨!
【三、展開複仇行動】
曹操的複仇行動還未及展開,陶謙那邊反倒先動起了手。
陶謙率先向兖州發起進攻,時間大約是初平四年(193年)的夏天。在此之前,陶謙這邊發生了幾件重要的事,需要交待一下。
一件事是,陶謙此時已被長安的“三人小組”正式任命為徐州牧,此前他一直擔任的職務是徐州刺史。
大約在曹操派王比出使長安的前後,陶謙也派人到長安進貢,他派的人叫趙昱,是當地的名士。當時陶謙手下有幾個名人,除了趙昱以外,還有王朗、張昭等。王朗字景興,是前太尉楊賜的學生,算起來跟靈帝劉宏和前大将軍何進還是師兄弟,他跟趙昱共同勸陶謙通使長安,陶謙接受了建議,派趙昱到長安。
與曹操的情況不一樣,陶謙的特使在長安受到歡迎,這是因為陶謙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刺史,而曹操的兖州牧則查無出處。最後,朝廷拜陶謙為安東将軍,由徐州刺史升格為徐州牧。同時任命趙昱為廣陵郡太守,任命王朗為會稽郡太守。王朗就是這時候離開陶謙到江南上任的。另一件事是陶謙與黃巾餘部闕宣聯合,勢力大增。
根據《後漢書·五行志》的記載,這一年夏天中原及華北地區出現了罕見的自然現象:正值炎夏,卻刮起了寒風,像冬天一樣。
這種神奇的自然現象鼓勵了想造反或者正在造反的人,在他們看來這是天亡劉漢的又一明證。徐州刺史部下邳國一帶有個叫闕宣的人領頭造反,響應的人很多,當他看到上天也出來懲戒當權者時,于是不再客氣,自稱天子,與長安的獻帝分庭抗禮。當時敢造反不算什麽本事,但敢于自稱天子那絕對是勇氣可嘉。
剛剛被朝廷任命為徐州牧的陶謙不僅不率兵讨伐,反而跟闕宣聯合起來,勢力進一步增強。陶謙一方面派人跑到長安向天子宣誓效忠,一方面與自稱天子的人稱兄道弟,這位仁兄的務實主義作風實在可以。
但是後世也有很多人對此表示懷疑,比如司馬光,他不相信身為徐州牧的陶謙真的會和造反分子公然攪到一塊兒,因為這種行為跟直接造反沒有什麽兩樣。持這種看法的還有黎東方先生,他認為不僅曹嵩被殺與陶謙無關,而且和闕宣聯合這樣的事根本就是子虛烏有。這代表了一種很流行的看法,在許多人眼裏陶謙是個謙謙君子,而非小人。
但是,如果結合陶謙早年在西北前線時就流露出來的獨特個性來看,說他現在已經成長為一個溫和的長者似乎有點不可能,陶謙到徐州後親信小人,打壓正直之士,玩弄手腕,大搞兩面派,一樁樁事件都有記錄,關鍵時刻與闕宣這樣的實力派結合也沒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
得到徐州牧的頭銜,聯合闕宣,如果把這兩件事合在一起看,此時的陶謙既提高了名分,又增強了實力,正是事業的上升期。他未必會把曹操放在眼裏,如果陶謙早就有挑戰曹操的想法,有意策劃曹嵩被殺事件,也有這樣的可能。
有意策劃也罷,被誤會也罷,眼下與曹操的一戰已是難以避免。陶謙與闕宣組成聯軍,率先向兖州發起了進攻。
他們進攻的方向不是曹操正面的陳留郡、濟陰郡,而是右翼的泰山郡、任城國等地。泰山郡太守應劭已棄官逃往袁紹那裏,曹軍在這裏的防守相對薄弱,任城國以及泰山郡的很多地方被陶謙占領。
面對敵人先發制人的進攻,曹操決定兵分三路:一路由夏侯統領留守兖州,重點是鄄城、濮陽、定陶、東武陽等戰略要地,荀、程昱留下協助他;一路由曹仁率領,由東郡的北部進入東平國、任城國,進而到泰山郡進攻那裏的徐州軍;一路由曹操親自率領,由濟陰郡南下,進入已為陶謙所控制的豫州刺史部沛國的北部,進而攻擊徐州刺史部的彭城國(治所在今江蘇徐州一帶)、下邳國(治所在今江蘇邳縣一帶)等地,直搗陶謙的大本營郯縣(今江蘇郯城)。
總體來說,就是以偏師對抗陶謙的主力,而将主力向敵人之側冀發起進攻,對于已失去先發優勢的曹軍來說,這不失為一個正确的選擇。
這是一場無法預料結局的戰争,曹操離開鄄城前告訴夫人卞氏說,如果自己回不來了,就讓卞氏領孩子們前往陳留郡投奔張邈(我若不還,往依孟卓)。
戰事從這年秋天拉開,曹軍一路順風,勢如破竹。曹操親自率領的這路一口氣拿下兖州境內十幾座被陶謙占領的城池,直逼徐州境內的戰略要地彭城,逼着陶謙從右路撤軍,親自率軍來戰,雙方在彭城進行了激戰。
古代九州裏就有徐州,徐州也被稱為彭城。彭城是座古城,城池四周雖然被大小不等的丘陵、高地所環繞,但交通卻十分發達。東漢有一條起自洛陽的東方大道,其基本走向前半段約沿着現在的隴海鐵路,後半段約沿着現在的京滬鐵路,彭城就是這條大道上的交通樞紐。
彭城周邊還有泗水、水在此交彙,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大兵團交戰的理想戰場。四百年前,劉邦和項羽曾在此有一場大戰,結果劉邦大敗,項羽險些把劉邦生擒。曹操與陶謙的彭城之戰沒有楚漢戰争時打得那麽慘烈,戰事呈現出一邊倒的趨勢。曹軍大勝,陶謙所部有近萬人被殺,陶謙撤軍,向東退到郯縣。
對于這場大戰,《三國志·武帝紀》裏只有十六個字:“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同書的《陶謙傳》與此大體相同,只是多了十個字:“死者萬數,泗水為之不流。”後面這一句翻譯過來,大意是:被殺死的接近上萬人,屍體阻塞河道,使泗水都要斷流了。
早期的正史關于這場戰争的記載就只有這二十多個字。可是後來,不知道哪位仁兄把“萬數”有意或者無意地改為了“數萬”,事情就有點不一樣了。到了司馬光的筆下,這件事已經演變成了下面的模樣:
“秋,曹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保郯。初,京、洛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于泗水,水為之不流……雞犬亦盡,墟邑無複行人。”
一次活埋了幾十萬人,簡直是駭人聽聞!
如果這件事真是曹操幹的,我們一定把漢魏惡人榜第一名的帽子從董卓頭上拽下來給曹操戴上,告他一個反人類罪!
可惜,這不是真相。
由于史料缺乏,還不太清楚這件事是如何從陳壽版演變到司馬光版的。在較早一些的桓帝時期,彭城國全部人口不足五十萬,當時全國人口是五千多萬。經過黃巾起義、自然災害、戰争屠殺,到再晚一些時候,全國人口已銳減到一千多萬,此時彭城國的人口想必也已大幅下降。
曹操一邊打仗,一邊還得派人四處出擊,把彭城國全國的老百姓都抓到一塊兒,然後全部活埋?真的匪夷所思!
曹操遠途奔襲,此時用在彭城的士兵人數充其量也就二三萬。攻破彭城後,曹操下令大家先不要打掃戰場,也不忙追擊敵人,而是幹一件更重要的事:每個人分配十多個敵占區抓來的士兵和老百姓,把他們領到泗水河谷裏活埋了,幹不完活不給吃飯!
即使被抓來的人已有人提前幫忙捆好、綁牢,即使将要被活埋的這些人願意配合,完成這項任務所涉及的工程量也是巨大的。
坑殺男女數十萬口,規模堪比南京大屠殺,你能想象得出來嗎?但由于司馬光的權威,很少有人動腦筋細想,這樣的說法在後世逐漸流行。
不說這樁公案了,且說陶謙退保郯縣。曹操繼續追擊,在郯縣以東的武原與陶謙主力部隊又進行了一場惡戰,再次取得勝利,兵臨郯縣城下。從鄄城出發到郯縣,直線距離已有上千裏,曹軍遠道而來,雖然節節勝利,但自身消耗也很大,士卒減員,戰鬥力下降。對方已退無可退,拼命死守,曹軍攻城不克。
郯縣難攻的原因還有一個:城裏來了生力軍。
陶謙開始還信心滿懷,原來想至少也能跟曹操拼一拼吧,但沒想到自己的部隊在曹軍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擊。眼看郯縣危急,在曹軍圍上來之前,他趕緊派人向盟軍公孫瓒求救。
袁術被打跑後,陶謙如果再被消滅,公孫瓒對袁紹、曹操南北夾擊的戰略部署就要落空,所以對陶謙的求救他不能不管。公孫瓒命令距離徐州最近的田楷、劉備馳援郯縣。
田楷和劉備分別是公孫瓒任命的青州刺史和平原國相。劉備帶着關羽、張飛、趙雲等人率先到達,這時候他兵力還很有限,只有一千多人,再加上一些烏桓騎兵,以及數千難民,那陣勢不像是來幫忙打架的,倒像是來吃大戶的。
但這些都是生力軍。兖州軍和徐州軍已經打了幾個月,雙方都很疲憊了。郯縣因為有劉備的加盟,防守力量明顯增強,所以盡管曹洪、夏侯淵等人親自督戰,試圖一舉拿下郯縣,但猛攻了幾次,都沒能攻下。
長期圍城是不現實的,這是敵占區,敵人的後援會越來越多,而自己隊伍将面臨後勤補給等方面的難題。曹操決定放棄攻城,回師兖州。
郯縣攻防戰想必給曹操留下了較深的印象,從情報人員的嘴裏他也許聽到了劉備這個名字。在此之前,他對這個名字可能還比較陌生,但今後他的生命将與這個人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相知、相交也相鬥,一直到死。
在泰山郡方向,曹仁進展得也很順利,打敗了陶謙在那裏的部隊,收複了開縣、華縣、費縣等地,将“曹統區”的範圍擴大到整個任城國和泰山郡。
過了年,在長安的獻帝劉協下诏改年號為興平。興平元年(194年)春天,曹操結束了為期近半年的第一次遠征徐州之戰回師鄄城,陳留郡太守張邈親自到州界迎接他們凱旋。想到半年前出征時生死未蔔、曹操以家室相托付的情景,兩位老戰友不禁“垂泣相對”。
【四、赤兔之奔】
在董卓被殺、李等人控制朝廷後不久,劉表也派使者前往長安,向獻帝表示忠心。像對待陶謙一樣,長安的“三人小組”對于曾經被朝廷正式任命過的劉表也表示歡迎,劉表不僅升了一格,由刺史變為州牧,而且被同時加上了鎮南将軍的頭銜,封為成武侯。
沒有跟關東聯軍攪和到一塊,并且與袁術刀兵相見的劉表,被李等人寄予了厚望。
劉表的使者來回都應該走武關道,這條沿着漢水南下的道路,在當年來說比今天還顯得重要和熱鬧。劉表的使者在這條路上匆忙行走,也許會遇着一支數百人的馬隊,率領這支隊伍的是在當時已天下聞名的飛将呂布。
呂布從長安城殺出來,雖然狼狽不堪,但所幸把他最親近的子弟兵一塊兒帶了出來,綜合《英雄記》等書的記載,跟随呂布殺出重圍的數百人裏,有他手下的得力幹将張遼、高順、成廉、魏續、魏越、侯成、宋憲等人。
這裏對于呂布手下的這幾個人也順便介紹一下。張遼前面已經說過了,是資歷堪與呂布相比的并州軍将領,董卓死後依附于呂布。高順是呂布手下的猛将,善長指揮騎兵作戰,歷來對他評價不錯,因為他不僅能打,而且人品也好,不争功,不搞內鬥,即使人家鬥到他的頭上,他也不記仇。呂布看他是難得的人才,也用他,但對他卻不是很好,高順并不在意,至死都忠心耿耿地跟着呂布。
成廉後面這幾個人的詳細情況都不太清楚,反正都很能打,恐怕要想讓呂布看得上,這是首要條件。但他們似乎不怎麽團結,看來武人也相輕。魏續、魏越或許是兄弟,他們跟呂布好像有親戚關系,呂布對他們是無條件地信任,每當他們與高順鬧別扭,呂布總是袒護他們。
呂布領着這哥幾個還有幾百名騎兵順着武關道到了南陽郡的治所宛縣,見到了袁術。其後的情形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種說法是袁術隆重地接納了呂布,但呂布卻不好好待着,他自恃親手殺了董卓,是袁家的恩人,所以一安頓下來就要這要那。要知道袁術此時被劉表逼迫得日子也不好過,對呂布自然不能有求必應。袁術稍有怠慢,呂布就放縱手下人去搶,結果二人的關系鬧得很僵,呂布在南陽郡待不下去,就領着哥幾個還有幾百名騎兵走了。
另一種說法是,袁術壓根沒有接納他。袁術知道呂布這個人,在丁原手下殺了丁原投董卓,在董卓手下又殺了董卓,現在來投自己,莫非自己就是下一個丁原和董卓?袁術這個人一向很迷信,也經常神經兮兮的,有這些想法也難怪。袁術不接納,呂布無奈,只好領着人另找出路。
前一種說法來自《後漢書》,後一種說法來自《三國志》。但不管說法怎麽不同,結果都差不多:呂布的南陽郡之行很失敗,高興而來,掃興而走。
其實,即使他不走,在南陽郡也待不長,因為沒有多久,袁術自己也集齊大軍前往豫州、兖州方向打曹操去了。
離開袁術,呂布下一個去依靠的人是張楊。
呂布和張楊是并州老鄉,過去都在丁原手下做事,董卓把持洛陽朝政以後,張楊沒有像呂布和張遼那樣投靠董卓,而是率領自己招募來的幾千人在黃河北岸的河東郡、河內郡一帶發展。這一地區也是黑山軍、白波軍以及南匈奴的游擊區。張楊跟他們結成了一個松散同盟,在袁紹和公孫瓒之間傾向于公孫瓒。
呂布到河東郡見到了老同事張楊,但形勢仍然不容樂觀,長安朝廷的“三人小組”對呂布恨之入骨,一直在通緝他。張楊的防區離長安最近,早已接到懸賞捉拿呂布的通告,他手下看到長安開出的賞金很高,就想把呂布殺了換賞錢。
呂布聽到風聲,有點害怕,主動跟張楊說:“看在咱們是同鄉的情誼上,我給你出個主意,殺了我未必劃算,不如把我活着押到長安,可以得到更高的獎賞。”
呂布這話像是老朋友之間在開玩笑,那時他哪有心思開玩笑的,不過是想試探張楊的态度。但張楊卻把呂布的話真當成玩笑了,所以也回了句玩笑話:“我認為你說得很對。”劉震雲在《故鄉、面和花朵》裏開篇第一句話是:“為什麽你的眼裏常含滿淚水,因為玩笑開得太過分。”現在呂布的眼裏就該有淚水了,那是因為張楊的玩笑開得太過分。
呂布決定再跑,河東郡之行宣告失敗。當然,還有一個說法,說張楊其實一直在保護呂布,在張楊的調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