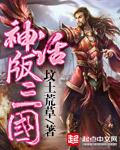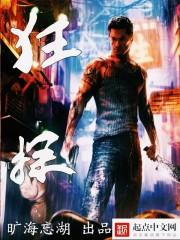第18章 (2)
歧相約,不久之後将迎獻帝回洛陽(與歧期會洛陽,奉迎車駕)。這個約定對袁紹來說也就是說說而已,他現在滿腦子都是公孫瓒,送走趙歧,袁紹回去就開始謀劃新的軍事計劃去了。
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意外情況,着實讓袁紹受驚不小。
袁紹送走趙歧返回邺縣,路過漳水之上的渡口薄落津時,在此大會賓客,曹操也有可能在其中。正吃喝熱鬧的時候,突然接到情報說他的後方基地魏郡有人造反,叛軍與黑山軍的于毒部取得聯系,人數多達數萬人,已經把袁紹的大本營邺縣占領,郡守被殺。
在座的很多人家都在邺縣,聽說之後頓覺五雷轟頂,“皆憂怖失色”,有的人當場就哭了起來。面對突然而來的變故,袁紹再次表現出從容不迫的氣概,他當時正在玩投壺游戲,就是把箭投向遠處的一個壺中,看誰投得準,輸的人罰喝酒。聽到消息,袁紹仍然言談自若,催促監壺的人繼續玩(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後來,幸虧黑山軍裏有一個叫陶升的人投降袁紹,把袁紹以及衆人的家屬送到斥丘,并幫助袁紹重新收複了邺縣。後來袁紹任命陶升為建義中郎将。此事發生于初平四年(193年)三月,記錄在《獻帝春秋》一書中。
唯一認真思考了趙歧建議的人就是曹操了。朝廷特使一行帶來了長安的最新消息,也表達了奉迎天子回洛陽的渴望。曹操回到鄄城,就與荀、程昱、毛(應該還有戲志才)等人商議此事,荀贊成派人出使長安,向朝廷進貢。
毛的看法更進一步,他提出了一個更大膽的計劃。毛說:“現在天下分崩,天子流亡,國家沒有儲備,百姓不能安居,這種狀況難以持久。袁紹、劉表等人,雖然人多勢衆,但都缺乏遠大志向,不能樹基建本。當今之計,應該奉天子以令不臣,發展農業,積蓄軍資,這樣以來,霸業可成。”曹操認為他分析得很有道理(敬納其言)。
毛字孝先,是兖州本地陳留郡平丘縣人,當過縣吏,為人清廉公正。中原地區陷入動蕩後,他本想到荊州投奔劉表,聽說劉表政令不明,能力有限,于是轉道去了魯陽。曹操擔任兖州牧以後,征他為州政府的治中從事,負責州裏的人事工作。曹操發現毛深有謀略,清正無私,就改任他為奮武将軍府的功曹,從事人才選拔工作。以後曹操的地位不斷提升,毛一直是人事系統的領導。
曹操一邊忙着鞏固兖州,一邊考慮派人到長安走一趟,至于派誰去,曹操一時沒有想好。這個人首先要有膽識和能力,因為此去長安路途險阻,要穿越各種勢力以及黑山軍的防地,必須随機應變,保證順利到達長安并安全返回;其次要熟悉那邊的情況,最好認識長安那邊的人;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忠誠可靠,因為除了代表他以兖州牧的身份向朝廷進貢以外,還要找機會替他拜會幾位在長安的老朋友。
想來想去,曹操覺得只有一個人具備上面的條件,這個人就是王比。
王比的個人情況不詳,似乎很早就跟着曹操了,類似于家臣的角色,曹操多次委他以特別的任務,體現出對他不同一般的信任。如果真是曹操的家臣,他有可能在曹嵩時代便在洛陽的曹府呆過,熟悉此時仍在長安的丁宮、丁沖、鐘繇等曹操的朋友。
初平三年(192年)冬天,王比受命出發,但一開始就極不順利。
他們一行剛到河內郡,就被河內郡太守張楊扣留。曹操雖然沒有跟張楊發生過沖突,但張楊跟袁紹曾經有過降而複叛的經歷,曹操是袁紹的人,張楊自然不把曹操當成好人,他不想讓王比過境。
這時候張楊身邊出來一個人,勸他說:“曹操雖然跟袁紹是同盟,但二人情況不同,不可能永遠相親近(勢不久群)。曹操現在雖然弱小,但他的确是個英雄,将軍您應當結交他。現在剛好是個機會,應該幫他完成通使長安的事,并且上書表薦他。如果事情成了,曹操一定感激将軍您。”
張楊想了想,覺得說得也是,于是同意王比過境。
這個幫曹操說話的人不是張楊的手下,而是張楊的客人,他的名字叫董昭。
董昭字公仁,老家是兖州刺史部的濟陰郡,就是曹操現在的大本營鄄城所在的郡。他被舉過孝廉,當過縣令,後來在袁紹手下當參謀(參軍事)。袁紹屬下的钜鹿郡太守李邵等人想叛變投靠公孫瓒,袁紹抽不出兵來征讨,董昭自告奮勇願只身前往把事情擺平。袁紹大喜,還以為他有什麽好主意,問他具體如何辦,董昭實話實說:還沒有想好,只能随機應變(計當臨時,未可得言)。袁紹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只好讓董昭去試試。
董昭到钜鹿郡經過明查暗訪,發現李邵反叛這件事是由郡裏的大戶孫伉等人在背後策劃的。
董昭當即立斷,将幕後分子一網打盡。由于來不及向袁紹請示,董昭僞造了袁紹的公文,說抓到敵人的間諜安平、張吉,據他們交待,孫伉等人暗中通敵,以為內應,現在發布檄文,将其逮捕,軍法處置。
董昭用這一手段迅速平定了钜鹿郡,為袁紹立下大功。後來冀州治下的魏郡發生動亂,袁紹又派董昭兼任魏郡太守。董昭到境後軟硬兼施,又平定魏郡。
董昭一再立下大功,但在袁紹那裏卻待不住。起因是董昭有個弟弟叫董訪,在張邈手下任職。袁紹跟張邈因為一些事已經鬧翻,這一對革命戰友發展到勢不兩立的程度,袁紹欲除掉張邈而後快。這時,有人在袁紹面前進讒言,說董昭不可靠,是張邈派來的卧底,董昭聽到風聲,不敢再待。他想幹脆到長安去在朝廷裏謀個職,但也是在路過張楊防區的時候被扣下。
董昭确實不錯,自己的事沒有弄明白呢,還替曹操說了話。其實董昭也是為自己鋪路,他是真的看好曹操。正是因為有這件事,日後曹操見到他時,将其視為自己人,引以為心腹智囊。
王比總算離開了河內郡,輾轉到了長安。“三人小組”對袁紹、曹操都不太感冒,想把王比扣下。他們認為曹操是袁紹陣營的人,袁紹對天子的态度一向暧昧,一會兒另立天子,一會兒散布謠言說天子不是靈帝親生的。
這時,曹操昔日的好朋友、現任黃門侍郎鐘繇出來說話:“現在群雄并起,大家都以天子的名義行獨斷專行之事,只有曹兖州心系皇室,如果我們拒絕他的誠意,那些也有同樣想法的人必會感到失望。”李等人想想也有道理,于是放王比回去,并給了一些回禮。
鐘繇不僅跟曹操相熟,還跟荀是同鄉兼同事。根據謝承的《後漢書》記載,南陽人陰修當穎川郡太守時,把穎川郡的才俊都延攬到自己手下,其中鐘繇擔任人事處長(功曹),荀擔任辦公室主任(主簿),荀攸擔任司法處長(賊曹掾),郭圖擔任駐京辦主任(計吏),還有名士張禮、杜等人,堪稱當時天下最強的郡級領導班子。
王比回到兖州後,詳述了通使的經過。曹操多少有些失望,他原本想,此行與朝廷建立正常聯系,朝廷對他即使不升官晉爵,也會正式下達命令對他的兖州牧一職給予确認,但李等人壓根沒理這個茬。
不過這次也有很多收獲,王比此行想必會讓獻帝以及長安的公卿們對自己忠于漢室的心跡有所了解,董昭、鐘繇等人在關鍵時候替自己說話,說明這些人以後還會對自己給予幫助,加上在天子身邊供職的丁宮、丁沖等人,日後真要按照毛說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話,這些人都能用得上。
【六、幽州風雲】
再來看看幽州,說說公孫瓒的事。
大約在曹操和于毒、眭固等人在東武陽、頓丘一帶激戰的同時,袁紹率冀州的主力部隊向北移動,他們面對的敵人是公孫瓒率領的十分強悍的幽州兵團。
中平年間,公孫瓒在盧植、皇甫嵩等人麾下與黃巾軍交戰,因為作戰勇猛、戰功顯赫,先後升為騎都尉、降虜校尉、中郎将等,成為帝國的高級軍官,被封為都亭侯,率軍駐紮在幽州北部一帶,與黃巾餘部張純、烏桓首領丘力居作戰。
公孫瓒天生是打仗的好手,他最擅長使用的是騎兵,最喜歡騎的是白馬,他經常親自帶領幾十個善于騎射的人,一律騎上白馬,在戰場上呼嘯而來,又呼嘯而去,殺傷力很大,他給這個突擊隊起了個名字,叫“白馬義從”。
很快“白馬義從”就成了公孫瓒的一個招牌,烏桓人提起來都害怕,不敢再來進犯。公孫瓒一看這個牌子好使,幹脆把“白馬義從”擴編,總兵力達到數千人,全部是騎兵。“白馬義從”自此成為漢末馳騁在疆場上的一支鐵軍,所向披靡,很少打敗仗。至于這支騎兵部隊是不是全都騎白馬,則有點可疑。因為白色的戰馬是比較難得的,找幾十匹還行,一下子找幾千匹,那是相當的困難。不過,要是真的能湊齊幾千匹白馬來,往陣前一列,不用開打,光那白花花的一片,就夠晃人眼的。公孫瓒看來還懂點行為學,這個創意挺不錯。
自從有了這支部隊,公孫瓒實力大增,按照槍杆子裏出政權的看法,他成為帝國北部邊界一帶的實際控制者。但公孫瓒自己總覺得不爽,因為朝廷派劉虞來當幽州牧,成為公孫瓒的頂頭上司。
劉虞跟公孫瓒的做法不一樣,對少數民族主張懷柔。他到任以後就派使者到烏桓各部族那裏曉以利害,丘力居等烏桓部族首領有感于劉虞的聲名和誠意,紛紛派遣使者表示願意歸附。
公孫瓒眼看劉虞不費一兵一卒就把邊境的事擺平了,心裏充滿嫉妒,他暗中派人搞破壞,挑撥朝廷與這些少數民族的關系,甚至不惜派兵在烏桓使者必經之路上埋伏,将使者殺害。但烏桓各族識破了其中真相,歸意堅定,他們就是繞道也要跟劉虞保持聯系。
邊境問題解決後,劉虞上報朝廷要進行裁軍,公孫瓒的部隊包括步兵、騎兵在內被裁得只剩下一萬來人,指揮部設在右北平郡。
公孫瓒郁悶壞了,敢情這個老頭子很陰呀,看着慈眉善目,手段倒挺黑,以和平手段解決了邊境問題,裁軍就有了借口。說是裁軍,其實就是削減公孫瓒的實力。
雖然公孫瓒很不滿,但劉虞卻獲得了更高的威望,後來張純被手下人王政殺死,把首級獻給了劉虞。張角兄弟死後,張純在黃巾軍中的影響力最大。此次消滅張純,對朝廷來說是一件大事,于是獻帝專門派使臣來幽州,拜劉虞為太尉,後來又升為大司馬,仍然兼任幽州牧。
公孫瓒因為助戰有功,被任命為奮武将軍。
公孫瓒心裏很不服氣,北部邊界的和平是靠他出生入死打出來的,憑什麽讓劉虞坐享其成?但是懾于劉虞的巨大威望,公孫瓒也只好忍氣吞聲,待在右北平郡為帝國站崗。
如果放在和平年代,公孫瓒這一輩子也就這樣了,但偏偏現在是亂世,在亂世中偏偏惡人、強人更容易出頭,公孫瓒的機會來了。
幽州的黃巾民變又起,為了鎮壓起義軍,公孫瓒的隊伍也得到擴充。在與青州黃巾軍的東光之戰中,他一次投入的兵力就達到兩萬多人,說明此時他的實力已迅速擴張,活動範圍也很廣。如此一來,他與劉虞的矛盾也更加尖銳了。
劉虞有個兒子叫劉和,此時在長安獻帝劉協身邊供職,都是老劉家的人,獻帝對劉和很倚重,他派劉和逃出長安,到幽州找劉虞帶兵來救駕。劉和路不熟,沒有走河東郡,也沒有走函谷關,而是走的武關道,奔南陽郡來了,結果進入袁術的防區,袁術将其扣留。
袁術扣下劉和,據說是想争功,不想把救駕的功勞讓劉虞一個人分享。他給劉虞寫了封信,讓劉虞發兵做後援,自己為先鋒,到長安救駕。劉虞接到袁術的信,想派兵去,公孫瓒勸他別去,因為袁術此人不可靠,派出去的人馬可能有去無回,但劉虞不聽。
公孫瓒一想不對勁,他說的話要是傳到袁術那裏,袁術肯定恨他。為此,他幹脆比劉虞更積極,派他的堂弟公孫越率領一千多騎兵去南陽郡,一方面支援袁術,另一方面暗中挑撥劉虞跟袁術的關系。
劉虞派的人大概是步兵,公孫越率領的騎兵因此先到了南陽郡。公孫越暗地裏讓袁術扣留劉和,等劉虞派來的人馬到了之後,又将其全部吞并。這些事當然瞞不過劉虞,公孫瓒和劉虞之間的關系徹底破裂。
事情還沒完,在孫堅攻打周昂的那一仗中,袁術派公孫越支援孫堅,結果被流矢射中而死。袁術擔心公孫瓒埋怨自己,就把火往袁紹身上引,說公孫越是袁紹殺害的。公孫瓒果然被激怒,咆哮道:“我弟之死,全是因為袁紹引起。”于是出兵磐河,進攻袁紹。
這個時候袁紹剛取得冀州,立足未穩,聽說公孫瓒來挑事,不敢硬來,跟公孫瓒趕緊談判,最後把自己擔任的渤海郡太守一職讓給公孫瓒的另一個堂弟公孫範,公孫瓒才怒沖沖撤兵。
公孫範上任後,他的領導應該是袁紹,但他專門跟袁紹搗亂,以渤海郡為基地,配合袁術把勢力往冀州、青州發展。公孫瓒以打黃巾軍為借口,大肆封官,任命嚴綱為冀州刺史,田楷為青州刺史,單經為兖州刺史,他還任命了郡太守、國相以及縣令等若幹。
公孫瓒的做法擺明了就是跟袁紹對着幹。任命冀州刺史是成心惡心冀州牧袁紹一下,任命青州刺史是趁原青州刺史焦和之死去搶地盤,兖州雖然現在還八竿子打不着,但兖州牧曹操是袁紹的人,先派個刺史去攪和他一下,這種未經允許就把筷子往別人碗裏伸的行為必然招打。袁紹與公孫瓒的矛盾不斷激化。
以上是史書所載袁紹與公孫瓒徹底鬧翻的經過。這個過程是沒有錯的,結果大體上也如此,但其中的內幕肯定更為複雜。
獻帝劉協派劉和搬兵是有可能的,但僅憑劉協的這道“口谕”,袁術、劉虞因此就要發兵前去救駕,尤其是袁術,看他的架勢肯定以為只要進兵長安馬上就能立下奇功一件似的,還要搶功,這就不好理解了。
長安是什麽地方?那裏有十多萬涼州精銳,袁術能不能打到函谷關下都十分難說。袁術會那麽幼稚嗎?
背後的真相也許是:袁紹、公孫瓒都意識到決戰不可避免,他們同時想到的,就是給自己拉外援,給對手制造敵人。袁紹拉的外援是劉虞,因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加之當初他曾力推劉虞為帝,雖然事情沒有弄成,但至少說明他對劉虞是尊重的,劉虞對他不會有惡感;公孫瓒拉的是袁術,因為二袁此時已交惡,周昂與孫堅之戰就是證據。
沒成想出現了新情況,公孫越意外戰死,公孫瓒與袁紹的矛盾進一步升級。不用袁術挑撥,這一仗也要開打了。
【七、“白馬義從”的最後一戰】
袁紹要與公孫瓒決戰,必須過一道難關:白馬義從,這又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
漢末的幽州鐵騎是騎兵中的精銳,“白馬義從”又是幽州鐵騎中的精銳。在公孫瓒的多年經營下,這支雄師百戰百勝,令敵人聞風喪膽。烏桓人之所以願意歸順,與其說是給劉虞面子,不如說是被這支鐵軍打怕了。
公孫瓒可以調用的總兵力有十萬人左右,除了“白馬義從”之外,在其他部隊裏騎兵所占的比例也比較高,這與幽州跟北方少數民族地理相近有關。袁紹一方的主力大都是韓馥原來的人馬,雖然張、義、顏良、文醜都是一流的猛将,但都是歸順不久,忠誠度尚待考驗,萬一戰場上出現失利的情況,他們會不會落井下石還不太好說。
相比較而言,義投奔自己比較早,與韓馥曾經徹底翻臉,可靠度較高,關鍵時候可以委以重任。
袁紹人馬數量不足,要守的地盤很大,能集中起來作戰的也就三四萬人左右,而且騎兵太少。在華北平原這樣的開闊地帶,用步兵打騎兵,人數又不占優勢,勝算實在很小,更何況敵人擁有“白馬義從”這樣的戰場終結者。
讓袁紹頭疼的還不止這些,有情報顯示,公孫瓒跟黑山軍的張燕聯系上了,同時還策反了剛剛歸順袁紹的張楊和南匈奴單于于扶羅。公孫瓒又跟徐州刺史陶謙建立了聯系,加上老盟友袁術,袁紹基本上算是四面楚歌了。
所以,當公孫瓒以公孫越之死為由南下興師問罪時,袁紹确實很緊張,趕忙把自己兼任的渤海郡太守一職讓給公孫範,用割地的辦法先把公孫瓒哄了回去。
在袁紹的陣營裏,只有曹操在兖州方面進展順利,但曹操此刻又不能動,他承擔着監視袁術、陶謙等人,護衛冀州南線的重任。袁紹整天跟沮授、田豐、逢紀、許攸等智囊一塊商議,試圖找到一條破敵之策。
袁紹還在冥思苦想之中,公孫瓒那邊已經等不及了,他先發布了一個“讨袁檄文”,然後調集大軍向冀州殺來。
這份“讨袁檄文”寫得挺下功夫,列舉了袁紹的十大罪狀,這些罪狀裏有歪曲事實和無中生有,有誇大其辭和造謠中傷,但也有實事求是。罪狀主要是:
一、制造了董卓之禍(袁紹确實負主要責任,但并非全部責任);
二、不反抗董卓,置天子于不顧,是為不忠(這個大家都有責任);
三、起兵反抗董卓卻不告訴家中長輩,使家族五十多口喪命,是為不孝(這個應該是董卓的責任);
四、起兵兩年來不對付敵人,只顧壯大自己(這倒是事實);
五、指使韓馥另立新君(這個也是事實);
六、信任一個叫崔巨業的江湖騙子、算命先生,打仗也要挑好日子,缺乏大臣的風範(人家喜歡,關別人什麽事);
七、殺害有功之臣劉勳(劉勳是誰沒查出來,以後曹操手下有個劉勳,但肯定不是此人,袁紹該不該殺他,待考);
八、向別人要物資,給得不夠翻臉就殺人(沒有具體線索,不好判斷真僞);
九、身為賤妾之子,還要與嫡出的後将軍袁術相争(揭人家的隐私,不厚道,而且這是袁家的私事,不關別人的事);
十、派周昂攻打孫堅,致使孫堅的讨董大業失敗(雖屬事實但有些誇張,周昂不去搗亂,袁術、孫堅的讨董大業也難以成功)。
在進行了強大的輿論宣傳之後,初平二年(191年)底,公孫瓒親率大軍南下,屯兵于界橋。次年初,袁紹整頓人馬也開到了,兩軍在界橋以南二十裏的地方擺開戰場。
兩軍對陣,公孫瓒一方陣容齊整、甲盔鮮明、旌旗飄揚,很有氣勢,尤其是隊列正中的“白馬義從”,更是令人聞風喪膽。對面的袁軍卻擺出了一個奇怪的陣形,也許是來不及訓練,也許不善于打這樣的陣地戰,袁軍列于正中的只有八百名步兵和一千多弓箭手,身後隐約有二三萬人,隊列不整,鬥志不高。
那一刻,公孫瓒的嘴角一定露出過一絲輕蔑的微笑,他太熟悉這樣的打法了,打張純、打青州黃巾軍,包括打烏桓都是這樣的打法:號令一發,他的“白馬義從”會風卷殘雲般殺過去,下面的事就只等後續部隊上去給敵人收屍了。
公孫瓒抽出指揮刀在空中劃出了一道果斷且優美的曲線,随後下達了總攻的命令。
數千“白馬義從”席卷而出,馬蹄聲如悶雷,夾着數千人的嚎叫,仿佛不用刀劍僅憑這吓人的氣勢就足以把任何敵人撕個粉碎!
當敵人的鐵騎呼嘯而來時,袁軍的隊形仍然沒動,但列隊于最前面的八百名步兵突然伏下身子,用随身攜帶的皮盾蒙住身體,然後一動不動地等待敵人騎兵的到來。
敵人一點點近了,這些人仍然不動。“白馬義從”都是馬上的射箭高手,離對方還有一箭之地時,他們一邊沖鋒,一邊在馬上搭弓射箭,雨點般的箭支射向袁軍,但袁軍有皮盾相護,沒有人受傷。
說話之間,騎兵就到了,伏在皮盾下的這八百人突然躍起,騎兵們這才發現,他們手持一種樣子奇怪的武器向自己刺來。這些袁軍像是受過專門訓練,把這種武器用得很老練,無論刺人還是刺馬,一刺一個準,把把不落空。
這種武器是袁紹專門為“白馬義從”設計和定做的,叫做“大戟”,是一種帶鈎帶刺的長槍,有點像岳飛大破金人連環馬的鈎連槍。這的确是經過特殊訓練的隊伍,它的指揮官是義,他們是袁紹的殺手锏和秘密武器,數月來他們秘密訓練,反複模拟,為的就是這一天。他們被袁紹稱為“大戟士”。
“白馬義從”遭受了自誕生以來最殘酷的重創,但這才是惡夢的開始。守候在這八百名步兵後面的一千多名弓箭手早已為客人準備好了豐盛的禮物:弓箭。待敵人接近時,一齊怒射而出。
弓箭手通常會分撥輪換射擊,這意味着雖然可以僥幸躲過“大戟士”的重創,但随之迎面而來的是由近距離射出的、密不透風的箭雨。威名遠揚、從未有過敗績的“白馬義從”成了袁軍弓箭手練習射擊的移動靶,紛紛被射落馬下。
“白馬義從”遭受到第一次、并且也是最後一次慘敗。此後,作為一個獨立完整的作戰單元,他們在戰場上消失了。
“白馬義從”神話般的覆滅震驚了公孫瓒的陣營。還在敵人錯愕的當口,袁紹即指揮後面的隊伍全線出擊。公孫瓒大敗,袁軍一路追殺,公孫瓒剛任命不久的冀州刺史嚴綱未及上任即戰死。
按理說這一仗可以就此結束了,但中間卻出了驚險的一幕,險些讓勝利的天平倒轉過來。
袁軍雖然得勝,但指揮系統和士兵的訓練可能真有問題。在追擊過程中,袁軍亂了章法,大家只顧追敵人,把主帥袁紹給忘了,此時袁紹跟前只有一百多人。在混亂中,他們與二千多敵人相遇,敗兵反而把獲勝一方的主帥團團圍住!
幸好對方不知道這裏面有敵軍主帥,所以攻擊并不激烈。袁紹指揮手下展開防衛,等待援軍的到來。
敵人開始射箭,情況十分危險。田豐跟袁紹在一塊兒,田豐拉着袁紹要到一處斷牆後面躲避,袁紹不僅不去,索性把頭盔也摔了,喊道:“是大丈夫何懼向前戰鬥而死(大丈夫當前鬥死)!”
有人說袁紹是草包,有人說公孫瓒、董卓是一介武夫,也有人說劉表、陶謙沒本事。凡此種種,其實都是誤解,犯了“勝者王侯敗者寇”的經驗主義錯誤,以為只有最終取得勝利的人才有資格稱為英雄。
其實,能在風雲莫測的歷史舞臺上嶄露頭角,能在群雄逐鹿中哪怕只是走個過場,都必然有過人之處。在袁紹的一生中,曾不止一次在危險關頭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事實證明袁紹不缺英雄氣,更不是貪生怕死之徒,關鍵時刻他能拉得出、頂得上,有時候也能打得贏。在危急關頭,他用行動給手下人做出了表率,激勵大家的鬥志。
在袁紹的帶動下,袁軍士兵拼死抵抗,袁軍的後援部隊也及時趕到,迅速化解了危機。界橋之戰雖然沒有全殲公孫瓒的主力,但給公孫瓒以重創。界橋之戰前袁紹處于挨打的局面,界橋之戰後,二人實力取得平衡,袁紹還逐漸占據了上風,公孫瓒雖然在北方一帶還能活躍幾年,但已經沒有實力發動大規模的決戰了。
界橋之戰是以步兵戰勝騎兵的經典戰例,也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典範,此戰的全勝,使袁紹打破了四面楚歌的被動局面,為最終統一北方各州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