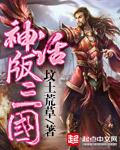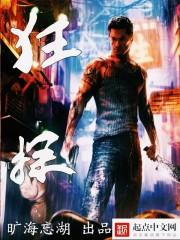第7章 (2)
。他經常會與朋友們讨論相關問題。皇甫嵩擔任北地郡太守前的職務恰巧是議郎,盧植也擔任過議郎,如果曹操與他們剛好在一塊兒共過事,他們應該比較熟悉,對于這個個子不高、但卻幹練果敢的青年,皇甫嵩或者盧植沒準有過深刻的印象。
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張奂、張溫等人的影響。張奂、張溫可以算作上一輩的軍事統帥,曹騰與他們的關系已如前述。這兩個人在軍界威望很深,并且仍然活躍于軍界,雖然因為邊境戰事脫不開身,沒有出現在清剿黃巾軍的序列裏,但在軍事方面無疑保持着重要的發言權。如果曹操事先得到消息并求助于他們,他們的建議應該在靈帝的決策中發揮一定的作用。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當時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這個原因看來荒謬,但也确實存在,帝國的教育體系雖然發達,但培養的都是文人,武将基本上靠自學成才,或者像張奂、盧植那樣棄文從武。由于教育結構的失衡,造成軍事人才的匮乏,到了需要的時候,還真找不到合适的人。
而且打仗不是好玩的事,現在面對的是來勢兇猛的黃巾軍,帶兵打仗、沖鋒陷陣、馬革裹屍,好多人還沒有做好思想準備。騎都尉看着很威風,但任職條件極苛刻,危險系數又大,前途不被看好,世家大族即使有子弟符合條件,也不會出這個風頭。如袁家的袁術,擔任過多年的虎贲中郎将,此兄一貫喜歡出風頭,但這回也沒敢吱聲,畢竟幹天子衛隊和上戰場厮殺是兩碼事。
這個時候,如果曹操主動請纓應該機會也很大。以曹操的個性,在朝廷裏做議郎,然後一步步往上爬,做個九卿,再到胡子一大把時混進三公行列,這樣的職業生涯規劃不是不可行,但卻不是他心中所想。
曹操欣賞許劭給自己的評論:“亂世之英雄,治世之能臣。”
以往認為,曹操只一心想當英雄,對當能臣不太感興趣。其實不然,曹操不是從來不想當能臣,而是他明白當不了。
因為當能臣需要條件,這個條件是“治世”。現在的情況剛好相反,天下已經大亂,亂世裏沒有能臣,亂世裏只有英雄。
曹操想做一個英雄,和曹操同時代的許多人也都有同樣的想法。
不管怎麽樣,曹操脫下文官的制服,換上一身戎裝,曹秘書成了曹師長,他要帶領臨時組建起來的這支五千人的隊伍,開往前線。
曹師長接到的命令是到達目的地穎川郡後,聽從左中郎将皇甫嵩的指揮。
在行軍的路上,曹師長不斷接到最新情報和皇甫準将發來的命令,中心只有一個:穎川前線戰事吃緊,火速增援!
【五、長社的大火】
對付黃巾軍的主戰場有兩個,一個是北部的冀州,北中郎将盧植任總指揮,他的對手是張角三兄弟;一個是南部的穎川郡,分別由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任總指揮,他們的對手是穎川黃巾軍的首領波才。
先說說南部戰場。
穎川郡的位置挨近洛陽,波才又是黃巾軍中最有謀略的将領,朝廷不敢怠慢,派了皇甫嵩和朱俊共同迎擊。黃巾軍作戰英勇,面對朝廷的兩路大軍,不急不怕,沉着應對。
皇甫嵩和朱俊雖然沒有吃到大敗仗,但一舉蕩平敵人的想法沒有實現。盡管有過平叛的經驗,這一次他們也不敢再大意,商議之後,他們決定采取穩紮穩打的辦法,與黃巾軍打持久戰和消耗戰。
這個決策本來是正确的,因為他們這次出征,隊伍是臨時組建而成,來不及訓練,各部之間和上下之間都還不夠熟悉,是一支戰鬥力還沒有完全形成的部隊,穩定一下慢慢來,是有必要的。
同時,大将軍何進在洛陽正抓緊組建預備隊,朝廷的援軍以後會陸續投入戰場,只要堅持下來,戰場敵我力量對比就會發生改變。
波才也看到了這一層,所以他不想長期對抗,而是全力攻擊。他選擇的主攻目标是朱俊負責的方向,結果朱俊盯不住,吃了敗仗。
皇甫嵩分析了形勢,認為得找一個堅固的據點屯兵築寨據守,這樣他帶兵退到了一個地方,叫長社。
皇甫嵩和朱俊的隊伍退到了長社城內,波才随後指揮黃巾軍将其層層圍住。黃巾軍的人數幾倍于朝廷的部隊,形勢十分危險。
皇甫嵩不斷向洛陽發出求援信號,這樣,新組建的騎兵師共五千餘人,在沒有經過訓練的情況下,即在師長(騎都尉)曹操的率領下投入戰場。這時是光和七年(184年)五月,距張角正式起義僅兩個多月。
長社是一個小縣城,去過北京西南郊宛平城的朋友們可能會有更容易理解這一點,通常這樣的城池只有四個門,站在南門樓一眼就能看到北門樓。平時,裏面的常住人口至多數千人。依靠這樣的城池抵擋黃巾軍數萬人的進攻談何容易?皇甫嵩作為經驗豐富的将領,一面指揮守城,一面思考如何擺脫困境。
站在長社城牆上,他看到黃巾軍的營寨附近都長滿樹木和草,他們這樣做可能是為了宿營的時候更舒服一些,畢竟農歷五月的天氣已經很熱了。
皇甫将軍的臉上露出了一絲不易覺察的笑容,波才,看來你只靠自學成才還是嫩了點。皇甫嵩立即布置下來,準備引火之物和大量易燃品。士兵們趁一個刮風的夜裏沖出城去,他們個個手持火把和引火的東西,沖到敵營,見到樹也燒,見到草也燒,見到營帳也燒。這時候風很大,火勢很快起來,黃巾軍數十天攻城不下,已經比較疲憊,大部分人都在睡覺,突然火光沖天,喊聲四起,營帳裏一下子亂了套。
皇甫嵩立即率兵進攻。黃巾軍損失慘重,但他們沒有完全退卻,而是退到長社之外稍遠的地方重新紮營。這時,曹操率領的騎兵部隊趕到了。
三路人馬合在一處,由北中郎将皇甫嵩統一指揮,這次皇甫嵩改變了打法,主動尋求與黃巾軍決戰。對于黃巾軍來說,其實沒有更好的辦法,打持久戰只能對朝廷更有利,也只能選擇決戰了。
結果,這場決戰以朝廷軍隊大勝結束,波才棄軍而走,黃巾軍被斬首數萬。靈帝下诏封皇甫嵩為都鄉侯。
皇甫嵩、朱俊會同南陽郡太守秦颉、騎都尉曹操等人繼續追擊,不斷擴大戰果,于宛城斬殺了黃巾軍另一個首領張曼成,最後于陽翟和西華再次找到波才和黃巾軍首領彭脫率領的主力,取得大勝。
朝廷軍隊三戰全勝,黃巾軍被迫退出穎川、南陽等地,京師南部的形勢轉危為安。在首戰中朱俊所部曾經吃了敗仗,所以皇甫嵩在上報功勞的時候,特意将後面取得的功勞多分一些給朱俊,靈帝下诏封朱俊為西鄉侯,由右中郎将改任鎮賊中郎将。
過去雖然都是中郎将,但左在右之上,右中郎實際是左中郎将的副手。朱俊不再擔任右中郎将一職,意味着他将脫離皇甫嵩單獨行動。果然,朝廷命令二人分兵,皇甫嵩率領所部以及騎都尉曹操所部開住洛陽東部地區兖州刺史部的東郡,在那裏黃巾軍首領蔔巳漸成氣候。朱俊仍舊在南陽郡一帶平息黃巾軍餘部。
皇甫嵩、曹操率軍到達東郡,擊破了東郡黃巾軍,生擒蔔巳,斬首七千餘級。
再來說說北部戰事。
盧植到達冀州後,利用自己的名望,大量招募兵馬,壯大力量。在這次招募活動中,有兩個人不得不提,他們是盧老師的兩個學生:公孫瓒和劉備。他倆不是一塊兒來的,但都不是只身前來,還帶着不少人,其中公孫瓒帶的人裏,一定有一個叫趙雲,劉備帶的人裏,有兩個人分別叫關羽和張飛。
關于他們的故事先按下不講。先說盧将軍的對手張角兄弟,幾仗下來,張角兄弟漸漸不支,退到了廣宗。盧植在廣宗城外修堡壘、挖壕塹、造雲梯,準備攻城。正要一舉攻下廣宗的時候,意外發生了,盧植被解職。
朝廷往前線派來了一個人,名叫左豐,是個宦官,他來的目的說是慰問,實際上是監軍,畢竟靈帝劉宏對這些手握重兵的将軍們還不完全相信。這個左豐打仗是外行,搞錢卻是老手,他依照慣例向盧植暗示給自己行賄,但幾天過去了,盧将軍那邊絲毫不見表示,左豐于是很生氣地回去了。
宦官向前線的将領索賄,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打仗得花錢,戰争預算的制定和撥付掌握在宦官手裏,如果不打點好這幫貪官,什麽事都幹不成。當年猛如“涼州三明”之一的段深知其厲害,刻意巴結宦官。
但盧植不是段,他本質上是個學士,打從心底裏看不起這些宦官。盧植以為,到了現在這種時候,靈帝不應該再偏信這些宦官了。他也不相信宦官們會選擇這個時候找事,所以沒有理左豐的茬兒,繼續做攻城的準備。
但是盧将軍錯了,壞人做壞事是不分時候的。左豐回去向靈帝報告前線戰況,添油加醋說盧植消極怠工,故意不出戰,是想邀功。靈帝大怒,給盧植派來了一輛囚車,臨陣逮捕主将,押回京師問罪。
接任盧植的人名叫董卓。這厮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在這裏是第一次說他的事。董卓長期在羌漢雜居的涼州一帶長大,先後追随“涼州三明”之中的張奂、皇甫規與羌人作戰,因為很會打仗,被提拔為并州刺史、河東郡太守。朝廷下诏調董卓前來冀州,指揮前線作戰。靈帝重新設了個東中郎将給他,因為是盧植的職務此刻還沒有免除。
說實話,論打仗董卓是那個時代一流的猛人,但此君長期與羌人作戰,善長騎兵野戰,屬于速度型和力量型選手,拉到河網密布的冀州大平原上一試,居然找不到感覺。他多次想找張角的主力決戰,但總也找不着。靈帝等急了,因為左豐告訴他的是,董卓只需一頓飯的功夫就能拿下張角。盧植怯戰,怎麽換了個夠狠的角色,一樣沒有效果?
這反而救了盧植一命。他被押到京師本來要受到嚴懲,但由于董卓軍事上的失敗,從反面印證了當初他穩紮穩打策略的正确,于是他僅受到免官的處罰。
董卓眼看拿不下張角,幹脆向靈帝上書,說自己無能,然後向天子推薦了一個人代替自己,這個人就是正在東郡一帶清剿黃巾軍的皇甫嵩。
董卓是皇甫規的老部下,自己學藝不精,只好把老首長的侄子請出來。這樣皇甫嵩就接替董卓指揮對張角的戰鬥。
這一年對皇甫嵩來說實在是個人事業的颠峰,而且他運氣也好得不行。接替董卓以後,還沒等他拉開陣式,這場戰鬥就結束了。因為對方的主帥、太平道大賢良師、黃巾軍天公将軍張角不幸病故。
張角突然去世給黃巾軍造成了巨大的打擊,他兩個弟弟張梁、張寶繼續統領黃巾軍主力。在皇甫嵩指揮下,朝廷軍隊在廣宗這個地方取得了決戰的勝利,張梁、張寶先後被殺。張角雖然死了,皇甫嵩仍然撬開棺材,戮屍、斬首,将張氏三兄弟的人頭傳送京師。
到這一年底,朝廷軍隊在各個方向都傳來捷報,各種戰利品以及砍下來的人頭不斷運到洛陽。靈帝下诏将亂軍的人頭集中起來,上面蓋上土,居然像小山那樣高,被稱為“京觀”。
本次平叛功勞最大的當數皇甫嵩,靈帝下诏封皇甫将軍為槐裏侯,拜為左将軍,由準将升為中将,同時兼任冀州牧。朱俊也升為右将軍。
凡參與平亂的都有不同的獎賞,騎兵獨立師師長(騎都尉)曹操因為配合皇甫嵩作戰有功,被任命為濟南國相。
好了,一切太平了,張角兄弟死了,人頭帶回來了,各地的黃巾軍都被鎮壓下去了,盡管還有一些地方有黃巾餘部在活動,但已經成不了氣候。靈帝想,該喘口氣了,這一年真緊張得要死。
光和七年(184年)十二月,靈帝下诏改元為中平,寓意天下經過一場大亂開始走向安寧和平。
但如果他能未蔔先知,他的心情一定會更沉重,因為這才是風暴的開始。
【六、群雄初亮相】
在這場平息黃巾軍的戰役中,還有幾個人嶄露出頭角,引人矚目,換句隆重點的說法,就是登上了歷史舞臺。
其實,這幾位算來也都是大家的老熟人了。
一位是王允,字子師,太原郡祁縣人,他很早就表現出異人之處。著名黨人郭泰曾經“奇之”,稱他為“王佐才也”。史書上說他“少好大節,有志于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跟青年曹操很相像,是文武兼修并在內心斷定天下一定會大亂的人。
黃巾起義前,王允擔任侍禦史,負責監察方面的工作。這時朝廷抽調一部分中央幹部到地方任刺史、太守,充實地方實力,王允被任命為豫州刺史。到任後,王允很重視領導班子建設,先後引進了兩個名士,一個是穎川的荀爽,即“荀氏八龍”之一,是荀的叔父;另一個是孔聖人的後代孔融。皇甫嵩、朱竣與曹操在穎川郡與黃巾軍交戰,穎川郡是王允的地盤,他給予充分合作,給中央軍搞後勤,同時組織地方武裝作戰。
在一次打掃戰場時,王允從黃巾軍那裏發現了中常侍張讓的賓客與黃巾軍暗中相通的書信,立即呈報給靈帝,張讓吓得半死。可奇怪的是,靈帝除了痛罵張讓一頓外,并沒有再作深究。張讓“懷協忿怨”,捏造了一個罪名誣告王允。中平二年(185年)王允下獄,差點沒了命,幸虧大将軍何進出手相救,才保住一條命。王允随後隐居了一段時間,接着到何進手下任職。
中平元年從中央下派到地方的幹部裏還有一個陶謙,字恭祖,丹陽郡人,“以不羁聞于縣中”,他的父親做過縣長,但很早就死了。十四歲的時候,由于缺少管教,陶謙整天騎着根竹棍滿街跑(乘竹馬而戲),但是有人卻看好他,這個人是同郡的甘公,以前擔任過倉梧郡太守。甘太守甚至想把女兒許配給陶謙,遭到了甘夫人的強烈反對。
甘太守不以為然,非把女兒許給陶謙不可,最後陶謙成了甘家的女婿。甘太守沒有看走眼,陶謙後來被舉為茂才,擔任縣令,又做了幽州剌史。名将張溫主持西羌戰事的時候,把陶謙調過來擔任參謀(參軍事)。
黃巾起義暴發時,陶謙還在張溫那裏當參謀,後來轉任徐州剌史。與王允不同,陶謙擔任徐州刺史可能是他要求或者積極活動的結果,因為他與上司張溫正在鬧別扭,急于走人。
張溫對陶謙很不錯(接遇甚厚),但陶謙偏偏看不上這個上司。一次軍中宴會,張司令讓陶參謀負責行酒,就是當酒司令,這位陶參謀還真當事兒,真以為自己是司令了,借着酒勁兒把張溫侮辱了一番。
張溫脾氣再好,這下子也受不了,一怒之下給陶謙判了個流放邊疆(徙謙於邊)。剛打發走陶謙,張溫的怒氣就消了些,有人又從中相勸,張溫于是下令将陶謙追回。按說陶謙該吸取教訓了,但他見到張溫的時候,仍然把頭擡得高高的,一副誓不低頭的樣子。
好在張溫沒有再發火,只是笑着說:“恭祖,你是不是得了癡病呀?”
在張司令那兒不好混,陶參謀開始考慮另謀高就。正在此時,黃巾起義爆發,朝廷往地方上派幹部。可能是在積極活動下,他最終被派到徐州當了剌史。陶參謀之所以敢清高,因為他确實有兩把刷子,到任後,“擊黃巾,破走之”。
陶謙從此就紮在這兒不走了,徐州成了他的根據地。
還有一個人,朱俊在被任命為右中郎将時,堅持提出來要調他來當幫手。這個人名叫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縣人,是孫武的後代,時任下邳縣副縣長(下邳丞)。
史書上說,孫堅生得容貌不凡,性情闊達,好交朋友,年輕時做過縣吏、郡保安團團長(郡司馬)。當時,他家鄉一帶鬧海盜,頭目叫許昌(此為人名非地名),孫堅以郡司馬的名義招募精勇,與其它地方武裝共同讨伐許昌,因為有功,被任命為鹽渎縣丞,後又改任盱眙縣丞、下邳縣丞。
孫堅的仕途看來不太順,換了三個地方都是副縣級領導,擱在別人(如劉備)肯定撂挑子不幹了,但孫副縣長幹得挺好,《江表傳》(這本書是重點吹孫吳的,不過保存了不少孫吳方面的史料)說大家都挺愛戴他(所在有稱,吏民親附)。
朱俊聽說孫堅打過海盜,軍事上有一套,就請孫堅到手下當副團長(佐軍司馬)。孫堅從下邳趕往穎川前線報到的時候,不是一個人去的,屁股後面還跟了一千多號人,可見孫堅挺有號召力。
在随後的戰事中,孫堅作戰勇敢,尤其是在朱俊指揮攻打宛城時,孫堅第一個登上城頭(身當一面,登城先入)。朱俊于是上報朝廷,升孫堅為所屬獨立團團長(別部司馬)。下面該說說盧植的兩個學生公孫瓒和劉備了。
公孫瓒字伯,幽州刺史部遼西郡令支縣人,屬于邊疆地區人氏。在郡政府當過文書(書佐),是一表人材,“有姿儀、大音聲”,受到太守的賞識,把女兒許給了她。
成為太守的女婿後,為了進一步栽培他,太守出學費把他送到幽州當時最有名的大學者盧植那裏學習。
在此期間,公孫瓒認識了同學劉備。
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據說是西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劉勝之後,但這頂多是個象征意義,因為此時是東漢不是西漢,雖然都姓劉,待遇差得老遠了。劉備的祖父叫劉雄,曾經做過東郡下屬的範縣令。父親叫劉弘,很早的時候就死了。
劉備的母親以“販履織席”為業,是個體戶兼手工業者。家境雖然不好,但這個母親卻很偉大,她知道讀書有文化最終才能出人頭地,所以劉備十五歲時,母親就給他收拾行李讓他去上學,拜的老師也是盧植。
這樣,劉備跟公孫瓒做了同學。上學期間,他們的關系很好,公孫瓒比劉備大,劉備喊他作大哥(以兄事之)。
除了公孫瓒這個同學外,劉備還有一個同學叫劉德然。劉德然的父親叫劉元起,是個大款,非常看好劉備,經常資助他,還有中山國的大商人張世平、蘇權等人,也資助過劉備。
看來,劉備年輕時就挺有魅力,太守的女婿跟他稱兄道弟,大款家的孩子跟他交朋友,大商人争着資助他。他的獨特之處在哪裏呢?如果有的話,按說這些光輝事跡史書都會記上一筆的。
但是翻開史書卻讓人傻了眼,關于劉備同學的個人鑒定,史書是這樣說的:“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是個典型的不學無術少年。史書還說他“身長七尺五寸(合一米七六),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并且說他“好交結豪俠,年少争附之”。
這也許才是他的長處,這個個體戶家出來的孩子,最大的長處是能廣交朋友,會交朋友,能交到真朋友。
交朋友是件大學問,僅靠慷慨大方不夠,僅靠以誠相待也不夠,僅講義氣也不行,要交到真朋友、好朋友,交很多很多的朋友,最需要的是什麽?答案是:個人魅力。
事實證明,劉備最大的特點就是有個人魅力。這個特點終其一生,同時代很少有人能超越,因此劉備幹出了一番大事業。
公孫瓒、劉備在盧植那裏畢業後各自發展事業去了,公孫瓒繼續在岳父手下當公務員(郡吏),劉備四處結交朋友,成果顯著,他認識了兩個陪他走過大半生的患難朋友:關羽和張飛。鑒于這兩位老兄的大名已為全宇宙的人所熟知,這裏就不再饒舌了。
盧植在冀州召兵,公孫瓒和劉備先後來到軍前效力,盧植對二人的安排是不一樣的。公孫瓒參軍前已經是國家幹部,有一定資歷,被盧植直接任命為團長(軍司馬)。常山國真定縣人趙雲,這時就在他的手下。史書上說,趙雲“身長八尺(合一米八八),姿顏雄偉,為本郡所舉,将義從吏兵詣公孫瓒。”
劉備是布衣百姓,盧植把他以及關羽、張飛,還有追随他們的一幹人編到校尉鄒靖的下面,暫不明确軍職,幹着再說。
在讨伐黃巾軍的戰鬥中,公孫瓒和劉備都立了功,公孫瓒後來被提升為騎都尉,成為高級軍官,之後歸幽州牧劉虞統轄;劉備被任命為安喜縣副縣長兼縣公安局長(安喜尉)。如果沒有黃巾起義,王允可能混個九卿之類的官當,如果祖墳上冒出青煙來,也有希望位列三公;陶謙恐怕還得在軍隊裏混日子,由于跟上級關系處不好,自己又是一身的臭脾氣,所以前途較為黯淡,幹到年紀一大把,轉業回家;孫堅要稍微好一點,這小子能吃苦、心态好,不過因為沒有後臺,能幹到郡太守這一級,也得累個半死;公孫瓒行情最好,有可能混到邊防部隊裏跟北部少數民族作戰,如果戰績好的話,沒準能封個侯;劉備情況最差,建議他向商業、娛樂業方面發展,或者重新回爐,到盧老師那裏繼續上學,然後專心搞學問;趙雲群衆基礎看來不錯,可以在家鄉真定縣當個公安局長(縣尉)什麽的,如果有機會到部隊裏發展,沒準能混到校尉、中郎将這一級;關羽和張飛嘛,一個是流竄犯,一個是什麽事都愛管的閑人,都屬于社會不安定因素,估計擺脫不了受窮的命,如果不服氣想造反的話,結局不會比張角兄弟更好。
如果沒有黃巾軍,曹操想當“亂世英雄”的可能性不大,不過他可以轉行向“治世能臣”方向發展,以他的智商應該也能青史留個小名。
但是不久的将來,他們都人五人六起來,抄起家夥大打出手,跟別人打,互相之間打,嘴裏都喊着“光複漢室”的口號,手底下幹的都是私活。東漢帝國搖搖晃晃地又走了幾十年,終于葬送在這幫人及其子孫們的手裏。
這一切,都是因為有了黃巾起義。一場黃巾起義,改變了那個時代大部分人的命運。
因為黃巾起義,曹操過了一把帶兵的瘾。現在,他又要脫掉戎裝換上文官制服了,他是品秩二千石的地方大員,即将到那個陌生的地方上任了。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