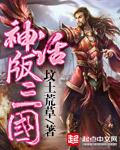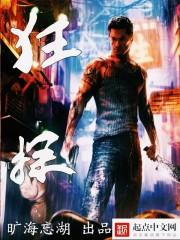第6章 (1)
〔假如沒有黃巾起義,劉備、孫堅、劉表、陶謙等這些名字可能就會湮沒在歷史的長河裏了;假如沒有黃巾起義,曹操頂多成為一名“治世能臣”。黃巾起義的怒火照亮了一個時代,也給曹操的未來提供了一個新選項。〕
【一、太平道要造反】
一個好端端的國家讓不懂事的皇帝、窮兇極惡的宦官以及好鬥的朝臣們折騰成了這樣,國敗民窮、社會凋零、政治黑暗,老百姓願意嗎?
答案是:老百姓不願意,他們正準備造反!
其實早在安帝時,在現如今的四川一帶,當時的益州、永昌、越等郡便發生了大規模的騷亂和農民起義,被稱為“西南夷騷亂”,持續了50餘年。帝國在這一區域的統治受到嚴重挑戰,到靈帝時情況似乎更嚴重,天子跟前的部分家夥甚至提出一個馊主意:把益州從帝國的版圖中分割出去。
此議雖然沒被通過,但對此起彼伏的民變,帝國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
安帝統治十九年,爆發農民起義四次;順帝統治十九年,爆發農民起義十三次;沖帝、質帝兩位皇帝雖然還是小朋友,但農民起義絲毫沒有忽視他們,也爆發了四次;桓帝在位二十一年,爆發農民起義十四次。
從安帝到桓帝,不過六十來年光景,記載在冊的農民起義就多達三十五次。
這些農民起義來勢都很猛,開始時都轟轟烈烈,一旦遭到鎮壓,就很快沉寂。其原因很多,有兩條至關重要:缺少明确的思想綱領,沒有特別牛的領導。
這種情況到靈帝時終于發生了變化。起義等來了一位猛人,他成了東漢帝國的掘墓人。這人是一個流民,純粹的無産者,名字叫張角。他之所以能成為猛人,沒有像其他數十個農民起義領袖那樣,被殺後在歷史上連名字都沒能留下來,是因為他有文化。
有文化的人在那個時代是絕對的少數,張角有文化,所以可怕。張角喜歡看書,他最喜歡看的是一本叫《太平清領書》的書。
傳說《太平清領書》的作者是著名方士于吉(也叫幹吉、幹室)。所謂方士,就是有方術的道士。所謂方術,是古代用自然的變異現象和陰陽五行之說來推測、解釋人和國家的吉兇禍福、氣數命運的醫蔔星相、遁甲、堪輿和神仙之術等的總稱。東漢以後,“方士”這個詞不太常用了,代替它的是“道士”。
于道士寫的這本《太平清領書》,據說篇幅很浩大,分為十部,每部十七卷,共一百七十卷。裏面內容龐雜,以老莊之道、鬼神信仰以及陰陽五行、神仙家的方術為基礎,創造了一套極為神秘複雜的神學體系。這部書裏既有老子的宇宙觀,《周易》的元氣論,也談長生不老的修道思想。
但這些都不是主要的,這本書真正想談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政治。在本書中,于吉陳述了一套完整的政治設想,即太平盛世的建設綱領。他不僅描繪了太平盛世的模樣,也闡述了要達到太平盛世,必須做到君明、臣良、民順。
所以,這部書不是教人如何造反的,而更像是向君王提出的合理化建議。于吉的學生宮崇把這部書直接獻給了順帝劉保,劉保讓大臣們讨論了一下,大家認為這是“妖妄之經”,于是把它封存在國家圖書館(東觀)裏。
桓帝劉志一直沒有兒子,聽人說有個叫襄楷的方士很有法術,就下旨召他進宮,幫助他生個兒子。襄楷不是專科大夫,治療不孕不育不是他的長項,他能做的就是給皇帝弄一些所謂的靈丹妙藥,這是他的特長。
桓帝吃了襄楷獻上的藥,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他甚為歡喜,給襄楷安排了工作。桓帝對他很是信任,處理國家大事遇到疑難問題時也經常向他請教。這個襄楷,是于吉的另一個學生,為了完成于老師的心願,他舊事重提,再次将《太平清領書》呈報給桓帝。
可是,桓帝的興趣只在能不能生出兒子,以及那些靈異事件如何解釋,對于襄楷的治國理念沒有太大興趣。
後來襄楷與黨人攪到了一塊,在黨锢事件中因為替黨人求情而被治罪。襄楷出獄後,依然癡心不改,但這次他對皇帝失去了信心,開始把活動的重點轉向民間,最後成為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颠覆活動的專家,後面還會再講到他。
張角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得到了這部書,也有說法稱他是襄楷的朋友,二人志同道合,一個是理論家,一個是實踐者,立即聯起手來。張角對《太平清領書》佩服得要命,那些皇帝沒有實施的政治綱領,他決心試試。
張角是冀州刺史部钜鹿郡(今河北寧晉)人,出身于社會下層。他有兩個弟弟,一個叫張梁,一個叫張寶。張角早年信奉黃老學說,對神秘預言學之一的谶緯學也深有研究,懂民間醫術和巫術。他領着兩個弟弟,手持一根九節杖,經常活動在冀州一帶,用符水、咒語等為人治病,深得窮人的擁戴。名氣一大,就有人跑來表示願意給他當學生,張角開始吸收徒衆。
沒有想到,來的人越來越多,多到讓張角感到吃驚。不過,他沒有害怕,因為他是個有膽識的人,想幹出一番大事業,于是琢磨如何把這些人組織起來。
張角深受《太平清領書》中政治主張和治國方略的影響,創建了一個民間宗教團體:太平道。其綱領、目标、教義、稱號、教區組織、口號、宗教儀式、活動內容、傳教方式等都依據《太平清領書》來設計。
當時社會上有大量的流民,這些失去土地無家可歸的人都是土地兼并的受害者,沒有人關心,也沒有前途。太平道的出現,至少給了他們溫暖和希望,所以不用動員,這些人都攆着跑着來入道。
還有一些人,雖不屬于流民範圍,但看到這個組織挺厲害,于是也加入進來,就像一些有錢人願意給青紅幫老大當門生一個道理,遇到事好有人罩着。這些人裏,有基層官吏,也有宮裏的宦官。
張角自稱大賢良師,是太平道的總首領。他兩個弟弟張梁、張寶自稱大醫,是太平道核心領導班子成員。他派出八個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傳教義、發展徒衆。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太平道勢力已遍布全國十三個州中的青、徐、幽、冀、荊、揚、兖、豫八州,徒衆達數十萬人。張角把這些徒衆劃分為三十六個教區(方),大的萬餘人,小的六七千人,每個教區都設一個渠帥作為首領。
鬧出這麽大動靜朝廷那邊不知道嗎?其實朝廷是知道的,而且很早就知道了。熹平六年(177年),靈帝的老師、時任太尉的楊賜和他的屬下著名黨人劉陶,分別上書靈帝,報告了這個民間組織的動向,請求給予關注。劉陶更是指出,據他得到的情報,張角的黨羽已經潛入京師,活動于民衆和官宦之中,大有觊觎朝廷之意,應速加偵緝,并诏令天下,重賞捉拿張角。不知什麽原因,如此重要的上書竟然沒有下文。後來楊賜因故離職,劉陶找個機會向靈帝尋問此事,靈帝居然莫名其妙地岔開話題,讓他給自己編一本容易閱讀的《春秋》。劉陶沒有辦法,只得到圖書館裏埋頭完成天子交付的新工作。
從各種跡象看,靈帝本人确實沒把太平道當回事,甚至覺得有個民間團體把流民組織起來,教人向善做好事,還挺好。這種心理可以從靈帝意識形态變化的蛛絲馬跡裏尋找答案。靈帝這時已經開始崇信黃老之學,對老子的思想充滿崇拜,他可能認為,這個同樣視老子為先師的教派,與他的思想還有些吻合呢。
前來投奔太平道的人越來越多,人數呈幾何倍數增長。張角想,既然事情已經幹大了,想收手是不可能的,未來的結果只有兩個:要麽太平道消滅劉漢政權,要麽太平道被劉漢政權消滅掉。
太平道的公關工作做得很出色,就連宮中的高級宦官封謂和徐奉都成為它的信徒,這樣,朝廷中樞機構的消息很快就能送到張角的面前。綜合分析各種情報之後,張角對形勢做出了判斷,他看出太平道和劉漢朝廷翻臉的時刻越來越近了。
誰先動手誰主動。張角馬上召集幾個大弟子和弟弟張寶、張梁商議,大家決定發動武裝暴動,目标是推翻現政權,建立太平盛世。以冀州南部與司隸校尉部結合的邺縣地區作為暴動中心,由張角全面負責,前線總指揮為大方首領馬元義。暴動的時間定為光和七年(184年)三月五日。
這個日子選得很有講究,它葬送了這次起義。
【二、精挑細選好日子】
即将到來的光和七年是甲子年,在六十年一輪回的歷法周期中,甲子年是新周期的開始,讓人聯想到新天命的降臨。
這一年的三月五日又是甲子日,也就是說,太平道确定的武裝暴動時間,是更為難得一遇的“雙甲子”。
張角和他的謀士們在選擇暴動日期上可謂動了一番腦筋。但問題是,确定這一時間是在光和六年底,離“雙甲子”還有三四個月,從籌備起義的角度說,時間充裕一點,可以把準備工作做得更細些。但從另外一個方面看,這又是致命的,那就是夜長夢多。
暴動是策劃實施一場規模盛大的集體活動,參與的人數衆多,涉及的區域廣泛,在沒有現代化通訊工具的情況下,溝通信息、協調各部行動、保證命令暢通已經十分困難,更困難的是,做這些工作的時候還必須完全保密。
像起義時間這種極端機密的事情,起義總指揮部竟然在幾個月之前就已下達到基層,甚至還發布了起義口號:“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就在前線總指揮馬元義帶着他的骨幹分子潛入京師後不久,洛陽城裏的小孩甚至把這幾句話編成了歌謠到處傳唱。朝廷各辦事機構的大門上,也時不時地出現用白土書寫的“甲子”二字。
事後來看,這可是一大敗筆。
起義軍內部果然出現了叛徒,只要學過中學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這個人,他叫唐周,濟南國人,他是張角的弟子之一,在起義軍內部屬于高級幹部。光和七年(184年)剛過了年,朝廷便接到唐周的密報,整個起義計劃暴露。
有人遺憾地說,黃巾大起義都毀在這個唐周的身上,如果不出這個叛徒,起義的結果就會兩樣。問題是,如果沒有唐周,張角、馬元義他們就一定能于當年的三月五日這一天順利發動起義嗎?
其實基本上不可能。不是因為東漢王朝強大到不能推翻,事實上東漢王朝已經很虛弱,無論政治上還是軍事上,只要組織得當,推翻起來應該不難。問題在于,起義軍不可能把保密工作做得那麽好,保證在長達三個月時間裏不出現第二個、第三個唐周。
由于唐周的告密,劉宏不敢再大意,他立即下令對馬元義等骨幹分子實施秘密抓捕。馬元義被抓,處以車裂之刑。
然後靈帝清查太平道的徒衆,他以通令(周章)的形式下達三公府、司隸校尉,派鈎盾令周斌總負責,清查在宮省直衛、朝廷各辦事機構以及百姓中的太平道信徒,很快查出來一千多人,全部予以誅殺。根據偵察到的線索,靈帝要求各州郡同時搜捕張角等太平道骨幹人員。
起義軍只好倉促起事,正史記載他們“殺人以祠天”。之後,張角稱“天公将軍”、張寶稱“地公将軍”、張梁稱“人公将軍”、在冀州正式起義。起義軍個個頭戴黃巾,因此被稱為“黃巾軍”,但在官府下達的通緝文書裏,一律稱他們為“蛾賊”。
雖然動作倉促了點,但一開始仍然很順手。黃巾軍所過郡縣,“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
東漢的地方政權如此不堪一擊,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是起義軍深得民心,有長期準備,來勢很猛,另一方面是東漢國家軍制特點造成的。
東漢沿襲了西漢的軍制架構,全國主要軍力集中于南軍、北軍兩大塊。南軍負責四方征戰,是野戰部隊,北軍即前面介紹過的北軍五營,駐紮在洛陽附近,負責京師的防衛。北軍之外,天子還有一部分近衛部隊,如衛尉、虎贲、羽林等,性質與北軍差不多。
這些都是中央軍。除此之外,東漢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地方部隊,即州郡不能典兵。郡、縣以下雖設有都尉等職,如曹操曾擔任過的洛陽北部尉,但他們的職責是維護社會治安,屬于警察部隊,而非正規軍。
國家遇有事情怎麽辦?這項任務基本上都交給了南軍。南軍是一支常備部隊,也是精銳之師,但不幸的事,此時此刻,這支武裝力量卻指望不上。
數十年來,南軍主力一直奮戰在西部和北部前線。在西部,帝國陷入與羌人作戰的泥潭,進不可全勝,退不得脫身。在北部,雖然匈奴人暫時消停下來,但新崛起的烏桓和鮮卑,跟當年的匈奴人一樣強悍不遜,你來我往陷入膠着狀态。
帝國劃出了幾大邊防區,設立護羌校尉、護匈奴校尉、護烏桓校尉等職,負責邊境作戰,所使用的主力,正是南軍。也就是說,此刻帝國所能依仗的主力部隊正擔負着保衛邊疆的重任,輕易調離不得。
面對已經軍事化組織起來,雖然打仗不一定在行、但打起來不要命的黃巾軍,州、郡、縣統屬的治安部隊不堪一擊。黃巾軍節節勝利,京師洛陽震動。
朝廷一下子慌了神。宦官平時權大勢大,但流血打仗的事從來沒想過,朝官士人文的在行,與宦官鬥、跟皇帝吵都不怕,但打仗從來沒有弄過,面對四面開花的局面,一下子也傻了眼。看來看去,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一個人身上,仿佛只有他才能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于将頹。這個人曾經是曹操的同事,也是議郎,名叫皇甫嵩,是名将皇甫規的侄子。皇甫嵩字義真,安定郡朝那人,他的父親皇甫節是名将皇甫規的兄長,曾擔任過雁門太守。皇甫嵩少年既好詩書,也好弓馬,是一個文武全才,在皇甫規的栽培下仕途比較順利,擔任過一段時間的議郎,目前擔任北地郡太守,此時正好來洛陽出差。
北地郡屬幽州刺史部的邊境地區,在這裏當太守與內地不同,主要職責是配合正規軍對敵作戰。因為有長期邊防作戰的經驗,又身為名将之後,大家都想知道他對當前局勢的看法。在靈帝主持的禦前會議上,皇甫嵩列席會議,他不負重望,提出了化解時局危機的具體方案。這個方案包括以下內容:
下诏各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組織地方武裝,修築防禦工事,制造軍器。其中,在洛陽周邊地區各個方向重點構築八個戰略據點,即洛陽八關,分別是函谷關、大谷關、廣城關、伊闕關、轅關、旋門關、孟津關、小平津關,每關設一個都尉,負責軍事。
對現有的軍事力量進行整合,主要是北軍及天子的禦林軍,分路讨擊冀州刺史部(中心是邺縣一帶)和穎川郡的黃巾主力。同時他建議将天子西園小金庫裏的錢和西園的廄馬拿出來,以充實軍力。
還有,就是推行政治改革,解除黨禁,重新任用黨人。
對于前兩項,靈帝都認可,目前看來也只能這麽做了。靈帝是少有的比較貪財的皇帝,自己建有小金庫,屬于個人財産,積累了大量錢財,現在國庫空虛,籌備常規軍費已經很吃力,根本拿不出來錢,只得由皇帝出血了。
但對于最後一條,即解除黨禁一事,靈帝仍然猶豫。實行黨禁是他做出的政治決定,解除黨禁等于推翻自己以前的主張,面子上下不來,而且會不會因此造成混亂?
從內心來說,靈帝比較讨厭黨人,這些人一天到晚吵吵鬧鬧,不是對他進行批評,就是跟宦官找茬。與宦官比起來,靈帝更喜歡宦官。
而且,讓靈帝感到困惑的是,當前要解決的是黃巾軍,與解除黨禁有多大關系呢?但是很快靈帝的思想工作就被做通了,一個叫呂強的宦官,只用一句話就讓靈帝堅定了決心。他說:“聽說黃巾軍也在大量招募人才,如果我們不赦免黨人,這些家夥難免會跑到黃巾軍那裏去。”
這一下靈帝總算是聽明白了,立即下诏赦免黨人。
呂強字漢盛,司隸校尉部河南尹成縣人。從小即為宦官,擔任過小黃門、中常侍,在宦官中是少有的正直之人,《後漢書》裏有他的傳,稱他“清忠奉公”。
于是靈帝下令組建讨伐部隊。在這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曹操的命運也将發生又一次改變。
【三、靈帝的讨伐兵團】
光和七年(184年)三月,靈帝下令調整帝國的軍事領導機構,升河南尹何進為大将軍,坐鎮洛陽,指揮全國武裝力量,總司令部設在洛陽城內的都亭。這是繼梁冀、窦武之後,再次設立大将軍,并且繼續由外戚擔任。
同時組建讨伐兵團,由何進兼任總司令。該兵團包括三支人馬,約五萬人左右。一支由新任命的北中郎将盧植統帥,讨伐冀州的張角,另外兩支分別由剛任命的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統帥,讨伐豫州刺史部颍川郡的黃巾軍。
東漢将軍的名號比較多,也比較亂,不弄清這些就會影響到對史料的理解。有一個笨辦法不一定準确,但卻比較簡單省事。
最高一級的是大将軍,可以理解為上将;其次是車騎将軍、骠騎将軍、衛将軍以及所謂的四方、四征、四鎮将軍,四方是前将軍、後将軍、左将軍、右将軍,四征是征西将軍、征東将軍、征南将軍、征北将軍,四鎮是鎮西将軍、鎮東将軍、鎮南将軍、鎮北将軍,這些都是沿襲前代的固定稱號,可以理解為中将;再下來,就是偏将軍、裨将軍以及雜號将軍,雜號将軍即臨時起個名號,也稱将軍,如奮武将軍、讨虜将軍、揚威将軍等,名目很多,均因事而設,事罷就撤,這些都姑且理解為少将。
這樣理解未必準确。大将軍的地位高于三公,車騎将軍、骠騎将軍等與三公同列,似乎把他們理解為元帥更妥當。但是,為了便于閱讀和理解,上面的理解大體上還是可以的。中郎将就容易理解了,可以看做是準将,介于将軍和校、尉之間。以後大家再遇到的時候可以先這麽理解,至于東漢軍隊的編制,後面再作介紹。
在何進被任命為大将軍前,帝國軍隊擁有高級軍銜的将軍還比較少,地位最高的名将“涼州三明”(即段、張奂、皇甫規)除投靠了宦官、又在宦官內鬥中被殺的段外,張奂、皇甫規此時分別承擔着西線和北線的防衛作戰任務,他們的職務是護匈奴中郎将、護羌校尉,大體上是個準将或大校。再往上的軍銜,這時候基本上都空缺。
所以,靈帝一口氣任命了一個上将、三個準将,已經是很破例了。
何進、皇甫嵩的情況前面已有提及,現在看看另外兩個人的情況。
盧植字子幹,幽州刺史部涿郡涿縣人。他有幾個明顯特征,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八尺二寸約合現在一米九三。有資料顯示,當時的人平均身高普遍低于現在,所以盧植往人堆裏一紮,絕對是大高個,東漢要是組建CBA聯賽,盧植即使打不了中鋒至少也能打個後衛什麽的。他聲音洪亮,适合做配音演員或者演舞臺劇。《後漢書》還說他酒量特別好,一次能喝一石酒(約合一斤裝的二鍋頭六十多瓶,這種酒量實在不好理解)。
但盧植沒有向體育界、娛樂界發展的打算,他的志向是做學問。他和日後的學術泰鬥鄭玄一道拜大名士馬融為師。這個馬融,除了是個大學士,還是外戚,他的一個表姨當過皇後,所以被稱為“外戚豪家”。馬大師有一個愛好,喜歡一邊研修學問一邊請些女演員表演歌舞(列女倡歌舞于前)。馬大師性情超脫,他做這些事從來不避學生,講課講累了就把私人歌舞樂隊叫到講室裏來消遣,別的學生都争着看,可盧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眼珠都不帶轉的。盧植謝絕了馬老師的挽留,從馬氏民辦學院畢業回到家鄉涿縣當起了教書先生。他在教育方面挺有成就,學生裏一口氣出了兩個名人:一個叫公孫瓒,一個叫劉備。
眼看就要混成一代名師了,但盧植心裏很不滿足,因為他“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靈帝熹平四年(175年),揚州刺史部九江郡的蠻人造反,盧植因為“才兼文武”而被公府選中,由布衣直接拜為品秩二千石的九江郡太守。盧植還真有兩下子,到任後三下五除二就把蠻人制服了,名聲大震。
但在此時,他卻以生病為由提出辭官。後來,朝廷多次征召,盧植實在沒有辦法,才來到洛陽,不過提出請求說只想擔任輕閑自在一點的官職,于是被任命為議郎,與谏議大夫馬日、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人志趣相投,整天待在國家圖書館(東觀)裏校書,補撰《續漢記》。在靈帝眼裏,盧植是難得的軍事人才,從事文化工作是極大的浪費。黃巾起義爆發後,便拜他為北中郎将,任命護烏桓中郎将宗員為他的副手,帶領一部分由北軍五營中抽調的兵士和臨時征募的人馬,讨伐冀州的張角。為了便于指揮,靈帝下诏盧植“持節”,即帶着天子特頒的信物,形同天子親自出征。
再說說朱俊。
在《後漢書》裏與皇甫嵩合為一傳的人就是朱俊,說明了他的名氣和歷史地位。
朱俊字公偉,揚州刺史部會稽郡上虞縣人,家境較苦,小的時候父親死了,母親以販賣一種叫缯的紡織品為業。朱俊年輕時擔任過縣政府的文書管理員(書佐),“好義輕財,鄉闾敬之”。後來發生過一件事,讓大家對他刮目相看。
朱俊有個朋友叫周規,“為公府所辟”,也就是在中央機關找到一份固定工作,這是一件讓人羨慕的事。但是,他卻幹了件蠢事,差點去不成。
周規想現在要到京師任職了,得弄點路費、置裝費,不能太寒酸,于是偷偷挪用了“庫錢百萬”。這當然是一筆大數目,部長級官員月薪不過一到兩萬錢,百萬錢虧得周規也敢挪用。周規原來的想法是,反正這一去未必再回來了,就是以後被發現也奈何不了自己。但是,管後倉的人偏巧發現了,要周規歸還挪用的錢,可這筆巨款已經讓周規花掉了。
這個時候,朱俊幫了他。朱俊幹了回小偷的勾當,偷的對象是自己的母親。他們家雖然也不富,但朱俊母親搞的是缯帛貿易,他把母親的貨物偷偷賣了,拿錢為周規解困。而朱俊的母親,無奈失業了。
母親恚責朱俊,朱俊說:“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
朱俊的回答耐人尋味,他沒有說為朋友兩肋插刀、人要講義氣、不要把錢看得太重這些空話,而是說現在看是受到小損失,将來沒準會因此得到更大的回報。說明朱俊對未來有遠大的規劃,也有深謀遠慮。
他很快得到了回報。這時候上虞縣縣長叫度尚,這是一個老黨人,以後群雄混戰的時候他還會出現。度尚聽說朱俊的事跡後連連稱奇,把他推薦給會稽郡太守韋毅,再後來尹端接任韋毅,任命朱俊為郡政府辦公室主任(主簿)。
熹平二年(173年),會稽郡許昭起義,尹端讨伐不利,被州刺史糾舉,經過有關部門審理,處以棄市的刑罰。作為尹端的辦公室主任,朱俊又幹了件讓人稱奇的事,他帶着一筆巨款到洛陽,拉關系、走後門,上下打點,費盡周折,把老領導的死罪改判為勞動改造(輸作左校)。尹端保住一條命,但并不知道是什麽原因,朱俊也從不向別人提起。
後來交州刺史部梁龍造反,沒有人能平息,光和元年(178年),派朱俊為交州刺史參與平亂。朱俊到任後,“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朱俊被封為都亭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官拜谏議大夫。皇甫嵩是名将之後,有邊疆地區與少數民族作戰經驗,盧植、朱俊分別在地方上平定過農民起義。從這三個人選的确定上,可以看出靈帝這回是真急了。以往出風頭的事都被宦官壟斷,就在數年前,宦官們還謀劃過征鮮卑的軍事行動。但那是形象工程,要玩真的,不能指望宦官,還要靠人才。
三路大軍出發後,坐鎮京師的最高軍事統帥大将軍何進也沒有閑着,他開始組織招募戰略預備隊,并很快編成了一支騎兵部隊。
而何進對這支騎兵部隊指揮官的任命,讓很多人大吃一驚。
【四、也是一個兵】
這支被賦予厚望的戰略預備隊共有五千人,其指揮官是騎都尉,任命公布後,雖然名字大家都知道,但很出乎意料。
新的騎都尉是議郎曹操。這一年他虛歲整三十歲。
都尉次于中郎将,中郎将次于各種名號的将軍。如果把中郎将理解為準将,都尉就是校級軍官。
東漢叫都尉、校尉的實在很多,前面已經出現過的有北軍五營的校尉,還有司隸校尉、城門校尉、洛陽北部尉等。這些職務,除了司隸校尉更偏向于行政職務外,其它的都可以視為軍隊或警察部隊裏的校官或尉官。
具體說來還有些不同,縣下面的都尉,如曹操曾經擔任過的洛陽北部尉,估計應該是個上尉;而北軍五營的校尉,則相當于上校。現在曹操将要履職的騎都尉,不是常規編制序列,下面有大約五千人,可以理解為大校。這個職務如果再上一級,就該是中郎将或雜號将軍了。所以,曹操擔任的這個新職務,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中央直屬騎兵獨立師大校師長。
說到這裏,必須談談東漢的軍制問題了。
讀漢魏歷史,無論正史還是演義,往往感到其長于敘事或議論,而短于對歷史細節的關照。比如,歷史人物的出生時間,除了零星地夾雜在敘事之中外,大部分只能靠前後推理,實在推不出來的,後面寫史的人只好用“?”來代替。所以,翻開歷史人物傳記,到處是這個符號。
歷史細節的不足也表現在軍隊編制問題上,無論正史還是野史,要麽簡單化,要麽模糊化,一般只說某某人帶着幾百、幾千或幾萬人到某某地方跟某某打,而那個某某又是帶着多少多少人,很少談及雙方部隊的內部組織結構。軍職裏除了上面講過的各類名號繁多的将軍外,其下的各級建制要麽不詳細,要麽很混亂,讓人讀得一頭霧水。
其實,東漢的軍隊編制是很系統化、規範化的。其基本單位是軍、營、部、曲、屯、隊、什、伍,類似于現代軍隊的軍、師、旅、團、營、連、排、班,但編伍方法和人數略有不同。
從下往上說:伍即五個人的戰鬥小組,是最基層的戰鬥單位,主官為伍長;二五為一什,主官為什長;二什為一隊,主官為隊率;二隊為一屯,主官為屯長;五屯為一曲,主官為軍侯。這樣算下來,每曲的人數是五百人。
再往上,二曲編為一部,主官為軍司馬或別部司馬(假司馬、軍假司馬為其副職),是一千人;五隊編為一營,是五千人,主官為都尉或校尉;二營為一軍,人數為一萬人,主官一般為校尉或各類将軍。
這種編制方法,從秦到魏大體上沒有變化,不過寫史的往往是文人,對軍事要麽不重視要麽不在行,于是留下來的史料中,一涉及這些方面讀起來就比較費勁。
比如,曹操的這個新職務騎都尉,手下是五千人,如果按照正規的編制,應該是一營(不是現在的營),營是軍以下、部以上的編制,這個營下面應該有五個部,約相當于五個團。
曹操自光和二年(179年)擔任議郎到現在已經六年了。這段時間,除了偶爾上書之外,曹操沒有更多的活動。後來,曹操連上書的事也很少做了,從來沒有涉足軍事的曹操,怎以會突然被委以如此重任呢?
對曹操而言,這的确是一個重要的人生轉折。但是,所有的史料都沒有記錄或探究過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只好猜測。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曹操喜歡軍事,并且有了點名聲。曹操不好讀死書,好讀雜書,尤其是法家、兵家的著作。近幾年,他酷愛一本叫《孫子兵法》的書,而且學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