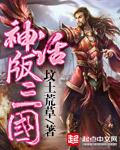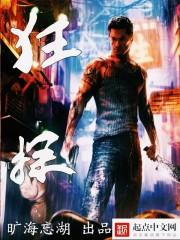第4章 目标,(1)
〔作為太學生他不安心學業,心思都用在交友上,他頻繁地拜訪各地名士,希望得到他們的好評。剛剛走上工作崗位,他就以令人吃驚的方式挑戰了最有權勢的那些人,在清濁分明的社會裏,青年曹操開始了什麽樣的政治謀劃?〕
【一、亂世激流】
在曹操十三歲的時候,三十六歲的漢桓帝劉志駕崩了,這一年距他親自指揮誅殺梁冀一族,奪回政權已經八年了。
作為一個忍受十多年的壓制和磨砺的有志青年,一個剛剛經歷了一場生死較量并且憑借自己的果敢、智慧和領導才能取得最終勝利的年輕天子,開始的時候,劉志也想有一番作為,成為漢武帝、光武帝那樣的一代明君。
劉志經常埋頭于宮裏的國家檔案館——蘭臺,翻出前代君王治理國家留下的檔案資料認真學習。
在誅殺梁冀的那一年秋天,劉志草草處理完梁黨的清查工作,雖然天氣已經很冷,但他還是堅持在年內就開始了全國的巡游計劃,第一站是西京長安。
來不及準備龐大的儀仗,天子的車隊由虎贲和羽林衛士前後護衛着,緩緩離開了洛陽。桓帝下诏,凡是沿路所經過的縣,每人賜粟三斛。漢代一斛為十鬥,一鬥粟約相當于今天的十三點五斤,一斛即一百三十五斤,三斛超過四百斤,基本上是一個人一年的口糧。
車駕到了關中,桓帝更慷慨,對設有前代陵寝的縣鎮,每人另外多賜兩斛,京兆尹下屬的長安縣,每人更是賜粟十斛。當時,京兆尹的人口超過二十八萬,如果其中僅五分之一生活在長安縣,僅賜粟米一項也能達到天文數字。
桓帝的大手筆來自于他的底氣。出巡之前,廷尉寺、少府寺以及洛陽縣共同奏報說,查抄梁氏家族的財産,變賣後可得數十億錢,有了這筆錢,劉志覺得自己是個闊皇帝。
但是,不好的消息随後傳來,與長安近在咫尺的涼州刺史部所屬的隴西、金城(今甘肅蘭州)一帶,爆發了羌人起義。雖然在東漢一朝,羌人從來沒有消停過,但這次情況有些不同,八個部落同時起事,金城陷入危機。劉志下令調名将段前往鎮壓。
劉志也不敢在長安多呆,車駕匆匆返回洛陽。全國出巡計劃僅進行了一站便無果而返,劉志十分不悅。
更大的苦惱随即而來,段在那邊大搞種族滅絕計劃,軍事上雖然節節勝利,但軍費開支也讓朝廷招架不住。
桓帝也許很快會像他的多位前任一樣明白一個道理,對羌戰争是一個大坑,是把帝國引向崩潰的陷阱。在段後來上給朝廷的一份奏折裏記述了前代對羌作戰的財務支出情況,在永初至永和年間的二十一年裏,共花費三百二十億錢,平均每年超過十五億錢。須知,當時帝國每年的稅收才六十億錢左右,這就意味着在此前二十多年裏,朝廷每年都要拿出四分之一的稅收扔到西羌這個無底洞裏。
段司令打仗有一套,但花起錢來也不含糊,劉志抄梁家的三十多億錢根本不夠花。加上當初梁冀倒臺時桓帝一高興,曾下诏免除天下半年賦稅,西巡長安時又大賞粟米,帝國財政頓時陷入嚴重危機。
延熹四年(161年),財政危機爆發,劉志下诏令公卿以下的公職人員全部減薪,并向王侯借一半的租稅。即使這樣也還不能支撐龐大的戰争費用,第二年甚至連天子的虎贲、羽林衛士也接到了減半俸的命令。
快入冬的時候,虎贲、羽林衛士們都在等着換冬天的軍服,卻接到命令說,凡在營地值勤站崗沒有外出任務的都不換裝(住寺不任事者勿與冬衣)。朝廷裏公卿以下各級公職人員的官服,原本也是朝廷供給,因帝國財政困難,當年的冬衣全部減半供給。
劉志沒有想到,好不容易從梁家人手裏奪回來的天下竟然是這樣的,大司農卿作為財政部門的主管,天天愁眉苦臉,一見着皇帝就訴苦,劉志煩得幹脆不見他。管理皇家財務的少府寺那邊,雖然情況稍好,但也緊緊巴巴,劉志這個皇帝當得有點憋屈,既不能花天酒地,也不能大手大腳。
宦官和朝官士人們還在繼續開打,把劉志夾在中間。好在劉志是一位平衡術大師,也是抹稀泥高手,同時又能裝豬扮虎,他今天哄哄這個,明天吓吓那個,總之讓誰都不能太得勢,又讓他們覺得皇帝始終站在自己這一邊。
“五侯”過于得意時就收拾他們一下,士人風頭起來了就培植新的宦官來壓朝臣。在一系列平衡手段付諸實施以後,他對“梁黨”突然也有了新看法,何不啓用他們,把局面攪得更豐富些?于是,“梁黨”成員陸續被啓用,梁冀伏誅後被免官的胡廣、韓演等人回到了朝廷,胡廣擔任太中大夫,韓演任司隸校尉。
不僅國事衰敗,人事頹唐,連老天爺也跟劉志作對。延熹五年(162年),從正月裏開始,皇宮和多處陵園發生了神秘的連環大火。
先是這一年的正月,南宮一個叫丙署的地方起火。緊接着四月的一天,埋葬着安帝的恭北陵東門起火,大火還沒有滅,位于宮內的虎贲寺掖門也起火。五月,殇帝康陵園寝發生火災。七月,南宮承善門內發生大火。
從正月到七月,共發生了六場大火,這些大火背後有沒有不可告人的陰謀?對此我們不得而知,但多數人已習慣于把這些突發事件與五行、天道、神秘預言聯系在一起,認為這些事件不是人為而是天意。
這還不算,四月裏洛陽發生了地震,雖然震級不大,沒有造成嚴重破壞,但與那些神秘的大火聯系在一起,就更加令人惶惶不安了。
還是四月,一匹驚馬和一頭從禦苑中跑出來的大象居然闖進了皇宮,這兩個家夥在宮內橫沖直撞,引發了更大的不安。在五行學家們看來,失控的馬預示着“馬禍”,是政治衰敗的表現。其實,這是一種附會,起碼這一次不是上天的預言,而是一種正常的自然現象。聯系到洛陽發生的地震,這次驚馬和驚象事件很可能是地震的前兆。
後來又發生了更令人恐慌的事,延熹七年(164年)的一天,在德陽殿的禦座上竟發現了一條大蛇。蛇是有鱗甲的動物,五行學家認為蛇預示了甲兵之災。
劉志是東漢諸帝中最信五行學說和神秘預言的一個,這些事接連發生,讓他心情沉重。更讓他感到惡心的是,在野王山上發現了死龍。
延熹八年後,各種靈異現象發生的頻率更高,不斷出現神秘大火,一會兒這裏地震,一會兒那邊的河水原來清的突然變渾,原來渾的突然變清。
還有一次,是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洛陽的居民突然發現夜空中有一團火光在飄動,看到的人無不感到恐懼。
如果是現在,這一現象将成為UFO愛好者探究的對象,但在那時幾乎所有的人都相信這件事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上天在表達某種感受。
桓帝被這些事搞得很疲憊,中興之事早被置于腦後,現在桓帝想,只要能平平安安地過好每一天就謝天謝地了。
這就是劉志最後的日子,他才三十多歲,享受着人間最好的生活和醫療條件,享受着最高的權力,但他的生命活力還比不過一個農夫山民,他被周圍的一切折磨得無比虛弱。
他終于死了,死的時候沒有留下任何政治遺言,沒有留下愛和恨。更要命的是:沒有給帝國留下一個小太子。
桓帝劉志駕崩于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天,以太尉陳蕃為首的內外朝官員一致尊皇後窦妙為皇太後“臨朝”,主持帝國的工作。
歷史似乎正在重演:先皇帝駕崩,皇後升格為太後,臨朝,醞釀新皇帝人選,太後和外戚總攬朝政。
程序确實如此,但不同的是,這次主角換了,太後和外戚不姓梁而姓窦。
在太尉陳蕃和皇後的老父窦武一手策劃下,河間王劉開的曾孫、解渎亭侯劉宏登上皇位,這就是靈帝。劉宏是個亭侯,比劉志的縣侯矮了一級;劉宏本年十二歲,比劉志當年小了三歲。陳蕃和窦武聯手之後,勢力很強大,朝野上下無不對他們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一鼓作氣,鏟除日益不得人心的宦官集團。但是,在這一輪拼死較量中,宦官們再次占得上風,陳蕃、窦武被殺,以曹節、王甫、侯覽、張讓為代表的新一代宦官重新把持了朝政。
大約在劉宏登基前後,曹嵩重新回到了洛陽,随後目睹了陳蕃、窦武被宦官誅殺的事件。此時距離他返回谯縣守孝大約已有十年。
這時,朝廷中有大批官員因為受到陳蕃、窦武事件的誅連而被罷官。宦官們不斷以靈帝的名義發布新的任命诏書,當然大部分都是他們的心腹和親屬,同時,還有胡廣、橋玄這樣政治上相對溫和的士人。曹嵩就是在這個時候被任命為大司農卿的,這個任命遠遠超出了曹嵩的預期。
曹嵩被宦官陣營重用,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在近年來的多次流血事變中,他都是局外人,與各派沒有瓜葛;二是朝廷官吏在短時間內大量減員,雖然宦官也任用了不少親信作補充,但維護帝國的正常運行更需要一些專業型官員;三是曹嵩是曹騰的養子,盡管大長秋已去世多年,現在的宦官大多與大長秋沒有多少私人來往,但作為前輩,曹騰的威名仍在。
大司農卿是九卿之一,正部級官員,負責帝國的經濟工作,農業、水利、倉儲、手工業、商業流通都管,同時還是帝國的財政部和稅務總局,除皇室之外的財政支出都由大司農卿來調配。從靈帝永康二年(168年)開始,曹嵩在這個職位上供職多年。
【二、不安分的太學生】
熹平元年(172年),曹操即将年滿十八歲,曹嵩決定讓他到洛陽來,進太學讀書。于是,曹操第一次遠離故鄉谯縣,來到了京師洛陽。
作為帝國的最高學府,同時也是各級公職人員的培養基地,太學是所有讀書人心中向往的地方。前朝初建太學時,規模僅五十人,後來逐漸擴大到三千人,王莽時更是擴大到上萬人。太學歸九卿之一的太常卿管轄,太學的老師稱為博士,太學的校長稱為博士祭酒。“祭酒”就是在社交活動中擔當首席的那個人,如“軍師祭酒”,就是首席軍師,也就是參謀長。
太學招生實行推薦、考試加保送的辦法。地方上以郡為單位可以推薦本地優秀學子入學,有固定的名額。此外,在當時組織的一種明經考試中,凡取得優異成績的,也可以入太學學習。保送的對象是公卿官員之子,品秩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員,都可以送一名子弟到太學學習。曹操入太學,走的就是這條路。
從熹平元年(172年)到熹平三年(174年),曹操一直在太學學習。這裏的教育完全按照儒家經學标準模式進行,重點講授五經,又按五經家法的不同,分別設立不同的專修方向,類似于不同的系。
這些系不教別的,教的都是經學,太學其實就是經學院。
但曹操對這些都不感興趣,他是一個偏科生。在校期間,他的興趣一是博覽雜書,另一個就是廣交朋友。
這個高幹子弟、億萬富翁家的長子、從沛國谯縣來的小個子青年,以他的爽朗、率直、慷慨和好交往贏得不少同學的好感,很快成為太學裏的活躍分子。
這些同學有依靠家庭背景入學的,也有不少是全國各地推薦來的優秀青年,能跻身太學,個個都不簡單。
這些人帶來了各地的新聞,有奇談怪事、風土人情,也有山川風物、歷史傳說,曹操最喜歡跟大家聊這些話題。
關于曹操的太學生活,史料實在太匮乏,但從零星的記述中,可以推測曹操在此期間可能接觸過下面這些人:
王俊(也作王隽),字子文,汝南郡人,與曹操關系最好,後來,王俊避亂到武陵郡,曹操征劉表時他剛好去世。曹操曾經親自到河邊祭奠他。
周颀、周昂,來自于會籍郡的周氏家族,這個家族在揚州刺史部有一定勢力。多年以後,他們在關鍵時刻曾支持過曹操。
劉勳,字子臺,琅邪郡人,後來做過沛國建平縣長、揚州剌史部廬江郡太守等,最後歸附曹操。
許攸,字子遠,南陽郡人,也是一個活躍分子,交際很廣,後來與袁氏兄弟關系尤其密切,官渡大戰時從袁紹陣營投奔曹操。
張邈,字孟卓,東平國壽張縣人,家境富裕,年齡稍大,是一個俠士,一邊上學一邊交結各路英豪,後來與袁紹、曹操的關系均很密切。
還有一個人,曹操總想結交他,但沒有成功。這個人叫宗世林,南陽郡人,是太學裏的學生明星,曹操主動找他想交朋友,但他卻對這個宦官養子家的後人不感冒。
在一次聚會上,曹操和宗世林都在,曹操一直想跟宗世林說話,但沒有機會。後來宗世林起身離席,估計是上洗手間,曹操抓住機會跟上去,拉住宗世林的手,想與他交往。但宗世林一點情面都不留,表示拒絕。
這件事在曹操的心裏留下了傷害。越是心裏自卑的人,越渴望別人的尊重。他對此事一直耿耿于懷。後來曹操當了司空,讓人把宗世林找來,接到許縣。
曹操說:“這一回可以交個朋友了吧?”
宗世林回答:“松柏之志猶存。”
這件事記錄在《世說新語》裏,它說明,太學讀書期間的曹操,多麽渴望交結更多的人,得到大家的認可。
這是一個輿論可以左右一切的年代,就連炙手可熱的宦官們,有時也不得不向輿論低頭。
曹騰的生前好友橋玄此時擔任司空一職,是外朝的領袖之一。因為祖上的關系,曹操到橋前輩家去的比較多,橋玄對這個年輕人格外器重。
橋玄字公祖(不是那個大喬、小玄的父親喬玄),是梁國睢陽縣人,他是從縣政府科長(功曹)一路幹上來的實務型官員,一生廉潔自守。
橋玄善于評點人物,在清議界擁有一定聲望。橋玄第一次見到曹操,就覺得這個青年很不一般,他對曹操說:“天下将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意思是:現在天下将要大亂,不是經邦濟世的人才是不可能使天下安定下來的,能夠安定天下的,大概就是你了。
橋玄還說:“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托。”意思是:我見過的天下名士多了,沒有一個像你這樣的,你要好好努力。我已經老了,願意把妻子兒女托付給你。
這是極高的評價。顯然一個六七十歲的大名士兼朝臣領袖不需要對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年輕人表示恭維,橋玄的确看出來曹操身上的與衆不同之處,他對時局的判斷,以及對曹操未來發展的判斷,都是完全正确的,這說明橋玄作為清議界的權威之一,不是徒有虛名。當時還有一個名士特別賞識曹操,也願意在死後“以妻子兒女相托”,這個人是黨人領袖李膺的兒子李瓒。他對曹操十分推崇,經常向別人推薦他。
李瓒臨死時,對兒子李宣等人說:“國家即将大亂,天下英雄沒有一個能超過曹操的。張邈雖是我的好友,袁紹雖是你們的親戚,但你們也不要投靠他們,你們一定要去投靠曹操。”
獲得了兩個重量級人物的推介,曹操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橋玄認為還不夠,他建議曹操應當找清議界最負盛名的汝南許氏兄弟,通過“月旦評”這個平臺進一步擴大知名度,橋玄為此還給許氏兄弟寫了一封推薦信。
汝南郡有一對堂兄弟,名叫許靖和許劭。二許憑借識人之術,在家鄉清河的小島上開辦了一個講壇,每月初一命題清議,評論鄉黨,褒貶時政,不虛美,不隐惡,不中傷,辯人之好壞,分忠奸善惡,或在朝或在野,都在品評之列,凡得好評之人,無不名聲大振。
曹操懷揣橋玄寫的推薦信興沖沖跑到清河島,卻遭許氏兄弟冷遇。二許對于這個宦官後人一開始不願意做出評論,後來經不起曹操的死磨爛纏,加上橋玄的面子,許劭最後還是送給曹操兩句很有名的話:“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
對于這個評價,曹操相當滿意,這趟汝南郡之行沒有白跑。
此外,曹操還得到了名士何的高度評價。何很有名氣,與李膺、範滂等黨人交往很多,他是一個俠士,喜歡交結天下英雄,善于做一些幕後策劃工作,日後成為袁紹的得力助手,是袁紹秘密組織“奔走之友”聯誼會的骨幹成員。
何見到曹操,交談之下也給予了很高評價:“漢家就要滅亡,能夠安定天下的,必定是這個人了。”
太學期間的生活是忙碌的,時間過得很快,一晃兩年過去了。舉行完秋射大典,曹操這一批太學生就要畢業了。
【三、成為政壇新銳】
畢業的太學生,一般由國家負責分配工作,根據成績随才而用。
各郡來的貧寒子弟學業期滿後很多都要返回鄉裏從事教學工作,或者在地方政府裏被征辟為吏,慢慢走上仕途,也可通過舉孝廉察舉等方式進入官員行列。
公卿子弟則有一條更便捷的通道,他們可以直接被征為郎,即宮中或朝廷各機構裏的實習生,根據實習情況再由朝廷正式分配到政府部門工作。
曹操在二十歲成人冠禮之後,在家鄉沛國被舉為孝廉。
孝和廉是漢朝選拔官吏的兩個科目,孝指孝子,漢朝以孝治國,很看重一個人在這方面的品行;廉即廉潔之士,有清廉的操守。二者合稱即孝廉。
除了從太學畢業進入仕途之外,被地方推舉為孝廉也是一條重要的入仕方法。其名額實在有限,東漢規定以郡和國為單位,二十萬人口以上的每年只能推薦一個人為孝廉,二十萬人口以下的,每兩年推薦一人。
東漢不到一百一十個郡國,按照這個标準,每年能成為孝廉的只有幾十人。這些人跟太學生一樣,先被授為郎官,在天子身邊或朝廷其它部門實習一段時間,然後可以到地方政府任職,也可以在中央政府任職。
曹操被推舉為孝廉,其家庭背景無疑占有重要分量,沒有在朝中身居九卿要職的父親,曹操被推舉為孝廉的可能性基本上沒有。不是他不夠優秀,而是這種二十萬裏挑一的選舉,跟買彩票中大獎差不多,實力不重要,重要的是運氣。
被舉為孝廉後,按慣例曹操被聘為郎官,即朝廷的實習生,這段時間主要是熟悉朝廷行政運作程序和禮儀,等待正式分配工作。
郎官轉為正式官吏,一般品秩在四百石到六百石之間,其中擔任縣令或縣長的最多。郎官實習快要結束時,由所在的實習部門出具個人鑒定,然後由尚書臺統一安排任職。
這時,洛陽令司馬防升為河南尹,曹操特別渴望能得到洛陽令這一職務。洛陽令雖然是縣令一級,但卻是其他任何縣級行政長官無法比拟的,在帝國權力機構中占據重要位置。洛陽令的品秩也比一般縣令要高,為一千石,而其他縣令僅為六百石,縣長為四百石。縣令和縣長都是縣一級的行政長官,所在縣超過一萬戶的稱為縣令,不足一萬戶的稱為縣長。
要得到洛陽令,有兩個人很關鍵,一個是原任洛陽令、現任洛陽令的上司河南尹司馬防,另一個是主管二千石以下官吏選任的朝廷秘書局人事處處長(尚書臺選部尚書)梁鹄。司馬防即司馬懿的父親,是司隸校尉部河內郡溫縣人,也是士族大家出身。他不怎麽好說話,也許看不起曹操的出身,也許聽說曹操學習成績并不怎麽樣,總之不願意推薦曹操為洛陽令。但礙于曹家的影響力,勉強推薦曹操為洛陽令下屬的洛陽北部尉,品秩四百石。
就這樣,曹操沒有得到洛陽令一職,被任命為低一級的洛陽北部尉,歸洛陽令管轄。
一般的縣,縣令或縣長之下設有都尉一職,負責本地的治安,相當于公安局局長。洛陽人口衆多,地位重要,在東、西、南、北各設了一個都尉。洛陽北部尉,就是洛陽北部地區公安局局長,拿易中天先生的話說,是個副縣級。
曹操對這項任命相當不滿,多年以後,曹操再見到司馬防時,他已經是魏王了,司馬防的兒子司馬懿、司馬朗都在曹操手下做官。曹操有揮之不去的懷舊情結,這回又像對待宗世林那樣,讓人把老上司接來設宴款待。曹操說:“如果換作現在,你還推薦我做洛陽北部尉嗎?”司馬防回答:“當初舉薦大王時,大王您只适合為尉呀。”
曹操于是大笑。
曹操雖然只得到一個副縣級公安局長的職務,但他沒有氣餒,而是努力在這個崗位上幹出點成績來,以期引起外界的注意。
他一到任,就把官署的四門修繕一新,還做了不少五色大棒,懸挂在各門口,規定凡違反治安條例的,無論平民還是權貴,一律五色棒伺候。
前面說過,東漢的行政執法體系比較亂,尤其是執法環節,伸縮的餘地很大,一個副縣級的公安局局長,手裏也握有生殺大權。
曹操的這番做派,分明是要引起各方面的關注。當然,他也有另外的選擇,比如在這個崗位上慢慢幹下去,通過勤懇工作,搞好與轄區內群衆的關系,做些好人好事,慢慢提高聲譽,得到上面的認可,等待提升的機會。
這需要忍耐,也需要時間。但曹操需要的是盡快向世人證明,自己是治世的能臣,也是亂世中的英雄,他渴望建立功業,不是在漫長的未來,而是在眼前。
偏巧,這個機會就讓曹操等來了。在一次夜間巡查中,曹操帶人遇到了一群不速之客,對方違反夜間禁行的命令讓曹操抓個正着,領頭的人是當朝紅得發紫的大宦官蹇碩的叔父。
曹操不管對方是誰,立即下令大棒子伺候,并且悄悄囑咐手下:盡管往死裏打!一頓暴揍之後,蹇碩的叔父一命嗚呼了。
這是曹操剛上任幾個月時就做出來的驚人之舉。在常人看來,這件事也太生猛了,畢竟對方不是一般人物,結下了如此的深仇大恨,蹇碩能饒得了你嗎?
但是,經過思考和判斷,曹操看到形勢對當權的宦官未必有利,這件事不至于釀成太大的危機,所以值得一試。對于已經親政的靈帝來說,平衡宦官、黨人、外戚的關系本來就已頗費腦筋,此時如果再因為一個宦官叔父而發起報複,則必須考慮事件造成的後果,更何況蹇碩的叔父的确違反了夜間禁行的命令。
曹操甚至想好了,最好因為此事自己落個撤職查辦什麽的,丢掉這個微不足道的四百石小官,收獲的可能會更多。但這件事不聲不響地過去了,從蹇碩那邊沒有傳來一絲要報複的消息,而曹操棒殺權貴的事情卻瞬時在京師傳開了,“京師斂跡,莫敢犯者”。
曹操聲名大振,以前沒有聽說過他的人,這一回也都知道了洛陽城裏有個年輕的曹局長。對于這個結果,曹操心裏相當滿意。
但是,有一個人的看法卻剛好跟他相反。
【四、遭遇短暫挫折】
對曹操棒殺蹇叔行為持完全否定态度的是他的父親曹嵩。對于兒子這次所謂的壯舉,曹嵩只想給予兩個字的評論:幼稚。
在曹嵩看來,即使想表達與宦官陣營的決裂,也斷然不能采用如此簡單粗暴的方法。權勢熏天的蹇碩在一個區區四百石都尉面前丢了面子,他一定會想辦法找回來的。
想到這些,曹嵩覺得很可怕。他一面動用養父留在宮裏的關系,試圖與蹇碩溝通;一面苦思冥想,看有什麽辦法讓曹操脫身。
蹇碩那邊仍然很平靜,既沒有立即展開報複,也沒有想跟曹家化解恩怨的意思。這讓曹嵩心裏更吃不準。
曹操依然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繼續當他的公安局長,而且幹得更帶勁,領着一幫屬下整天抓社會治安,把轄區內治理得井井有條。一些作奸犯科的人,都逃到其他三個區躲起來。久而久之,曹操的名氣更大了。
蹇碩不實施報複計劃,曹操心裏反而有一絲失望。在他的計算中,蹇碩應該惱羞成怒,立即将他免職,投入北寺獄。
如果那樣的話,曹操相信,太學生們會第一個起來營救他,他們會到北宮外集體上書,為他鳴冤。還有士人朝官,知道他與不知道他的,都會蜂起而奏,把他當成威武不屈、剛直不阿的英雄。
這不是曹操的空想,當時有一股直之風非常盛行。所謂直,就是明知不是對手,也要站出來與權貴單挑。因為他們知道,背後有強大的輿論支持,盡管會面臨受迫害的危險,但同時也會獲得巨大的社會聲望,知名度一夜暴升。
有一個例子,很說明當時的這個風尚。主角是著名黨人領袖李固的兒子李燮,李固被梁冀誣殺之後,李燮四處逃亡。後來桓帝殺了梁冀,李固成了與梁氏集團長期作鬥争的英雄,桓帝四處打聽李固後人的消息,終于把李燮找了出來,拜他為議郎。
這個小李跟他父親老李一樣耿直,官雖不大,卻嫉惡如仇,尤其對宦官及其爪牙,小李聲稱見一回打一回。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個叫甄邵的人,這厮品質惡劣,出賣朋友、投靠宦官,最差勁的是一次遇着要升官,不巧他母親死了,按制度來說本人要回家守孝三年,可這樣一來升官的機會就會錯過。
甄邵偷偷把他娘埋在馬棚裏,等拿到委任狀以後才發喪,道德水平差到如此地步。但他投靠宦官,官場上一帆風順,沒有人敢惹。
小李也知道這個人,早就看他不順眼,這回恰巧遇上,怎能放過?他下令讓随從把甄邵的車子推翻,扔到溝裏,上去将其一頓暴揍。打完之後還不解氣,小李找來一個條幅,批了幾個大字:“谄貴賣友,貪官埋母”,挂在甄邵的背上,讓這小子游街出醜。
事情過後,李燮竟然什麽事都沒有,反而名聲更大。
這是因為宦官們權勢雖大但內心很虛,尤其一涉及到民意、輿論,他們更是膽顫心驚,在貌似強大的外表下,他們實則有一顆脆弱不堪的心。
直的人之所以不害怕宦官報複,是因為這件事情已然被他們鬧大。這是全部的要領,一定要鬧大,成為輿論的焦點,這樣結果只有一個:風平浪靜。吃了虧的也不敢立即報複,否則反而成全了鬧事的一方。
所以曹操棒打蹇碩叔父時偷偷告訴手下往死裏打,打而不死,就是沒有鬧大,減弱了事件的影響力,反而對己不利。
蹇碩按兵不動,也許是想發作但卻找不到發洩口。蹇碩或許這樣安慰自己:你狂,讓你狂,你小子等着點,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曹操等不了那麽久,他心裏希望來一場風暴,而他居于風暴的正中心,他要利用這場風暴使自己的人氣進一步飚升。
但依然是什麽事都沒有。到了熹平五年(176年),他任職滿兩年,按照制度有關部門将對他進行述職考核。結果出來了,他居然考核為上等,這意味着他可以升一級。
有關命令随後下達,他被任命為頓丘縣令,品秩提高到六百石。
這個任命有什麽背景我們不得而知,是蹇碩等人的陰謀,還是曹嵩為了使兒子避禍而争取的結果?似乎都有可能。
但這不是曹操希望的結果。可沒有辦法,他必須離開洛陽,告別父親,前往頓丘上任了。
對于這兩年在洛陽的任職經歷,曹操自我評價還不錯,後來常常回憶。有一次征孫權,曹操留下兒子曹植守邺縣,曹植剛好二十三歲,與曹操當時年齡相同。曹操告誡曹植說:“我當年擔任頓丘令的時候,也是二十三歲,回想之前在洛陽的所作所為,至今無悔。”曹操臨終前的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天,他從漢中前線回師路過洛陽,還特意關照有關方面把洛陽北部尉的衙署重新整修一下。
現在,曹縣長要去頓丘上任了。
頓丘縣在兖州刺史部的東郡,離東郡治所濮陽縣很近。比曹操大十歲左右的袁紹,幾年前曾在濮陽擔任過縣長。如今的袁紹,因為母親去世的緣故,正呆在汝南郡的家中守孝。東郡在洛陽的右翼,因為同在黃河沿岸,所以戰略地位非常重要,自古以來多有大的戰事在這裏發生。頓丘縣雖然不大,但因為接近黃河和濮陽,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