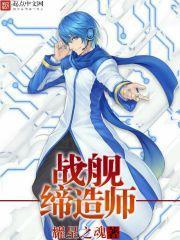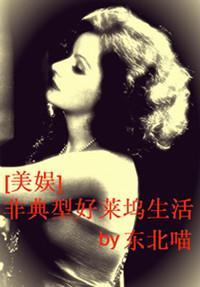第12章 巡鹽禦史有點鹹
“如海,”景隆帝親切地叫着林如海的表字,“你不要緊張,朕召你來,只是問一點意見。”
林如海伏在地上,并不敢擡頭直犯天顏,聽皇帝聲氣平和,知道大約不是十七殿下惹了禍,心裏略平定了些,小心道:“皇上請說,臣知無不言。”
景隆帝絲毫不提方才這東暖閣裏的明槍暗箭,只是說道:“你父親當年也做過巡鹽禦史,你當時雖然年少,但總也有所見聞。朕問你——”他前面的話都說得極為和緩,似閑話家常般,至此突然話音一變,語氣沉斂,顯出帝王的威儀來,“你于鹽務可有心得?”
林如海頓首再拜,道:“回皇上,鹽務這樣大的課題……”
他畢竟是官場上的人。
既然不是十七殿下闖了禍,而太子與五皇子、田大人都在,外面還跪了一個大皇子,此刻皇上又問出了“鹽政”二字——那多半跟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巡鹽禦史貪腐案有關。這樁事情裏,不管哪一方,惹上了都是一個“死”字。
景隆帝卻不容臣子瞻前顧後,道:“你只管說。”雖是笑着,卻是命令。
林如海眼睛一閉,斟酌着道:“回皇上,鹽政雖系稅差,但上關國計,下濟民生,積年以來委曲情弊,難逃皇上洞鑒……”
永嗔這會兒已經站到太子所坐的太師椅旁邊。
景隆帝惱他擅闖,不許太監給他搬座,算是變相的要他“罰站”。
永嗔可絲毫沒有罰站的自覺,一只胳膊抵在太子哥哥腿上,手掌橫伸剛好托住下巴,腦袋微微一偏——這可真是個看“演出”的好姿勢。
聽着林如海條理分明的奏對,永嗔腹中暗笑:平時上課只見林師傅嚴肅正經的一面,課下只見他惜字如金;原來到了緊要關頭,林師傅也能口綻蓮花——這就先給父皇套了個“難逃皇上洞鑒”的高帽。
他看得津津有味,林如海官帽下的額頭卻是出了密密一層冷汗,當着皇帝、太子與五皇子三方,談與國體休戚相關的鹽政,真好似懸崖間走鋼絲,生死一線的事兒。
景隆帝盤腿坐在榻上,聽得入神,最後竟輕輕點了幾下頭。
待林如海講完,景隆帝還未說話,田立義便先笑道:“林大人說的這些問題都是有的,只是所說的解決方案,卻還是急躁了。鹽政乃國之命脈,治大國如烹小鮮,急不得。”
景隆帝笑道:“他說的很好。他不比你,朕只要他管好一方之中的一項事便足夠了。哪裏能要他像你一樣老成謀國呢。朕取的,正是他這樣的銳氣。”
一個“銳氣”可就把所謂的“急躁”當成優點來誇了。
田立義笑道:“到底還是皇上會看人。臣推己及人,反倒是迂腐了。林大人對鹽政的這些見解頗為難得,臣恭賀皇上喜得佳才!”他在權力中心打熬了半輩子的人了,見風使舵是練熟了的本領。
五皇子永澹在一旁殺雞抹脖子地給他遞眼色,田立義只做看不到。
太子永湛仍是低頭吃茶,嘴角微微上翹。
景隆帝哈哈一笑,走下塌來,舒展着手臂。
林如海就見天子穿一雙金黃色的便鞋在眼前踱來踱去,聽話聽音,在景隆帝和田立義的一唱一和中,他隐隐明白了什麽;渾身都因為期待與緊張而緊繃。
“如海,鹽政有如此多的弊端。朕問你,你敢不敢往兩淮走上一遭,做個巡鹽禦史?”
本朝的巡鹽禦史一共才四個人,兩淮、兩浙、長蘆、河東各一人。
其中猶以兩淮為重,一處可抵半個國家。
從翰林院的編修擢升為正三品的巡鹽禦史,這是天大的升遷,大好的前程!
林如海頓首再拜,激動地大聲道:“臣蒙皇上天恩,願往兩淮,理鹽政、報君恩!”
永嗔見此事塵埃已定,在一旁笑嘻嘻接了一句,“赴湯蹈火亦在所不惜。”
景隆帝正走到他旁邊,見他拿戲文裏的話來胡亂接,順腿就給他屁股上輕輕來了一腳,笑罵道:“就你這猕猴會說話。”又道:“你原有這樣好的師傅,偏偏不知用功。以後尋不到好師傅,你且追悔莫及吧。”
永嗔仍是笑嘻嘻的,“父皇手底下人才濟濟,走了林師傅,說不得就來個森師傅。”
“什麽森師傅?”景隆帝皺眉。
“林師傅有倆木頭,就能管兩淮的鹽政;森師傅還多一個木,豈不是要管三淮的鹽政?”永嗔怕再挨一腳,一面跟景隆帝鬥嘴,一面就躲到太子哥哥另一邊去了。
景隆帝被他氣樂了,罵道:“不學無術,偏還要現眼。滾出去吧。”口上這麽說,眼睛裏全是笑意。
永嗔笑道:“兒子聽命。”卻又道:“父皇,兒子還有一事相求。”
林如海仍低着頭,不敢看,耳朵裏聽着,又為這個學生着急。他雖然在上書房也見過十七皇子跟皇上“你來我往”說“胡話”,但到這種程度的,還真是聞所未聞。
“說。”景隆帝言簡意赅。
“兒子昨晚聽母妃說,珍母妃犯了秋咳……”
珍妃原是景隆帝身邊的宮女,是大皇子永清的生母,母以子貴而封妃。
永嗔難得嚴肅地禀了一句,立馬又轉為笑嘻嘻的,道:“外頭秋風賊冷,大哥這也跪了小半個時辰了。父皇您看,兒子滾的時候,是不是叫上大哥一塊滾?”
景隆帝揮揮手,笑罵道:“滾滾滾。你們一大一小,都給朕滾。”
永嗔唱個喏,蹦蹦跳跳地就出去了。
景隆帝臉上笑意淡去,環視着因為永嗔的離開突顯靜默下去的屋子,肅容道:“朕今兒留你們用晚膳,細細把兩淮鹽務捋一遍……”
***&
林府。
“再去查探,到底為了什麽事兒。”賈敏揪着帕子,坐立不安,命那婆子,“怎麽突然就給皇上召見了?接老爺的小厮與車夫也恁的糊塗,連個話都傳不明白!”
賈敏身邊的大丫鬟勸道:“夫人,您且寬寬心。您想,皇上問話,為了什麽豈是尋常人能打聽到的。老爺為官清正,吉人天相,說不得竟是好事呢。”
話是如此,卻如何能真正放心。
賈敏撫着胸口,只覺心慌,臉色白得吓人。
她想派人去娘家問一聲,卻又怕讓賈母也跟着憂心,況且家裏兩個哥哥在朝中也并不得意,哪裏還有什麽門路?正沒主意處,卻見奶娘抱了黛玉過來。
這是賈敏身邊大丫鬟着人去喊來的,好讓賈敏分分心。
賈敏見女兒被抱過來,喜慶的紅襁褓裏半露着一張秀美的小臉,不由自主就伸出手臂來接。
奶娘笑道:“小姐醒了,一雙黑嗔嗔的眼睛只是四處看,奴婢就知道小姐準是在找夫人。”
賈敏看着女兒清亮的雙眸,見女兒一眨不眨地望着她,心底一片柔軟,輕輕晃着懷裏的女兒,道:“雖是你奶着她,我卻是她的親娘,血濃于水,可不是一點也不假?”
她逗着黛玉,把臉貼在女兒的小臉上,低低道:“乖女兒,保佑你爹平平安安回來吧……”
正在賈敏無計可施,百爪撓心之時,卻聽外面丫鬟喜道:“夫人,老爺身邊的福兒回來了!”
賈敏忙道:“快讓他到外間去。”
福兒跪在地上,笑道:“夫人大喜!”
賈敏把黛玉交到奶娘手中,見他神色欣然,心中一松,腿上一軟就坐到了椅子上。她急道:“到底是怎麽回事!”
福兒笑道:“到底是怎麽回事兒,奴才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好事兒。奴才別處也不能去,只能在翰林院裏等消息,到了這個時辰,翰林院裏衆大人都走了。奴才接了家裏傳來的信,知道夫人心焦,卻也沒處探問消息,正是急的要抹脖子的時候……”
丫鬟叱道:“誰管你抹不抹脖子!你撿要緊的來說!”
“是是是,奴才這就講到要緊的了……”福兒忙道:“夫人,您再猜不到是哪個來通的信——”他不敢再賣關子,立馬接道:“竟然是十七皇子殿下!”
賈敏“嗳喲”了一聲,忙問道:“殿下怎麽說?”
“殿下說,你們家老爺要升官了,旨意還沒下,他不好細說,只是白告訴奴才一聲,要奴才回來告訴家裏夫人,讓夫人不要挂心。”福兒半點兒磕巴不打,把十七皇子的話複述來,“還說等老爺上任離京,他要親自來給師傅送行,再來拜見夫人,也見見小姐;說是自生辰那日見了,一直很想小姐這個妹妹。”
他說一句,賈敏就在嘴邊念一句“阿彌陀佛”。
“殿下還說,說不得老爺能回祖籍看看。”福兒歪着腦袋又想了想,似乎沒了。
說是“旨意沒下,不好細說”,可是這位十七皇子殿下卻簡單幾句,把她最可能擔心地事情給交代了——是升官,不是禍事;是外放,要離京上任;要去的是地方,大略在姑蘇一帶。
賈敏一顆心放下來,思量着,口中只道:“殿下也太體貼了些,竟費神親自往翰林院走一趟……”
“奴才也這麽說呢。”福兒笑道:“十七殿下說,是怕讓別人傳話不清明,萬一有疏漏,讓夫人受驚,就是他的過錯了。”
賈敏深為感動,心道,老爺教了十七殿下一年,當真是天降的善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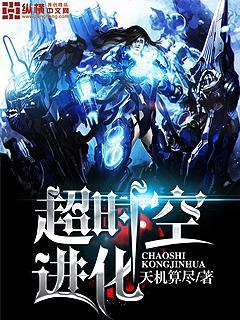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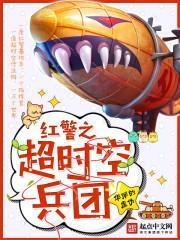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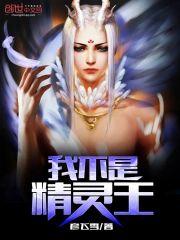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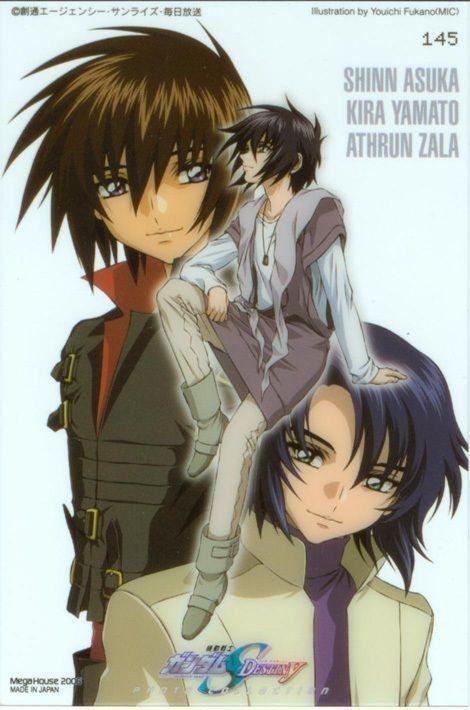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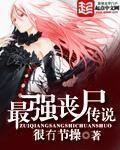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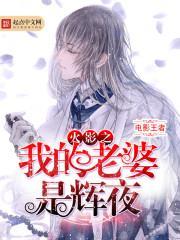

![[神夏+HP]以探案之名](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32779.jpg)
![[綜武俠]俠客們的反穿日常](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2907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