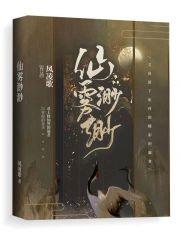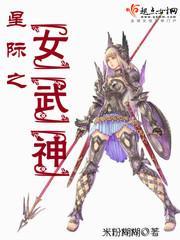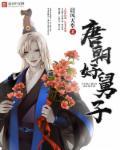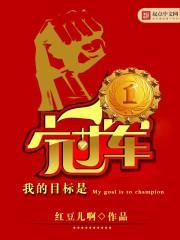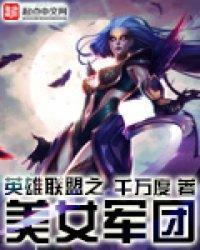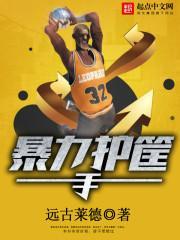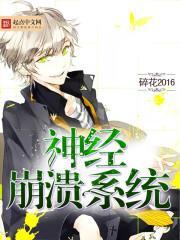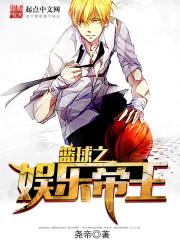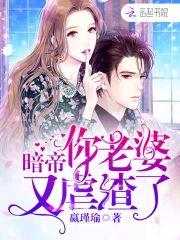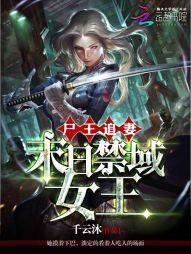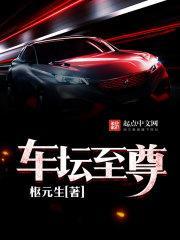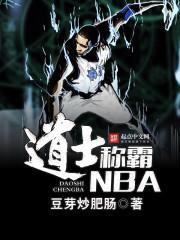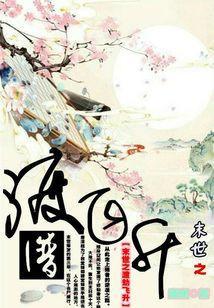第2章 二
二
誰能想到太空探索任務有一天會和純粹的數學聯系起來呢?
至少在那位俄羅斯數學天才阿列克謝·緬什科夫誕生前是沒有的。這位天才天生聰穎過人,13歲就上了大學,18歲已經獲得了兩個數學碩士學位,在23歲獲得博士學位時,他已經是國際數學界令人矚目的一顆新星。之後,緬什科夫來到了普林斯頓做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混沌理論。
2047年夏天,也就是他來到這裏的第三年,緬什科夫發表了一篇論文,就是這篇論文震驚了整個科學界。在這篇名為《混沌系統背後的的普适性:非線性系統的通用計算公式與常因子》的論文中,緬什科夫給出了一個天才的公式,這個數學公式或它的變形可以用于當時已知的所有非線性系統的規律運算,也因此被稱為緬什科夫混沌方程。
唯一的問題是,這個公式中要用到一個常數因子(緬什科夫命名它為宇宙因子,因為他認為這是代表宇宙規律的數學因子)。類似自然對數或是π值,這個無限不循環小數的精度決定了緬什科夫方程的計算精度。舉例而言,比方你想預測未來一個月下雨的概率,你只需要一個精确到小數點後二百位的宇宙因子,但如果你要預測一小時後的下雨概率,你可能需要一個精确到小數點後七千位的常數。
随着各大國對這個數字精确度計算的進步,人類對各項事物的預測成功率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而這個技術的結果,就像《時代周刊》上說的,“科學的大預言術已經成為了新的競争手段。”每個大國都通過精準預測股市、彙率、天氣、災害、犯罪率等各項數據,成功做到了趨利避害,之後他們甚至可以使用這項技術來預測競争對手的各項指标、政策變更、戰略方向等的概率,以此來決定國家間的競争策略。于是,如何更精确的計算出這個因子,就成為了各國科技競争的新目标。
在這件事情上,太平洋兩岸的兩大強國把其它對手遠遠抛開,畢竟這兩國在量子超級計算上本來就是超越它家的。但是當彼此都達到了目前技術的瓶頸時,雙方又一次站到了同一條線上,又無法進一步預測出對手的下一步動作來了(根據緬什科夫方程推導公式之一的鄭-維爾曼-緬什科夫博弈方程式,如果一方根據計算結果選擇有利動作,則另一方只有使用更高精度的因子才能計算出對方的選擇,而一旦雙方的因子精度相差很小,那麽彼此的選擇和預測将塌縮到完全随機化的場景)。對此,華盛頓自然是不高興的,但是無論政府如何要求,當前的技術水平就決定了只能達到這個精度。
已經年近六十的緬什科夫再次出手了。他發表了一篇新的論文,論述宇宙因子的另一種計算方式。他使用了一個很巧妙的方法,即使用一組統計量來計算這個因子,這個新方式的計算量大大減少了,只是這些統計量的要求是出自同一個高度非線性系統,譬如某塊土地上風的流向,雨滴在一定面積上落下的個數等等。這下子大家又開始挖空心思,來選擇合适的統計量。
對此,一位名叫羅阇·拉合都爾的天文學家提出了一項計劃,即利用木星大氣運動的高度複雜性,在木星軌道上部署數量龐大的觀測衛星,各自觀測一小塊區域內木星氣層的風速與流向等做為統計量,然後使用木星軌道上的奈克忒空間站做為中心節點彙總這些數據,并直接為空間站配置一臺超級計算機來進行計算,最後将計算結果每一段時間發回地球一次。于是,他們在三年前發射了“卡俄斯”號節點艙和“X”號計算艙到空間站,并開始派出數學家做為任務組成員來協助計算工作。
這個想法确實是天馬行空,巧妙已極。要知道,木星上的大氣運動,可以說是整個太陽系範圍內可觀測的最為複雜的非線性系統了,那些環流、漩渦等等,往往毫無規律可言(當然就全星球來說還是有一定的規律可循的),這些自然産生的參數,就随機性而言,比起計算機生成的随機值要複雜得多。這項觀測,讓美國在宇宙因子的計算精度上再次領先,在之後的一年中,他們的多項策略預判都先于對手,成功地在國際局勢中獲取了一定優勢。
但是去年開始,合衆國的預測部門(聯邦戰略分析局)發現他們又一次和大洋對岸的對手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對方設計了一個更巧妙的統計值,即該國公民使用個人終端的某種參數(公開信息中并示披露是哪種參數),基于其龐大的人口基數和近乎全員的聯網率,盡管其每個樣本的随機性可能低于木星大氣變化,但最終通過數量上的優勢達到了類似的效果。
美國政府再次無奈地向緬什科夫求助,試圖在數學理論上再次超越對手。這一次,他們幾乎是将緬什科夫軟禁起來,并且準備阻斷新算法的任何外洩可能。緬什科夫勉為其難地接受了這個任務,從那一天開始,他就隐身于洛基山中的某個私人莊園裏,日複一日的開始推導新算法的可能。
可惜他這回沒有迸發出新的天才想法。在花費了半年多時間後,他提出要向木星空間站提供一組新的算法,要求站中的數學家根據這套方程組來對觀測統計值進行運算。在經過了多次失敗和反複調整後,直到近日,新算法似乎出現了一線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