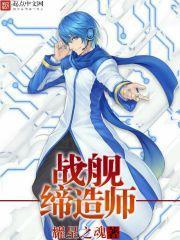第69章 公元前2800年
離開長老院, 吉爾伽美什滿腔的怒意未消,渾身上下都散發着凜冽的寒氣。
小獅子哈基什似乎也被王的怒意所感染,一路上只管瞪着路人, 喉嚨裏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如果不是伊南使勁兒拽着它脖子上的“貓繩”,這家夥一準闖禍。
但是氣歸氣, 吉爾伽美什未失冷靜:“說到底,長老們還是為了自己着想,為了利益着想。”
長老院為什麽會做這樣的決定, 吉爾伽美什翻過來一想,很容易就能想明白。
他轉頭問伊南:“朵, 你說, 王這時候動用神權怎麽樣?”
“王前往神廟, 以神明之子的身份, 在守護神伊南娜面前祈求神谕,女神……會降下神谕,要王遵守承諾, 庇護所有人的對嗎?”
說這話的時候,吉爾伽美什眼神有些閃爍。
他言語之中曾經略有停頓與游移,這證明他正在考慮與神廟的聖倡們“合作”,就算伊南娜女神沒有什麽“神谕”送至人間, 他也打算“聲稱”收到了神的谕令。
這和當年杜木茲站在伊南娜神廟的臺階上, 取出巫師丹留下的安全繩, 號召烏魯克人保衛城市的手法本質上是一樣的。
“但是, ”伊南适時地潑了一瓢冷水,“王能想到這一點, 長老們應該也能想到吧?”
而且神廟的聖倡人數衆多, 未必人人都與王是一條心。神廟距離長老院又近, 萬一有人把消息洩露出去,對吉爾伽美什的“神性”将會是個致命的打擊。
吉爾伽美什緊抿着嘴,思考伊南說的這種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伊南小聲地提醒他:“王難道忘了‘公民大會’?”
吉爾伽美什雙眼一亮,轉過身,激動地伸出手,握住伊南的雙肩,突然覺得這個舉動太過親昵,臉上一熱,趕緊放開伊南。
他一握拳,大聲說:“王怎麽就沒想到呢?”
此前烏魯克人的“公民大會”确實開過一次,但是是基于長老會已經通過的議題進行再讨論,不曾涉及反對或是推翻長老會的決議。
Advertisement
王還不大習慣這種集體決策的方式。
但這确實是一條新路。
吉爾伽美什重重地将右拳砸在左手掌心裏,整個人精神煥發,眼裏出現光彩。
他說出的話卻是老成持重的:“王要就這件事好好計議計議。”
果然,吉爾伽美什沒有馬上宣布召開烏魯克城的“公民大會”。他先實踐了承諾,将早先随他一同出征阿摩利的一千名民夫,升格成為烏魯克的“公民”(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自由民”)。
一直以來負責烏魯克城牆工程的幾名高級匠人也同時獲此“殊榮”,他們大多滿足了在烏魯克“服役三年”的條件。與他們一樣符合條件,獲得公民資格的,大約還有四五百人。
長老院聽說王将烏魯克城的“公民”人數增加了一千五百人左右,都沒在意:畢竟他們此前做出的決議,讨論的是“兩萬人”與“五萬人”的區別,而不是“兩萬人”與“兩萬一千人”的區別。
随後,吉爾伽美什開始緊鑼密鼓地布置,打算召開“公民大會”。上一次參加“公民大會”的人,基本上都是已成年的男子。但是這一次,伊南說服了吉爾伽美什,讓他允許成年女性一起參加。
“女人也應當參與決策——烏魯克也是她們的家園。”伊南說。
就在吉爾伽美什正皺着眉猶豫的時候,伊南又補了一句:“王試着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女人們雖然不上戰場,但是她們會負責守城時的後勤。關于抵禦阿卡德人,她們的疑慮也不會少。如果現在沒辦法說服她們,将來守城的時候一定會有麻煩。”
最後讓吉爾伽美什下定決心的,是伊南的一句話:“女人是最慈悲也是最需要安全感的人,王覺得她們希望城裏人多些還是希望城裏人少些?”
吉爾伽美什啞然失笑,當即拍板,召開烏魯克城的“公民大會”。有資格參加大會的,包括所有擁有“自由民”身份的成年男子和女人。
另外,所有在烏魯克築城的民夫,附近村莊的代表,每十人可以派出一名代表,前往“公民大會”旁聽。
城中的制陶作坊在燒制陶磚之餘,趕制了四萬枚陶籌,兩種形式:圓籌與方籌,在公民大會召開之際,發到了每一個與會公民的手裏。
身在長老會中的長老們,也同樣身為烏魯克的公民,都同樣接到了王派人送來的請柬與陶籌。
幾個長老都找到了赫伯,把陶籌交到赫伯手裏,表示他們不願費這神去開會了,由赫伯代為出席一下就行了。
“王不讓人去趕着修城牆,反而費這工夫開什麽‘公民大會’,真叫人搞不懂。”
“長老會已經做出的決議,難道‘公民大會’還能翻過天不成?”
“王為什麽不肯相信人性——在這種時候,人都是自私的。”
赫伯也是這種想法,他認為吉爾伽美什這是在浪費寶貴的築城時間——但是幫他們築城的人,卻是已經被長老會決議,即将被趕出城,無法得到城牆庇護的人——這一點長老們卻是根本想不到的。
第一次參加大會的人們,拿着這兩枚陶籌正在納悶,旁邊就有人湊過來解釋:“王想聽聽你們的意見——如果你們是烏魯克的王,你們會做什麽選擇?”
如果我們是……烏魯克的王?
人們都睜圓了眼睛:有這可能嗎?
王竟然讓他們假想這個?
“是的,如果你們是烏魯克的王,你們會做什麽選擇!”吉爾伽美什站在神廟高高的臺階上,朗聲發話。他手裏拿着一個青銅制成的空心圓錐,雄壯的聲音為那錐體所聚攏,回蕩在神廟跟前廣闊的空地上。
“但是在這之前,王要将這座城現在所面臨的全部實情,全部告訴你們。”
吉爾伽美什說話的時候,伊南就坐在他的腳邊,默默觀察着階下的人們。上一次她這樣做還是兩千多年前,那時的烏魯克還是一個只有五千人口的小城市。
現在,僅僅是“常駐”人口就已經達到了二萬,人們從事于各行各業,與整個兩河流域都有往來。
他們……還會像以前那座城市裏的居民一樣,高喊着“力量屬于我們自己”,願為保衛這座城市付出一切嗎?
或者,現在依然會有很多人願意出力保衛他們的家園,但是,他們願意把家園分享給外來人口嗎?那些為了他們的城市修築城牆的普通民夫,還有那些在城外種田放牧,為烏魯克人供應糧食,但是卻在城裏沒有家的農夫牧民。
果然,吉爾伽美什把這個議題抛出來的時候,在場所有的人都非常吃驚。
烏魯克人很不确定他們的城市能不能容納下五萬人,而民夫的代表們則吃驚于他們辛辛苦苦地幫助烏魯克人修築了這麽久的城牆,在危機到來之時,竟然在城裏沒有他們的一席之地。
吉爾伽美什将他在長老院的論點重新論述了一遍。他認為,阿卡德人攻打烏魯克,烏魯克不可能只靠一味死守,城裏的人要能阻止抵抗和反擊。城中沒有足夠的人口和兵力,根本不能支持他們擊破阿卡德人的圍攻。
再者,民夫們在為烏魯克築城的過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與犧牲,于情于理,都應保證他們的安全,讓他們得到城牆的庇護。
這一番話聽得人連連點頭。伊南在旁觀察,她覺得民意很明顯地開始向吉爾伽美什這邊傾斜。
但是吉爾伽美什剛剛說完,身為長老院成員的赫伯突然開口,大聲向王發問:“可是,王,您想過沒有,現在城內的糧食,只能夠供應城內所有的自由民兩個月,但是您把這麽多‘外鄉人’留在城裏,糧食就只夠供應所有的人吃一個月。”
“王,您生來高貴,從沒有經歷過艱苦的時期。您可知道,五萬張嘴一起吃東西,究竟是什麽概念?”
赫伯的話瞬間引起了不少共鳴——
“五萬人啊……”終于有人心裏開始發怵。
前一段時間烏魯克神廟的糧倉在拼了命的以王之名收購糧食,城裏人都看在眼裏。當時看見,人們心中都還覺得挺安慰的,但是現在想到,他們竟然要與一倍多的人分享這些糧食。
這太可怕了。
熱情開始消減,自私的欲望開始在心裏蔓延——當有民夫和鄰近村莊的代表表示抗議的時候,竟然有烏魯克人沖他們激動地大喊:“閉嘴——”
人性就是如此,沒有人能做到完全無私。
伊南抱着膝,坐在臺階上,她擡頭望望吉爾伽美什,希望這個年輕的王不至于因此而大發雷霆。
誰知吉爾伽美什氣定神閑,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樣。在赫伯說話的過程中,他一直保持傾聽,甚至末了還主動問問人家:“您說完了沒?”
赫伯尴尬地點點頭:他說完了。
吉爾伽美什沖他微笑:“道理越辯越明,王歡迎各種不同的聲音。”
“但是,在王眼裏看來,人才是最重要的,有了人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糧食。”
“有了足夠的戰士,烏魯克就能對來犯之敵發動反擊,就能保證商路的通暢——王以神廟和王室積累多年的財富作為給各位的保證,就算是阿卡德人圍城,烏魯克也一定能從其他地方,買到供應烏魯克所有人的糧食。”
“神廟和王室積累多年的財富”——這話一說出來,赫伯的臉色又變成了紙莎草色。他萬萬沒想到吉爾伽美什竟然敢當衆做這樣的承諾。
的确,神廟和王室多年來積蓄頗豐,赫伯身為長老,深知其中的內情。只不過說要将這些財富都拿出來購買糧食,養活城內所有的居民,此前沒有任何一個王曾經做到過。
吉爾伽美什這句話說了出來,相當于給很多人吃了一顆定心丸。
但是吉爾伽美什還沒有說完,他繼續說:“各位,這樣的‘公民大會’,之前也開過一次,但是那時候大家讨論的問題,還只是要不要為烏魯克城建成一座水上城門,如果要建,怎麽建。”
“在那次的‘公民大會’上,你們之中的很多人都提出了非常精彩的意見,這才令烏魯克有機會擁有一座直通幼發拉底河航道的門戶。”
“這次王前往幼發拉底河上游,從各城邦執政官那裏得到了保證——只要母親河上的航道沒有斷,他們就都會不遺餘力地支援烏魯克。”
“也就是說,只要水路商道能夠不斷,咱們城裏,就絕對不會斷糧!”
“好呀——”頓時有人歡呼起來。
吉爾伽美什說得沒錯,這次面對阿卡德人的進攻,烏魯克人事實上占據着前所未有的優勢,只要他們團結一心,是不會有過不去的坎兒的。
“如果沒有上一次‘公民大會’的決議,就不會有今天烏魯克的局面。”
“也正是因為這個,王才決定召開這一次的‘公民大會’,希望你們能夠好生考慮,如果你們是王,你們會做出什麽樣的選擇。”
“想想你們的朋友,這麽久以來,一直在你們的身邊與你們并肩築城的人。他們也同樣需要城牆的庇護,需要一個安全的容身之所。”
“有他們在城內,也會和我們一樣,是抵抗外敵的頑強力量。”
吉爾伽美什說到這裏,頓時有民夫的代表抓着胸口的袍子,用力地拍着胸膛,應和着吉爾伽美什的話。
“總之,王在,這城就在。王絕不會輕易犧牲你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這是王對你們的莊嚴承諾。”
“好了,所以烏魯克的公民們,你們已經都聽見了王的心聲——王已經就差要剖開胸膛,将心掏出來給你們看了。”
聽見吉爾伽美什說得真誠,不少烏魯克的婦人們感動得眼中淚光盈盈。伊南在一旁看着,知道吉爾伽美什的形象和他的真誠一樣,為他加了不少分。
“請你們拿出手裏的每一枚陶籌,仔細辨認它們的形狀。然後,假想你們就是這烏魯克的王,是這座城市的主人,你們在盡力權衡了所有利弊之後,用你們的全部誠意,投出這最為重要的一枚陶籌。”
“不需擔心投出這一籌最後會導致什麽樣的後果,你們只需要認真對待手中的陶籌。”
“至于這結果……王會尊重‘公民大會’的意見——一切的後果,由王來背負。”
吉爾伽美什一旦說完,從他身後立即湧出了一群官員和聖倡。這些男男女女們人手拿着一枚麻袋,走入人群之中,從他們手中接過人們投出的陶籌。
在一邊旁聽着的民夫和鄰近村莊代表們也在向他們認識的朋友大聲吶喊與乞求:“留下我們,我們希望能和你們在一起。”
“我們不會讓你們失望!”
“投出方籌,投方籌!”
“哦,看在女神伊南娜的份上,投出你們的方籌吧!”
坐在吉爾伽美什腳邊的伊南仔細觀察附近的人投出的陶籌,想借此推斷到底是支持吉爾伽美什的人多,還是支持長老會的人多。
但是她目力所及,既見到了投出方籌,也見到了投出圓籌。
她還看見了赫伯——這個家夥滿臉悻悻之色,但是卻從袍子的衣袋裏掏出了一大把圓籌,數也不數,全部倒進了官員遞來的麻袋裏。
——這是個漏洞!
伊南很想大喊一聲。
她知道赫伯是代投,恐怕是将長老院那些長老們家裏的男男女女領到的陶籌都拿來,讓他一個人投了。沒準長老的家屬們來到現場,聽見吉爾伽美什的真誠表态,也會被他打動,投出方籌呢?
看來以後烏魯克城裏再開這樣的“公民大會”,一定要現場發陶籌現場投籌才行。
但這些制度都可以以後摸索,這一場大會卻因為事先沒有說過不許代投,必須接受眼前的結果。
很快,兩萬多名“公民”(去除未成年的孩子之外大約只有一萬七千人左右)投出的陶籌全部收集到了伊南娜神廟之前。
神廟裏所有的聖倡此刻都出現在世人面前,她們在伊南娜的聖殿跟前虔誠祈禱,然後再各自分工,開始清點起陶籌。
清點陶籌是經過嚴格分工的,每一道程序都由兩人完成,一人執行,一人檢查。
收在麻袋裏的陶籌先是經過篩選,将方籌和圓籌區分開;然後是清點,每六十枚陶籌會由聖倡們在泥板上記錄一次。
清點陶籌的過程任何人都可以上前監督,但是烏魯克的居民多半抱着對吉爾伽美什和伊南娜女神的信任,不曾上前。反倒是赫伯,皺着眉頭背着手,上前将所有清點的過程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遍,頗有些恨不得上前親自動手的架勢。
伊南只等着看到底是方籌還是圓籌會先達到3600枚。誰知出乎她的意料,圓籌先滿了3600枚。
吉爾伽美什臉色不善,赫伯卻得意洋洋,背着手離開聖殿跟前,直接去等結果。
但是,漸漸地,負責清點圓籌的聖倡已經清點完畢,無所事事地等待着。而清點方籌的人們面前還堆着如山的陶籌,數之不盡。
伊南看見清點圓籌的女人們還在繼續忙碌着,額頭沁出細細的汗珠,她終于放了心,揚起頭,向吉爾伽美什那裏看了一眼。
沒想到吉爾伽美什也正看着她,見到她看過來,吉爾伽美什趕緊将臉轉了過去。
“這家夥……”伊南小聲說,“肯定是在緊張。”
她相信吉爾伽美什一定也是在緊張公民大會投籌的結果,她也知道吉爾伽美什緊張的時候偶爾會別過頭沉思——因此伊南絲毫沒有多想。
最終結果是由神廟裏年紀最長的一位聖倡宣布的,她拿着一枚泥板,泥板上用蘆葦杆劃上了新鮮出爐的數字。這枚泥板在聖倡宣布之後,就要立即送到陶窯裏被燒成陶板,并且這枚陶板将被放置在伊南娜女神的聖殿之中,由女神見證這個結果。
“圓籌的數目是:四千二百一十七枚。”
聽見這個數字,伊南長長地舒出一口氣。不用聽另一個數字,就可以想見:烏魯克人聽進去了王最為真誠的解釋,并決心敞開城門,擁抱那些曾經和他們一起并肩出力的人。
果然,只聽聖倡高聲說:“方籌的數目是:一萬三千五百六十六枚!”
好家夥!——這方籌竟然是圓籌的三倍之多。
吉爾伽美什當即向前踏上一步,将右手貼在心口,莊嚴地說:“各位,王聽見了你們的聲音。女神伊南娜作證,王會尊重你們的意見,依照多數人的意見行事。”
他說話的時候,眼神凜然,看向站在階下的赫伯。
赫伯緊緊地繃着一張臉,可就是沒有勇氣反駁“公民大會”的這個結果。
畢竟贊成吉爾伽美什的有一萬三千多人,每人一口吐沫,就能把長老會淹死。吉爾伽美什以這樣的民意為基礎反對長老會,而不是以神權和王權強壓,長老會沒有任何理由堅持原有的觀點。
因此,盡管赫伯心裏可能正在罵着“瞎鬧”“瞎鬧”,但事情已經再無轉圜的餘地——吸納築城的民夫和周邊村莊的居民進城,已成定局。
這一場大會之後,烏魯克城繼續加強戰備。
民夫們都如吃了一枚定心丸,轉而将注意力都轉向那最後一段還未修好的城牆。
居住在烏魯克城外的農夫們,将已經成熟的大麥小麥全部收割,打包送進烏魯克城,然後放了一把火,将田裏的青苗全部燒光,一點兒糧食都不給阿卡德人留下。
他們之前還有很多人聽過關于吉爾伽美什“初夜權”的傳聞,死活不肯搬進烏魯克城來;但是在村裏的代表向他們傳達了烏魯克“公民大會”的實況之後,人人都争相搬家,要趕在烏魯克城門開始封鎖,人員開始管制之前,把家什都搬進烏魯克城裏去。
正在烏魯克人手忙腳亂地做着各種準備的時候,第一批阿卡德人出現在了烏魯克城外的平原上。
他們的“裝備”很特殊,像是當初那些埃及商人一樣,叫人一見就能認出來。
阿卡德人,全部都是騎在公牛的牛背上的——只要牢牢把住公牛的牛角,他們就能來去如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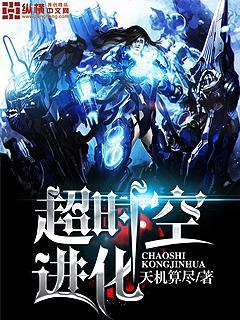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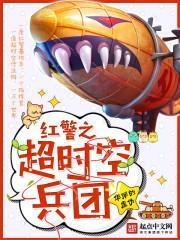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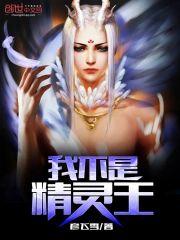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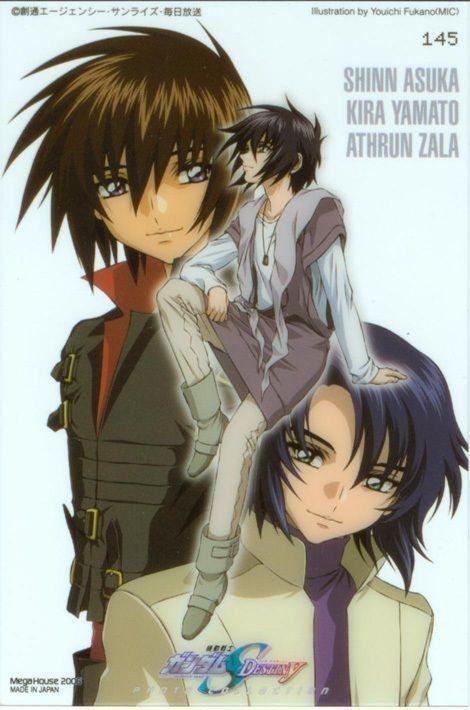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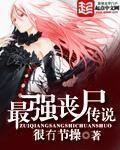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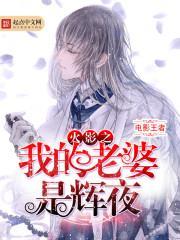


![[神夏+HP]以探案之名](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32779.jpg)
![[綜武俠]俠客們的反穿日常](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2907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