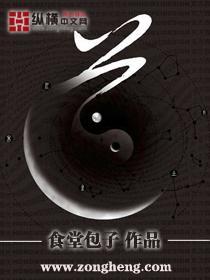第15章 章節
家所有財
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赈貧乏。錄用材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
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複
完壘。及敗,人尚懷之,故順得脫去三十餘年乃始就戮。”沈括雖稱李順為“賊”,但文
字中顯然對他十分同情。李順的作風也很有人情味,并不屠殺富人大姓,只是将他們的財
物糧食拿出來赈濟貧民,同時根據富戶家中人丁數目,留下各人足用的糧食。《青瑣高議》
中,又記載李順亂蜀之後,凡是到四川去做官的,都不許攜帶家眷。張詠做益州知州,單
騎赴任。部屬怕他執法嚴厲,都不敢娶妾侍、買婢女。張詠很體貼下屬的性苦悶,于是先
買了幾名侍姬,其餘下屬也就敢置侍姬了。張詠在蜀四年,被召還京,離京時将侍姬的父
母叫來,自己出錢為衆侍姬擇配嫁人。後來這些侍姬的丈夫都大為感激,因為所娶到的都
是處女。《青瑣高議》這一節的題目是“張乖崖,出嫁侍姬皆處女。”蘇轍的《龍川別志》
中,記載張詠少年時喜飲酒,在京城常和一道人共飲,言談投機,分別時又大飲至醉,說
道:“和道長如此投緣,只是一直未曾請教道號,異日何以認識。”道人說道:“我是隐
者,何用姓名?”張詠一定要請教。道人說道:“貧道是神和子,将來會和閣下在成都相
會。”日後張詠在成都做官,想起少年時這道人的說話,心下詫異,但四下打聽,始終找
他不到。後來重修天慶觀,從一條小徑走進一間小院,見堂中四壁多古人畫像,塵封已久,
Advertisement
掃壁而視,見畫像中有一道者,旁題“神和子”三字,相貌和從前共飲的道人一模一樣。
原來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為,字無不為,五代時人,有著作,便以“神和子”三字署名。
在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同樣有個先知預見的記載:張詠少年時,到華山拜見陳抟,想
在華出隐居。陳抟說:“如果你真要在華山隐居,我便将華山分一半給你但你将來要做大
官,不能做隐士。好比失火的人家正急于等你去救火,怎能袖手不理?”于是送了一首詩
給他,詩雲:“征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也須多謝鬓邊瘡。
”當時張詠不明詩意,其後他知益州、知杭州,又知益州,頭上生惡瘡,久治不愈,改知
金陵,均如詩言。世傳陳抟是仙人,稱為陳抟老祖。這首詩未必可信,很可能是後人在張
詠死後好事捏造的。
沈括是十一世紀時我國淵博無比的天才學者,文武全才,文官做到龍圖閣直學士,曾
統兵和西夏大戰,破西夏兵七萬。他的《夢溪筆談》中有許多科學上的創見。英人李約瑟
在《中國科學文明史》第一卷中,曾将該書內容作一分析,詳列書中涉及算學、天文歷法
、氣象學、地質、地理、物理、化學、工程、冶金、水利、建築、生物、農藝、醫學、藥
學、人類學、考古、語言學、音樂、軍事、文學、美術等等學問,而且各有獨到的見地,
真是不世出的大天才,《夢溪筆談》中另外還記錄了張詠的一則轶事:
蘇明允常向人說起一件舊事:張詠做成都知府時,依照慣例,京中派到鹹都的京官均
須向知府參拜。有一個小京官,已忘了他的姓名,偏偏不肯參拜。張詠怒道:“你除非辭
職,否則非參拜不可。”那小京官很是倔強,說道:“辭職就辭職。”便去寫了一封辭職
書,附詩一首,呈上張詠,站在庭中等他批準。張詠看了他的辭呈,再讀他的詩,看到其
中兩句:“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不禁大為稱賞,忙走到階下,握住他手
,說道:“我們這裏有一位詩人,張詠居然不知道,對你無禮,真是罪大惡極。”和他攜
手上廳,陳設酒筵,歡語終日,将辭職書退回給他,以後便以上賓之禮相待。張詠性子很
古怪,所以自號“乖崖”,乖是乖張怪僻,崖是崖岸自高。宋史則說:“乖則違衆,崖不
利物。”他生平不喜歡賓客向他跪拜,有客人來時,總是叫人先行通知免拜。如果客人禮
貌周到,仍是向他跪拜,張詠便大發脾氣,或者向客人跪拜不止,連磕幾十個頭,令客人
狼狽不堪,又或是破口大罵。他性子急躁得很,在四川時,有一次吃馄饨,頭巾上的帶子
掉到了碗裏,他把帶子甩上去,一低頭又掉了下來。帶子幾次三番的掉入碗裏,張詠大怒
,把頭巾抛入馄饨碗裏,喝道:“你自己請吃個夠罷!”站起身來,怒氣沖沖的走開了。
他有時也很幽默。在澶淵之盟中大出風頭的寇準做宰相,張詠批評他說:“寇公奇材,惜
學術不足爾。”後來兩人遇到了,寇準大設酒筵請他,分別時一路送他到郊外,向他請教
:“何以教準?”張詠想了一想,道:“《霍光傳》不可不讀。”寇準不明白他的用意,
回去忙取《霍光傳》來看,讀到“不學無術”四字時,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說:“張公
原來說我不學無術。”他治理地方,很愛百姓,特別善于審案子,當時人們曾将他審案的
判詞刊行。他做杭州知州時,有個青年和姐夫打官司争産業。那姐夫呈上岳父的遺囑,說
:“岳父逝世時,我小舅子還只三歲,岳父命我管理財産,遺囑上寫明,等小舅子成人後
分家産,我得七成,小舅子得三成。遺囑上寫得明明白白,又寫明小舅子将來如果不服,
可呈官公斷。”說着呈上岳父的遺囑。張詠看後大為驚嘆,叫人取酒澆在地下祭他岳父,
連贊:“聰明,聰明!”向那人道:“你岳父真是明智。他死時兒子只有三歲,托你照料
,如果遺囑不寫明分産辦法,又或者寫明将來你得三成,他得七成,這小孩子只怕早給你
害死了,哪裏還能長成?”當下判斷家産七成歸子,三成歸婿。當時人人都服他明斷。中
國向來傳統,家産傳子不傳女。張詠這樣判斷,乃是根據人情和傳統,體會立遺囑者的深
意,自和現代法律的觀念不同。這立遺囑者确是智人,即使日後他兒子遇不着張詠這樣的
智官,只照着遺囑而得三成家産,那也勝于被姐夫害死了。《青瑣高議》中還有一則記張
詠在杭州判斷兄弟分家産的故事:張詠做杭州知府時,有一個名叫沈章的人,告他哥哥沈
彥分家産不公平。張詠問明事由,說道:“你兩兄弟分家,已分了三年,為甚麽不在前任
長官那裏告狀?”沈章道:“已經告過了,非但不準,反而受罰。”張詠道:“既是這樣
,顯然是你的不是。”将他輕責數板,所告不準。
半年後,張詠到廟裏燒香,經過街巷時記起沈章所說的巷名,便問左右道:“以前有
個叫沈章的人告他哥哥,住在哪裏?”左右答道:“便在這巷裏,和他哥哥對門而居。”
張詠下馬,叫沈彥和沈章兩家家人全部出來,相對而立,問沈彥道:“你弟弟曾自我投告
,說你們父親逝世之後,一直由你掌管家財。他年紀幼小,不知父親傳下來的家財到底有
多少,說你分得不公平,虧待了他。到底是分得公平呢,還是不公平?”沈彥道:“分得
很公平。兩家財産完全一樣多少。”又問沈章,沈章仍舊說:“不公平,哥哥家裏多,我
家裏少。”沈彥道:“一樣的,完全沒有多寡之分。”
張詠道:“你們争執數年,沈章始終不服、到底誰多誰少,難道叫我來給你們兩家一
一查點?現在我下命令,哥哥的一家人,全部到弟弟家裏去住;弟弟的一家人,全部到哥
哥家裏去住。立即對換。從此時起,哥哥的財産全部是弟弟的,弟弟的財産全部是哥哥的
。雙方家人誰也不許到對家去。哥哥既說兩家財産完全相等,那麽對換并不吃虧。弟弟說
本來分得不公平,這樣總公平了罷?”
張詠做法官,很有些異想天開。當時一般人卻都十分欣賞他這種別出心裁的作風,稱
之為“明斷”。
張詠為人嚴峻剛直,但偶爾也寫一兩首香豔詩詞。宋人吳處厚《青箱雜記》中雲:“
文章純古,不害其為邪。文章豔麗,亦不害其為正。然世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
之正人君子,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