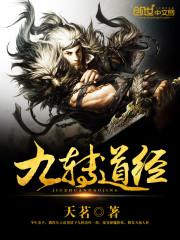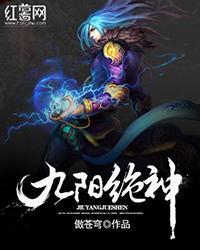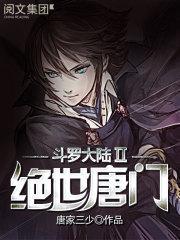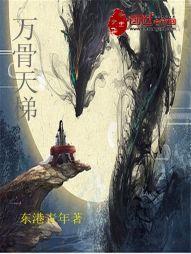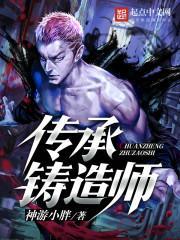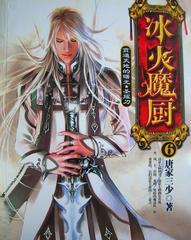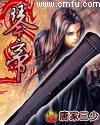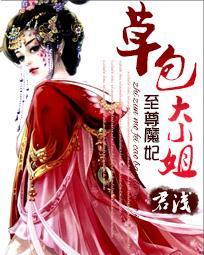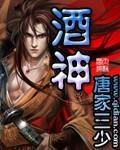第24章 (2)
上卿……
對方也當真是好算計,把上郡幾十萬軍隊全部托付給他,令他無法任性地扔下職責回鹹陽救人……
“将軍,該為大公子送行了。”親衛低聲提醒道。
王離站起身,面如沉水。
※鹹陽※
嬰站在升平巷的街角,目送着阿羅和宜陽王被虎贲軍簇擁着,離開了長街。
那些虎贲軍說是邀請,但看上去更像是押送。
不過只聽皇帝命令的虎贲軍,在鹹陽城向來都是橫着走的。嬰站在夜風中思忖半晌,覺得應該是自己想多了。
既然連百官都被叫去為始皇發喪,那麽身為皇室一員的嬰理應也要同去。被分到他名下的宮殿因為偏僻久不居住,他早已在鹹陽城私自建了宅邸,但因為作風低調,常居高泉宮,所以虎贲軍理應找不到。
嬰對始皇沒有什麽感情,也并沒有想去送葬,而且現今胡亥登基,趙高執掌權柄,他需要做的應該還有很多。在等待這一隊虎贲軍遠去之後,嬰才從藏身的街角走出,低着頭往自家的宅院而去。
這一晚注定是不眠之夜。
※下邳※
沂水靜靜地在深夜流淌,橫跨沂水的圯橋之上,一名青年男子正仰着頭看向璀璨的星空。
這名男子身形瘦削,肩上披着一件纖塵不染的白袍,他比一般人要瘦上許多,臉部的顴骨都瘦得微凸了出來,更顯得他的五官分明。他的面容清俊,但也架不住他的不修邊幅。他的長發因為懶得打理,只松松地系在腦後,臉頰邊還有未刮淨的胡茬,給人一種邋遢的感覺,可那雙銳利的眼睛又讓人不容忽視。
沒有人知道,這名男子曾經在博浪沙行刺過秦始皇,雖一擊不中,卻全身而退。
這名男子遙望星空,許久之後,幽幽地嘆了口氣。
Advertisement
“星象紊亂,亂世又将重啓……”
※會稽※
操練了一整日的魁梧男子走進屋內,把手中的虎頭磐龍戟随意地放在了兵器架上。這柄虎頭磐龍戟是他少年時在戰場上撿到的,用起來順手至極,便一直沒有離身。
不過相比起來,他還是更在意床邊的花花草草。
低頭欣賞了一陣後,魁梧男子拿起一旁的水壺,一邊細心地澆着水,一邊溫聲唠叨道:“多喝點水,早點發芽哦!”
※龍城王庭※
順利逃回王庭的冒頓王子,此時正親手雕刻着一塊雪白的狼骨,在他面前的案幾上,整整齊齊地擺放着數十支已經做好的骨鳴镝。
每當他制作一支骨鳴镝的時候,都會忍不住想起草原上被他戲弄的那個小兵。
好像……是叫什麽韓信來着……
也不知道最後死了沒有。
寥寥幾刀修整了骨孔邊緣,冒頓王子心不在焉地把玩着剛剛做好的骨鳴镝,用滲着血一般凜冽的語氣緩緩道:“從此以後,本王的骨鳴镝所射之處,爾等也要齊箭射之!”
“諾!”帳篷中的親衛們,低聲整齊地應喝道。
※鹹陽※
胡亥站在銅鏡前,伸開雙臂,任憑內侍一件件地為他穿上皇帝冠服。
中衣中褲、羅縠單衣、玄衣绛裳、襭夾……因為他登基得太倉促,織室并沒有為他準備合适的冠服。據說織室的首席織婢若是在的話,一晚就可以用現成的皇帝冠服為他改好尺寸。只可惜據說那位首席織婢因為急症已不幸身故,織室那邊還在加急做他的冠服。
所以他便只能拿來父王的冠服應急。在最外面的衮服穿好之後,就更顯得寬大而不合身,銅鏡中的人影透着幾分滑稽,像是小孩子在偷穿大人的衣服。
就像是他偷來的皇位一般。
胡亥至今還有些茫然,他就這麽輕易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不知道第幾位被命名為孫朔的內侍轉到了胡亥的身前,為他系上內側的深衣腰帶,然後理順了衣服的褶皺,最後纏上刺繡上滾雲紋的黼黻腰帶。
另外旁邊的小內侍手中的托盤之中還放着通天冠,和只有帝王才能佩戴的五彩绶,黃地骨、白羽、青绛緣、五采、四百首……還有秦始皇的随身佩劍,長七尺的太阿之劍。
胡亥頭一次身上被挂着這麽多東西,一開始還比較新奇,被折騰到現在就只剩下厭煩和勞累了。
“如此足矣。”胡亥瞥了一眼牆角的青銅漏壺,不耐煩地催促道。他也要去骊山為父王送葬,眼看着就要來不及了。
內侍們紛紛加快了速度,但他們都是第一次服侍皇帝穿戴服飾,這樣一着急反而更加手忙腳亂。
“不須如此,汝無須去了。”一個身穿五彩魚鱗絹深衣的男子信步而入,他的聲音毫無起伏,聽起來好似無害,但胡亥身周的內侍們早就熟知其暴虐,捧着托盤的小內侍不禁都顫抖起來,其上的飾品配飾叮叮當當地響個不停。
“爾等暫且退下。”此人淡淡地吩咐道,等他最後一個字剛說完,屋中就只剩下他與胡亥兩人了。
胡亥的臉色有些陰沉,他雖然貴為皇帝,但他身邊的人卻在他沒有發話的時候,就已經擅自聽從別人的命令而離開。
頭一次,他開始覺得當這個皇帝,并不是他所想的那麽好玩。
要不……等他大兄從上郡歸來,就還給對方吧,反正他大兄也一直包容他的任性……
胡亥的腦中胡亂地轉着念頭,口中卻問道:“為何孤無須去骊山為父王送葬?”
趙高勾起一抹別有深意的笑容,看向窗外已經開始發白的天際,緩緩道:“因為今日前去送葬的那些人,是務必要把始皇送到黃泉之畔的。”
胡亥震駭地臉色發白,一時無言以對。
【敬請期待《啞舍·零》之漢朝卷】
後記
“啞舍”又完結一本!撒花~~
這回不同于“啞舍”的正篇,我寫了一本“啞舍”的前傳,被命名為“零”。嗯,挺好的,符合我要書名整齊的強迫症……
不過說到整齊,我本來想一本寫完“啞舍”的前傳的,結果……果然低估了我自己的寫作熱情……挖坑什麽的,一挖起來就停不下來了……
所以《啞舍·零》不止一本哦……接下來是漢朝卷,而漢朝卷的卷名我還沒想好,暫時空着吧。
看完《啞舍·零》的各位,應該都知道這篇前傳講的就是老板之前的故事了吧,對于這一段故事好奇的同學們,希望你們喜歡。
我雖然寫得開心,但過程真的非常痛苦……
這還是我首次嘗試“啞舍”通篇十二個故事連續性地在一個時間軸上進行。雖然大長篇幾十萬字的故事我也寫過好多個了,可“啞舍”這個故事本身就與其他故事不同,畢竟是在真實歷史上構架的。
所以我在寫的時候,查了許多資料,考慮了許多方面。
舉例來說,其實我最開始寫“啞舍”正篇第一章魚紋鏡的時候,根本沒有想把對話寫成古文。因為生澀的古文會不利于流暢閱讀,但還是接受了當時編輯的建議,把“你”、“我”等稱呼改成“汝”、“吾”“雖然有了點古風的意味,但行文上卻有些不倫不類。
因此在《啞舍·零》裏,我盡量避免了這種稱呼,只有語境符合才會使用。而為了行文流暢,大家就當古人對話的時候就是如此吧,否則就真不能寫了……
還有成語問題,我幾乎在用一個詞之後,只要想起來,就會查一下這個成語的來源,
在秦朝的語境下是否已經出現。如果沒有出現,就努力替換成其他已經出現過的詞語。但後來發現這樣簡直太過于約束,如果大家如此通篇看下來的話,肯定會以為我全篇都是錯字。
例如“夥伴”一詞,古代軍人以十人為火,共竈炊食,故稱同火時為火伴,所以只能用“火伴”。哦,如果再細研究的話,這個詞在元魏時才出現,秦朝時根本沒有。
不光詞語,物品也是如此。
但我最後還是釋然了,我寫的是小說,并不是教科書,也不是歷史書。最終的目的是為了我的故事好看,文筆流暢舒服。所以大家若是在文中看到什麽不該在秦時出現的詞語和物品,請多多諒解。
說起查資料,我順便就唠叨一些這回的收獲,史書裏面自相矛盾的地方非常多。
例如魏王假,《史記》上說他沒有死。但《資治通鑒》上卻寫的他是被殺的。這一點就令我非常糾結。
也許有人會問了,這個人死不死又有什麽關系,畢竟不管他是不是當時被殺,對于現在來說,他也已經死了。
可是這個涉及到很多問題。例如之前秦滅的韓國、趙國,甚至之後的燕國、齊國、楚國,這五國的國君,全部都是滅國之後被俘虜的。沒有一個人被殺,那麽為何魏王假語焉不詳甚至史料都互相有矛盾昵?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
【《資治通鑒》;始皇帝下二十二年(丙子,公元回國二五年),王贲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魏王假到底是降了還是被殺了,這是一個問題。也可能是因為《史記》上沒有記錄他被受封在哪裏,所以司馬光也就腦洞大開,直接寫了“殺之”。
另外,上述《資治通鑒》的這一切之中,“三月”這個翻譯,有的資料上說是水淹大梁城三個月。這在理論上應該是不可能的,從《資治通鑒》的通篇行文來看,這只代表着是三月份而已,按照農歷的計算方式,正好是春汛的時間。
否則随便舉個例子:【二十五年,五月,天下大酬。】
酬是指飲酒,古指國有喜慶,特賜臣民聚會飲酒。那麽按照前面的翻譯方法,那就是君王賜大家飲酒五個月……這科學嗎?
不過貌似也不能怪司馬光巨巨,關于項燕之死,在《史記》中就有兩種不同說法——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二十三年,秦複召王翦,疆起之,便将擊刑。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荊王。秦王游至郢陳。荊将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史記·項羽本紀》: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将項燕,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将,封于項,故姓項氏。】
喏,項燕到底是被俘還是被殺,還是俘虜了之後自殺……史書真是比較難解的一個謎啊。
除了人物是怎麽死的,同樣記載相悖的問題也有很多,我再舉一個例子。
史記上說俘虜燕王喜和破齊也有李信參與,但《資治通鑒》上這兩段軍事戰役跟李信沒啥關系,只說他參與了最開始的伐燕。
【《史記·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而王翦子王贲,與李信破定燕、齊地。】
【《資治通鑒》:始皇帝下二十五年(己卯,公元前二二二年)大興兵,使王贲攻遼東,虜燕王喜。
始皇帝下二十六年(庚辰,公元前二二一年)王贲自燕南攻卉,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裏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
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奸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日:“松耶,柏林,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沒錯,這段歷史,在史書上,也就是短短的幾段話,甚至就是一句話而已。但《資治通鑒》上所書的這段歷史,李信的名字壓根就沒出現過。
這裏其實就能看出端倪了,寫《資治通鑒》的司馬光也許認為李信打了敗仗,就不會被秦王所重用。但從我所查到的各種史料的字裏行間來判斷,秦王政是絕對不會如此的。
連承認自己是問客的鄭國,秦王都能重用他,更何況是領兵的将軍昵。一将難求,勝敗乃兵家常事。
以李信的這個例子,其實就可以反證前面的魏王假應該是被俘虜了,只是為何最後沒有被秦王安置郡縣,那就有可能有各種各樣的意外了。
所以史書真的是不斷再加工的産物。歷史是勝利者所書寫的,這個說法我是一直堅信的哦。
順便說下鹹陽城牆的考據。
鹹陽是真的沒有城牆的,《史記·滑稽列傳》中胡亥的某件轶事裏所提到的“欲漆其城”,恐怕是指的長城或者宮殿的牆壁。
劉邦進攻關中之時,也是讓武關的秦将反水,在進入關中之後,也并沒有大規模的攻城戰記錄,只有平原遭遇戰。喏,具體情況若是設定允許,我會在下一本《啞舍·零》裏面寫到的。
除了《史記》和《資治通鑒》這兩部史書外,我還查過各種各樣的資料。例如寫到黃河的水文資料時,所查的《水經注》。必須要吐槽古代時黃河不叫黃河,就是叫“河”,
長江也不叫長江,而是就叫“江”。寫得我這個別扭啊……
還有為了寫老板煉丹,我讀了《大洞煉真寶經妙訣》《石藥爾雅》《丹方鑒源》《魏伯陽七返丹砂決》《太上衛靈神化九轉丹砂法》《神仙煉丹點鑄三元寶照法》……感覺越看越入迷是怎麽回事,哈哈!其實還挺好玩的,寫的都是許多稀奇古怪的配方,還有詳細的煉丹手法……當然,感覺實際做出來就是做毒藥……
話說我査資料的時候還查到一個有趣的事實。
【《史記·秦始皇本紀》: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這裏說說“車同軌”。本來我以為所謂的車同軌,也就是修建了馳道,車輪的間距有規定的距離,不能超标而已。
結果,所謂的馳道其實就是軌道,木材鋪設的鐵路。
看到這裏大家是不是都震驚了?鐵路哦……而且還發現了遺址。就在河南南陽的山區裏,最近幾年發現的。
“經碳14測定,這段軌道是2200多年前的秦朝遺留。原理和現代鐵路無異,還是複線,不是用蒸汽機車牽引,而是用馬力拉動。專家們都驚嘆2200年以前我國古代竟然已經有如此先進的交通設施。這将是比兵馬俑更驚人的大發現。”
“現在鐵路不是鐵鑄造的,而是軋制的鋼軌。秦始皇的‘軌路’當然也不是鐵鑄造的,而用木材鋪設。作軌道的木材質地堅硬,經過防腐處理,至今尚完好。不過枕木已經腐朽不堪,顯然沒有經過防腐處理,材質也不如軌道堅硬,但還可以看出其大致模樣來。”
“由于使用軌道,摩擦力大大減小,所以馬也可以一次拉很多貨物。專家認為這是種最最節省的使用馬力的方法,或者說是一種效率極高的方法。公認的速度至少應該一天一夜六百公裏,有的人認為七百公裏。這是比八百裏加急還高接近一倍的速度。無怪乎秦始皇可以不用分封就有效地管理龐大的帝國,并且經常動辄幾十萬人的大規模行動,而且還一年年地經常往外面跑。東巡無數次,看史書上記載的時間就能計算出他出巡一個來回的速度相當快了。
上面引用了一些新聞報道,詳細的內容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查查,特別令人驚嘆。
以此來推斷,所謂的“車同軌”,應該就是因為軌道的間距是固定的,所以所有車車輪之間的距離必須符合國家标準,才能在馳道上行駛。
怪不得被稱為“馳道”,而不是普通的道路。
越了解秦朝的歷史,就越覺得秦始皇巨巨是穿越的……好吧,我腦洞又大開了……
類似星相、占蔔、服飾、玉石、首飾之類的資料書我看得就更多了,暫且不提。
以後有機會的話,我整理整理,順便出個與“啞舍”相關的歷史吐槽資料書,都是
“啞舍”寫到的故事背後的歷史知識,都特別好玩。因為篇幅問題,也都是沒辦法在正文中體現的。
總之,又完成一本“啞舍”啦,總覺得這個坑是越挖越大的趨勢……還有好多好多想要寫的東西……去面壁一會兒……
※·※
鄭重感謝一下中南天使的老板鄒輝先生、鄧理主編和綠貓等文編的努力,還有美編妹子們的支持。《啞舍·零》的漫畫版改編也要非常感謝梁潔主編的大力支持。
當然,還要特別感謝下曉泊,現在“啞舍”開業正好已經五年,從插圖到畫集,再到漫畫,和他的合作也越來越好,《啞舍·零》的漫畫版也在《神漫》上開始連載,我們一起繼續努力。
最後還要多謝讀者朋友們的支持,“啞舍”的成長也離不開你們的關注。如果喜歡這個故事,喜歡這家店,喜歡老板,郡麽就請繼續期待吧!
“啞舍”一本書十二個故事,一個月一個故事,一年一本書……真的咩?自從去年《啞舍·肆》出版延後之後,我的規律就被打亂了,所以先寫了《啞舍·零》,《啞舍·伍》估計要2016年才能出版了……這還算快的……我努力!
所以,下本見喽!~(≧▽≦)/~
玄色于2015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