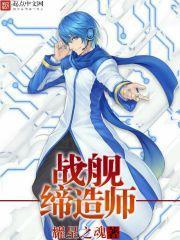第61章 最沒勁是戰群儒
論起雅舍之崛起, 實乃水到渠成, 卻又別有淵源。
本朝尚武, 武将、武生地位尊崇, 自不必說。且聖上喜開疆拓土,四鄰來朝之盛。
年輕人但凡有幾分真本事, 入了軍營,經過歷練, 要不了幾年, 總能成就一番事業,就是封妻蔭子,也全不在話下。
可是,做文臣就難多了。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天下才子, 真如雨後春筍, 一茬又一茬。科舉卻只三年得一回, 還需千裏跋涉,遠赴京城參試。
窮苦書生, 要麽沒有路費、盤纏, 不得進京;要麽常年苦讀,身子虛弱, 還沒走到京城便病死異鄉;再或者有些經不住誘惑的,鄉野荒廟、秦樓楚館、煙花柳巷,遇見了知音,就此堕落……不一而足。京城路遠, 那高高的城門,就不知攔住了多少才子。
而且,哪怕,歷經千難萬險,最終到了京城,春闱嚴寒,單衣陋室,連試三天,能順利下場者又寥寥無幾。
再有時運不濟者,空有滿腹才華,卻屢試不第,最終心灰意冷,潦倒終生。
總之,真正能金榜題名者,萬裏挑一。就這些人中,狀元郎當七品官者,照樣有之。
士子入朝難,且文人相輕,俸祿微薄,真正能清廉正直,養家糊口,少之又少。那入閣拜相者,又有幾個真的是白身?
至于像林如海這等勳貴出身的翰林,自然另當別論。
可是,治國安邦,卻獨獨少不了文臣。教化萬民,更是切切需之。故而,文臣總是有幾分清高孤傲又格格不入的格調,手無縛雞之力,舌燦蓮花卻能。
當今天子,最是将文臣脾性摸得透徹,重用文臣,推動教化,卻對言論、文字管控也尤為嚴格。
口誅筆伐,字字誅心,文人說出的話,有時賽過武将千軍萬馬。當今深知此理。
而林如海曾為禦史言官,聖上心腹,又乃宰輔杜明得意門生,同年故舊也可謂遍布朝野,自然深知聖心。
從前,沒動過開書閣的主意也罷,既然黛玉提出了,林如海便要幫她辦成,且要辦得漂漂亮亮的。
黛玉前腳離開,後腳林如海就給皇帝上了折子,将書閣構思說了,明言一為書籍張目,二為士子鋪路,三為言官開道,四嘛,為聖上耳目。
皇帝一看,禦筆朱批,大大一個“善”字。
如此林如海才敢明目張膽去揭匾,更請了恩師親筆題寫匾額。
這雅舍既然有了這般驚人的來頭,想不在京城竄紅也難。
何況,黛玉和林如海也是真心為士子謀福。拿出的善本、孤品全是林家幾代珍藏。更有林如海從恩師、同年乃至同僚、親朋處獲贈,淘換甚至奢借的。當今也喜讀書,曾為皇子時,便是文武全才,大內藏書,有些不甚機密的,也任由林如海命人抄錄。
相當于傾舉國之書袋,興一家之書閣,如何不包囊萬象,莫可匹敵?
再有,書閣要求,士子抄書可自帶筆墨,無者,亦只需出幾個銅板,抵作紙張錢。除謄抄的第一本書要交給雅舍外,之後再謄抄多少,均可自己留下。也可攬活兒替他人謄抄,價格自談,只彼此均需言而有信,否則,無論你是王公大臣還是宗親豪紳,一律趕出門,再不接待。
這還只是書閣最基本的營生,真正引起文人轟動的,還是二樓的論與三樓的賞。
文人墨客,誰沒點雅癖嗜好,誰不想棋逢對手琴遇知音?雅舍全能滿足你。
等到黛玉自己玩心起了,又開了內舍,越發勾引得後妃們都想出宮一游了。
短短數月工夫,雅舍便成京城一景,但凡瓊林人,不到雅舍非好漢。
有了這等前情,京城發生逆案,且是兄弟阋牆,外人雖不明就裏,但沒有不透風的牆,最怕的就是閑言碎語。文人們的嘴——防人之口,甚于防川。
雅舍動向,聖上十分關心。
不過文人也不是傻子,真正勇不畏死者到底少之又少。內城大街小巷一片死寂之時,雅舍雖仍門戶大開,除了常住此處的窮儒酸生,士子、文臣一個也不敢登門。
還是近日,宮裏放出話來,七夕将至,依舊例大肆慶祝,內務府采買人員內外城這麽一轉悠,徹底放出風去,風頭過了。那些縮居的人這才敢露頭,雅舍才三三兩兩又有了客人。
人一多,就會有人管不住自個兒嘴。聖上旁敲側擊一說,林如海就得行動。
可是,防患未然為先,真等那群不知深淺的文人闖出了禍,興了大獄,豈不違逆黛玉初衷,大傷其心?
林如海如何也不舍得,故而提前給黛玉放了風,讓她安排人控制場面,引導風向。
聖上理政最勤,興利除弊,發展生産,國力日盛。弘皙謀逆,确屬逆天而行。一将功成萬骨枯,放着太平盛世不要,非得自己創個盛世霸業,不是明君,只是國賊。
對比,黛玉看得清清楚楚。
只是,似黛玉這般“小女子”見解的人并不多。
黛玉還沒下車,就聽見大堂裏傳來激烈的争論聲。
雅舍掌櫃林周自然認得自家姑娘的馬車,早迎接出來。見英蓮撩着車簾,黛玉探頭張望,卻不下車,趕忙湊近前,低聲道:“回姑娘知道,這回兒裏面正熱鬧着。不知怎地,士子、秀才來了好多位,達官貴人也不少,其中就連南安郡王世子霍霖也在。”
“哦?霍霖?”黛玉疑惑問道。自打圍場別後,她便再沒聽過霍霖消息。至于南安王府,雖然僥幸逃過一劫,但是,南安王主動請辭,交了兵權。皇帝只是嘴上客氣了幾句,二話沒說就答應了。如今南安郡王也不過賦閑在家。這種時候,霍霖不在家裏閉門思過,跑她家雅舍幹甚?
黛玉還在思量,見林周欲言又止模樣,挑眉問道:“周叔有何顧忌,但說無妨。”
林周四下看了看,路上并無甚人,大堂裏那群人舌戰正酣,根本沒人主意到外間情況,這才壓低聲音道:“您外祖家,榮國府寶二爺也在。”
“寶玉也在?”黛玉脫口問道。
林周點頭,“他原先倒不曾來過。今日像是來湊熱鬧的。老奴引他去二樓雅座,他卻不肯,非要和那些秀才們擠在一處。老奴看他身邊也只有一個小厮伺候着,不像是府裏老太太的意思。”
黛玉冷了臉。寶玉不是向來看不起國賊祿蠹嗎?他擠在這群讀書人堆裏幹什麽?簡直比霍霖還不知所謂。黛玉心裏一急,跳下馬車,就要往裏闖。
孫氏一個沒拉住,眼瞅着黛玉就要闖進去,斜刺裏,竄出一位白衣公子,橫身擋在了黛玉面前。
“林妹妹留步。妹妹這樣子進去,豈不是白白便宜了屋子裏那群沒見過世面的俗人?”永玙搖着扇子,搖頭晃腦地道。
黛玉萬沒想到會在此時碰見永玙,擡頭就看見他又換上了那身纨绔子弟的打扮,想起裏面一屋子“不學無術”的家夥,忍不住挑眉問道:“你怎麽也來了?”
永玙因着不久前那場對話,本來還有些羞赧,見黛玉坦蕩磊落模樣,相形見绌,忽覺自家怎地這般小氣了,收起绮念,一本正經地道:“這雅舍裏可也收着我們家不少孤本名作呢,便宜這群酸儒以博妹妹一笑也罷,再被他們曲解了去,禍國殃民,本世子可不允許。”
“合着你還是心疼自家那點兒東西呀!”黛玉聽着那句妹妹,到底有些耳熱,故意調侃道。
“嘿嘿,”永玙腆着臉湊近一點點兒,輕聲道,“都是給妹妹攢的。”又怕言語過分,惹了黛玉的厭,趕忙找補道,“林妹妹,且請二樓雅間看戲,這幫人,區區在下,一根手指便可應付。”
黛玉睨他一眼,“如此,我可瞧好了。”說罷,在林周招呼下,和孫氏等人一道,從旁邊側門,直接轉入了二樓雅間。
那邊廂,永玙接着搖扇子,晃起八字步,身後跟着提着金絲鳥籠的文竹,邁步進了雅舍大門。
門內,以霍霖為首,分四方坐了四撥人。
永玙也是才解了禁就跑去林府拜訪,被應妙陽告知黛玉來了雅舍,掉頭就追了過來。只遠遠看了幾眼大堂情形,就見黛玉悶頭往裏闖。哪裏舍得自家林妹妹被一群俗漢看了去,箭步沖上前,攔住了。這會子,走将進來,才把屋內情況看分明。
二樓雅間內,林周推開雕花窗棂,指點下面人物與黛玉看。
“趕巧了這幾家,正和了四位異姓王。東面的是東平王妃母家侄子藍善,家裏給他捐了個大內侍衛,現屬禁軍編制。西面那個,是西寧郡王家庶子金祥,是個沒事人,整日在外閑混。南邊的是霍霖,倒是幾位裏最出息的一個。至于北邊這位——”林周一一指點道。
黛玉随之望去。藍善、金祥都是一臉傲氣,無甚出奇模樣,她只看了一眼便扭過頭去。而霍霖,經過圍場兵變,整個人倒是成熟許多,褪去了那些遮掩不住的傲氣,卻也顯得暮色沉沉,有矯枉過正之嫌。
“北邊的怎麽了?”黛玉看着北邊坐着的那位書生打扮的少年,不解問道。
林周又壓低了聲音道:“這位恕老奴眼拙,竟一時認不出來。可他見解不凡,在那三位來之前,一個人辯跑了十幾位酸秀才,這才得了那個位置。”
“哦?想來是個有本事的人。那寶玉呢?”黛玉問道。
林周指了指那藍布袍少年身後三步遠距離站着的一個人,“寶二爺便在這兒。他聽了有些時候了,卻不見說話。”
黛玉點點頭。
寶玉戴着書生帽子,黛玉從上往下,看不見他的表情,也不知他站在旁人背後,在想什麽。
“我當是誰?妄議國事,還敢有這般大的陣仗,原來是南安郡王世子呀!”永玙陰陽怪氣地道。
本來在座四方正争得面紅耳赤,有罵人的,有褒揚的,有引古的,有論今的,有呼天搶地的,也有故作高深的……都是七情上面,全沒工夫注意永玙。
可是,永玙這一開嗓,聲音不高不低,語氣不疾不徐,卻偏偏輕飄飄地就飛進了所有人耳中。真瘋的假傻的,都停住了。目光齊刷刷聚到永玙身上。
不看還好,一看各個兒吓了一跳。
這少年好風采!
當庭一立,似寶劍出匣,賽芝蘭玉樹。劍眉飛揚,星目攝人,偏偏,面上神情清冷無比,目無下塵。薄唇微挑,便是睥睨天下的姿态。
嘴裏說出的話,更比他的模樣驚人。
衆人看罷永玙,都是驚嘆,卻也忍不住回頭去看霍霖。在場衆人許多做作,八成便是沖着霍霖去的。畢竟,圍場裏的事,知道的人并不多。南安郡王就是被奪了兵權,也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巴結上了霍霖,自然前途無限。
可是,永玙一進門就把霍霖貶得一無是處。
霍霖擡眼看了看永玙,別人不認識永玙是誰,他卻門清。想起這些日子,他在家中受的閑氣,和父親的教誨,咬咬牙站起身,躬身給永玙行禮道:“不知賢親王世子駕臨,霍霖——”
“別介。小爺可受不起你這一拜。”永玙說着,負手在大堂內溜達起來,邊道,“怎麽此處便是大名鼎鼎的雅舍?不見士子抄書,沒有墨客作畫。除了銅臭就是酸腐,還有人學那等市井小民做井底之談、紙上征伐,啧啧,不倫不類,不三不四,不學無術,不……”
随着永玙語聲,适才那些争論得最激烈的人都臊紅了面皮,卻畏懼永玙身份,敢怒不敢言,眼裏面上都是郁忿之情。
永玙卻渾不在乎,正停在金祥面前,卻轉身指着文竹問道:“文竹,你說,還有‘不’什麽?”
“不知所謂,不顧死活,不懂裝懂,不根之談,不攻自破,不仁不義,不測之禍,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文竹那張嘴,開了口,就如決堤之水般一氣兒奔騰下去,半點面子也不留。
“放肆!不過一個小厮,這裏哪有你大放厥詞的地方?我等文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如今,國朝不穩,風雨飄搖,我等更該身先士卒,激揚時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一個五十上下,一身藍衫的山羊胡老文士受不住文竹譏諷,跳起來,反唇相譏道。
永玙就愁旁人顧忌他的身份,不敢插話,這才給文竹使眼色,讓他出頭。正好立時便有傻子撞上門。
永玙勾勾手指,便有雅舍夥計搬來太師椅。永玙好整以暇坐下,夥計奉上熱茶,永玙吹着茶沫子,擡頭往雅間瞟了一眼,正對上黛玉目光。
低頭,勾唇一笑。
永玙慢悠悠開口道:“打住!就你編的這套八股,怪不得白了頭還不如我家小厮。小爺且問你,何謂國朝不穩?怎生風雨飄搖?是路有餓殍、民不聊生還是科場舞弊、官官相護?是不許吃閑飯的文人說話了還是卸磨殺驢八道金牌自毀長城?”
永玙連串诘問下來,那老頭兒汗出如漿,卻一句話兒也不敢接下去。
他乃南安王府門客,和賈政養的那撥閑人并無二樣。肚子裏沒有幾兩墨水不說,還沒有眼色,總不得用。好不容易有了機會,陪在霍霖身邊,見霍霖受辱,有意出個風頭,顯擺顯擺,也是個忠心護主的意思,卻不成想一下子捅了馬蜂窩。
“小爺問得太狠?太虛?你答不上來。那小爺跟你說點你們這些人總挂在嘴邊兒上的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小爺聽說,黃河水患,每年必發,你可有疏導良策?今夏雨水少,北邊兒眼瞅着就要鬧旱災,農田灌溉,水文地理,幾個人能說上來?遠的不提,平安州前不久鬧了蝗災,流民大批進城,你們說是讓進還是不讓進?”永玙拿折扇敲着太師椅扶手,每敲一下,便問一句。
将才永玙質問“國朝”時,尚不服氣,仍舊梗着脖子暗地耍橫的窮儒們,這會兒徹底沒了聲息。
空談容易,實幹誰會?別說水患旱災和蝗蟲,這批秀才,講究君子遠庖廚,柴米油鹽醬醋茶只為應對琴棋書畫詩酒花,米面怎麽賣,糧食咋種的,十個裏八個人不知道。
鴉雀無聲,落針可聞。
在這一片靜谧裏,卻突兀傳出一片沙沙聲響,是毛筆滑過宣紙的聲音。
永玙帶頭望去。大堂最偏僻的角落裏,兩個長衫少年正頭挨着頭奮筆疾書,面前書稿已摞起老高。對周遭發生的一切,二人猶如未聞。
黛玉站高望遠,一眼認出,其中那個穿白衣的人正是趙煦,不由得回頭去看英蓮。
英蓮果然笑眯眯點頭。
原來,今日一大早,雅舍便莫名其妙來了許多閑人,風言風語亂說話,惹得許多膽小的文人都避走了。
趙煦被煩得受不了,只得挪到角落裏去,自顧自看書,抄書。
正好,也有一個少年,看去不及弱冠,也捧着一摞書,和他坐到了一處,兩人倒是一拍即合,認真做起學問來。不僅黛玉到了,趙煦沒發覺,就是永玙那番質問,他也沒聽見。
永玙背着手走到二人身後,探頭張了一張,見兩人竟是在做策論,議的還就是平安州的蝗災。有理有據,切實可行。
“好!”永玙撫掌大笑,“這才是治國平天下的樣子。打擾二位,把您高見,給這些庸才聽聽。”永玙躬身向趙煦擺出恭請姿态。
趙煦還要拒絕,遠遠看見林周向他點頭,與少年對視罷,雙手将寫滿對策的紙張遞給永玙。
永玙轉手拍給了那個高坐北面位置書生。
那書生卻也不客氣,接過宣紙,大聲誦讀起來。
“論平安州蝗災治理與災民安置……”
書生語聲在雅舍內回旋。漸漸,便有些文生打扮的人悄悄從雅舍溜了出去。
等到書生讀完,放下紙張,大堂裏竟只剩下了藍善、金祥、霍霖、寶玉和他們各自的随從。
藍善和金祥彼此對視,起身向永玙行禮,灰頭土臉離開。霍霖卻還不動。
永玙沖他挑挑眉,開門見山道:“怎麽,看來霍世子此來倒和朝堂大事無關。難不成是沖着七夕百花宴?”
從頭到尾一直呆呆站着,不曾說過一句話的寶玉聽見“七夕百花宴”五個字,忽然擡起頭,整個身子都顫了顫。
二樓雅間裏,黛玉雖被永玙戰群儒風采所迷,卻也沒忘記觀察衆人神情。此刻自然發覺了寶玉的異常,又聽見永玙問話,罥煙眉緊緊擰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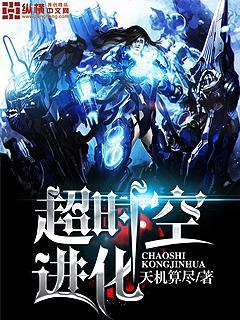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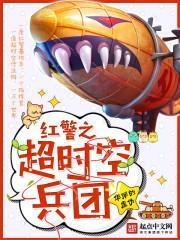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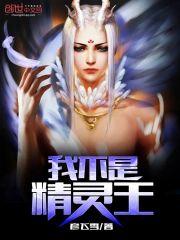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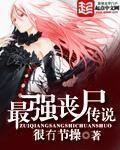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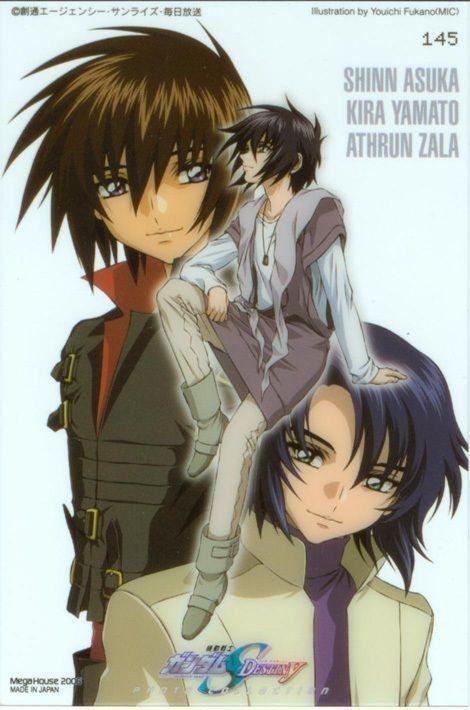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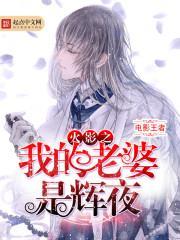

![[神夏+HP]以探案之名](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32779.jpg)
![[綜武俠]俠客們的反穿日常](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2907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