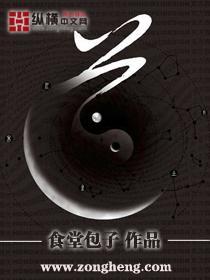第27章 僖宗、昭宗和哀帝:(2)
最差的,但恰恰是這最差的條件,成就了他和他的後梁。
何以這麽說呢?
要知道,朱溫與諸藩鎮不同,諸藩鎮大多不過是朝廷自己的兵馬,只是日漸坐大,最終形成了自己的勢力,終于可以和朝廷分庭抗禮了。然而正是這樣一個原因,他們反而對李唐宗室懷有幾分忌憚之心。比如說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他是最早将昭宗控制在手中的,盡可以挾之以令諸侯,可是由于他的官兵出身,他每逼迫昭宗一步,無形中都讓自己的形象更顯得不堪。到他火焚長安宮室、驅逐昭宗的時候,他的道義資源已經耗盡,近乎破罐子破摔了。此時他在諸藩鎮心目中的形象,已經是欺主的惡奴,再也無法獲得支持。
相反,朱溫原本是強盜出身,是食人狂魔黃巢手下的大将,只是因為自己的勢力愈發坐大,引起了黃巢的不安,為求保身,索性投靠了唐室。
所以在諸藩鎮中,朱溫是不具絲毫道義資源的,仍然是一介賊寇。而賊寇幹出什麽壞事來,都是可以理解的。這反倒讓朱溫在逼迫昭宗的時候,沒有任何心理負擔,更不會背上太多的惡名——他已經惡到底了,再加上這麽一樁,也不過如此而已。
孔子曰:春秋責備賢者——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做好人是要吃大虧的,而做一個壞蛋,卻是占盡了天下的便宜。惡人做了惡事,是理所應當可以理解的,而好人哪怕是品德上稍有污點,都難以獲得諒解。
朱溫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惡棍,在黃巢手下幹久了,沾染上了幹壞事沒有底線的壞毛病。他淫行公然扒灰,刑殺不分骨肉。史書上記載說,在他晚年的時候,幾個兒子争寵,于是朱溫就下旨命幾個兒媳婦入宮,輪番讓他幸禦——這種事情都幹得出來,諸藩鎮再壞到家,也是沒法與他相比的。
實際上,對好人苛刻無端、對惡人無限寬容,惡化了大唐帝國末年的生存環境,導致了社會出現逆淘汰現象。對好人苛刻無端,導致了我們身邊的好人越來越少;對惡人無限寬容,導致了我們身邊的惡人越來越多。當惡人的數量達到足夠高的比例時,整個社會的文化走向,就以惡為價值取向,表現為越是邪惡之人,越是容易占到上風;越是善良之人,越是受到公衆的嘲弄。
這個規則并不是大唐高祖李淵創立的,但是他奪得大寶之後,并沒有對此稍加改良,反而以邪惡的皇家權力,進一步惡化了這種态勢。當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徹底轉向邪惡之時,這最終的惡果,就只能落到李淵的子孫頭上了。
所以,當我們在社會上占據主導位置的時候,就有必要建立一個公正無私的社會競技法則。這個法則表面上看起來讓我們吃虧,但卻會加倍回報在我們後人身上。所以規則從來不是為我們自己所建,是為我們子孫後代撐開一片天空。
盡管面臨着如此惡化的社會環境,但大唐帝國仍然有機會,只不過,無論是僖宗還是昭宗,他們都錯過了這個機會。
這個機會,就在沙陀軍事将領李克用身上。
如前所述,諸藩鎮或是原有的官兵,或是投降的賊寇,只有李克用是從邊境調入的少數民族軍隊。相比于國內諸藩鎮,沙陀人對中原文化較為生疏。實際上,李克用是從儒家的書本上了解中原的,而儒家的書本,向以仁義為核心。結果事情搞到最後,諸藩鎮之中,只有李克用這個外國人還保留了儒家文化的印痕,而其他人,只把書本當成哄呆子的廢紙。
或許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想法在作祟,盡管李克用将食人狂魔黃巢剿殺殆淨,又曾解救過昭宗的危局。可是昭宗卻對李克用心懷忌憚,不敢将自己托付給他,結果錯失了最後挽救大唐的機會。而事實上,正如我們所知,當李克用百戰身死之後,其子李存勖承襲家業,卻仍然采用了大唐的國號。這表明,沙陀人真的被儒家書本感化了,他們一直在懷祭大唐。
假若懿宗或昭宗能夠稍有眼光,選擇沙陀人李克用,讓他承擔起替皇權護法的工作,不排除歷史被重新拉回到肅宗李亨時代的可能,盡管終究無法改變帝國的毀滅,但垂死掙紮幾下,這卻是很刺激的——然而歷史不能假設,因為人性無法改變,所有的假設都是基于違背人性的構設上。說到底,所謂歷史的規律,不過是人性的規律,人性規律如此,歷史也因此被注定了唯一。
比較一下唐宗室所面對的這些敵人,李克用比諸藩鎮可靠,諸藩鎮比朱溫可靠,朱溫比皇帝身邊的太監可靠。而昭宗最後的選擇,卻是帶着太監走入了朱溫的軍營,他選擇了最不應該選擇的路,正如大唐開國之初,李淵選擇了最不應該選擇的一樣。不是昭宗有多蠢,也不是李淵有多麽的聰明,他們只是人性規律中的兩個必然步驟,由此而及彼,如此而已。
Advertisement
當大唐帝國的汩汩塵風就此沉寂,我們于歷史之中解讀出皇權的本質邏輯就是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