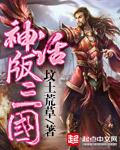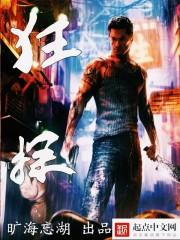第3章 (2)
最萬無一失的所在。沒想到,四年前的一個冬夜,一場大火燒光了柏梁臺!
問題是,那石鏡水火不侵,就算遇火,也不可能被燒毀。可我命人篩遍了火場的每一寸灰燼,都沒發現那石鏡的蹤跡。所以,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有人故意縱火,趁亂偷走了石鏡!
我命人搜遍全城,結果發現,就在柏梁臺失火的那個晚上,有一個人曾連夜出宮,不知所蹤。我立刻诏令天下各郡國,緝拿此人,但他卻像從空氣中消失了,再也沒能發現他的蹤跡。
直到第二年,他才再次出現,那時他已經在匈奴,并且還被匈奴封為丁零王。
現在,我想你大概猜出那個人是誰了吧?對,衛律!那個叛國投敵、後來還助敵攻漢的逆賊!
他曾和你一樣在宮中為郎,不知道你是否……認識?
哦,對了,那時你早就去了栘園。
那逆賊在宮中多年,很了解宮中的地形、人員職守,也很清楚阿妍在我心中有多重要。
他做得很成功,用這種方式給匈奴人獻上了一份絕妙的見面大禮——直到現在,我還沒完全從石鏡失蹤的打擊中恢複過來。這、這簡直等于把我的阿妍又殺死了一回!難怪他區區一介騎郎,一到那邊居然被尊為王侯。他太聰明了,什麽事最能刺痛我的心,他就做什麽事!
不!我不甘心!他盜走的若是別的什麽金玉珠寶,倒也罷了,可他盜走的是石鏡,關系着阿妍的魂魄的石鏡!為了阿妍,我說什麽也要找回那面石鏡!
然而這又是多麽渺茫的事!以匈奴與我朝的關系,就算派人去了,也未必能找到那東西,就算找到了那東西,也未必拿得回來。
現在那邊居然主動示好,送回了此前扣押的所有漢使。真是天助我也!我已經宣布,同樣釋放此前扣押在漢的匈奴使節,并遣使護送他們回去。
我想,你大概已經明白,我要做什麽了。是的,我需要一個使臣,一個負有特殊使命的使臣,到那邊去找回那面石鏡!
這個人很難選。關鍵在于,潛英石鏡不是一件普通東西,它是術士的法器。
我聽說過,巫蠱詛咒不是世間普通的勇武或智慧能克制的,但它會在兩種人身上失效:一種是修道之人;另一種就是完全不信的人。朝廷裏沒有修道之士,所以我選擇了你,一個完完全全不信方術、不懼方術的人。并且要你完全出于自願同意——做這種與方術打交道的事,內心的意願最重要。
說吧,你願意嗎?
◇◇◇◇
雨勢越來越大。密集的雨點打在昆明池中,已經聽不出噼啪作響的點點雨聲,只聽到一陣陣或疏或驟的嘩嘩聲。池水一下又一下拍擊着石砌的池岸,站在高大寬闊的靈波殿中,也偶爾會被狂風裹挾進來的雨點打到。
他終于明白今天這一切莫名其妙的事為什麽會發生了:因為皇帝瘋了!
不,那不是一般的瘋狂,那是一種理智和迷亂并存的瘋狂!皇帝知道發生的一切,可全都用自己那套毫無理性的念頭來解釋。
什麽關亡術,什麽輕如毛羽的招魂石鏡,什麽夜焚柏梁盜竊法器,簡直是白日見鬼!
少翁如果真是能起死者于地下的神仙高人,怎麽會連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
衛律的叛變明明是起因于李延年的倒臺,此事朝廷早有定論。那年他出使匈奴,回來正碰上李家勢衰,将有大禍。衛律和李家關系密切,當初得以出使,就是延年兄弟出的力,因懼怕株連,這才叛逃的。
這些都是明擺着的事,皇帝怎麽會視而不見?
問題是現在他該怎麽辦?接受那個荒唐的命令?
“陛下,”蘇武小心翼翼地道,“人死不能複生……”
“住口!”皇帝忽然暴怒起來,“你這是什麽意思?別以為這世上就你一個明白人,別人都容易受騙上當!朕親政治國的時候,你還是個三尺孩童!告訴你,朕腦子清醒得很!比任何時候都清醒!”
蘇武連連叩首,惶恐地道:“臣不敢,臣豈敢對陛下心存不敬……”
“你不敢?”皇帝一揮手,冷笑道,“你已經這麽做了!你和許多人一樣,別看恭恭敬敬地跪在朕面前,可在心裏,你從頭到尾就沒相信過朕的話!你認為朕是個瘋子,你以為朕被李夫人的死弄得神志不清了,以為朕不知道?!好,朕也不強求你相信。你可以當朕見到阿妍只是幻覺,可以當石鏡的怪異是朕的幻覺,但幻覺不會焚毀一座七十丈的高臺,不會制造出一面石鏡再讓它失蹤!你不是跟太史令熟嗎?待會兒問問他去!他親自鑒定過那石鏡的銘文!這世上有些事你永遠不會了解,也永遠不會明白!”
蘇武道:“是,臣愚昧……”
皇帝打斷蘇武道:“不,你不愚昧,你只是和朕根本不是一類人!算了,朕只問你一件事:到底願不願意去?”
願不願意?
中郎将,秩比二千石,持節出使,無上榮耀,他會不願意?不要說此時局勢緩和,就算明知一去不複返,他也願意啊。被庸碌無為的生活慢慢殺死,難道就好過驚心動魄地死于非命嗎?
可問題是,他明知這是一個亂命,怎能趁着皇帝一時糊塗,竊取本不該屬于自己的好運?他沒有任何經驗,對那邊一無所知,萬一贻誤國事……
“說啊,去不去?”皇帝看出他的猶豫,有些不耐煩了,“朕只要你說實話,不必勉強,也不用擔心。不管你肯不肯,朕絕不會怪罪于你。”
不,不能這樣。皇帝發瘋了,他能跟着一起發瘋嗎?
可、可過了這一次,恐怕就再也沒機會了。這不正是他暗暗渴盼的命運轉機嗎?難道他願意一輩子就待在那個肮髒的馬廄,永無出頭之日……
“臣願為陛下做任何事情。”終于,他艱難地道,“可是出使異域,非同小可。臣才具有限,只怕誤了國事……”
皇帝一揮手,打斷了他的話:“不,用你是朕的選擇。誤不誤事,是朕應該擔心的事。朕只問你的意願,告訴朕實話,你到底願不願意?”
蘇武道:“臣不敢欺騙陛下,若問臣本心,求之不得。可臣甚至、甚至連一句胡語都聽不懂……”
“你願意就行!”皇帝松了一口氣,滿意地道,“準備一下,下個月就出發。副使張勝懂胡語,熟悉蠻夷事務,和匈奴交涉的事,他會辦妥的。記住,朕用你,不是因為你會和匈奴人打交道,而是因為你能和一種奇怪的力量打交道!”皇帝頓了一頓,看了他一眼,眼裏有一絲疑惑的神情,“說實在的,朕有時真有點弄不懂你。你父親和匈奴人打過仗,還在邊境做過多年太守,而你居然一句匈奴話都不懂?”
蘇武低頭道:“是,臣是先父最不成器的兒子。”
皇帝搖搖頭,道:“他好像不太喜歡你,從不給你機會放開手腳做事。罷了,現在機會來了,好好把握吧。朕再說一遍,朕不是要你做使節,是要你去尋找一件重要的失物。記住這一點!”
蘇武點點頭。
好吧,盡力而為,成敗由天。他會盡自己的努力做好一個使節,完成這次出訪。
至于那個什麽招魂石鏡,他壓根兒就不指望能找到,因為這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這種荒謬絕倫的東西。當然,他還是會奉命去找的,只是為了證明皇帝的妄想的錯誤。
他不認為皇帝會為了一件不存在的東西殺了他,因為沒有一個統治天下的帝王會發瘋那麽長時間而沒人發現,無人谏阻。但願他歸國時,一切已經恢複正常了。
◇◇◇◇
未央宮北,石渠閣。
精心打磨的白石砌成了一條長長的溝渠,從閣前蜿蜒經過。因為剛下了一場大雨,所以渠中清水潺潺,水量比平日大了許多。聽說遇上連降大雨的時節,渠中還會有從滄池游來的小魚,在這森嚴得叫人喘不過氣來的未央宮一帶,倒實在是一道頗為宜人的小景致。閣以渠得名,不過,這條石渠的作用卻不單是一種裝點,更主要是為了防災——因為這裏收藏着整個帝國的歷史。
走進閣中,一股竹木的氣息就撲鼻而來。
一排排、一列列堆滿簡牍的書架向閣中深處延伸,一眼望不到頭。從開國丞相蕭何自秦國宮廷收集來的圖籍文書,到此後歷年積存的文檔秘錄,無不彙聚在此。自建成至今,這間巨大的藏書閣還未發生過一起偷盜或火災。看來當初蕭丞相把石渠閣定址在此确有遠見——還有比托庇于帝王的起居之所更安全的所在嗎?
蘇武站在一排排書架之間,前後左右,觸目所見,都是鋪天蓋地的簡牍。對這些東西,他有些敬畏。他雖然識字,但和周圍許多将門出身的郎官一樣,很少接觸這個文人儒生的聖地。
那些厚重的史料,晦澀的古文,對他都是只能敬而遠之的東西。
也許只有大名鼎鼎的太史令能讀得完那些東西吧。他是當朝最善于與文牍古籍打交道的人。聽說他的父親——前任太史令司馬談,在他十歲前就開始教授他先秦諸子之說。十歲後,又先後師從董仲舒、孔安國研讀《春秋》、《尚書》等古籍。所以,二人雖因曾同為宮中郎官、又都是京兆人而交好,但在這位家學淵源、學識廣博的同僚面前,蘇武總有些自慚形穢。
“沒想到,陛下居然選擇了你。”太史令捧着一卷絲帛,從兩列書架深處走出來,道,“子卿,我真羨慕你。”
“羨慕?”蘇武苦笑一下,道,“子長,你知道我要去哪裏嗎?”
太史令道:“知道,而且我曾主動向陛下請命前往,可惜陛下不準。”
蘇武吃驚地道:“知道你還想去?”
太史令點頭道:“出使匈奴,人皆視為畏途,可在我,是求之不得的美差——我鑒定那石鏡上的銘文時就對那鏡子産生了極大興趣,那可真是一件罕見的古物。”說着将手中那幅帛書在幾案上鋪展開來,坐下道,“子卿,你看,這就是那石鏡上的銘文。當年我将之拓印下來,現在石鏡失蹤,這成了唯一的憑據。”
真有這麽件東西?
蘇武驚訝地走過去細看,一看之下,卻是一頭霧水。
那方錦帛中,印着一圈銘文,個個形狀詭異,似字非字,似畫非畫,一眼看去,竟沒有一個是認識的。數一數,這“字”共有八個。
蘇武道:“這、這是什麽文字?先秦的嗎?”
“我也說不清。”太史令道,“這石鏡極其樸素,沒有任何可借以識別的款式紋飾,只有鏡背後刻了這一圈鏡銘,但字形奇古,似字非字,似畫非畫,沒有一個是在古器上常見的。當年陛下命我識讀這些文字,我自負博學,八體精通,可一見這鏡銘,還是愣住了。這鏡銘文字和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種古文(作者注:漢朝“古文”是指先秦的古文字,而非文言文)都不同,只能勉強看出它有個別結構接近史籀大篆,但遠比它們簡易淳樸,又有一絲蟲書的古老谲美。我只能肯定,那必是一種比我們現今所知道的古文古老得多的文字,或許就是傳說中上古的‘蝌蚪書’吧。我費盡心力琢磨了一個多月,才識讀出這些字來。”
“你讀出來了?”蘇武驚奇地道,“寫的是什麽?”
“說起來,這文字內容倒平淡無奇,”太史令嘆了口氣,轉身迅速從身旁的書架上抽出一冊簡牍,打開來道,“居然就出自這普天下儒生都讀過的《詩經》!‘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頌·玄鳥》篇的第一句。唉,說穿了一錢不值。”
“《詩經》?玄鳥?”蘇武好奇地接過簡牍,看着上面那密密的文字,皺起眉道,“子長,你以為人人都像你那麽好的學問嗎?《五經》我是一看就頭痛。這首詩講的是什麽?”
“哦,是我想當然了。”太史令搔了搔頭,在幾案前坐下,道,“不過這首詩還算平直,說的是商朝始祖的傳說。相傳很久以前,有娀氏有個女子叫簡狄,為帝喾次妃。一天簡狄和兩名女伴沐浴于玄丘水,天上飛來一只燕子,産下一枚鳥蛋,簡狄拾起那鳥蛋吃了,就懷孕生下了商朝的始祖契。燕子是黑色的,所以古稱‘玄鳥’。”
吃鳥蛋生子?蘇武覺得有些好笑,道:“子長,你不會就為了這想要去匈奴吧?”
太史令搖搖頭道:“不是為了這個。唔……那個人,衛律……他……有些與衆不同。”
蘇武道:“怎麽?你認識他?”
太史令點頭道:“很久以前,就在這裏,他曾經問過我一些奇怪的問題,令我至今無法忘懷。那時他來這石渠閣借閱一些典籍——你知道,這種藏書閣向來冷清。宮中諸郎,極少會來這裏,而衛律是來這石渠閣次數最多的人。他要的書很雜,內容又大多冷僻,這引起了我的注意。後來我特地留意了一下,發現他似乎在找與商朝有關的典籍。商朝史料不多,除《詩》、《書》外,大多散見于先秦諸子的著作中。我因為家傳的緣故,對先秦諸子素有研習。有時見他為了查個資料的出處,要翻閱數百石簡牍,便忍不住幫他一把。我本跟他不熟,他是個話不多的人,這樣一來二去,才有了些交流。在交談中,我發現他骨子裏有一股說不出的邪異之氣。後來出了叛逃的事,我聯想到他說過的那些話,感到他偷走這面石鏡,只怕其中大有文章。”
蘇武好奇地道:“他跟你說過些什麽?”
太史令看着前方,像是陷入了沉思。隔了很久,才緩緩地道:“他問我,為什麽商朝的史料這麽少?他說,這石渠閣簡牍萬千……”
◇◇◇◇
“這石渠閣簡牍萬千,”衛律道,“上至堯舜,下迄周秦,皆有史料留存,唯獨商朝這一段,不但正史匮乏,就連野史逸聞也寥寥可數,這是怎麽一回事?”
我點點頭。
我知道,他不是在炫耀自己對商史的熟識,而是實實在在很困惑。
因為這困惑我也曾經有過。
你知道,我這些年在編撰《史記》,而商朝是讓我感到最頭疼的朝代。
商朝統治六百多年,歷經三十餘位帝王,除了開國的商湯、亡國的商纣,幾乎全是面目模糊、毫無特征。我寫史喜歡刻畫人物,商朝卻時常使我覺得無從下手。擺在我眼前的,只有一個個幹巴巴的以天幹命名的符號:外丙、小甲、中丁、外壬……我知道他們的世系更疊,卻不知道他們的形貌、性情、喜惡、功過。
只是若非以治史為業,很少有人會注意到這個現象。衛律是來這石渠閣的人中,唯一一個提出這疑問的。我不由得暗贊他眼光敏銳,問道:“足下怎麽會想到問這個?”
衛律翻着幾案上剛看完的那幾冊簡牍,道:“沒什麽,就是疑惑。我記得商的先祖契任職司徒,掌管教化百姓;《書》雲‘唯殷先人有冊有典’,可見其文教之昌盛。這樣一個朝代,歷史卻幾近空白,難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點頭沉吟道:“不錯,商史匮乏,我也感覺到了,我修史之時,也曾為此煩惱過。也許是時日太久,導致史料遺失的緣故吧。”
衛律不置可否地笑笑,道:“還有,商朝文字,最可信的,當是見諸《尚書》的那幾篇吧。而就這《尚書》中流傳下來的那僅有的幾篇商朝文诰,語言都艱澀難明,什麽‘蔔稽曰其如臺’,什麽‘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幾乎無一字能以今義解讀。這又是何故?”
我又是一怔。《尚書》文字晦澀,世人皆知,尤其涉及先商的篇章,多少飽學之士窮一生精力鑽研此書,也未必能讀得懂,卻從沒人想過問一句:它為什麽這麽難懂?
我沉思了一會兒,道:“‘尚’者,上也。想來既是上古之書,年深日久,自然晦澀難懂。”
衛律搖頭道:“語言文字,總是一脈相承的。商人遣詞造句,為什麽會和我們現在所用的相差那麽大?太史大人,你不覺得,那些文字的怪異艱澀,已經超出了時間久遠可能造成的語言的變異?”
我被他說得也有些疑惑起來,道:“你是說……”
“我想,”衛律若有所思地道,“有沒有可能,這是周武王故意造成的結果?”
“周武王?”我大感意外,道,“這跟周武王有什麽關系?”
衛律道:“武王滅商後,曾借着大封宗親功臣,将周語作為雅言雅音,在各諸侯國推廣。也許,周朝正是要借着這種手段,使得殷商的語言文字逐漸變成無人知曉的死文字,從而斷絕殷商文史典籍的傳承!”
我心中一驚,隐隐感到此人話裏有些令人不安的東西。
我道:“你、你怎麽會這樣想?周朝為什麽要這麽做?武王伐纣,是以有道伐無道,何至于對前朝戒懼至此?”
“不錯,”衛律耐人尋味地道,“問題就出在這裏。一方面,說是民心所向,前徒倒戈,兵不血刃就入了朝歌;另一方面,卻對一個聲名狼藉的前朝如此戒備防範,連語言文字都要禁絕。恐怕商周鼎革的那段歷史,并不像我們通常所知道的那麽簡單!”
我倒抽了一口冷氣:“你知不知道你在說什麽?殷商無道,周武王吊民伐罪,世人皆知……”
“世人皆知,世人都看見了嗎?不說別的,此書就與這世傳的正史多有矛盾。”說着,衛律拿起幾案上一冊簡牍,道,“根據此書的記錄,從文王到武王,對到底要不要伐纣這件事,其實一直帶有很深的疑慮。文王托言吉夢,宣稱‘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如果真是天下苦商久矣,何必挖空心思造這樣的輿論?豈有宣告自己繼承一個臭名昭著的王權統緒以争取民心的?武王出征之前,做了一個噩夢,便驚恐地對周公說:‘嗚呼,謀洩哉!今朕寤,有商驚予。’不是堂堂之鼓,正正之旗嗎?怎麽聽起來好像見不得光的密室陰謀?武王幾次與周公交談,都提到‘天命’一詞,言語中既敬又畏,并且是畏的成分居多,以致需要周公多次開導解釋,才能把那種深切的恐懼壓下去。我很好奇,他到底在恐懼什麽?他說的‘天命’究竟是什麽?在三分天下已有其二的情況下,難道說還有什麽不可測的力量可能使父子兩代的努力毀于一旦?”
我看了看那冊簡牍,松了一口氣,道:“你怕是言過了。這部《周書》我看過,用語雖古,但所記之事聳人聽聞,和傳世的《尚書·周書》出入太大,不太可信,十有八九是後世僞托。”
“僞托?”衛律笑了笑,用一根手指輕叩着幾案,悠悠地道,“到底什麽是真,什麽是僞?你是史官,應該比我更清楚,所謂的‘史實’是怎樣打造出來的。拿着史筆的,都是最後的勝利者。商周之交的那段歷史,是誰記錄的?還不是西周的史官!文王武王,是自古以來被奉為楷模的明君聖主,幾乎有如完人。這形象從何而來?食君之祿,自然忠君之事,根據需要取舍材料,抑揚塗飾,也是題中應有之意……”
我猛地站起來,忿聲道:“并不是所有的史官都像你以為的那樣!”
衛律看了我一眼,笑道:“好吧,是在下失言。不過,抛開那些真假難辨的定論,只以一個正常人的常識來判斷:赤雀丹書、飛熊入夢、白魚入舟、火流王屋……這吉兆也太多了吧?到底是天降祥瑞,還是對手實在太強大了,以至必須百般捏造、托言神跡,才能打破民衆根深蒂固的恐懼,鼓動起事?武王牧野誓師,列舉商纣王三大罪狀:聽信婦人讒言;不祭祀自己的祖宗;不任用自家兄弟。多麽奇怪,讨伐一個不共戴天的敵手,理由竟是對方虧待自己人!設身處地地想想,周武王到底為什麽會作出如此異常的宣戰誓言?一切事後看來反常的東西,在當時必然有足夠的理由使它顯得正常。《牧誓》的字裏行間,給人一種強烈的感覺,武王要讨伐的對象,擁有時人心目中不可撼動的正統地位,以致以任何借口向之宣戰,都是大逆不道的行為。唯有譴責他背棄了自己的宗族和祖先,才能證明征伐的正當!”
“再看那一道道頒行天下的號令文诰,遣詞行文中,周也從未否定商的正統地位,舉事之前,稱受商之命于皇天上帝。滅商之後,說‘皇天上帝,改厥元子’,總之反複強調這不是改朝換代,而是奉天命繼承商的大統。”
“武王進入朝歌後,首先做的,不是除惡務盡,斬草除根,而是安撫商的貴族遺老:釋放佯狂被囚的箕子,修繕王子比幹的墳墓,甚至把殷商遺民都封給了纣的兒子武庚!對一個惡名昭著的舊政權,為什麽不能正大光明地取而代之?為什麽要這樣處處施恩事事示好?就算周王仁義謙退,那些殷民難道沒腦子嗎?舜避帝位于堯子丹朱,天下人都知道丹朱不肖,不朝丹朱而朝舜,禹避帝位于舜子商均,天下人不朝商均而朝禹。商朝遺民難道不知道他們的前朝舊主何等罪惡滔天?怎麽不自發地棄武庚而朝武王?”
“不惟如此,周初甚至還發生了管蔡之亂。管叔、蔡叔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居然寧願背叛自己的同宗至親,也要幫助一個前朝王子複辟!武庚成事,帶給管、蔡的好處,還能超過西周的?周公為鎮壓這次叛亂,東征三年,死傷無數,《詩》雲:‘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如果殷商真有傳說中那般殘暴不仁、民心厭棄,何以清除殷商的殘餘勢力,竟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
“也許,這種種不解之謎的答案,就藏在那些被禁絕的商朝典籍之中。西周千方百計要毀滅商朝典籍,就因為那裏面記載了一些周人不想讓後世百姓看見的東西!當然,我也不知道那些東西到底是什麽,但以常理而論,隐瞞得越嚴重,真相必然就越驚人!”
衛律緩緩地說着,語調平靜自然,然而在我耳中,卻不啻響起一個又一個炸雷,震得我心驚膽戰。
這是我有生以來所聽到過的,在史學上最大膽、最聳人聽聞的言論。然而他的每一句話,又似乎都持之有據、言之成理。我呆呆地看着衛律,半晌才道:“知道嗎?你這人……很危險。”
“危險?”衛律淡淡地一笑,道,“真有意思。我聽說太史大人為人正直,治史嚴謹,素以晉之董狐、齊之太史自勉,想不到連探索這樣一個遙遠時代的真相,都視為畏途。你難道就沒有一絲好奇:真實的商朝到底是什麽樣的?”
我被他說得竟一時呆住了。
衛律合上簡牍,站起來對我躬身一揖,道:“多謝大人這段時間給在下的幫助。在下職分卑微,無以為報,給大人一個建議,希望對大人有用:商朝對巫術的偏好,似乎到了不正常的程度。自古未聞以鬼神治天下而能長久者,但殷商卻是個例外。從這裏下手,也許會有意外的收獲。”
說完,衛律向我再施一禮,便向石渠閣外走去了。
從那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
蘇武一時聽得有些發怔,好一會兒,才道:“他後來說什麽?商朝人……喜歡巫術?”
太史令點點頭道:“他提醒了我。這确實是個奇怪的現象——歷代商王都極其重視鬼神,甚至不惜以大量活人祭祀殉葬。雖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可畢竟殺人以殉,非仁義之舉,這麽殘忍的事情,為什麽從沒有危及他們的統治?還有,商王室迷戀占蔔,田獵、祈雨、征伐、稼穑、疾病……幾乎無事不蔔。占蔔這種事,誰敢保證次次都準?萬一錯失,豈不有傷王室威信?可最叫人吃驚的是,他們幾乎每發必中!那種準确的程度,遠超我們現在的太常、太蔔。這确實令人難以索解,他們究竟是怎麽做到的?而西周禁絕商朝文字典籍,和這又有什麽關系?”
蘇武不假思索地道:“哪會有這種荒唐事?!一定是假的!若靠占蔔治國,早就天下大亂了。西周禁絕商朝史料,說不定就是因為那裏面這種虛假欺詐的東西太多了!”
太史令道:“商朝是甲骨蔔,蔔辭、結果都一一刻寫在龜甲之上,怎麽做手腳?下雨就是下雨,不下就是不下,根本無法含糊其辭。”
蘇武想了想,道:“也許他們只留下正确的蔔筮結果,那些失誤的記錄都被銷毀了,所以給後人造成每發必中的錯覺。”
太史令搖搖頭道:“你拿作僞的想法去揣度,再多的證據在你眼裏都是假的。世上有些事,确實非常理所能解釋,但不能解釋不等于就不存在。占蔔大行其道,就是從商朝開始的。商以龜蔔,周以蓍占,傳到今日,陰陽五行、命相堪輿,洋洋大觀,方式越來越精細,準确度卻越來越差。前幾年陛下選了個日子要娶婦,命太常署算一下那天吉利不吉利,結果五行家說可以,堪輿家說不可,建除家說不吉,叢辰家說大兇,歷家說小兇,天人家說小吉,太一家說大吉,竟無一相同。弄得陛下大發雷霆,罵他們都是些欺世盜名的騙子。幸而我正奉旨編制新歷,沒有參與,否則也難逃罪責。其實陛下罵得也沒錯,今日之占蔔和上古已相去甚遠,許多幾乎就是在撞運氣。可是你想,如果占蔔最初就是這樣,誰會相信?就算用什麽小伎倆騙得臣民百姓一次兩次,時間長了,總會引起懷疑,總會露出馬腳,怎能蒙騙天下人幾百年而不敗?”
蘇武道:“商朝人若事事都能預知,何至于被周所滅?”
太史令搖頭道:“我不知道。倘若果真事涉鬼神,那必不是我們平常人所能揣測的。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但我相信,精确的占蔔确實曾經存在過,只是不知何故,這種技能在現世漸漸消退了。即使如此,市井鄉野偶爾還是會出現一兩個擁有這樣能力的異人。像本朝的許負、司馬季主、傅仲孺等人,不都是……”
“傅仲孺?”蘇武道,“東市那個江湖騙子?”
“江湖騙子?”太史令一臉錯愕,像聽到了什麽極其不可思議的事,“你管‘長安第一神相’叫‘江湖騙子’?!太蔔有疑難,都要向這個‘江湖騙子’請教!他準确地預言過骠騎将軍的早逝。他東市那間相肆的門檻都要被人踩爛了,多少勳臣貴戚在他面前低聲下氣,重金延請以求一相,還得看他心情好不好!”
蘇武不以為然地道:“他有那麽神嗎?可那年李少卿他們硬拖我去看相,結果看出來的事,十有八九是錯的。”
太史令的表情更驚愕了,道:“還有傅神相會看錯的事?他說錯你什麽了?”
蘇武不屑地道:“他說我的出生地附近有一片大水。可你知道的,我家在杜陵一片高地上,很遠才有一條小河。他還說,我一世孤獨命,不會有妻子。我說我孩子都有三個了,他就狡辯說,就算有也早晚會失去。他還胡說我母親不幸早逝,見我發怒了,又改口說我雖命帶刑克,但天生貴相,貴不可言。這叫什麽高人?!”
太史令一時呆在那裏,愣了很長時間,才喃喃地道:“傅仲孺觀相斷人,從來言無虛發。偏偏在你的事上錯誤百出,真是怪了。”
蘇武不屑地一笑,道:“八成是以前那些人都被他的花言巧語繞昏了頭,自己言語間洩露了真相,被他利用了吧。我是從來不信邪的,他什麽都套不出來,自然就技窮了。”
太史令搖搖頭,道:“就算傅仲孺是假的,世間之事,有假就有真。星占術數、命相蔔筮,本就缥缈難循,如果從來就沒有實實在在的效驗,何至于自古及今那麽多才智之士趨之若鹜?傅仲孺、少翁是否有真本事,我不知道,但我不相信衛律那種人會被一出無聊的騙局所惑。你看看他探究的那些東西,再看看那石鏡,銘刻着的恰好是商朝的始祖傳說,這會是巧合嗎?”
蘇武忽然想起一事,道:“子長,你用了一個多月才識讀出那石鏡的銘文,那衛律又看不懂古文,怎會知道這鏡銘跟商朝有關?”
“他不懂古文?”太史令笑了笑,道,“他會不懂古文?!他跟我老師安國先生學過!”
孔安國?蘇武一愣,孔安國是本朝公認古文方面造詣最高的學者,那叛賊居然曾經師從這樣一位大名鼎鼎的學者?
蘇武道:“衛律他……跟安國先生學過古文?”
太史令嘆道:“而且他舉一反三,觸類旁通,是罕見的奇才。直到現在,每當安國先生百般譬解都無法使我們理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