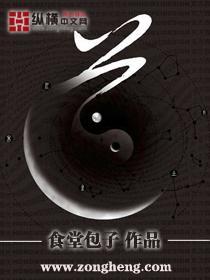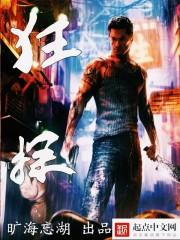第64章 (2)
1月10日,張謇就南京臨時政府一事,拍電報給袁世凱解釋:
南省先後獨立,事權不統一,暫設臨時政府,專為對付獨立各省,揆情度勢,良非得已。孫中山已宣誓,大局一定,即當退位。北方軍人,因此懷疑,實未深悉苦衷。若不推誠布公,急求融洽之方,恐南北相峙,将兆分裂,大非漢族之福,心竊痛之,國會議決政體,既雙方承認,所須磋商,止開會手續及地點耳。若因是再肇戰禍,大局何堪設想?謇前曾以第三者自任,今危象已露,不容坐視。
袁世凱收到了電報,尋思了一會兒,叫過他的幕僚洪述祖。
袁世凱:小洪啊,聽說你是惜陰堂趙鳳昌的姐夫,我沒弄錯吧?
洪述祖:……錯得太離譜了,我不是趙鳳昌的姐夫,趙鳳昌是我的姐夫。我姐姐就是嫁給了趙鳳昌……
袁世凱:……反正都差不多吧,橫豎也是你們一家子的事。南方那邊的情形,你姐夫到底是怎麽說的?
洪述祖笑道:老板啊,這還用說嗎?那孫文只是個口頭理論家,沒有任何實際政務經驗。這個臨時大總統,原本是我姐夫安排他做大元帥的,卻被他偷梁換柱,忽悠各省代表說他從美國弄到了美金千萬,兵船百艘,代表們傻啊,孫文說啥他們都信,結果就投票讓他當大總統了,現在那些代表們後悔死了……
袁世凱:嗯,那麽南京那邊的財務狀況如何呢?
洪述祖:老板,這你可問到點子上了,我就告訴你一件事,現在滬軍的軍費無法開支,民軍包圍了陳其美的大都督府,揚言不給錢就放火,陳其美吓得躲在我姐夫家裏,不敢出來。黃興更慘,揚言要剖腹以謝天下……
洪述祖在歷史上出場,他居然是惜陰堂主人趙鳳昌的小舅子。只要我們不是太笨,馬上就會知道,這人要慘了——倘若有人用暴力将惜陰堂及趙鳳昌,從歷史上抹除,那麽,洪述祖此人必然在劫難逃。事實上,他死得很慘很慘,盡管他一再解釋他不是謀刺宋教仁的兇手,但他越是辯解,死得就越是沒個名堂。
但此時,饒是袁世凱老謀深算,又怎麽會想到有人琢磨着将他的這個幕僚從歷史上抹除?所以袁世凱聽了洪述祖的彙報,點頭道:既然如此,那你就起草個給張謇的電報吧。
電報上說啥呢?洪述祖問。
袁世凱道:實話實說,就說我……以後回家種地,別尋思着把南方軍的亂攤子丢給我!
洪述祖聽了後搖頭:袁公,你想回家種地,我琢磨這事夠嗆,那幫吃貨才不會答應呢……頃刻間,電文一草而就:
探投唐少川先生湘轉伍轶翁、張季翁同鑒:
現天下糜爛,經濟困難,将來扶民治軍頭緒萬端,而分蒙問題尤難措手,所非凱衰病之軀所能料理。共和之議已達目的。凱将勉盡義務,愛我者适足相害,務請三公切商中山,仍以利國福民為念,始終其了,勿棄前功,凱候接代有人,仍返洹上務我農業,皆三公之大賜也。感且不朽。
Advertisement
袁世凱、銑二。
【09.傾倒得不得了】
孫文的南京政府陷入麻煩,袁世凱這邊的爛攤子也出現了問題。
問題出在袁世凱派出來的使者唐紹儀身上。說起袁、唐二人,那真是鐵打的交情,兩人當年在朝鮮合鬥日本五大師團,險象環生,險死生還。按說這麽深的交情,是不應該出問題的,可問題還是出了。
問題出在唐紹儀身上,臨行前,袁世凱再三叮囑他:小唐啊,咱們北方的态度是君主立憲,記清楚了啊,君主立憲,不然的話,那我老袁就是逼宮的王莽、曹操、嚴嵩、賈似道……所有的大奸臣加在一起,也沒有我的罪名嚴重。所以一定要君主立憲,不能讓我留臭名于青史……
唐紹儀當面答應得好好的,可到了南京,見到伍廷芳,唐紹儀卻說:
美利堅之平民政治,我們游學此邦時,即已醉心。自奉新大陸,益領悟其共和政體有利于國計民生,更是傾倒得不得了……
原來,唐紹儀對美國的平民政治傾倒得不得了,一輩子的夙願啊,眼看就要得償,這時候真的顧不上和老袁那血與火的交情了,讓老袁去死吧,中國非得共和不可。
朝廷派來的使者,居然對共和傾倒得不得了。這讓南方使者伍廷芳反倒不知說什麽了。但唐紹儀哇哇哇說個不停,根本不給伍廷芳機會:
共和立憲,萬衆一心,我等漢人,無不贊成……今所議者,非反對共和者,但求和平達到之辦法也。
唐紹儀擺了老夥計袁世凱一刀,結果在這場談判中,袁世凱就被動了。雖然老袁發現事情不妙,急急地撤銷了唐紹儀的談判權,可已經來不及了,南方抓住唐紹儀的話,逼老袁表态:你們自己的使者說過的話,總不能不算數吧?
袁世凱無奈:共和……你們非要共和,那就共和吧。
北南雙方,秘密達成五項條款:
1.确定共和政體。
2.優待皇室。
3.先推翻清廷者為大總統。
4.南北将士,皆不負戰争責任。
5.組織臨時議會,恢複各地秩序。
雙方商定了這五款之後,袁世凱一琢磨,嗯,現在剩下來的事情,就是逼宮了。
通知宮中的隆裕太後,以禦前會議決定共和制國體。
這段歷史,唯一的目擊證人是宣統帝溥儀。當時小溥儀咬着手指頭,坐在龍椅上,看着太後哇哇大哭,太後的腳下,跪着一個糟老頭子,也在哇哇大哭。
皇太後哭道:汝看着應如何辦,即如何辦。無論大局如何,我斷不怨汝,亦不能怨汝。
糟老頭袁世凱哭道:臣等國務大臣,擔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計,應請垂詢皇族近交王公,論政體本應君主立憲,今即不能辦到,革命黨不肯承認……如開戰,戰敗後,悉不能保全皇室。此事關系皇室安危,仍請太後召見近支王公再為商議,候旨。
于是就召開禦前會議,有請皇族王公赴會。會議上,一聽說要共和,皇族轟的一聲就炸了窩,齊聲大罵袁世凱:丢你老母,不能共和,這錦繡江山,是俺們愛新覺羅家的私産,允許你們這些奴才在我們家裏生存,這已經是天大的恩德了,現在你們竟然想分俺愛新覺羅的家,簡直是豈有此理!袁世凱,你個狗奴才,着你即時三刻,立即把南方的亂黨剿平,否則提頭來見。
袁世凱連連點頭:剿平亂黨,小意思,太小意思啦……不過你們諸位,既然這萬裏江山是你們的私産,現在北洋軍正在為你們的産業與南方軍血拼,可前線的将士們吃沒得吃,喝沒得喝,你們看看是不是一家掏點兒銀子,湊點兒軍費……咦,你們人呢?我的話還沒說完呢,人都跑哪兒去了?
一聽說要掏銀子資助軍費,衆皇族頓時一哄而散,再也無人出頭言語一聲。袁世凱心情大悅,登上馬車,入宮去欺負小寡婦隆裕太後。
稍候袁世凱出宮,踏上回家之路。車行之間,忽然一物飛空而來,砰地擊在袁世凱的馬車車轅上,然後是轟的一聲巨響,馬車傾覆,将袁世凱扣在車下。
當時袁世凱驚叫一聲:糟糕,孫文派人丢炸彈來了……
【10.烈血之士】
關于袁世凱被革命黨人丢炸彈一事,最早的記錄是在其子袁克文撰寫的《袁世凱紀》書中提到:
……一日,先公入朝,有宄徒懷彈,伏東安門外道左樓中,俟先公歸邸,乃擲彈向車……且傷駕車之馬,馬被彈,力馳而歸,入邸,馬亦斃,先公神色自若,微言耳震微聾耳……
袁克文這混蛋,好不容易寫本書,還偏偏不交代刺客的來歷因由,真是太不負責了。
推究這次刺殺事件,責任還在汪精衛身上。
話說那汪精衛,因為謀刺攝政王載沣而入獄。武昌首義後,各省紛紛獨立,于是清廷為示好革命黨,遂将汪精衛釋放。出獄之後,就有一個貴胄學堂的學生前來拜訪。既然是貴胄學堂,學生當然是官家子弟。
果然,所來之人,叫張先培。他的祖父張良曾任安徽提督,後因平滅六合會之亂而補授副将。而張先培在學堂讀書,偏偏教書先生是個革命黨,勸他為革命灑一腔熱血。張先培心動,就來找汪精衛。
汪精衛問他:你說你家鄉是貴州,那為何不回貴州起事?
張先培說:我不想回貴州,我想在這裏跟你一塊幹。
汪精衛問:一塊幹?幹什麽?
張先培建議道:你看,咱們聯手炸掉袁世凱如何?
汪精衛:……炸袁世凱?為何要炸他?
張先培道:這還用問嗎?現在清廷所依賴的,唯有袁世凱一個人,只要将他殺掉,革命就差不多成功了。
汪精衛搖頭:不然不然,實話跟你說吧,那袁世凱實際上也是心慕共和的,久有反正之意。你如果殺了他,只恐天下兵連禍結,戰火四起。所以我的意思呢,你先不要急着動手,先聯絡同志,做好準備再說。
張先培答應了,就去聯絡同志。這邊汪精衛卻被袁世凱派去了南京,與孫文彙合,而後汪精衛不說快點兒回北京,而是在西湖一帶瞎轉悠。張先培一個人在北京好生寂寞,結果就遇到了老鄉黃之萌。
黃之萌,相貌魁梧,天姿敏慧,他有一段非常傷心的往事。早年,法國佬搶占了越南,越南人向中國求救,可清廷自顧不暇,遂有許多烈血義士,紛紛前往。當時黃之萌也要去越南,父母得知,騙他去一間屋子裏取東西,等他一進去,就在外邊嘩啦一聲把門鎖上了,不讓他再出來。黃之萌急得在屋子裏跳腳,到了半夜,他的妻子悄悄來到門前,替他打開門,鼓勵他去邊疆殺敵。可黃之萌沒有路費,妻子就拔下頭上的釵環,交給黃之萌,讓他在路上賣錢用。
黃之萌拿着妻子的釵環當路費,歷盡辛苦到了越南,卻見各地自費趕往越南的義士頭顱,被法國佬懸挂在旗杆上。黃之萌大哭而歸,回家告訴妻子,妻子聽後憂傷國事,竟一病不起,一縷香魂,就這樣悄然散盡。
愛妻憂國而死,黃之萌心中發誓終身不娶,遂入京師,進入軍咨府辦的測繪學堂讀書,暗中搜集了許多地圖。
張黃二人相遇,不勝欣喜,暢談了一整夜,決定于北京城中豎起義旗,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次日,黃之萌飄然而去,不知所蹤,幾日後再回來,給張先培又帶來一個人。
與黃之萌同來之人,姓楊,叫楊禹昌,原在保定陸軍中學教書。武昌首義之後,他對學生們說:大丈夫建功立業,正在此時,諸君與我分投各省,暗聯黨人起事,以救國危。然後他率一批學生去了上海,卻發現上海革命黨人紮了堆,滿大街都是,都圍着陳其美的大都督府開槍放火,要求補發工資。
于是楊禹昌說:擒賊當擒王!于是取路北京,沿途聯絡黨人,卻莫名其妙地被衆黨人懷疑他是清廷奸細。楊禹昌大怒,曰:最險無非要命,不死總能出頭,看我給你們幹一個大的!
于是,張先培、黃之萌并楊禹昌三義士同抵北京,三人同心協力,準備擊殺袁世凱。
【11.富二代的刺殺歷程】
三義士北京盟誓,楊禹昌詢問張先培欲從何處下手。
張先培說:吾所慮者,唯土字頭耳——土字頭,是袁世凱的袁字土頭,因北京密探遍布,所以說此隐語——此前汪兆銘告訴我說,土字頭有心反正,所以我就遲遲未下手,可等到今天,并不見有絲毫動靜,而局勢日益糜爛,再不動手的話,只怕禍莫大矣。
楊禹昌以之為然,三人搞來了手槍炸彈,商議決定,于1912年1月15日,帶領十數個黨人來到東華門,見有馬隊簇聚栅外,湊近一看,正是袁大腦袋的馬隊。三人欣喜,張先培和楊禹昌就在近前一家店鋪前轉來轉去,黃之萌轉東安市場,準備截住袁世凱的去路。
不長時間,就見袁世凱從內廷出來,坐着雙馬車,前面是保護的馬隊,嘩啦啦奔這邊而來,張先培、楊禹昌各執短槍在手,突然沖出,率衆黨人砰砰砰一頓狂射,打得馬隊目瞪口呆,而後丢出炸彈,轟的一聲,掀翻了袁世凱的馬車。
雖然彈飛如雨,現場卻無一人受傷,豈料有一粒子彈嗖地打在了路邊的自來水管上,砰的一聲彈了回來,正擊中袁世凱的衛隊長袁金标的馬腦袋,就聽砰的一聲巨響,那馬腦袋炸了開來,袁金标跌下馬來,不曉得傷勢如何,總之是再也未能爬起來。
馬隊衛兵早已瘋了一樣撲将過來,将張先培、楊禹昌雙雙捉住。
東安市場那邊還有個黃之萌,眼見袁世凱鑽出馬車,向着前面狂奔,黃之萌大怒,執槍在手,追殺而來。不提防路邊各有兩名捕探突然撲至,一左一右,猛地架住黃之萌手臂,将黃之萌生擒了。
這時候巡警聞聲趕到,将那家茶葉店團團圍住,命令裏邊的人全部高舉雙手走出來,巡警一搜身,接連搜出幾枚炸彈,又将數名黨人一并拿下,其中還有一名女黨人。
正在搜身之際,突然不知何處響起一槍,一名騎在馬上的巡警大頭朝下,栽了下來。衆巡警急忙拔槍追趕,開槍者卻早已遁去無蹤。
這次暗殺,被捕獲的黨人除了張先培、黃之萌、楊禹昌外,尚有蕭生、陶鴻源、許同華、傅恩遜、黃永清、薛榮、李懷連及一名姓鄭的黨人。
有關三位血烈之士,一說是張先培刺殺不中,腦後中彈,死于當場。一說是三人兩日後同綁刑場處決。還有一說指袁世凱部将陸建章,将三名義士用棉被裹了,澆上煤油,縱火活活燒死。
臨終之時,黃之萌留下絕命詩:
在昔頭皮拼着撞,而今血影散成斑。
紅點濺飛花滿地,層層留與後人看。
三義士死,孫文先生不勝悲憤,于傷悼悲恸中發布命令,謂楊禹昌等烈士“奔走津、滬,組織一切,厥功甚偉,而卒就義于北京”,封三義士為右都尉,給家屬發放撫恤金。
此事過後,袁世凱繼續逼宮,并遣黨人彭家珍刺殺了宗社黨頭子良弼。說起那良弼之人,實乃一條響當當的硬漢,他被彭家珍炸傷,需要截肢,卻咬牙不肯打麻藥,要效法古之關羽刮骨療毒。他真的瞪眼看着自己的腿被鋸掉,現場煞是吓人。奈何血未流盡,良弼已自失血過多而死。若然此人還活着,仍難免一場龍争虎鬥,這共和革命之路,還得再起波折。
就在良弼遇刺之日,北洋将領張懷芝正坐着火車,從北京去天津。車行至新站,臨時停車。張懷芝坐在車裏,看着窗外,曰:大好河山,可惜淪陷于夷狄之手,三千紅粉,竟與羯奴同眠……語未畢,就聽忽悠一聲,一枚炸彈從窗外丢進,正砸在張懷芝的腦殼上。砸得張懷芝叫一聲娘親,定睛看時,就見一個風姿秀麗的美少年,滿面煞氣,手提短槍,躍入車中。
幸好那枚炸彈沒有爆炸,張懷芝更不猶豫,掉頭就跑,美少年舉槍追來,砰砰砰只管對着張懷芝狂射。幸好張懷芝的侍從瘋了一樣拿自己的身體遮住張懷芝,蜂擁而上,将美少年擒獲。
問其姓名,美少年厲聲道:大好河山,可惜淪陷于夷狄之手,三千紅粉,竟與羯奴同眠。兀那清廷的狗奴才聽好了,某家乃上海華榮洋行的少東家薛成華是也,家裏有錢,心慕革命,遂與同志車錫元、張墨林、曲振宗齊來北京,欲殺馮國璋、鐵良、蔭昌及良弼四人。只恨革命黨給的炸彈都是臭彈,一粒也不炸,要不然你這羯奴難逃一死。
張懷芝聽後喃喃地道:有沒有搞錯,你是個富二代,居然也搞刺殺,這革命思想,對年輕人的影響實在是太可怕了……
盡管美少年薛成華被張懷芝偷偷殺掉,但其人最後一擊,不唯是吓壞了皇族,連北洋軍人都感受到了革命風暴的恐怖。
抓緊吧,快點兒抓緊逼宣統皇帝退位吧,再遲會被炸死的。
【12.你太有才啦】
北南和議達成,袁世凱将決議條件呈報隆裕太後。
太後打開和議,登時放聲大哭,曰:真個将我大清朝推倒啊?連那“帝號相承不替”一語都不許我,讓我母子算何等人物?
旁邊的太監、宮女、侍衛俱各大放悲聲,袁世凱沒得法子,也假裝跟大家一起哭。等大家哭得累了,他耐心地解釋道:太後啊,皇上遜位,這是堯舜公天下之心,是好事啊。臣跟南方那夥子煞星争執了好長時間,可是沒得法子,這是他們的最後通牒了。
隆裕太後哭道:袁世凱,我母子二人既然将身家性命托付于你,肯定不會埋怨你的,你就照決議上的去做好了。
袁世凱大喜:臣遵旨。
急匆匆地出了宮,袁世凱回到家,立即吩咐洪述祖:快快快,趕快拿筆開寫,寫皇上的退位诏書。
洪述祖:……讓我來寫嗎?
袁世凱:廢話,不是你來寫,還讓我來寫嗎?
洪述祖:是,是,我寫,我寫,我寫寫寫寫……洪述祖回到書案旁,不長時間揮筆而就,拿過來給袁世凱看:老板,看看這個怎麽樣?
袁世凱接過诏書,看了起來。看着看着,他突然吼叫起來:丢你老母,這是他媽的哪個混蛋寫的退位诏書?又臭又長,就這麽會兒工夫,讀這個诏書讓我睡了兩覺,這豈不是扯淡?
洪述祖:……這又怎麽怪得我?我說過我寫這個不擅長……
袁世凱:那馬上拍電報給你小舅子趙鳳昌,讓他馬上拟定皇上遜位诏書。
洪述祖:說過了,趙鳳昌不是我小舅子,我是他小舅子……
袁世凱:甭管誰是誰小舅子了,你抓緊辦去吧,少在這裏扯淡。
稍頃,洪述祖回來,手裏拿着厚厚的一疊電文:老板,這是我小舅子趙鳳昌發過來的清帝遜位诏書,都寫好快半個月了……
袁世凱:你看你看,我說趙鳳昌是你小舅子吧,你還老是擡杠。
洪述祖:……不對不對,是我被你攪渾了腦袋,弄錯了,趙鳳昌真的不是我小舅子,我才是他的小舅子……
袁世凱:好啦好啦,別煩我了,讓我看看這個诏書。
朕欽奉隆裕皇太後懿旨:
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讨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确定辦法。南北睽睽,彼此相峙,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于前,北方諸将亦主張于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一姓之尊榮,拂兆人之好惡?用是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将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內義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安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哉?欽此。
袁世凱拿過來一看,大喜:小洪,你小舅子果然有兩下子,退處寬閑,優游歲月,寫得真是太有才了!
便拿這紙诏書去找徐世昌,徐世昌改了又改,然後入宮,請隆裕太後召王公大臣前來,宣诏。
太後哭道:現今王公大臣早已攜帶金銀細軟,逃到了租界,就我們可憐兮兮的娘兒倆,你就這麽宣诏吧。
宣诏聲中,隆裕太後放聲大哭,淚飛如雨,衆太監也随之大哭。
而此時,宮外,整個大中國,卻是一片歡天喜地,鞭炮聲震徹天地。
民主啦!
共和啦!
就在這普天同慶的大好時光中,噠噠噠,激烈的槍聲,從革命聖地武昌方向傳來。
又打起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