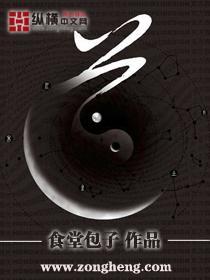第32章 (2)
有本事的官,也得靠了吏員來做事,行不行?
小夥計想了想,道:當個小吏也成吧?不信遇到有眼光的官,他會認不出我來。
于是老板替小夥計在廣州官衙捐了個縣丞,小夥計打起行李卷,就興沖沖的赴任了。到後沒多久,恰巧張之洞調任兩廣,對衙署的吏員一考核,就發現了這個小夥計,再有意給他幾樁事情去辦,小夥計辦理得妥妥當當。當時張之洞心想:此人雖然只是一個小吏,但辦事的才幹,只怕大清國也難找出幾個來,這麽能幹的人,我得把他留在身邊,以後有活就讓他替我幹。
再後張之洞來到湖北,就把小吏帶到了身邊,小吏但有進言,張之洞言聽計從。起初只是個言聽計從,再往後,張之洞幹脆當上了甩手掌櫃,什麽政事也不管了,全聽這個小吏吆喝,小吏吩咐他什麽,張之洞就做什麽。官場之人,多聞此事,于是有句話在官場上不胫而走:
兩湖總督張之洞,一品夫人趙鳳昌。
趙鳳昌,就是這個小吏縣丞的名字了。雖然他是個大男人,因為他隐于張之洞幕後,對張之洞耳提面命,所以被人戲稱為張之洞的一品夫人。
而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張之洞所謀所思,盡皆出自于趙鳳昌的腦殼。所作所為,盡皆出自于趙鳳昌之手。
話說大清帝國,原是有言官制度的,類似于今天的紀檢委,但沒有執法權,只是一些專門盯緊了各級領導的官員,發現有什麽不正之風,就立即上奏。一品夫人趙鳳昌事件爆發之後,衆言官義憤填膺,紛紛上奏:啓奏太後,不得了,我靠不得了了,張之洞那厮,放着正事不幹,和一個叫趙鳳昌的服務生好上了。
言官紛紛彈劾,慈禧太後就吩咐老幹部兩江總督劉坤一,帶隊來解決張之洞的問題。劉坤一來到之後,細一看趙鳳昌替張之洞出的主意幹的事,由不得怒發沖冠,惡上心頭。
看看趙鳳昌幹出來的好事,他替張之洞建立了陸軍測繪學堂,陸軍中學堂,陸軍小學堂,普通中學堂,工業,農業,商業,礦業,鐵路,方言,理化,省師範,道師範等學堂,還有武昌路五路小學堂,以及教會所辦的博文、文學和文華大學等。感情趙鳳昌這一個小夥計,竟然比大清帝國的整個朝廷都能幹,數萬名官員兩百年幹不成的活,讓他一個人稀哩哩嘩啦啦全給幹完了。
這人怎麽這麽能幹?
真是太不像話了,趙鳳昌這麽能幹,讓那些混日子的庸官們,還怎麽混啊?他這麽個搞法,豈不是斷了庸官的生路,剝奪了大家混日子吃飯的神聖權力?
情知趙鳳昌能力過強,居然敢以一人之力,砸整個朝廷的飯碗,已經犯了衆怒,劉坤一左思右想,決定舍帥保卒,幹掉趙鳳昌,保護張之洞。遂上奏建議:将趙鳳昌廢黜,逐出官場,永不許進入朝政——他一個人比整個朝廷都能幹,所以決計不能讓他再在官場上折騰了。
由是趙鳳昌在張之洞的資助下離開武昌,轉道上海,居住于上海南陽路10號,其居所號惜陰堂,從此摩拳擦掌,打定主意要做一番驚天的事業。
【09.風雲嘯聚上海灘】
離開張之洞的趙鳳昌,如同離開水缸跳入大海的鯊魚,從此無人可制。他到達上海之後,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雄厚政治勢力。
Advertisement
據革命元老黃炎培在《我親身經歷的辛亥革命事實》一文中稱:
……我在上海有一群政治意識不完全相同而一致傾向于推翻清廷,創立民國的戰友。其中教育界為主力,包括新聞界、進步的工商界和地方老輩如馬良(馬相伯)、張謇(季直)、趙鳳昌(竹君)……我們在上海很自然的成立起幾個據點來,經常集會……又一處是趙竹君的家惜陰堂,張謇來上海,時時會集在那裏。而奔走聯絡這幾個據點的是我……
黃炎培先生的社會地位姑且不論,我們來看看他提到的,與趙鳳昌相提并論的幾個人物:
馬良馬相伯:統領北洋的袁世凱的老上司,早年袁世凱赴朝鮮打天下的時候,職稱是“幫辦”,幫辦幫辦,就是幫着老領導馬相伯辦點雜事。再後來,馬相伯老人膩歪了官場上的勾心鬥角,進入教育界,創辦了上海的複旦大學。所以在這裏,黃炎培将他列為教育口人士。
張謇張季直:他是大清帝國的末代狀元郎,早年也曾去過朝鮮闖蕩,當時他的身份,是慶軍統領吳長慶的幕僚,兼差教導吳長慶的兒子,還有一個袁世凱讀書,只因為袁世凱讀書疲憊,不上心思,張狀元一怒之下,進入工商界,回到家鄉開辦紗廠,成為晚清赫赫有名的大資本家。
不論是馬相伯還是張謇,或者是離退休老幹部,或者是赫赫有名的狀元郎,都是大清國的名流,唯獨這個趙鳳昌的身份有點尴尬而別扭,往小裏說,他不過是雜貨鋪的小夥計,往大裏說,他不過是張之洞的“一品夫人”,而在行文中黃炎培竟然将趙鳳昌與馬相伯,張謇并列,甚至選擇了趙鳳昌的家作為集會場所。而這時候黃炎培的身份,不過是“奔走聯絡這幾個據點的是我”——一介跑腿的小夥計而已。
全亂套了,原來的小夥計居然成為了上海灘笑傲風雲的人物,黃炎培先生居然給他跑腿。這個趙鳳昌,本事大到了怕人的程度。
再來看看黃炎培先生此時的身份:
……那時我任江蘇省咨議局常駐議員、上海工巡捐局義董、江蘇省教育總會常任幹事、蘇州江蘇地方自治籌辦處參議……
黃炎培先生這夥人,在當時有個名堂,叫君憲派。
說起這君憲派來,也是孩子沒娘,說來話長。話說大清帝國早年為了愛新覺羅氏的統治,鎖國愚民,拖累了中華民族的發展,臨到鹹豐年英法聯軍殺到北京,甲午年北洋水師為日本殲滅,庚子年又來了八國聯軍,追得慈禧老太太撒丫子狂逃。愛新覺羅氏一點也不傻,眼瞅着天天挨人家列強的暴打,就商議說:不對頭啊,以前那麽個搞法不對頭啊,對頭還能天天讓人家暴打嗎?大家商量商量,看有什麽好法子,強大咱們的大清國,也免得天天叫人家揍。
這麽一商議,就商議出來個君憲派。
君憲派主要由比較激進的體制內左翼人士所組成,比如說張謇就是江蘇的君憲派頭子,而湖北的君憲派頭子是湯化龍,湖南的君憲派頭子是譚延闿……君憲派甫一登陸歷史,就搶了革命黨人的風頭,概因君憲派的政治主張,與孫文的革命黨一般無二,都是個要求愛新覺羅皇氏無條件出讓股權,強大國家。最讓革命黨人鬧心的是:君憲派人士是體制內的,革命黨人是體制外的,雖然大家的政治主張沒什麽本質的區別,可君憲派人士幹了革命黨人的活,屬于國家立憲範疇,是朝廷允許的。而革命黨人幹了君憲派人士的活,卻屬于亂黨,是要殺頭的。
總之,朝廷許可君憲派人士的話語權,目的就是為了從道義上否定革命黨。所以革命黨大怒,當朝廷派了五大臣出國考察,為立憲做準備的時候,黨人吳樾殺奔而來,一枚炸彈,炸得君憲派人士驚心不定。
雖然如此,但君憲派人士和革命黨人,終究能夠在政治上達成諒解。而趙鳳昌竟然能夠跻身于君憲派人士之中,這表明民主共和由軍事行動轉型為政治運動的條件,已經成熟。
【10.共和革命三級跳】
據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元老周雍能回憶:
……辛亥革命一起,一般人都認為是中山先生的功勞,實際上中山先生奔走革命遠在海外,在海外的力量遠比國內為大,而在國內的革命思想影響,可能比不上梁啓超,由于各方面力量的彙合,終于獲致辛亥革命的成果,這是追随孫中山先生多年的我不能不承認的……
辛亥革命時,周雍能老先生才剛剛17歲,是個年輕稚嫩的學生兵,當時他人在江西的南昌,響應了辛亥革命,但是他讀到的書,卻是梁啓超先生編的《新民叢報》及《少年中國魂》等報刊,才産生了民族思想,并終身追随孫中山。他敘述說辛亥時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在國內的影響有限,這應該假不了。
但我們知道,梁啓超先生是建設型人才,其思想觀念是主張建設,讀他的書,民族思想會複蘇,但定無可能産生暴力革命的念頭,而辛亥革命的第一槍之所以率先在武昌打響,就是因為武昌學生們,讀到的書比較特殊。
話說武昌首義時,有個叫喻育之的12歲小朋友,正在張之洞建立的湖北陸軍測繪學堂當學生兵,革命黨發現這孩子比較機靈,就跑來勸說他參加革命,于是喻育之在他的《憶在武昌第一次見到孫中山先生》一文中,這樣說道:
……我開始看到一些傳播革命思想的書刊,如《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猛回頭》、《警世鐘》、《湖北學生界》等,從而萌發了排滿革命思想……
注意喻育之老先生的敘述,他和周雍能老先生不大一樣,周雍能讀梁啓超,萌發的是民族思想,而喻育之這裏,萌發的卻是“排滿”思想。
啥個叫“排滿思想”呢?
說到這排滿思想,也是清王朝自尋死路。我們在前面敘述過,為了強大清國,清王朝在一系列高人的運籌之下,建立學校培養高素養的軍官,準備設立三十六鎮新軍。比如說湖北新軍第八鎮,南京新軍第九鎮,福建新軍第十鎮,都是這一政策的系列産品。
新軍将士,清一色高級知識分子,也就不會對認同皇權觀念,革命思想必然興起,所以清王朝一看這情形,心說咋整呢?能不能找個好辦法,讓這些新軍既有高素養,又對皇家忠心耿耿,死心塌地的做奴才呢?有了,要不給新軍中派一标旗兵過去,看着新軍點。
于是朝廷從北方調來了旗兵,駐紮在武昌的楚望臺與紫陽路一帶,專門負責監視高素養的漢人新軍。漢人新軍走在路上,迎面來了旗兵,就會攔下,先啪啪啪幾個大耳光,然後喝問道:日你娘個鬼,你吃的是誰的糧?漢人新軍必須要立正,以響亮的聲音回答道:吃皇上的糧!然後旗兵再啪啪啪幾個大耳光,喝問道:你穿的是誰的衣?漢人新軍再立正,響亮的回答:穿皇上的衣!然後旗兵再啪啪啪幾個耳光:你睡的是誰的女人?漢人新軍立正:睡的是皇上的女人……若是回答的慢了,輕者蹲禁閉,重則以革命黨之罪殺頭。
所以武昌的第八鎮新軍,恨旗兵恨到了牙根癢癢的程度,這種仇恨,就稱之為“排滿思想”。
敘述到這裏,我們就能夠對馬上爆發的辛亥革命整體過程,進行一次清晰的梳理了:
武昌新軍,其激進者所接受的主要思想是“排滿”,排滿也是革命,但其主要表現為對旗兵的仇恨,與共和思想還有一定的距離,而完成這一距離的跨越之人,就是張之洞伏下的三步棋。
哪三步棋?
第一步:是先有富戰鬥力的武昌新軍,才有可能将對旗兵的仇恨轉化為殺戮行為,這就是辛亥革命第一槍的初始意義。
第二步:先是由黎元洪的弟子吳兆麟出來,将一場無以名目的流血暴亂,轉型為以排滿為目的的兵亂。再有黎元洪出來,将一場排滿兵亂,轉型為具有着正确革命訴求的軍事行動。
第三步:由一品夫人趙鳳昌負責,将一場軍事革命轉型為社會革命,最終促成共和革命的成功。
看看這共和革命的三級跳,我們就會發現,革命黨人的具體工作,是負責拉開引線,引爆事件,而最終的革命,卻是由張之洞設置的軍事體制來完成。
現在,張之洞已經為大清帝國掘好了墳墓,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等革命黨人跑來,用力将滿清推進墳墓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