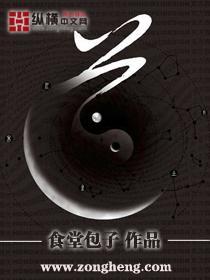第3章 (3)
朝廷請示的情形下,擅自向美國總統遞交了國書。
這件事标志着“朝鮮特區”脫離中國的第一步,袁世凱如何能夠允許?當即對國王李熙及闵妃嚴詞相诘,要求嚴懲樸定陽,可是闵妃卻使出了人海戰術,大批的朝鮮官員紛紛找到袁世凱替樸定陽說情,而闵妃自己幹脆更進一步,籠絡袁世凱,要求袁世凱和她一起糊弄大清國。
雙方鬥智鬥勇,唇槍舌劍,為這件事整整扯皮了十年,最後的結果是清廷準許朝鮮再度啓用樸定陽,但“不得委以重任或再充使臣之職”。
這事因為鬧得太亂,袁世凱和大清國始終沒顧得上找德尼的麻煩,可是闵妃卻不知為何瞧德尼不順眼了,她自己偷偷找來了一個叫李仙得的日本美國人——李仙得是美國人,卻在日本打工,後來失業下崗,就由日本跳槽到朝鮮,故稱日本美國人——準備用李仙得取代德尼。
這時候德尼不再給闵妃出馊主意了,跑來袁世凱這裏來哭訴。
袁世凱狠狠地罵了這個缺心眼的美國佬一頓,然後告訴他:
你奉中國的委派,韓國如欲撤換,應先咨請中國調回,如擅自派代,你不應遵從,可随時告我诘問韓廷,斷不可遽自交代。
但是李仙得還是興沖沖地來了,還帶來了一個美國大富翁葛累好士。闵妃下令停發德尼的薪水,德尼只好哭哭啼啼地離開了朝鮮。
李仙得開始替朝鮮借外債,以推動朝鮮脫離中國,袁世凱立即發表聲明:
……朝鮮貧窮而浪費,償還貸款極為困艱,各國紳商不宜與該國訂立合同,貸以巨款,将來如有借債不償之事,中國不會為之擔保。若各國因欠款而索債于朝鮮海關,中國也決不允許。預為聲明,以昭和睦之誼。
發表了這紙聲明之後,袁世凱就急急返回中國老家,去辦一件重要的事情——替他的四妹妹找個老公。
18.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外交戰雜七雜八,說也說不清楚,聽也聽不明白。而袁世凱家裏那本難念的經,念出來更讓人哭笑不得。
袁世凱在朝鮮的外交戰中一路升官,倒也容易,可是他的家事之麻煩,說起來幾乎讓人難以相信:
誠弟如晤:
來書均悉,此次吾家諸生均落孫山,只好以待來年。惟吾弟自此可與八股永別矣。
Advertisement
兄近來時帶各營操演行軍對敵諸法,跑得頭暈眼黑,尚能耐勞。
寓內均好,孔君媒事已囑君曼作書,景丈作冰。如能有成,甚好。昨告以四妹二十六七歲,拟告瞞一二歲,未知可否。望将八字送來為盼。沈家罷論,亦未始不好。匆匆,此詢。
雙吉。
四兄泐
看了袁世凱在幾年後寫的這封家書,我們知道了袁世凱面臨着如下的麻煩:
第一:老袁家的人都随了他袁世凱,最是沾不得科舉二字,一碰這個科舉,結果就是“均落孫山,只好以待來年”……丢人啊。
第二:袁世凱有個四妹,乖乖,這四妹已經二十六七歲了,還找不到樂意娶她當老婆的男人……二十六七歲,擱現在也是剩女了,放在晚清時代,這麽個老姑娘擱在家裏,能把全家人活活愁死。
第三:袁世凱吩咐家人,再給四妹妹這個老姑娘說婚事的時候,不妨弄虛作假,把年齡報低一點……
第四:年齡報出來是假的,還要對方的八字來合,那能合得上嗎?如果對方也隐瞞了真實的年齡,這八字合得可就熱鬧了……
經過袁世凱幾番折騰,他這個寶貝四妹妹終于嫁出去了,而且還是嫁給了中國的千年望族——山東曲阜孔家。由此可見,老姑娘四妹妹不是嫁不出去,而是找不到能夠與袁氏家族門當戶對的婆家……
袁世凱丢下朝鮮的政局不顧,回家處理的,就是這樣一些麻煩事。
半年之後,家務事處理停當,袁世凱又返回了朝鮮。
這半年他走得好,自從他走後,朝鮮就花李仙得從德國人那裏借來的錢,這點錢早在袁世凱回來之前就花光了,朝鮮駐美國使館,駐日本使館,天天打電報哀求發工資,國王李熙和闵妃卻是束手無策,只好眼巴巴地等着袁世凱替他們解決問題。
袁世凱想要的就是這個結果。
他告訴朝鮮人:想讓我幫你們解決錢的問題,容易,可是你們得聽話才行——徜有正宗要需,不妨商請中國設法。
這時候闵妃和國王李熙再也沒有精神頭折騰了,袁世凱怎麽說,他們就怎麽聽——被人追着屁股要債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啊。
于是朝廷傳令:袁世凱外交手段麻辣,升任駐朝公使……
跟闵妃姐姐在一起,升官就是快。
修理闵妃,總比替二十六七歲的老姑娘找個婆家要容易得多。
應該說,袁世凱是非常喜歡這個工作的,每次他把闵妃修理過一番,都會官升幾級,這工作誰不喜歡幹?
袁大頭是高興了,可是日本人卻受不了了。
在火箭幹部袁世凱嗖嗖嗖升官的這些年裏,日本人想盡了千方百計,想再擠進王宮裏去,可是被袁世凱擋在這裏,憋得日本人瘋了一樣在狹小的列島上蹦來跳去。
于是圖窮匕見,日本人開始考慮武力解決這個問題。
19.萬夫當關,一夫莫開
到了1894年,袁世凱已經幸福地在朝鮮待了整整十二年。
這也是日本人痛不欲生的十二年。
世凱不除,日難未已啊!
日本人咬牙切齒,要徹底解決掉袁世凱這個麻煩。
時逢東學黨于全羅道大鬧事,派出彈壓的朝兵被打得頭破血流,連武器都被奪走,袁世凱急電朝廷,請求派兵支援,遂有直隸總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清兵三千人,乘招商局的汽船于牙山登陸。
日本人也趁機湊熱鬧,派了八百名士兵跑來起哄。
等這八百日軍登了陸,袁世凱才發現不對頭,八百日兵人數是不多,但問題是人家這是先頭部隊,另有五個師團的大隊人馬還在後面呢。而且還包括了馬步炮工各個兵種,一進入漢城,一萬多名日本兵就熱火朝天地挖起工事來。
袁世凱大急,急電朝廷,請求增兵。
朝廷回電:已經和日本人說好了,中國不增兵,天朝大國,豈能反悔?
袁世凱急得跳腳,就聯合各國駐朝鮮公使,大家一起去日本兵營,面見五大師團首腦大鳥圭介,以道義相責,迫其退兵。
然而,武力控制朝鮮是日本人制定的國家戰争策略,大鳥圭介正在全力推行,又豈是口舌之争能夠解決得了的?
然而日本氣勢甚為兇悍,各國官員一時亦無可奈何。
知道與日本人兵戎相見勢不可免,袁世凱左思右想,終于想出了一個最有效的解決方案:
調葉志超的三千清兵入漢城,将王宮團團保護起來,這樣日本兵哪怕來得再多,也是沒咒可念的。
于是袁世凱立即打電報給朝廷,朝廷回答:老葉這人脾氣不太好,誰也不敢惹他,要不……你自己跟他好好談談?
袁世凱沒得法子,只好致電葉志超,商量如何渡過難關。
葉志超回電:別理我,煩着呢。
大勢已去。袁世凱仰天長嘆。
日本人的工事修好了,九個高高的炮臺上,九尊巨炮居高臨下地俯對着袁世凱的使署。
袁世凱無可奈何,只有致電朝廷:
津約日已先違,我應自行,若以牙軍與日軍續來兵相持,釁端一成,即無歸路,乞速裁度……
袁世凱的意思是說:俺要回家……
這封電報讓朝廷大嘩,群情激憤,物議洶洶,這個袁世凱怎麽這麽膽小?于是朝廷拍來電報:要堅貞,勿退怯。
袁世凱只好硬着頭皮繼續挺下去,可是使署員工都被大炮吓壞了,趁夜紛紛翻牆而逃,剩袁世凱老哥一個人,連飯都沒得吃,于是他只好再次致電朝廷:
凱等在漢,日圍月餘,視華仇甚。賴有二三員勉力辦公,今均逃去,凱病如此,惟有一死,然死何益于國?至能否邀恩拯救,或準赴義平待輪,乞速示。
朝廷煩透了這個袁世凱,吓唬誰呀,還日人視華仇甚,有這麽對日本友人說話的嗎?更何況袁世凱一回國,豈不是讓外人說中日不和?讓友邦驚詫嗎?
回電不準。
于是袁世凱不再拍電報,但是朝廷卻收到了海關下崗員工唐紹儀的電報:
現在漢城兩署辦公,只餘兩員,今聞南北進兵,均已逃去,無法挽留。儀一人譯電辦公,已難料理。而袁道病又須照拂,勢急情迫,乞速示遵。
——原來袁世凱是真的病了,偌大個漢城,就剩下他和唐紹儀這倆難兄難弟了。到了這一步,朝廷終于動了恻隐之心,發來電報:
本日奉旨,袁世凱著準調回。欽此。希将經手各事,交唐紹儀代辦,即回津。
朝廷是開了恩,允許袁世凱回去了,可是此時袁世凱的使署門外,是擠得密麻麻的日兵、日本浪人、武士及東學黨的刺客,袁世凱又有什麽辦法平安地走出門去呢?
20.老幹部發揮餘熱
究竟袁世凱這厮是如何從鐵桶一般的漢城中逃走的,這件事讓日本人傷透了腦筋。
後來日本人才發現,早在五大師團的日本兵趕赴朝鮮修理袁世凱之前,漢城中就有一頂華麗的轎子,每天來來往往,等到日軍到了漢城,這頂轎子仍然在城門裏進進出出,日本兵看得久了,也就習慣了。
原來這頂轎子卻是狡猾的袁世凱為自己預先伏下的退路,他和唐紹儀化裝逃出了使署,就一頭鑽進了這頂日本兵熟到了不能再熟的轎子裏,由唐紹儀手提兩支駁殼槍一路護送,英國公使朱爾典早已為袁世凱備下了英艦,當袁世凱回到天津的時候,日本兵們還瞎子一樣地在漢城裏到處追殺他呢。
弄清楚了事情的究竟如何,日本人一邊驚于袁世凱的老謀深算,一邊把火氣全都撒到了倒黴的下崗職工唐紹儀身上。
日兵沖入中國使館,要活捉唐紹儀,唐紹儀展開兩條飛毛腿,于漢城的街道上狂奔如飛,一萬名日本兵竟然逮他不着,被唐紹儀逃入了英國使館,不久朱爾典也将唐紹儀送回了中國。
來了一萬多名日本兵,卻一個中國員工也沒逮到,日本人這下子火大了。
四十多名日本浪人沖入了王宮,他們殺掉了王宮的守衛,毆打了國王李熙,闵妃吓得躲進了密室,卻仍然被日本浪人将她搜了出來。
浪人殘忍地殺害了闵妃,死後她的屍體還遭受到亵渎。
然後日本浪人毀屍滅跡,于王宮後面的松林中燒掉了闵妃的屍體。
正如袁世凱所說,中朝兩國,唇齒相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大清帝國遭了難,朝鮮也落不得個好。
牙山的清兵領隊葉志超脾氣不太好,但腳程卻是了得,當日兵大舉進攻的時候,他逃得比兔子還要快,三千名清兵每人各舉一塊顏色不黃不白的裹腳布,哭喊連天地各自逃命。日軍奇之,逮到清兵俘虜,問他們為何把裹腳布舉得那麽高,難道不嫌味道臭嗎?
清兵答曰:這是咱們宣布投降的白旗……
甲午海上戰役,大清帝國的水師悉數被摧毀,從此帝國徹底失去了控海權。
日軍終于沖出了列島,他們大踏步地前進,兵分三路,由平壤直搗蓋平,由旅順陷牛莊營口,此時遼東全部,盡落入了日本人之手。
翌年,日軍攻陷威海衛。
光緒皇帝命丁汝昌火速出擊,“斷賊歸路”。然而沒有歸路的不是賊,而是大清帝國自己。
丁汝昌力不能支,服藥自盡。
就在大清帝國落幕的慘淡時分,中國的第一個總統出人意料地跳了出來。
在臺灣!
唐景崧!
這個聞所未聞的總統是千真萬确的,只因為葉志超耍脾氣,不肯驅兵進駐漢城,導致了朝鮮的失落,由此而造成了大清帝國的全面崩盤,馬關議和,被迫又割讓了臺灣和澎湖列島。
臺灣人民不肯承認這個屈辱條約,呼籲朝廷不要将他們抛棄,臺灣巡撫唐景崧上書,言稱“臺灣屬倭,萬衆不服”,“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若戰而不勝,待臣等死後,再言割地”。
唐景崧這番慨烈之言,絕非大話。早年他本是吏部一個小小的文官,只因為法國佬侵入越南,于是他挺身而出,主動請纓,要求赴越招募黑旗軍義士劉永福,劉永福為其膽智而傾倒,從此追随于唐景崧之後,效命于國。
但是唐景崧的忠勇之心,為朝廷斷然拒絕。
朝廷說:臺灣算個卵子——臺灣雖重,比起京師則臺為輕,倘若敵人乘勝直攻大沽,則京師危在旦夕。
臺灣士紳大怒,遂推選巡撫唐景崧為大總統,士紳丘逢甲為副總統,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為大将軍,從此不認朝廷這個卵子,就和日本人拼了起來。
十二日後,臺灣淪陷。
大總統唐景崧乘船而走,黯然逃歸。
這就算下野了。
可大清帝國雖大,也沒地方擱這麽一個下野的大總統啊。
無奈之下,唐景崧隐居桂林,埋頭于文化事業的發展,組建了“桂林春社”,并創編了桂劇,以退休老幹部的身份,為中國的文化建設事業發揮了一點餘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