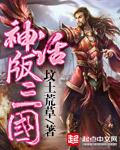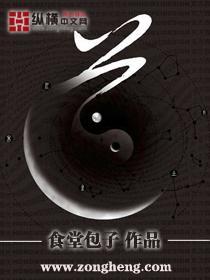第42章 (1)
〔經過數年的艱苦努力,曹操終于占據了整個北方。這是一個艱苦卓絕的過程,其艱難程度也許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轉戰于太行山上,迎着呼嘯的北風,聽着熊虎嘶嚎,看着迷失的道路,曹操不禁發出了“艱哉何巍巍”的慨嘆。〕
【一、袁氏兄弟相攻破】
建安七年(202年)五月,一代風雲人物袁紹因病去世,他留下了未竟的事業,留下了深深的遺憾,也留下了一個爛攤子。
倒不是說他留下的家業不夠大,實力不夠強。相反,雖然經過官渡之戰的慘敗,但他一手締造的袁氏集團仍然保持了強大的實力,只是直到臨死前他都沒有解決好本集團內部的紛争問題,尤其是繼承人問題,随着他的死去,這個集團開始了嚴重的內讧。
袁紹的原配夫人姓氏不詳,他續配的妻子姓劉,是一個厲害的女人,在很多方面都能當袁紹的家。在袁紹的三個兒子中,劉氏喜歡小兒子袁尚,經常在袁紹面前說他的好話(數稱于紹),而對老大袁譚抱有成見。在劉氏的影響下,袁紹也逐漸傾向于袁尚。
家和萬事興,家裏不合則外人欺。袁紹遲遲不明确繼承人的問題,官渡之戰前夕又分別委派三個兒子和外甥高幹為四個州的刺史,無異于向世人宣告他們家庭內部出現了分歧。
沮授、田豐這樣有責任感的人看到後會向袁紹苦谏,而逢紀、審配、辛評、郭圖這些投機分子則看到了機會。于是,逢紀、審配依附于袁尚,辛評、郭圖依附于袁譚,形成了兩大派。
據《英雄記》說,逢紀和審配原來并不和,但官渡之戰後二人關系發生了戲劇性改變。袁紹官渡之敗審配應該負重大責任,後來有人向袁紹說審配的壞話,袁紹問于逢紀,逢紀使勁幫審配打圓場,弄得袁紹很奇怪,放在以前,這正是逢紀求之不得的落井下石的好機會。
袁紹于是問逢紀原因,逢紀這小子居然冠冕堂皇地說:“以前我們鬧矛盾是私人恩怨,現在可是國家大事。”
其實他們眼裏的私人恩怨從來都是重于國家大事的,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此。逢紀之所以護着審配,是因為郭圖、辛評已經團結在一起,他沒有別的人選可聯絡,只能團結審配。為了共同的目标,這一對曾經互為眼中釘的對手走到了一起。
袁紹大概沒想到他會死得那麽早,一直到閉眼的那一刻還沒有給大家一個明确的政治交待。袁紹死後,大多數人認為袁譚是老大,應該推舉他做接班人。但此時袁譚在外地,逢紀、審配等人在劉氏的幫助下掌握了先機,僞造袁紹的遺囑,搶先讓袁尚接班。
據《典論》記載,袁紹的後妻劉氏生性嫉妒,為人兇殘,袁紹剛死還未來得及入殡,她就把袁紹生前寵愛的五個小老婆全部殺死。劉氏很迷信,她怕這幾個人到陰間見到袁紹告她的狀,于是把她們的頭發剃了,用墨塗黑她們的臉(髡頭墨面),把她們全部毀容。她心愛的小兒子袁尚倒也挺孝順,幫助老媽把她們的家人全部殺光。
史書對袁譚的評價較袁尚好,認為袁譚頗為仁愛聰慧,而袁尚僅僅是長得英俊而已。袁譚此前擔任青州刺史,雖然說不上有什麽特別建樹,倒也基本稱職,在實踐中鍛煉了才幹。
袁紹吐血而死的時候袁譚估計在青州,他聽到消息趕到邺縣時,袁尚已經宣布繼位,大勢已去,于是袁譚在辛評、郭圖等人跟随下移駐黃河邊上的戰略要地黎陽,自稱車騎将軍。
開始袁氏兄弟還沒完全翻臉。據《三國志袁紹傳》記載,逢紀、審配擁戴袁尚是“代紹位”,即接替袁紹的職位。袁紹死前是大将軍,袁尚繼承的應該是這個職位,雖然這個職位應該由朝廷任命,但現在的實際情況已經不可能,袁尚比較方便的做法就是把朝廷頒給他老爹的印绶拿過來自己用就行了,反正那上面也沒刻名字。袁譚自稱車騎将軍,這是大将軍的副手,說明他名義上仍服從袁尚的領導。
黎陽是與曹軍對峙的前線,袁譚替兄弟袁尚看大門,可袁尚卻不給支援(少與之兵),還把逢紀派過去監視他的行動。袁譚請求增兵,審配鼓動袁尚不答應,袁譚忍無可忍,把逢紀殺了,兄弟倆正式翻臉。
曹操得到報告後認為這是個機會,于是在這年九月渡過黃河,進攻黎陽的袁譚。袁譚告急,再次向袁尚求援。
有一句話叫“兄弟阋于牆,外禦其侮”,說兄弟們雖然在家裏争吵,但一有外面人來欺負便能立刻團結起來對付敵人。這句話出自《詩經》,用到現在最合适不過了。袁尚再笨,也知道哪是敵我矛盾,哪是內部矛盾,在曹軍的進攻面前,他決定親自率兵支援大哥。
袁尚之所以親自來,不是出于對敵情的重視,而是害怕派別人來鎮不住大哥,讓袁譚趁機把他的人給奪去了(恐譚遂奪其衆)。袁尚讓審配守邺縣,自己率部到達黎陽。
事實證明,袁紹即使死了,他留下來的軍隊仍然具有很強的戰鬥力,從這一年的九月一直到次年的二月,曹操親自指揮圍攻黎陽,居然沒能打下來。
後來,袁譚、袁尚估計實在守不住了,突然率部趁夜逃出黎陽,退還邺縣。曹操率軍追擊,袁尚終于找着了露臉的機會,在路上打了曹軍一個埋伏,曹軍敗退。之後,曹軍竟然放棄追擊,直接退回黃河南岸了。
曹操此舉讓人不解,但這是明智的,或許曹操也想到了《詩經》裏的那句話,對于随時會反目成仇的袁氏兄弟來說,加強進攻只能讓他們更團結,而一旦外界壓力減輕他們就會陷入內鬥。
事實果然如此。
曹軍撤退後,袁譚對袁尚說:“我部铠甲不精,所以前面讓曹操打敗了。現在曹操退兵,将士都盼着回家,等他們還沒有渡過黃河時,突然發起進攻,可以讓他們大敗,這個好機會千萬不能錯過呀!”
袁譚自願為前部,請求更換将士铠甲并派兵進行支援。
對于袁譚的建議袁尚猶豫不決,既不增兵,也不給袁譚換裝備。袁譚大怒,郭圖、辛評趁機對袁譚說:“當初挑撥你們父子兄弟關系的是審配,都是這小子進的讒言(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袁譚相信,于是率兵攻打袁尚,雙方交戰于邺縣城外。此戰袁譚失利,退到了渤海郡的南皮(今河北南皮)。
袁氏兄弟互相動了手,曹操看了心裏自然高興,但有個人看了卻揪心,他就是劉表。
《魏氏春秋》記載,劉表看到袁譚和袁尚不和,十分擔憂,他派人分別給這兄弟倆送信勸和。他給袁譚的信中寫道,你弟弟雖然做得有些不對,但事已至此,争鬥也是徒勞無益,仁義之士應該忍辱負重。劉氏雖然不喜歡你,但還沒有到春秋時期的鄭莊公與姜氏那樣的程度,你們兄弟倆之間的關系也沒有舜與象那樣尖銳,鄭莊公尚且能築地道與母親團聚,舜也能把象分封到有鼻這個地方,你們更應該和好。
鄭莊公和舜的典故說的都是一家人之間如何抛棄舊仇重新和好,劉表為了勸袁譚着實查了不少資料,下了不少功夫。
劉表寫給袁尚的信也一樣,引用大量典故,勸他以事業為重,先與兄長合作把曹操消滅了再來論誰是誰非。劉表說,如果兄弟能和好,袁家和漢室就都有指望了,如果不是那樣,同盟也就永遠完了(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
劉表對袁氏兄弟的事這麽上心,是因為他慢慢看清了形勢,袁紹集團的滅亡對他來說不是什麽好事,陶謙、呂布、劉備、公孫瓒、袁術在短短幾年時間紛紛凋落,曹操要打擊的下一個目标不就輪到自己了嗎?劉表的危機感越來越重。
但此君向來是個只喜歡動嘴不喜歡動手的人,有想法卻沒有行動。當初袁曹在官渡相峙,他要麽支持袁紹,堅定不移、結結實實地在曹操背後捅上一刀,幫助袁紹打天下,事後當個窦融那樣的開國功臣;要麽像張繡那樣歸順曹操,受到朝廷的嘉獎。這兩種道路都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可他卻猶豫觀望,只想坐山觀虎鬥,沒有任何動作。
現在看着袁氏兄弟鬧分裂,明顯是便宜了曹操,他更着急,但也僅限于心裏着急,實際行動也僅限于引經據典的兩封信,一再錯過了時機。
對于機遇,有一句話叫“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機遇對大家是公平的,前面給你留了機會你沒能抓住,後面再想要的時候就沒有了。當擺在劉表面前的機會被他自己浪費完的時候,也就是他徹底失敗的時候。
現在,當劉表飽含深情、下了很多功夫寫成的這兩封長信分別送到袁譚和袁尚手中時,這兩個人看都沒怎麽看一下,因為他們已經殺紅了眼,只想接着打。
論實力,袁譚處于下風。袁尚被立為繼承人後,袁紹的大部分政治遺産和軍隊都讓袁尚得去了,袁熙和高幹在他們的争鬥中雖然還沒有明确表态支持袁尚,但他們都想觀望,更不會表态支持袁譚。
袁譚退到南皮後,處境更加不利。袁尚親自率軍來攻,袁譚再次大敗,退到嬰城,袁尚又圍攻嬰城,袁譚逃往青州刺史部的平原郡。
這時,有人給袁譚出了個主意:幹脆投降曹操吧。
袁譚吓了一跳,以為聽錯了,但他又想了想,發現自己除此之外竟然已經無路可走。
于是,袁譚做出決定,派人向曹操求援。
【二、一樁臨時婚姻】
袁譚敗退到南皮時,也有人前來幫忙,是他青州刺史府的秘書長(別駕)王修。
王修字叔治,青州刺史部北海國人。孔融在北海國當領導的時候,征召王修當他的辦公室主任(主簿)。袁譚到了青州,任命他為別駕。王修勸袁譚:“兄弟就像左右手,有人打架先把自己的右手砍斷,而對人家說我必贏,這可能嗎?現在的問題是有讒人在其中搗鬼,請您不要聽他們的,可以殺上幾個佞臣,然後兄弟和睦,則可以橫行天下!”
對于王修的建議袁譚自然聽不進去,即使能聽進去,袁尚也未必肯合作。袁譚環顧四周,發現眼下能幫他渡過難關的只有一個人:曹操,原因只有一條:曹操是袁尚的敵人。
據《英雄記》記載,袁譚在邺縣失利後,郭圖曾勸他:“如今将軍地盤小、人馬少,糧食匮乏,顯甫(袁尚字顯甫)若再來攻,時間長了我們無法抵擋。我以為為今之計,可以聯絡曹操來抗拒顯甫。曹操到,必先攻擊邺縣,顯甫回救,将軍再率兵出擊,如此一來邺縣以北的地區都可以歸将軍。如果顯甫不是曹操的對手而遭到失敗,他必然出逃奔亡,将軍可以收留他以拒曹操。曹軍遠道而來,糧饷不繼,打上一陣必然退去,到那時,整個燕趙之地盡歸我們所有,足以與曹操相抗衡!”
袁譚開始聽不進去,覺得這條路也太過卑下了。但事到如今,不聽看來也不行了。袁譚問郭圖誰可以出使曹操,郭圖推薦了辛評的弟弟辛毗。辛毗字佐治,颍川郡陽翟縣人,跟荀、郭嘉等人既是同鄉又是熟人,曹操剛當上司空時,四處搜羅人才,經荀推薦,曾打算征辟他,但是辛毗當時在袁紹手下而未能成行。
因為有這樣的關系,郭圖推薦他跑一趟。
曹操攻克黎陽後,大家都主張追擊,郭嘉卻主張不要追。郭嘉說:“袁紹對這兩個兒子,不知道讓誰繼位好,結果讓郭圖、逢紀等人做他們的謀士,他們必然會争權奪利。現在,如果進攻太急他們就會團結在一起,進攻稍緩他們就會內讧,不如做出南征劉表的樣子,讓他們內讧,然後趁機出擊,一舉攻占河北。”曹操認為這個意見很好。
于是,曹操回師到黃河以南,趁着袁氏兄弟鬧內讧的這段時間親自帶隊到汝南郡的西平(今河南西平),做出一副遠征荊州的姿态。
這樣,辛毗到許縣沒有找着曹操,于是南下西平,在這裏見到曹操,轉達袁譚的問候(毗見太祖致譚意),曹操十分高興。
這正是曹操想要的結果,不戰而使敵人自亂,坐收漁人之利。現在袁譚主動送上門來,哪有這麽好的事?
曹操召集內部會議研究對策,根據《三國志荀攸傳》的記載,在這次會議上出乎曹操意料的是,大多數人都認為劉表勢力強大,應該先平定劉表。袁譚和袁尚反正已經開始內鬥了,暫時不會對曹軍構成威脅,沒什麽值得顧慮的,不用管他們,抓緊時間把劉表解決掉。
表面來看也是這樣,河北二袁內鬥,曹操正好騰出手來解決南面的問題。但這只看到了眼看的一步,而沒有看到下一步。
荀攸就持不同意見,他認為:“現在四方都有戰事,而劉表坐擁江漢之間沒有什麽作為,說明他缺乏雄才大智。袁氏仍然有四州之地,十萬之衆,在河北一帶有一定群衆基礎,如果他們兄弟二人聯合起來,那是很難攻破的,現在他們內鬥,正是各個擊破的難得機會,這個機會千萬不能錯過。”
曹操認為荀攸說得也有理,但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現在也正是解決荊州問題的最佳時機。到底先解決哪一邊,曹操有點舉棋不定,他也很想抓住現在的時機,把南面的問題先解決了,至于黃河以北的事,既然二袁相攻正急,不妨讓他們多打一陣再說(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弊)。辛毗看到這個情形心裏很着急,他此行顯然不只是轉達袁譚對曹操的良好祝願來的,他肩負着搬救兵的重任。辛毗找到老朋友郭嘉,向郭嘉求助,經過郭嘉從中幫忙,曹操認真考慮了他的請求。
曹操問辛毗:“袁譚可靠嗎?袁尚是否一定能被打敗?”
辛毗回答:“明公其實不用管袁譚可靠還是不可靠,只需要分析現在的形勢就行了。袁氏兄弟相伐,是他們自願的,也不是誰能從中間挑撥得了的,這就是天命。現在袁譚能向明公求救,明公就應該知道這裏面的事情了。二袁目光短淺而自相殘殺,弄得河北士者無食,行者無糧,确實已經到了快滅亡的地步。四方之難莫大于河北,河北平則天下震動啊!”辛毗的話提醒了曹操,現在袁尚強而袁譚弱,如果坐視袁譚滅亡,袁尚的力量便會迅速強大起來,這顯然不符合曹操的戰略利益。
于是,曹操決定揮師北上,援救袁譚。
建安八年(203年)十月,曹操率軍北渡黃河,再次來到黎陽。這一次他做了較為充分的準備,專門派程昱跟李典運送軍糧,作長期遠征的打算。
程昱和李典主要的糧道是黃河水運,袁尚派他任命的魏郡太守高蕃在黃河岸邊屯紮,斷絕了河道。曹操給程昱、李典發布作戰命令:“如果船不能通過,就改行陸路。”
李典分析了實際情況後認為:“高蕃所部善習水戰,士卒盔甲較少,而且缺少鬥志,擊之必克。只要有利于國家,暫時違命我認為是可以的(茍利國家,專之可也)。”李典的想法得到了程昱的支持,于是他們違反曹操下達的作戰命令,北渡黃河,攻擊高蕃,果然将高蕃攻破,水道得以恢複。
此時,曹操擺出了大打一仗的架式。袁尚正率主力在平原郡圍攻袁譚,聽到消息,立刻回師邺縣。袁尚的部将呂曠、呂翔二人對前途灰心失望,于是投奔曹操。
平原之圍解除,袁譚暫時化解了危機,他悄悄拉攏呂曠和呂翔,刻了将軍的大印給他們送去。此事被曹操偵知,但他沒有聲張,看到袁譚暫時不會被消滅,他決定回師。
能在高處随心所欲地走鋼絲的人,必須有時刻保持兩邊力量均衡的本領,要做到這一點,除了表演者藝高膽大之外,手中還要有一根木杆,以此調節平衡。當這根木杆要向一邊落下時,旁觀者及時出手把它擡起來,一旦恢複了平衡,就可以悠閑地在一邊看熱鬧了。
曹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也決定就此收手。為了穩住袁譚,讓他堅定不移地跟袁尚打到底,他還跟袁譚結成了兒女親家,其子曹整娶了袁譚之女。辦完這樁婚事,曹操領兵而還。
曹整是李姬所生,李姬納于何時不詳,她一共生了三個兒子,分別是曹乘、曹整和曹京,除曹整外其他兩個兒子都早殇。
曹整的年齡也不詳,此時應該不超過十歲,這樁婚事不僅是政治婚姻,而且屬于典型的早婚。曹整後來被封為侯,比曹操早死了兩年,死後又被追封為戴公。
這門親事很有意思,曹操的兒子娶了袁紹的孫女,意味着曹操自願比袁紹降低了一輩。後來曹操的兒子曹丕又娶了袁紹的兒媳婦,曹操又跟袁紹變成了同輩。
有了這門親事,曹操覺得差不多了,于是撤退。
這邊一撤,袁尚那邊果然又行動起來。建安九年(204年)二月,袁尚讓審配、蘇由守邺縣,自己再次率大軍攻打平原郡的袁譚。
袁尚走後,留守邺縣的蘇由就打起了戰場起義的主意,他悄悄跟曹軍聯絡,準備殺了審配獻出邺縣,結果情報洩漏,審配發覺,雙方戰于城中。此時袁尚的主力在洹水附近,距邺縣并不太遠,只有五十來裏。蘇由不敵審配,闖出邺縣投奔曹軍。
蘇由只出場這一次,此前和此後的情況均不詳。
曹操得到蘇由為內應的情報後,立即率軍向邺縣殺來,但晚了一步,蘇由已經敗逃出邺縣,曹操率軍順勢把邺縣圍了起來。
【三、攻克邺縣】
建安九年(204年)二月,邺縣攻防戰正式展開,對曹軍來說這又是一次艱難的攻城作戰,從二月直到八月,整整打了半年。期間曹軍堆土山、挖地道,把什麽攻城辦法都使上了,就是遲遲攻不下來。
邺縣拿下,整個黃河以北的大局可定,所以這次曹操下了決心,圍則必打,打則必勝。但邺縣在袁紹手裏經營了多年,城防堅固,曹軍一時無法得手。曹操看到這種情況,于是決定從肅清外圍之敵入手,打起了持久戰。
并州是袁軍目前最重要的後勤供應來源,其後援基地主要集中在上黨郡一帶。由上黨郡到邺縣必須經過太行山區的毛城(今山西黎城東),袁尚的部下武安縣長尹楷駐紮在此。
建安九年(204年)四月,曹操留下曹洪主持進攻邺縣的事務,自己率軍攻打毛城的尹楷,将其擊破而還。此後,曹操又率軍擊破了袁尚駐守在邯鄲的部将沮鹄,攻占了邯鄲。袁尚任命的易陽縣令韓範、涉縣縣長梁岐見勢,舉縣投降曹操。
徐晃建議曹操:“二袁未破,他們手下其他諸城都在觀望,應該重賞這兩個縣給大家看。”曹操認為有理,将韓範、梁岐都賜爵為關內侯。
這一招果然奏效,引起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不僅又有多位袁尚任命的地方官員投降,而且還招來一位重量級人物:黑山軍首領張燕。
張燕一直是袁紹的勁敵,多年以來也是袁氏集團揮之不去的夢魇。在袁紹與公孫瓒的對抗中,張燕堅定地支持公孫瓒,公孫瓒失敗後,張燕所部被袁紹打散,後來趁着袁紹忙于官渡之戰的機會,張燕才慢慢恢複了元氣,這次得以卷土重來。
張燕看到曹軍勢大,于是主動聯絡要求投降曹操。在此前的戰史中,張燕跟曹操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戰略上的敵人,他們彼此分屬于不同陣營,但他們之間卻很少有直接交手的記錄。
張燕的投奔進一步鼓舞了曹軍的士氣,加速了袁氏集團的滅亡。
但是,直到這一年的五月,邺縣仍然未能攻下,曹操改變了打法,拿出了秘密武器。
這一天,站在邺縣城牆上的審配看到曹軍的工兵們圍着城牆開始挖戰壕,整個戰壕連結起來長達四十裏,但是又淺又窄,一使勁就能跨過去(示若可越)。
審配看到後微微一笑,心想這樣的東西是沒有任何實際作用的,他也不派人出擊搞破壞,曹軍有勁沒處使就讓他們挖吧。
豈料,入夜之後曹操下令全體将士都投入到挖戰壕的工作中,一夜之間把這四十裏長的戰壕全部擴充到二丈深、二丈寬。這一回審配不笑了,他大為吃驚,但一時間也鬧不清曹操搞出這種超級工事來做什麽用。
審配的好奇心馬上就有了答案,這些戰壕裏神奇般地灌滿了水,這些水借着設計好的地勢一路前奔,直撲城內。原來,曹軍挖的不是戰壕,而是人工運河,要把附近漳河裏的水引來灌城。
最近我專程去了一趟河北省臨漳縣的銅雀臺遺址,據說現存的并不是銅雀臺而是它附近的金鳳臺,真正的銅雀臺已被改道的漳河給沖毀了。
金鳳臺遺址在一個鎮子邊上,鎮子的另一側就是漳河,現在河裏已經沒有什麽水了,站在橋上可以看到金鳳臺,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修的京珠高速公路。
因此,漳河就在邺縣跟前,雖然方便了生活和生産,但也暴露出一個隐患:邺縣很容易被水攻。
城裏本來就快撐不住了,現在又泡在了水中,更是雪上加霜。好在是夏天,要是換成冬天,不知道情況又會糟糕到什麽地步。即便如此,城裏的人也餓死了一半以上。
但城裏仍然拼命死守,袁軍的戰鬥力看來也并非不堪一擊。轉眼到了秋天,形勢對城內的袁軍越來越不利,在冀州北部一帶活動的袁尚也拼了,率領一萬多人前來救援。
袁尚想最好城裏和城外能聯絡起來,以便統一行動,這樣就得有人冒死入城傳遞消息。但此時曹軍圍城很嚴,要想順利進城,之後再順利從裏面出來,幾乎不可能。
袁尚跟他的辦公室主任(主簿)李孚商議,李孚想了想說,派個一般的人去也不頂事,不如讓我去吧。李孚雖然不是什麽大人物,但他真不錯,硬是憑着智慧和膽量順利地到已被曹軍圍得像鐵桶似的邺縣走了一趟,不僅出色完成了任務,而且自己以及随行的人都毫發無損。
李孚字子憲,巨鹿郡人,他自告奮勇冒死進城,袁尚問他需要準備些什麽。李孚回答:“聽說曹軍圍得很嚴,人多了反而容易被察覺。我帶三名騎兵就行了。”李孚挑選了三名騎兵,備好幹糧,騎上快馬,卻不攜帶武器,他們先來到邺縣北面一個叫梁淇的地方,砍了三十多根問事仗捆好了放到馬上。
問事杖是軍中執法官所持之杖,大概是用來懲罰犯錯士卒的。李孚他們又在着裝上打扮了一下,裝得像個曹軍的人,之後趁着夜色來到邺縣城外曹軍大營附近。
到晚上八點(一更半),天已經黑透,李孚他們就大模大樣出來,自稱是執法官(都督),進到曹營,大模大樣地在曹營裏逛來逛去,每到一處都大聲呵叱曹軍士卒,有的還用問事杖就地處罰。
李孚他們甚至摸到了曹操大帳的附近(遂歷太祖營前),仍然沒被識破。他們再向南走,從南面又向西,最後來到營門前,又故伎重演,對守門的士卒一頓訓斥,還把他們綁了起來,之後打開營門,上馬疾馳,一口氣奔至邺縣城下,大聲呼喊,城上有認識李孚的,趕緊吊下繩索,把他們拉了上去。
城裏的人見到李孚等人後歡聲雷動,李孚迅速與審配交換了情況,約好了下一步共同行動的信號。
城裏的人被圍了幾個月之久,此時終于盼到了援軍,不禁悲喜交加。
曹軍士兵發現有人闖營而過,立即報告曹操。曹操說:“他們不僅要進去,肯定還要出來。”
李孚把事情辦完确實要出城,但外面圍得很緊,進來已不容易,想出去更難。李孚想了一個計策,他對審配說:“現在城裏糧食少,老弱之人在城裏沒有什麽用,不如把他們放出城去以節省糧食。”審配同意,于是在城裏集中起好幾千老弱之人,讓他們都手持白幡,從三個城門同時出城。打出白幡通常意味着投降,圍城的曹軍一看那麽多人從城裏湧出來投降,紛紛上來查看情況。在這幾千人裏,就隐藏着李孚等人,他們随着大家出了城,又趁亂向西北方向突圍而去。
有人又報告了曹操,曹操笑道:“看看,讓我說對了吧?”
曹操明白,那幾個進城又出城的人是袁尚派來的聯絡員,現在他們已經約好了行動方案,馬上就會有所行動,必須密切關注城內外敵軍的動态。
李孚見到袁尚,報告了城內的情況,袁尚決定立即行動,向邺縣進軍。
聽說袁尚大軍朝邺縣方向開來,曹軍大部分将領認為不如放過他們,避開鋒芒,然後再尋找機會殲滅。這樣的想法是有依據的,《孫子兵法》裏說“歸師勿遏”,意思是說正在撤退回來的敵人不要去攔阻,因為這些人回家心切,個個都會死戰。
曹操是研究《孫子兵法》的鼻祖,對這部兵書他比任何人都熟悉。他說:“那倒也未必,這要看袁尚從哪裏來,如果是從北面的大道而來,應當避開他;如果是從西面的山道而來,我料定可以擒獲他了(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曹操說得挺有把握,根本不像說着玩,弄得大家一頭霧水。
據《曹瞞傳》說,曹操派出多路偵察兵(侯者)在這兩個方向随時打探情況,後來接到報告,說敵人走的是西邊的山道,大部隊已經到了邯鄲一帶。曹操大喜,對諸将說:“我已經得到冀州了,諸君知道不知道?”大夥不知道領導賣的是什麽關子,都說不知道。曹操說:“諸君馬上就能看到了(方見不久也)。”
曹操并不會算卦,他依據的是心理戰原理。袁尚如果是從北面的大道而來,說明他們沒有給自己留退路,來了就會決一死戰。袁尚之所以繞到西面而來,說明他想的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退到太行山裏打游擊,有了這種心理,曹操料定袁尚必敗。
袁尚的主力進到了邺縣以西七十裏的陽平亭,在滏水邊紮營。夜裏,他派人向邺縣舉火報信,城裏也舉火回應,這是李孚與審配約定的共同行動暗號。
審配率兵從城裏殺出,想跟袁尚彙合。曹操早有準備,在兩個方向都派出阻擊部隊,城裏和城外兩路敵兵均被擊敗,審配退回城裏,袁尚被曹軍順勢圍在了漳河邊。
袁尚實在沒有信心打下去了,向曹操請求投降。
現在才想起來投降,可見袁尚沒有他哥哥袁譚機靈,但此時曹操已經不需要他投降了,曹操只想盡快消滅他們。袁尚無奈,趁夜突圍,逃到附近的太行山中,袁尚的部将馬延、張觊等人臨陣投降,袁尚在太行山裏也待不下去了,只好逃往中山國。
曹軍繳獲了大量辎重,還繳獲了袁尚的印绶、節钺、衣物等,曹操命人拿着這些東西到邺縣外面搞展覽,故意讓城裏的人看。城內守軍看到,信心和鬥志完全瓦解(城中崩沮)。
審配仍然很強硬,下令堅守死戰。審配給大家打氣:“曹軍也疲憊不堪了,二公子袁熙就要來救我們了(幽州方至)!”
一次,曹操在城外巡視,讓審配看見了,命令弓箭手悄悄埋伏,找到機會突然放箭,差點射中曹操。
但是,審配再死撐也挽救不了邺縣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絕境。對于袁軍的處境,城裏有些将領看得很清楚,他們不想跟審配一塊送死,這其中就包括審配的侄子東城門守将審榮。
八月二日夜裏,審榮打開邺縣東門迎接曹軍入城,審配雖然組織人在城裏繼續巷戰,但已無力回天,邺縣很快被曹軍占領,審配也成了俘虜。
至此,打了半年之久的邺縣攻防戰以曹軍最後的勝利而告終,曹操終于能騎着馬走進這個他做夢都想占有的當時北方最重要的城市了。
【四、不小心鬧出緋聞】
邺縣被攻破時,有一個人特別着急要進城,他就是袁譚的特使,此時正在曹營做客的辛毗。
辛毗之所以心急火燎地想在城破的第一時間沖進去,是因為哥哥辛評一家人還被審配關在牢裏,他怕審配最後時刻下毒手。
據《先賢行狀》記載,當初袁譚離開邺縣時,只帶走了辛毗、郭圖的家眷,而沒能把辛評的家眷帶走,結果被審配抓了起來。審榮打開東門的時候,審配正在東南城角上,他看到曹軍進城,知道大勢已去,出于對辛評等人的憤恨,他雖然來不及逃命,仍不忘派人趕到監獄裏,把辛評一家全殺了,辛毗晚了一步。
曹軍進城,很快把審配活捉了。據《山陽公載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