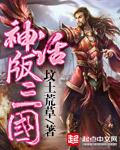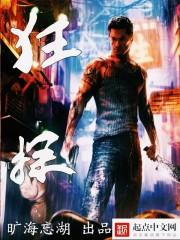第40章 (2)
例子,尤其說到了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按照這個說法,曹操僅在這兩個地方就吃了九次敗仗。
諸葛亮此處并非貶低曹操,他想說的是現實中沒有常勝将軍,像曹操那麽厲害的人,也有打不贏的時候。
但是,《後出師表》是不是諸葛亮本人所作目前仍存在争論,文中所提到的這些戰例則争論更多。其中“五攻昌霸不下”比較含糊,至今沒有統一的說法。
不過,這也是有來歷的,昌霸雖然不像呂布、劉備、袁紹那樣知名,但對曹操來說卻更麻煩。官渡之戰後,曹操曾一度分出了不少精力來對付他。
一般認為,《後出師表》中所提的昌霸即是昌,跟臧霸一樣都是“泰山幫”的成員。如前所述,“泰山幫”是曹操集團內部一個特殊群體,他們名義上服從曹操實際上自由得多,曹操想徹底解決他們但終其一生都沒有找到合适的機會。昌多次叛而又降,降而又叛,這大概就是“五攻昌霸不下”的由來。
前面講過,曹操滅呂布後專門把臧霸找出來,任命他以及昌、孫觀、吳敦、尹禮等人為郡守、國相,讓他們防守青州、徐州一帶。昌被任命為徐州刺史部的東海郡太守,該郡相當于現在江蘇省東北部、山東省南部地區,範圍涵蓋今天的連雲港到棗莊一帶。
建安五年(200年)劉備脫離曹操在徐州起兵時,昌也宣布起兵,配合劉備行動。曹操親征劉備,劉備逃到冀州,曹操急于回師官渡,無力追擊劉備,也沒有時間收拾昌,這大概是“五攻昌霸不下”的其中之一。
建安六年(201年),曹操取得官渡大捷的第二年,借着向東面調兵以及給部隊搞拉練的機會,派夏侯淵分兵攻打東海郡的昌,派張遼為副将。曹軍将昌的大本營三公山圍了起來,昌依托有利地形堅守。
現在全國叫三公山的地方有很多處,昌守的三公山在哪裏已經不詳,應該位于蘇北、魯南一帶。當年曹操征陶謙曾圍攻這一帶的郯縣,陶謙在外援劉備的幫助下打了一個漂亮的郯城保衛戰,曹軍攻城無果,被迫撤軍。如今曹軍又在昌面前一籌莫展,圍城數月,居然沒有打下來,曹軍準備的糧食眼看要吃完了。
夏侯淵考慮撤軍,但張遼不同意。張遼說:“最近我發現敵軍的箭和流石越來越少,大概這是昌心裏猶豫不定,不想力戰,我想試試能否把他招降。”夏侯淵沒有更好的辦法,就說那試試吧。
張遼來到三公山下,讓軍士朝上面喊話:“曹公有令,讓我來傳達!”昌聽到後,果然從山上下來跟張遼對話。張遼力勸昌投降,昌居然聽勸,表示願意投降。張遼為了取得昌的信任,主動提出一個人随昌上山。
張遼到了昌的家,像老朋友一樣拜訪昌的家人。張遼的真誠打動了昌,昌随張遼下了山,後來又一同拜見曹操。曹操對昌既往不咎,仍然讓他擔任東海郡太守。
曹操聽了張遼的敘述,想到張遼上三公山也有可能遇到危險,有點替張遼感到後怕,就責怪他說:“這可不是大将的處事方法呀(此非大将法也)。”張遼說:“明公您的威信著于四海,張遼奉命而行,昌必然不敢加害!”
昌的這次反叛雖然被平定了,但青徐一帶仍然是曹軍的軟肋,冀州形勢未定,曹操不可能在此過多停留。對于青徐事務,曹操除了繼續依靠臧霸、昌等人外,也想了一些辦法,他先後派出一批人到地方上任職,培養嫡系勢力,何夔和呂虔就是他們中間的代表。
何夔字叔龍,豫州刺史部陳國陽夏縣(今河南太康)人,以孝行著稱,他也是名門之後,跟袁術有親戚關系,袁術表兄袁遺的母親是何夔的姑媽。何夔避亂淮南期間曾被袁術征召,但他對袁術十分不看好,為逃避袁術,一度跑到山裏躲了起來。袁術很不高興,但由于是親戚,也沒有過于為難他。
何夔後來潛回家鄉。曹操擔任司空後,四處延攬人才,聽說何夔的名氣,就征召他為司空府下面的副處長(掾屬)。據《三國志何夔傳》記載,曹操治下很嚴,對于犯錯的辦事人員,動不動就施以杖刑,何夔身上常揣着毒藥,如果遇到這種情況打算誓死也不受辱。
據《魏書》記載,劉備在徐州反叛後,徐州一帶響應劉備的郡縣很多。曹操為了穩住形勢,派陳群等一批名士擔任地方官,何夔作為名士被任命為離曹操故鄉谯縣南面不遠的城父縣令。
後來,曹操開拓青州,在山東半島一帶設了一個長廣郡,下轄六個縣,治所在今天的山東省萊陽附近,這裏遠離“曹統區”,在當時近乎孤島,曹操想物色一個能幹的人到那裏任職,他看中了何夔。
當時長廣郡一帶海盜盛行,其中以管承、王營等海盜頭目勢力最大。何夔到任後,大力平息海盜,發展生産,在那裏站穩了腳。
針對曹操剛剛頒布的一些新法令及租稅征收政策,何夔認為長廣郡新建,又緊鄰敵占區,不宜立即推行這些新法,就上書曹操建議緩行,同時認為管理郡國應該分遠近新舊實行不同的标準,對于一些小事,可以由地方官權宜處理。
何夔的建議在現代管理學上就是分類管理、差異化經營,以及一級法人下的分級授權管理,對于長廣郡這樣成立時間不長、敵情又相當複雜的偏遠郡國來說,這些都相當重要。曹操爽快地接受了何夔的建議。
何夔經營長廣郡,為曹操在遙遠的山東半島打下了一根堅實的樁基,對于争奪青州、穩定整個東面的形勢意義都十分重大。
呂虔字子恪,兖州刺史部任城國人,前面已提到,曹操擔任兖州牧時便召呂虔為州政府屬吏,看到他有勇有謀,便派他帶兵駐紮在湖陸縣(今山東魚臺)。昌在東海郡反叛後,東海郡的襄贲縣(今山東棗莊東南)炅母等人響應昌,襄贲縣公安局局長(縣都尉)杜松無力平叛。曹操覺得呂虔有能力,就讓他代替杜松擔任襄贲都尉。
在《三國志》等史書中,襄贲都尉都寫為襄贲校尉,校尉通常設于郡國一級政府或邊境地區,此處襄贲縣應該只有都尉。
呂虔到任後,展示出他的謀略和果敢,他設計誘使炅母等幾十個叛亂頭目來喝酒,派壯士隐秘埋伏于周圍,等這些人喝醉之後,伏兵盡出,全部誅殺,形勢穩定了下來。
曹操發現呂虔确實有才能,就委派他擔任更重要的職務,到青州刺史部泰山郡當太守。泰山郡以出精兵而與江南的丹陽郡齊名,此地民風強悍,黃巾軍餘部活動頻繁,在其頭目徐和等人帶領下攻城占地,勢力很大。呂虔上任後,在夏侯淵所部配合下對徐和進行清剿,很快平定了泰山郡。
建安七年(202年),曹操下令表彰呂虔的功績。表彰令說:“有了志向就去完成它,這是烈士不惜犧牲所追求的。你到泰山郡以來,擒奸除暴,百姓得以安居樂業。作戰中你親冒箭石,每次出征必獲勝利。過去寇恂治理汝南郡、穎川郡出了名,耿在青州、兖州一帶建立了功業,古今如此。”
曹操後來還讓人舉薦呂虔為茂才,加授他為騎都尉,讓他在泰山繼續當太守。呂虔前後在泰山郡任職十多年,為曹操鞏固青州立下了大功。
【五、布局東南】
官渡之戰後的第二年即建安六年(201年),曹操陣營還發生了一件大事:曹操任命的廣陵郡太守陳登因病去世,這對曹操在徐州、揚州等東南一帶的發展是沉重打擊。
廣陵郡是徐州刺史部最南面的一個郡,大致範圍相當于今天江蘇省長江以北的部分地區,郡治廣陵縣即今江蘇省揚州市。揚州市在漢末屬徐州刺史部管轄,而揚州刺史部的治所在九江郡的歷陽(今安徽和縣),袁術統治揚州期間,又長期以九江郡的壽春(今安徽壽縣)為基地,後來把僞皇宮也設在了那裏。
廣陵郡西面與揚州刺史部的九江郡、廬江郡相鄰,南面與揚州刺史部的江南四郡相望,揚州在傳統上是袁術的占領區,曹操在這裏沒有什麽勢力。孫策崛起後迅速統一了江南,後來又驅逐了親曹操的劉勳,把勢力範圍擴展到長江以北。
孫策意外身亡後,孫權接替了兄長的事業,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大。曹操當時正集中精力在北面作戰,無力考慮東南事務,陳登占有的廣陵郡就成了曹操布局東南的唯一支點。
前面提到,徐州本土出身的陳登是地方實力派人士,先後輔佐過陶謙、劉備,後又跟随呂布,這些人都對陳登很倚重,因為他在徐州很有影響力。經過對形勢的判斷,陳登認為呂布難有成就,于是與其父陳暗中投靠了曹操,在曹操滅亡呂布之戰中出了大力,被曹操任命為廣陵郡太守,同時拜為伏波将軍,主持東南一帶的軍政事務。
曹操對東南方面的支持很有限,他原希望陳登能看住東南面的這個大門就行,沒有更多奢求,但陳登幹得很出色,遠遠超出了曹操的期望。
陳登到廣陵郡後首先抓幹部隊伍建設,他明賞罰、重威治,使各級官員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新,也贏得了百姓的信賴。有了良好的群衆基礎,他進一步安撫民衆,發展生産,很快便把地方治理得欣欣向榮,陳登也樹立起崇高威望(甚得江淮間歡心)。陳登還收編了郡內的流寇武裝,建立起自己的軍事力量。
陳登是個很有抱負的人,《先賢行狀》一書稱,陳登此時産生了“吞滅江南之志”。
陳登在廣陵郡的發展引起了江東孫氏的注意。建安四年(199年)孫策在世時,在與廬江郡太守劉勳作戰的同時,派孫權進攻陳登的軍事基地匡琦城(今江蘇射陽附近)。當時敵我力量對比是十比一,陳登泰然自若,根本沒把孫權當回事。
據《先賢行狀》記載,陳登下令關上城門,偃旗息鼓,向敵人示弱,自己登上城樓進行觀察。在城外的敵人不明究竟的時候,陳登突然下令打開南城門出擊。孫權所部沒有防備陳登會來這一手,陣形大亂。陳登親自擂鼓助威,殺得敵人大敗。此戰孫權損失了一萬多人。
孫權剛出道就遇上了老練的陳登,對此戰的記憶在孫權一生中想必都十分深刻。
敵人雖敗但依然強大,陳登一邊組織軍民積極做好守城準備,一邊派郡政府人事處長(功曹)陳矯到曹操那裏搬救兵。在救兵未到之前,為了迷惑敵人,陳登命令大家在軍營外十裏的地方準備大量柴禾,每隔十步放一堆,一到夜裏就點上火,然後組織大家使勁喊叫歡呼,好像跟援軍會師一樣。
趁着敵人疑懼之時,陳登再次主動出擊,又斬獲一萬多人,在未得到曹軍主力支援的情況下,就把危機化解了。
但廣陵郡位置太靠近江南,曹操考慮防守此地成本太大,于是收縮防線,在揚州和徐州之間的己方占領區新成立一個東城郡,由陳登以伏波将軍的身份兼任太守。
以陳登的軍政才能及個人志向,本應該在此大展身手,但他卻英年早逝了,死時才三十九歲。
有點奇怪的是,《三國志》裏沒有給陳登單獨立傳,只是在《呂布傳》裏順便對他進行了介紹,通常這意味着陳登有問題,要麽是叛徒,要麽因罪被殺,但在所有史料裏都找不到這方面的證據。
有分析認為,陳登并非真心依附曹操,他是地方實力派,有點像臧霸,甚至比臧霸還自由。陳登一直揚言要吞并江南,未必是想給曹操打天下,陳登也想建立自己的事業,成為曹操、孫權這樣的一方諸侯。
這樣的分析也只是推測而已,但似乎只有這樣才能解釋《三國志》裏沒有單獨為陳登作傳的原因。
不過,陳登的死因在《三國志方技傳》裏可以查到,他是得病死的。陳登就任廣陵郡太守不久,有一段時間感到胸悶,面色發紅,吃不下飯,就請他們家的老朋友名醫華佗來診斷。
華佗字元化,跟曹操同是沛國谯縣人,當時已經是享譽天下的名醫,他喜歡四處行醫,不分地位尊卑對病人一視同仁。陳登的父親陳當過沛國相,期間舉薦華佗為孝廉,因為這個原因,陳登和華佗有故交。
華佗對陳登進行了一番診斷,認為陳登吃海鮮水産等生腥的東西太多,在胃中生了大量寄生蟲,已經郁結難化。華佗煎了兩升湯藥,讓陳登先服一半,隔一會兒再喝另一半。
陳登按照醫囑服下湯藥,不到一頓飯功夫,即嘔吐出了三升多長相奇怪的蟲子,病也馬上好了。華佗說:“這個病三年後還會複發,遇上好醫生才有救。”三年後,就在陳登剛調任東城郡太守不久,他的病果然複發,可惜華佗這時不知道在哪裏,周圍的人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陳登不治而死。曹操在官渡前線開始發作的頭痛病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每次發病都心慌意亂,眼冒金星,一般醫生治療效果都不大。他聽說了這件事後,就派人把華佗找來。華佗采取針灸療法,紮曹操背上的膈腧穴,曹操的病情立即減輕,于是就把華佗留在身邊當專職保健醫生。
陳壽大概不太懂醫學,收集的資料也不夠詳實,膈腧穴在背部第七椎節下面一側的一寸五分處,紮這裏通常是治療咳嗽、反胃等病症的,要緩解頭部的眩暈疼痛,紮的應該是通天穴或天柱穴。
陳登之後,曹操急需物色一個能幹的人應對東南方面的事,他選的是在司徒府裏當處長(司徒掾)的劉馥。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縣人,是劉氏宗親但枝節已經很漫遠了。曹操剛到許縣時,劉馥說服袁術的部将戚寄、秦翊投誠,曹操很高興,讓司徒趙溫征辟劉馥為掾。
建安初年在荀推薦給曹操的人才裏有一個人叫嚴象,是關中人,博學機智,曹操對他寄予厚望,袁術死後派他擔任揚州刺史。曹操陣營的揚州刺史象征意義更多,他調動不了名義上是其下屬的孫策、孫權等人,要地盤必須自己去打。
建安五年(200年)孫權手下的廬江郡太守李術突然發難,攻擊嚴象,把嚴象殺了,嚴象死時三十八歲。
李術此舉并非孫權指使,李術也是想趁亂另起爐竈的一個人。像這樣的地方割據勢力在那時應該還有不少,陳登估計也算一個,但最終像孫權那樣成大事的就極少了,不僅要靠膽量和信心,還要靠實力和運氣,不能以為拉起一面大旗就能包打天下。
李術可能以為孫策剛死,孫權年輕沒有經驗和威望,而曹操又無力顧及東南事務,于是想自立門戶。但是他錯了,孫權年輕不假,但卻很有兩把刷子,對于李術不聽招呼的行為,孫權果斷地給予痛擊。
孫權知道曹操也恨李術,就先向曹操報告,打的旗號是給嚴象報仇,請求曹操在李術求援時不要理他。孫權急攻李術的大本營皖城,李術走投無路,果然向曹操求救,曹操不理,皖城攻破,孫權屠皖城,将李術枭首示衆。
李術失敗後,曹操和孫權加緊了對揚州江北二郡的争奪。曹操把劉馥從司徒府處長的閑職上調過來,破格提拔他為揚州刺史,派他到九江郡、廬江郡一帶跟孫權搶地盤。
當時,揚州的江北二郡除孫權、曹操各有一部分勢力外,還有梅乾、雷緒、陳蘭等流寇勢力。劉馥很能幹,他接受任命以後,單人匹馬來到九江郡的合肥縣(今安徽合肥),在這裏建立州治,然後招降了雷緒等人。
在此後的幾年中,劉馥積極開展地方治理,發展生産,招納流民,開展大規模屯田,興修和治理了芍陂、茹陂、七門、吳塘等水利工程。他加緊城防建設,大修合肥城,準備了大量的守城用具,使合肥成為重要的軍事基地,以後一次次抵擋住了孫吳的進攻。數十年間魏吳勢力此消彼漲,但孫吳從來沒能越過合肥一線,這與劉馥的貢獻密不可分。
劉馥主政揚州,阻擋了孫權勢力向北面的進一步發展,為曹操統一北方争取了時間。
遺憾的是,劉馥身體也不怎麽好,六七年後即赤壁之戰時,劉馥也因病去世了。
【六、莫欺負孫權年少】
讓我們把時間稍稍往前拉,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初四,孫策死于意外事件,死前急招張昭等人囑咐後事,當着衆人的面把權力移交給二弟孫權。不過,在張昭等人眼中,孫權其實并不是最佳繼承人。
據《三國志孫翊傳》記載,張昭最中意的人是孫策的三弟孫翊,理由是孫翊的性格更像孫策。張昭曾向孫策建議由孫翊繼位,但孫策沒有答應,而是選擇了孫權,當時孫權年僅十八歲。
如果孫權不是這塊料,那就是孫策看走眼了,也就沒有之後孫吳的基業了。可是,孫權确實是這塊料,別看他當時只有十八歲。
孫權的名字叫“權”,字“仲謀”,“仲”是因為他排行第二,一般說名如其人,孫權的名字也正如其人:機謀過人。如果這個名字是他父親孫堅起的,說明孫堅也很識人。
十八歲的孫權挑起了父兄留下來的大業。他面前的道路并不平坦,不僅外有強勢集團曹操、劉表,以及衆多山匪、流寇和割據勢力,而且本陣營內部不服他的也大有人在,李術敢挑戰他就是一例。甚至孫氏宗族的內部也有人不服他,堂兄孫輔就是其中一個,孫權剛一接班,孫輔就開始發難了。
孫輔的目标很明确:把孫權拉下馬,自己取而代之。
孫輔是孫羌的二兒子,孫羌是孫權的伯父,孫輔的年齡比孫策還要大,比孫權就大得更多。孫輔從小跟着哥哥孫贲作戰,在孫策開拓江東過程中,孫輔和孫贲都堅定地支持孫策。後來,孫策新成立了一個廬陵郡,任命孫輔為太守,因為孫輔功勞比較大,又授予他平南将軍,假節、領交州刺史。
孫策死前的最高軍職是讨虜将軍,這還是他向朝廷使臣求來的,本來朝廷只準備授給他一個讨虜校尉。現在,他私自授予下面人的官職比他自己的職務還高,并且還“假節”,說明他已經以朝廷代言人自居了。不過這也沒有什麽好奇怪的,袁紹、公孫瓒早就這樣做了。
孫權接班的時候,弟弟孫翊、堂兄孫都有資格和能力代替他,但他們也就想想而已,沒敢表露出來,原因是實力不足,而孫輔不一樣,他不僅敢想,而且敢幹。
孫輔想自己無論年齡、戰功還是在軍隊中的影響力都強于孫權,為什麽今後要聽這個小兄弟的指揮?孫輔決定與孫權分庭抗禮,為了增加成功的把握,他要拉個外援來作後盾,這個外援居然是曹操。
據《魏略》記載,孫輔趁孫權在東面用兵之際,偷偷給曹操寫了封信,這封信的內容不詳,只說“赍書呼曹公”,可能是要曹操派援兵來,一旦自己跟孫權翻臉,好站在自己的一邊。
孫輔認為曹操一定會答應,因為對曹操來說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可以分化瓦解孫氏集團。但曹操最終卻沒能看到這封信,原因是“行人以告,權乃還”,行人報告了孫權,孫權回兵了。
“行人”不是行路之人,也不是随便一個什麽人,而是使者的別稱。孫輔派去給曹操送信的人反水,把信交給了孫權。孫權趕緊回來,他與張昭商議對策,布局停當之後,佯裝不知,跟張昭一塊見孫輔。
兄弟倆言談之中,孫權突然發問:“兄弟間鬧點不愉快,幹嗎要呼外人來(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孫輔知道事情敗露,無言以對。
為了維護孫氏內部的團結,孫權沒有處死孫輔,但把他身邊的幕僚親信全部殺了,又将孫輔所部重新整編,分散到其他隊伍中,之後将孫輔軟禁了起來。
孫權接班伊始就分別遇到了李術和孫輔的挑戰,他依靠智謀和霹靂手段将危機一一化解,顯示出與他年齡不相符的沉着和老練,說明他天生就具有領袖才能。
經過這兩次危機,孫權的威望迅速提升,本集團內部想向他叫板的人不得不收斂了。
但孫權面臨的外部危機仍然存在。早在孫策剛死的時候,曹操就曾考慮過趁機讨伐孫權,孫權的舊部、此時已被朝廷征召為侍禦史的張竭力勸谏,曹操才打消了念頭。
其實,讓曹操打消念頭的根本原因是他分不開身。孫策死時,官渡總決戰全面打響,曹操即使認為此時是解決東南乃至整個江南問題的一個好機會,但也沒有舉兵讨伐的能力。
曹操于是以獻帝的名義拜孫權為讨虜将軍,兼任會稽郡太守,正式承認了孫權對孫策權力的繼承。曹操同時任命張為會稽郡東部都尉,這樣張又回到了江東。《三國志張傳》認為曹操之所以放走張,是想讓張影響孫權,最終使孫權“內附”。
但這只是曹操的美好願望,因為張不是陳登,張對孫氏的感情更深,當年孫策親自趕到江都聽取張對時局的分析,張的那一番足以與“隆中對”齊名的“江都對”,開啓了孫策拓展江東的大業。之後張全力支持孫策的事業,這樣的人,曹操是無法策反的。
張回到江東後,仍然深受孫氏集團的尊敬和重用,孫策的夫人吳氏因為孫權太年輕,就讓張和張昭共同輔助孫權,張也盡心竭力,兢兢業業,成為孫吳的重臣之一。
官渡之戰曹操大勝,兵強馬壯,于建安七年(202年)重新想起了孫權,他下書要孫權送兒子到許縣來做人質(下書責權質任子)。這是一件大事,孫權召集衆人商議,對于是否答應曹操的要求,大家莫衷一是(猶豫不能決)。
孫權自己的想法是不接受曹操的要求,但看到自己手下們思想并不統一,就派周瑜去拜見母親吳夫人,商議對策。周瑜堅決反對送人質,他認為江東有自己得天獨厚的優勢,将來一定有更大的作為,沒有必要搭理曹操的無理要求。吳夫人在周瑜、董襲等人的影響下,堅定了想法,最後由吳夫人出面告知大家這一政策,孫氏集團內部的思想逐步統一。
這是曹操讓孫權第一次送人質,以孫權置之不理而告終。曹操官渡之戰雖然大勝,但解決河北問題才剛剛開始,這一仗他又打了好幾年,期間一直無力追究孫權,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送人質事件讓吳夫人對周瑜另眼相看,吳夫人把孫權等兄弟幾個叫到跟前,對他們說:“公瑾跟你們的哥哥同年,比你們哥哥只小一個月,我把他當成自己的兒子一樣,你們也要以兄長之禮待他。”
孫策時期已經建立了自己的人才班底,文士方面有張昭、張、秦松、陳端等人,武将方面有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襲、呂範、淩統以及本族的孫贲、孫翊等人。這些人有的是孫堅時代的舊人,有的跟着孫策創業,孫策在他們面前有絕對權威,現在孫策不在了,孫權要想成事,必須也樹立起自己的權威來。
孫權除了将這些舊人團結在自己周圍外,還逐漸培養自己的嫡系,周瑜、魯肅等人的地位便迅速上升。
前面說過,周瑜是孫策的至交,孫策死前就寄厚望于他,讓他領重兵,任命他為江夏郡太守,但周瑜在孫氏集團內部的資歷當時還比較淺。
孫策死得毫無先兆,此時周瑜遠在巴丘(今江西峽江),距離吳郡上千裏,他得到孫策死訊後,立即率兵以急行軍的速度回師,對于穩定孫氏集團內部形勢、保證孫權順利接班發揮了重用作用。
事後,周瑜被留在吳郡,擔任中護軍,與張昭共同處理日常事務(共掌衆事),形成了武有周瑜、文有張昭的格局。周瑜此時的地位迅速上升,手中的實權超過了程普等老将以及孫贲等孫氏宗親。
張昭作為文官領袖,他對孫權的态度卻十分微妙,表面上看張昭是孫策托命之臣,處于輔臣的地位,孫權又以師傅之禮事之,但在張昭的內心裏,對于這個他原先并不屬意的接班人有一種複雜的想法。
把你當成師傅是領導的一個姿态,你千萬不能認為自己真的就是老資格了。對于一個集團來說,無論何時何地領導的權威都是第一位的,無論這個領導是否年輕,也無論你自己資歷多老、功勞多大,都要維護好領導的威信,可惜張昭不懂這些。
張昭在孫權面前常以長者自居,頻頻厲言進谏。孫權表面順從,但內心很不舒服。在這樣的背景下,另一個文士很快崛起,他就是魯肅。
魯肅字子敬,《三國志魯肅傳》說他是臨淮東城人。東漢沒有臨淮郡或臨淮國,此處的臨淮不知具體指何處。不過當時确有東城縣,在揚州刺史部的九江郡與徐州刺史部的廣陵郡交界處,屬于廣陵郡,一般認為此地在今安徽省定遠縣附近。魯肅小時候父親就去世了,由祖母把他養大,他們家很富有,是當地有名的大財主。
魯肅很有錢,他樂善好施,經常大散家財,甚至把地賣了,以赈濟窮人,他好結交朋友,在地方上很有影響力。據《吳書》記載,魯肅身材魁梧,相貌出衆(體貌魁奇),精于奇謀,又擅長騎馬射箭,經常召集一幫年輕人到山中狩獵,其實是去搞軍事操練,借狩獵演兵習陣。
周瑜投奔孫策後,被孫策任命為居巢縣長,該縣在廬江郡。有一次周瑜帶着數百人遠赴九江郡一帶執行任務,軍糧成了問題,他聽說魯肅家富有,于是來找魯肅,要求支援點糧食。
魯肅家有兩個大糧倉,每個糧倉存米三千斛,合三萬鬥,是一個大數目。魯肅随便指了其中一個送給周瑜,周瑜大為驚奇,于是和他結成好友。
袁術聽說魯肅的大名,想任命他為東城縣長。魯肅看到袁術成不了大事,予以拒絕。他知道袁術不會善罷幹休,于是組織本族人以及跟他平日交好的年輕人共一百多人到居巢找周瑜。
這個是《三國志》的說法,《吳書》記載與《三國志》略有不同,說魯肅不是到江北的居巢而是到江南去找周瑜的,帶領的也不是一百多人而是三百多人,這個說法似乎不确切。不過《吳書》記載了魯肅一行人此次出奔的細節,展示了魯肅除了有謀也有勇的一面。
據《吳書》記載,魯肅讓老弱者走在前面,讓強壯的人走在後面,他們剛出發,袁術的人就追來了。魯肅讓人在遠處立了個盾牌,他自己拉滿弓,對追兵說:“現在天下大亂,有功不能賞,不追也不會受罰,你們都是大丈夫,難道看不清這些嗎?為何還要苦苦相追?”
魯肅沖着盾牌射出一箭,箭杆射穿盾牌而過,把追兵震住了,于是不再追趕。
魯肅找到周瑜後,又因為祖母去世回到東城縣一段時間。孫權繼位後,周瑜把魯肅推薦給孫權,孫權在一次宴會上第一次見到魯肅,與他交談後十分高興,認為他是難得的人才。宴會散去,賓客們都走了,魯肅也要告辭,孫權卻把他留下,引到密室中,面對面進行交談。
孫權說:“如今漢室傾危,四方紛擾,我繼承父兄餘業,想建立像齊桓公、晉文公那樣的功勳,先生既然惠顧于我,如何來幫助我呢(君既惠顧,何以佐之)?”
魯肅回答道:“當年漢高祖劉邦想尊崇義帝,卻不能夠,因為有項羽的緣故。現在的曹操,就像當年的項羽,将軍為什麽還要當齊桓公和晉文公呢?據我看來漢室不可複興,曹操也不可能馬上滅亡。我為将軍考慮,只有鼎足于江東,以觀天下之變。這樣的計劃是現實可行的,因為北方多事(北方誠多務也),趁着多事,我們剿除黃祖,進伐劉表,占據整個長江流域(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稱帝以圖天下,這是漢高祖的事業呀,豈是齊桓晉文所可比的?”
魯肅的這番高論與日後諸葛亮“隆中對”中提出的“天下三分說”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魯肅提出這個觀點時至少比諸葛亮早了好幾年。官渡之戰曹操大敗袁紹後,中原局勢漸趨明朗,在魯肅、諸葛亮等有識之士看來,“漢室不可複興,曹操不可卒除”已成為一種共同看法,他們分別提出三國鼎立的構想,事後證明是很有遠見的。
魯肅迅速在孫氏陣營裏脫穎而出,《三國志魯肅傳》記載,孫權對張昭的話慢慢不以為然,而對魯肅越發重視。這引起了張昭的不滿,張昭經常責怪魯肅不能謙讓下士,對他非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