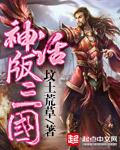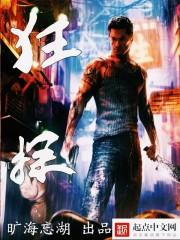第11章 (2)
人,也不信任他們。
董卓要完成的是自我奮鬥、自我救贖,他依靠的是自己的實力。
率領三千涼州精銳一路向東而來的董卓,與逃難中的少帝等人“不期而遇”,更加讓董卓堅信這是天意。
八月二十八日清晨,驚惶了一夜的洛陽百官及民衆,聽說天子、陳留王一行平安無事即将返回城裏的消息,都跑到北門外迎接。北門的正門是谷門,其大道兩邊都是人,以太傅袁隗為首的百官及民衆在這裏迎候天子歸來。
他們沒有看到天子的儀仗,看到的是穿戴着重甲的涼州鐵騎,這些士兵與洛陽官民平時見到的北軍和虎贲、羽林衛士不同,他們看起來更加強壯和冷血。
走在涼州騎兵最前面的是威風凜凜的董卓,此人有些胖,顯得很壯碩。身後有三千甲士幫襯,更顯得桀骜不馴。
站在路旁的袁紹看到這一情形,心頭是不是掠過了某種不安?
天子被衆人迎進了南宮,何太後受傷後也在南宮養傷。朝廷大事現在就要看太傅袁隗等人如何安排了。
主持國家大事,袁隗對此毫無思想準備,他已位極三公之上的上公,超越了同族中的前輩與同輩,足以在家族的光榮史上再續寫更耀眼的一筆,他只想在這個崗位上光榮退休,整個社稷江山如何治理并不在他的考慮之列。
他也許不知道,僅僅不到三年,他将以叛臣家屬的名義被砍頭,在袁氏幾世幾公的歷史上他也是獨一份的。
現在,好在有侄子袁紹支撐着,袁隗還算不太慌亂。袁紹好像早有主意,他請叔父出面召開一次會議,邀請公卿以及目前在洛陽的所有重要人物參加,包括董卓在內。
對于下一步如何安排董卓,袁紹還沒有想好,一切等到會上再看吧。
這時候,有一個人比袁紹看得更清楚,他就是剛從陳留郡(今河南開封一帶)募兵回來的鮑信。作為各路募兵隊伍中最先抵達洛陽的一支,鮑信建議袁紹趁董卓人馬較少之際一舉将其拿下,免生後患。
類似的話多年前孫堅曾跟張溫講過。但結果是一樣的,袁紹的反應跟張溫差不到哪兒去(紹畏卓,不敢發)。鮑信失望之下,借口回去再征點兵,重返陳留郡去了。
如果采納了鮑信的建議,拿下董卓的把握還是比較大的,但董卓兵團的大批人馬随後就會趕到,他們不會放棄這個用兵的借口,會趁機攻占關中乃至洛陽以西的地區,他們還會轉而跟韓遂、馬騰這些新崛起的反叛武裝聯手,整個帝國的西部将喪失。
然後就要看袁紹等人有沒有能力重新奪回這些地區的主導權。這個結果雖然不好,但卻比後面将要發生的事強得多。
由于袁紹膽氣不足,喪失了清除董卓的唯一機會。在後面召開的會議上,董卓因為有三千戰鬥力極強的涼州兵作後盾,左右了話語權,司空劉弘被當場罷免,因為他要給董卓騰個位子。董卓被任命為司空,成為三公之一。
沒過兩天,董卓又想當太尉,于是少帝下诏任命其為太尉。
在董卓的主導下,人事安排有了較大調整。袁隗仍任太傅,但錄尚書事(主持朝廷日常工作)不再提了。司徒由楊彪擔任。
袁紹仍任司隸校尉。袁術的職務有了變動,由虎贲中郎将改任後将軍,由準将直接升為中将,看起來挺美,實際是明升暗降。
虎贲中郎直接指揮天子的禦林軍,而後将軍只是一個名號,毫無意義,袁術掌握的兵權被剝奪了。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袁隗、袁紹都明白,眼前這個董太尉已經不是昔日那個仰袁家人鼻息的小董了,對于最壞的結局,他們必須有充分的打算。
曹操的職務也有了變動,此前他的職務是都尉,負責訓練步兵新軍。董卓任命曹操到另一支騎兵部隊任職。有人認為這也是明升暗降之舉,目的是奪去曹操手中的兵權。但還有人認為,董卓對曹操比較器重,在此用人之時,有意對他進行拉攏。
袁隗、袁紹在這次人事變動中也沒有完全失敗,畢竟董卓此時立足未穩,還要考慮合作。這樣,親袁氏一派的荀爽、王允、丁原等人進入九卿行列,何、鄭泰、周毖、伍瓊、鄭泰等成為董卓身邊的幕僚。
何等人是如何贏得董卓信任的,情況不清楚,這是一件頗為匪夷所思的事。如果一定要解釋的話,只能說何等人是優秀的地下工作者,此前一直隐藏得很深,董卓不太清楚他們與袁紹的真實關系。
從以後的事情發展看,何等人主動來到董卓身邊幫助出謀劃策,更像是一場精心設計好的潛伏計劃。
現在不是撕破臉的時候,對董卓是還不能,對袁紹是還不敢。接下來,雙方展開了各自的布局,在表面相安無事的情況下,跟時間賽跑。
【六、董卓玩起了心理戰】
印象中,這個時候的袁紹在董卓的淫威面前有點束手無策,禍是他闖下的,他卻沒有辦法收場,最後只好一逃了之。
印象中,董卓也就是靠耍野蠻鎮住了朝廷裏的百官,這個家夥之所以能大權在握,除了袁紹是個草包外,就是運氣實在太好。他掌權後無惡不作,縱容涼州兵禍害百姓,成為社會公敵。但這些都只能稱為印象,因為它不是或者不完全是真實的情況。
真實的情況是,袁紹并不是草包,董卓也不是一味耍橫。這二位都是有本事的人,面對何進被殺以後的新局面,他們都沒有坐等。
先說董卓,他此番能夠趁虛而入決不是靠運氣,靠的是嗅覺,是準确的情報工作和果斷的決策。在果斷這方面,袁紹比董卓差得多。
但董卓也面臨嚴峻的挑戰,他帶來的人實在太有限。
因為是去并州上任,按規定他只能自己去,後來經過跟朝廷讨價還價,允許他帶少數涼州兵前往。他能公開帶出來的只有三千人,盡管是挑出來的精銳,但人數也有點少。長驅直入到達洛陽後,實際上成為孤軍。
此時他的舊部還遠在長安以西的右扶風一帶,即使日夜趕路,沒有十來天也到不了洛陽。如果袁紹采納鮑信的建議,董卓必将在援軍到達之前被解決掉,但袁紹沒有這樣做,給董卓留下了反撲的時間。
董卓一方面派人急令後續部隊快速前進,一面玩起了小花招。
據《後漢書》記載,董卓每隔四五天就趁夜把隊伍調出城去,住在城外的軍營裏,第二天隆重地搞一個入城儀式,反複運用,造成涼州軍源源不斷到來的假象。
這種小把戲瞞不住袁紹等人,但卻在社會上造成了很大的影響,董卓的危機暫時得到緩解。不久之後,這種心理戰收到了實際效果,何進、何苗以前的舊部,在吳匡、張璋等人帶領下,率先向董卓表示效忠。
洛陽附近此時駐紮有許多互不隸屬的武裝力量,何氏舊部投奔董卓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更多的武裝力量倒向涼州軍,最有影響的是并州軍。
并州軍作為一支相對獨立的隊伍,雖不如涼州軍那麽聞名,卻也十分善戰。并州軍的核心人物是丁原,他是前并州刺史,現京城衛戍部隊司令(執金吾)。
丁原字建陽,出身貧寒之家,是一員猛将,打起仗來不要命,但在謀略方面相對較差(為人粗略)。他擔任并州刺史,張楊、張遼都是他的部下,他堅定地支持何進,派張楊、張遼領兵駐紮在洛陽外圍。
何進被殺後,丁原陷入迷茫,他不是袁紹一夥的,袁紹也沒有及時派人來跟他聯絡,丁原本來就缺少謀略,下一步如何行動,真是不知道。
丁原在用人方面也問題,呂布這時候給他當辦公室主任(主簿)。這是一個公認的反複無常的人,丁原将要毀在他的手裏。
呂布字奉先,并州刺史部五原郡九原縣(今內蒙古包頭一帶)人,骁勇而有武力,精于騎馬射箭,力量過人,號為飛将。
當時的洛陽,能單獨跟董卓動手的除了袁紹就是丁原,丁原在人數上占優,再加上張楊、張遼、呂布這樣的猛将,如果真打起來,袁紹、袁術、曹操這些人再幫把手,董卓必敗無疑。不管丁原有沒有這個想法,董卓都認為這很可怕,必須先發治人。但不能硬來,只能智取,呂布就成了拿下丁原的關鍵。
董卓也先摸了摸底,發現呂布這個人道德水準差,可以作為攻擊的目标。他策反了呂布,然後由呂布殺死丁原。董卓升呂布當師長(騎都尉),後來又升他為中郎将,封都亭侯。
丁原的舊部張楊見勢不妙退到黃河以北的河內郡,在那裏獨立發展,成為割據軍閥。丁原的另一個舊部張遼在洛陽無依無靠,也投降了董卓。
張遼字文遠,并州刺史部雁門郡馬邑縣(今山西朔縣)人,也是數得上的猛将,他勇力過人,為丁原所器重,此後一直追随呂布,呂布死後,成為曹操手下的重要将領之一。
董卓短時間內收服了何進、何苗舊部,策反了呂布,将并州軍納入自己帳下,一時間勢力大增。這時,他的後續部隊也到了,先期抵達的有兩萬人之多,兵力不足的危機完全解除。
當董卓大搞策反和兼并的時候袁紹也沒有閑着。經過與許攸、逢紀等核心幕僚商議,他采取的策略是保存有生力量,不跟董卓在洛陽死拼,積極向外部發展,擴充實力,積蓄力量,跟董卓在洛陽之外決戰。
這個戰略也不失為當前形勢下的一種高明之舉。在袁紹的安排下,王匡、橋瑁等人秘密帶人離開了洛陽,向東部的冀州、兖州一帶發展,加上此前離開的鮑信,袁紹在洛陽以東的外圍地帶布下了幾顆棋子。
在袁紹的秘密授意下,何、周毖、伍瓊等人搖身一變,成為董卓的謀士。董卓是個武夫,手下也都是武将,最缺文人和謀士,這幾個人取得很大成功,慢慢得到董卓的信任。
周毖等告訴董卓要想穩定局面必須重用一批黨人和名士,這與董卓的想法吻合,他絕不是街頭打打殺殺的混混,既然幹到了這個份兒上,做個中興之臣、開創自己的王朝也不是沒有可能。既然這樣,就必須提高品味,上點檔次,幹出點讓人稱道的事。
對于周毖等人的建議他全部采納。董卓讓何開出一份名單來,他全部任用。何先拿出一份名單,上面有荀爽、陳紀、韓融、蔡邕、申屠蟠等人的名字,董卓照單全部錄用。
這些人大多數是何進當年重用的名士,只有一個蔡邕,本朝最具知名度的大學者、音樂家,一直在外面流放,他是何的好朋友。何告訴董卓要是把他也能弄來加以重用,影響力将非同一般。于是董卓立即派人尋找蔡邕,果然被他找到了。董卓請蔡邕到洛陽來,加以重用。
周毖等人其實只是虛晃一下,他們的目的是取得董卓的信任,讓董卓覺得他們是真心為自己着想。這個目的達到後,他們亮出了自己的真實意圖,又給董卓遞上了第二份名單。這份名單上有韓馥、劉岱、孔、張邈、張咨、張超等人,這些人其實董卓都不大認識,全憑何忽悠。何說這些都是老實人,且都深得名望,如果能任用這些人當地方官,地方上的局面就能穩定下來。
韓馥、劉岱、張邈已經作過介紹。孔字公緒,陳留郡人,最初為名士符融所舉薦,在陳留郡太守馮岱手下當郡政府駐京辦主任(上計吏),能言善辯,有一定活動能量,也有一些小名氣。張咨情況知道得很少,張超是張邈的弟弟。
這些人有一個共同之處:都是袁紹的死黨。
董卓不明就裏,稀裏糊塗地把他們全部任命了:韓馥為冀州牧,劉岱為兖州刺史,孔為豫州刺史,張邈為豫州刺史部陳留郡太守,張咨為豫州刺史部南陽郡太守,張超為徐州刺史部廣陵郡太守。
接到任命,袁紹悄悄和這些人分別談了話,交待了下一步行動方略。然後,這些人一刻不停地離開洛陽上任去了。
這個任命很有講究,冀州、兖州、豫州以及陳留郡、南陽郡、廣陵郡,自北向南呈一個弧狀,在洛陽以東和以南地區構成了一個完美的半包圍圈。董卓,這就是給你預備的!董卓沒有心思照着地圖看這些,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整合洛陽的武裝上。除此之外,就是想辦法收買人心。
荀爽在老家穎川郡待得好好的,突然接到诏書,納悶極了,自己老百姓一個,怎麽會突然被任命到上千裏之外的青州刺史部平原國當行政長官?
但诏令寫得很明确,不接受就是抗旨。荀爽只能動身,剛出發就被人追上,讓他掉轉馬頭去洛陽,因為第二道诏令剛下達,他被改任為九卿之一的光祿勳卿,由副省長改任中央政府部長。總算到達了洛陽,就任部長剛三天,他再次接到職務晉升通知,改任三公之一的司空。
由一介布衣,成為國家領導人之一(司空高于部長級的九卿),有人會用一輩子時間,更多的人用完一輩子的時間也沒有完成,而荀爽前後只用了九十三天。
董卓确實有點求賢若渴了。為了進一步争取黨人的支持,他還做了一場秀:給陳蕃、窦武平反。
陳蕃、窦武的事已經過去了二十一年,董卓舊事重提,搞得極其誇張。他以太尉的身份,約了司徒黃琬、司空荀爽二人,身上套着刑具,跪到宮門外上書(俱帶詣闕上書),要求給陳蕃、窦武平反。
他們上書的對象是十四歲的天子劉辯,陳蕃、窦武被殺時他還沒有出生。現在哪怕是想給王莽搞平反,也只是董卓一句話的事,董卓把聲勢搞得那麽大,就是讓天下人知道他是黨人的可靠盟友。
有人相信,有人冷笑,有人不以為然。
韓馥等人赴任後,袁紹整天盯着日歷表算時間,他在做最後的等待。
該走的都走得差不多了,現在洛陽的盟友,只有身邊的許攸、逢紀,以及袁術、曹操等少數人。袁紹秘密通知他們也做好撤退的準備,因為跟董卓最後攤牌的時候快到了。
【七、分歧大爆發】
在袁紹琢磨如何跟董卓攤牌時,董卓先出手了。他突然提出來,想廢掉少帝劉辯,改立陳留王劉協為帝。
其實,董卓一來到洛陽就有這樣的想法。有人認為,董卓之所以固執地推行廢帝之舉,是因為九歲的陳留王劉協以機智、鎮定和回答問題大方得體給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劉辯在他眼裏懦弱不堪,不足以承擔天子的大任。
但這失于表象,于邏輯上似乎也不通。對于董卓這樣的人而言,擁戴一個智慧、賢明的君主還是擁戴一個懦弱、愚鈍的君主,哪一個更有利,回答肯定是後者,除非他腦子進水了。如果要解釋他執着地想立劉協為帝的原因,唯一靠譜的理由是年齡,因為少帝十四歲,陳留王九歲,擁戴小一點的做傀儡,便于掌握。
但這仍然不是真相。真相是:董卓要徹底肅清何進遺留下來的勢力。
少帝劉辯是何進的外甥,何進雖然死了,但忠于何進的人把希望寄托在這個十四歲的天子身上,再過幾年,天子成人就可以親政了,這是一部分人的想法。
董卓一直支持劉協,劉協的背後是靈帝劉宏和董太後。董卓跟董太後曾經續過家譜,皇太後很高興地認下了他這個“遠房侄子”,他成了劉宏的“皇兄”。如果劉協當了皇帝,他就跟皇室有了名義上的血緣關系。
劉辯登基後董卓的打算落空了,所以他第一眼看到劉辯時就沒有多少好感,還是想把劉協換上去。董卓的想法可以理解,這麽做也沒有大問題,但他犯了致命的錯誤:時機不對。
董卓的當務之急應該是解決袁紹,通過分化瓦解的辦法,将袁紹的同盟各個擊破。袁紹沒有了活動能力,其他事情都好解決。拉攏黨人也罷,廢立新君也罷,盡在掌握之中。
董卓選錯了順序,把廢立的事先提了出來。他身邊新近增加了何等一批謀士,這些家夥不會不在這個問題上給他支招,說不定還會給他支些損招,鼓動他把錯誤越犯越大。
廢掉劉辯、另立劉協對袁紹而言是不能接受的事。作為何進政治遺産的繼承人,袁紹深知周圍一部分人之所以仍堅定地支持他,很大程度上緣于何進。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他站在董卓一邊,這些人會從支持他轉為反對他。
對袁紹來說,這是個政治問題和立場問題,是絲毫不能妥協的。
今後,這個問題還将如幽靈一樣一直伴随着袁紹。他反對立劉協為帝,但反對無效,劉協最後成為天下公認的皇帝。後來,在要不要迎取劉協的問題上,盡管他比別人的機會和條件都好,可他一直猶豫不決,因為他并不承認劉協的合法身份。
結果,劉協被曹操迎走了,他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都無法改變事實。于是他改變初衷,承認劉協的合法地位,接受劉協的任命,也使自己的陣營內部産生了混亂。
每當面對這些問題,袁紹就會陷入矛盾和混亂中。
現在,是他必須表明自己态度的時候,盡管反對無效,他也要堅決反對。
矛盾在一次會議上爆發。據記載,董卓提出這個問題後,二人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最後董卓急了,手按劍柄,大聲喝叱道:“你是什麽東西,竟敢用這種态度對我!你難道還不明白,天下大事,已在我掌握之中,我想幹什麽就幹什麽,誰敢反抗!你小子難道以為我董卓的刀不夠鋒利?”
旁邊的人都吓傻了,因為董卓這個人說殺誰就殺誰,從不分時間和場合。
可袁紹一點都不怕,他也拔出佩刀,怒吼道:“天下的英雄,難道就你一個嗎(天下健者,豈獨董公)?”說完揚長而去。
這件事不會發生在朝堂上,因為在那個地方董卓和袁紹都不可能帶劍帶刀。這件事發生的地點可能是董卓的府裏,袁紹跟董卓鬧翻是需要一定勇氣的。
有人把袁紹稱為草包,事實上袁紹一點都不缺英雄氣概。
袁紹從董卓家出來,立即叫上逢紀、許攸、陳琳,并找來曹操、袁術等人商議,決定馬上逃出洛陽。
對于出逃,此前已經有了預案,袁紹往北逃,去找冀州牧韓馥;曹操往東,找陳留太守張邈;袁術往南,找南陽太守張咨。逢紀等人跟随袁紹行動。到了目的地,迅速組織力量,大家共同起事,讨伐董卓。
袁紹敢在大庭廣衆之下公然跟自己鬧翻,然後又不辭而別,這是董卓沒有料到的。董卓這時候想的還是如何讓袁紹屈服,把面子找回來,壓根沒有想到袁紹不跟他玩了。等确切消息傳來的時候,袁紹、曹操、袁術等人已經逃出了洛陽。
袁紹、曹操、袁術是如何逃出來的,史書沒作交代,但應該也不難,因為他們在洛陽還有一定影響力,且早有逃亡的準備。袁紹逃亡的時候一點都不狼狽,應該有不少人保駕,因為他還挺從容,出洛陽東門的時候,還不忘把朝廷頒發給他的司隸校尉的印信挂在門上。
早在去年(188年)四月,曹嵩的太尉一職就被罷免了。花一億錢買來的這個官職,幹了不到二百天,每天合五十萬錢以上,代價真是不菲。
曹嵩在任的六個月裏沒有到太尉府上過一天班,原因是根本不用。太尉執掌兵事,但是近些年來實際兵權被大将軍、車騎将軍、骠騎将軍等掌握,太尉既不管京師的防衛,也不管四方的戰事,成了名副其實的閑官。說到底,花錢從天子手裏買的只是個名義。
既然是個榮譽職務,曹嵩很明白千萬不能戀棧,差不多就得下來,空出來的名額,天子還可以繼續找買家。如果不識相,賴着不走,等到天子趕你走的時候,大家臉上可就都不好看了。曹嵩被免職後決定帶着小兒子曹德回谯縣養老。曹嵩走後,卞氏帶着剛兩歲的曹丕來到了洛陽。有跡象顯示,曹操逃離洛陽的時候很倉促,甚至沒來得及回家一趟。
據《三國志·武宣卞皇後傳》記載,曹操逃走後,袁術這小子臨跑路之前還幹了件缺德事,他拐到曹操家一趟,告訴卞氏說曹操已經讓董卓殺了,結果引起曹府上下的恐慌。
危難關頭,卞氏保持了鎮定,她告訴那些想各奔東西的家人:“曹君生死未蔔,如果大家今天散了,明天他回來,我們有何面目與他相見?再說,即使曹君發生了不幸,大家就是死在一起又有什麽了不起!”
關鍵時刻她穩住了局面,曹府上下安定了下來。後來,卞氏帶着曹丕居然平安地逃出了洛陽,與曹操會合。
【八、是是非非逃亡路】
有證據顯示,袁紹不是一個人逃出洛陽的,除了逢紀、許攸、陳琳等人,還帶着夫人劉氏,以及三個兒子袁譚、袁熙、袁尚。
袁紹的這幾個兒子也挺有本事,日後都顯露出過人的才能。但這似乎又不是什麽好事,無論一個組織還是一個家庭,能人太多反容易出事。
袁紹帶着老婆孩子和謀士浩浩蕩蕩地離開了洛陽,他剛走董卓就開始通緝他,但奇怪的是沒有關于他在路上遇到麻煩的記載,說明他的出逃是早已設計好的,沿途都有人保駕護航。
袁紹的目的地是冀州,州治在魏郡的邺縣(今河北臨漳),出洛陽走東北方向的大道可以直達。大體上的走法是,先沿黃河往東,過河內郡到達朝歌,然後一直往北。
在折往北方的時候,袁紹決定把妻子劉氏和三個兒子留在黃河以南,派人護送到兖州刺史劉岱那裏。劉氏與劉岱可能是同族,有親戚關系。
對于冀州之行,袁紹心裏不是完全有底,得給自己留條後路。
袁紹的擔心不無道理,“袁氏故吏”冀州牧韓馥對于袁紹的到來并不完全持歡迎态度。他把袁紹一行安排到治下的渤海郡,這裏是沿海地區,海岸線北起如今的天津市區,南抵山東省利津縣一帶。
韓馥告訴袁紹渤海郡是全國數得着的大郡,人口數超過涼州和并州,可以在此招兵買馬,積蓄實力。
等到袁紹一行到了那裏,發覺不太對勁,渤海郡已成韓馥的勢力範圍。韓馥的人整天盯着他們,說是搞後勤,實際上是搞監視,袁紹他們想幹什麽事都先要請示。那個時候沒有電話、電報,不能到互聯網上發郵件,一個請示就得一半個月,而且往往沒有下文。
實際上,袁紹他們被軟禁起來了。
往正東方向跑的曹操,運氣更差。
由于走得急,沒有帶上卞氏和曹丕,連個招呼都沒有來得及打,也不知道他們急成什麽樣,會不會遭到董卓的報複?曹操離開洛陽時,心境差到了極點。
曹操出逃的待遇也比袁紹差得遠。他是一個人跑出來的,身邊沒有人,遇到事沒有照應、沒人商量還在次要,關鍵是遇到事身邊沒有證人,因此鬧出了一樁說不清楚的公案。
曹操的目的地是陳留郡,老朋友張邈在那裏當太守,根據袁紹的安排,曹操到了陳留郡就以此為基地擴充實力,等待與各地同時舉兵。
從洛陽往陳留郡交通十分方便,曹操走的是東方大道,中途路過成臯、荥陽、中牟等地。在路過成臯附近時,曹操突然想起這裏有一個老朋友叫呂伯奢,于是就到他家串了個門。呂伯奢不在家,他兒子和幾個朋友想搶曹操的馬匹和財物,結果讓曹操發覺,親手把呂伯奢的兒子等人殺了。
這件事還有一個版本,說曹操到了呂伯奢家,呂伯奢不在家(同上一版本),他家五個兒子(數字更具體)熱情接待了他。曹操因為是逃命出來的,疑心很重,懷疑呂伯奢的兒子要殺他(沒有交待為何懷疑),于是先下手為強,親手殺了包括呂伯奢兒子在內的八個人(作案細節更清楚)。
但上面這兩個都不是流傳最廣的版本,最具知名度的版本是:曹操到了呂伯奢家,呂伯奢不在家(同上兩個版本),他兒子熱情地接待了曹操。曹操聽到食器相撞發生的聲音,以為是兵器相擊,此時他正在跑路,疑心很重,以為呂伯奢的兒子要殺自己(交代了原因),于是把他們全殺死。事後還說了一句曹氏名言:“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有情節有細節,更生動)
這三個版本一個比一個具體,令人仿佛身臨其境。但問題是,曹操如果真幹了這件事,當事人又全部被他滅口的話,是誰把這件事記下來的呢?
這個人只能是曹操。也有可能,有人喝高了,會說“想當初兄弟我怎麽怎樣……”曹操喝高了,也許會從嘴裏把這事突嚕出來,但是像後兩個版本那樣的生動鮮活,除非曹操是二百五,否則即便喝得再高他也不會說出來的。
答案只有一個:第一個版本或許存在,且轉述者是曹操本人;後兩個版本壓根不可能存在。第一個版本出自王沈的《魏書》裏,第二個版本出自郭頒的《世語》,第三個版本出自孫盛的《雜記》。這三本書的成書順序是:《魏書》最早,《世語》稍晚,《雜記》最晚。
最晚出的《雜記》對細節記錄得反而最詳細、生動,這是奇怪的事。
曹操的倒黴事還沒完。他離開成臯繼續趕路,下一站到達中牟,又出了意外。
當地有個派出所所長(亭長),工作責任心比較強,對來往的可疑人等都要認真盤問。結果讓曹操給撞上了,所長看着他臉比較生,形跡又可疑,就帶了回去,交給縣長。
這時通緝曹操的文書已經到了,縣政府人事科科長(功曹)一眼認出眼前這個人就是通緝犯曹操,但他沒有聲張,而是悄悄向縣長說情,縣長居然把曹操給放了。
這兩個東漢的基層官吏沒有想到他們無意間處理了一件關系到後世歷史走向的大事。他們都沒有留下名字(可以肯定的是,這個縣長名字不叫陳宮)。
就這樣,曹操驚心動魄地來到了陳留郡,接下來他比袁紹幸運得多。張邈比韓馥大氣,他熱情地迎接了曹操,安排曹操到治下的己吾縣、襄邑縣一帶展開募兵計劃。
再說說南路的袁術。
他很順利地逃到了南陽郡,但是到了以後發現很難開展工作,原因是沒有人支持他。
南陽郡太守是新上任不久的張咨,還沒有什麽實力。南陽郡再往南,是荊州刺史部,這時候荊州的主人還不是劉表,它的刺史叫王,不是革命黨,不好張嘴要支持。袁術一籌莫展。
這是中平六年(189年)年底的事,袁紹、曹操、袁術三個人逃出了洛陽,袁紹待在離海邊不遠的渤海郡每天曬太陽,曹操到陳留郡境內的己吾縣、襄邑縣一帶大張旗鼓開始了招兵活動,袁術窩到南陽郡,進也不是退也不是。
此時,他們三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朝廷的通緝犯。
過了年,朝廷改年號為興平,他們等來了朝廷撤銷通緝令的命令。不僅如此,袁紹還得到了一個新頭銜:渤海郡太守。
接到任命的袁紹心裏明白,潛伏在董卓身邊的那幾個兄弟開始工作了。
【九、在董卓身邊潛伏】
在洛陽,董卓要廢少帝立陳留王的想法很執着,盡管有不少人反對,董卓仍然要幹。
但是,每次他一開口,就立即有人反對。董卓很頭痛,這些士人不好對付,他們始終占據着道義的高地,你要進攻只能發起沖鋒,人家以逸待勞,動動嘴你就吃不消,弄得董卓郁悶至極,忍不住要發作。
董卓是個軍閥,是武人,也是流氓。事實證明,對付雄踞于道德高地上的士人們,流氓最有效。一天,董卓主持召開有關會議,很多人參加,有個叫擾龍宗(擾龍是複姓)的侍禦史有事向董卓報告,剛走到董卓跟前,突然,意外發生了,董卓從旁邊抄起一柄錘子朝擾龍宗腦袋上打去,擾龍宗頓時腦漿迸裂。
所有人都吓得目瞪口呆,董卓卻跟沒有事人一樣,用靴子底蹭蹭錘上的血水和腦漿說:“這小子到我跟前還佩着劍,肯定要刺殺我!”
大臣觐見天子不能佩帶武器,除非有特別允許。但董卓不是天子,大家還沒有養成跟他一起開會先交出武器的習慣,倒黴鬼擾龍宗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董卓的目的達到了,以後很多人見到他腿都開始發顫,這就是他要的效果。
董卓還時不時請大家吃飯,吃到中途,他突然說要表演個節目,在大家還沒明白過來怎麽回事的時候,幾個被綁着的人就帶了上來。董卓說這是剛抓到的罪犯,于是當衆玩開活體解剖,剝皮、挖眼、抽筋,凡能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