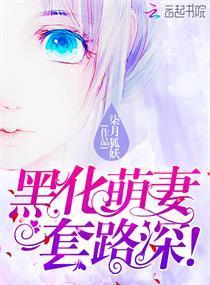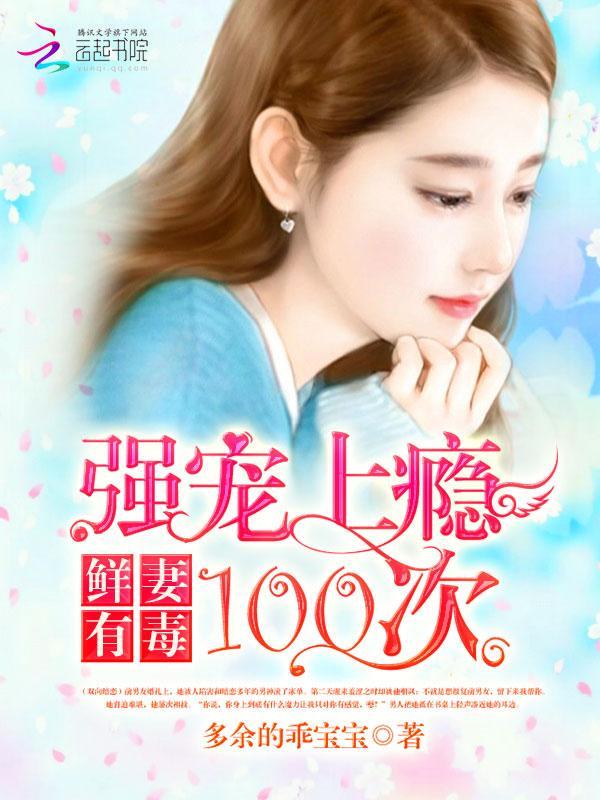第58章 Chapter58
第058章 Chapter58
Chapter58
1873年, 六月第一個星期五的維也納股市暴跌,不似很多人期盼的只是一場技術性調整。
短短一天,大盤居然蒸發了幾億奧地利盾。
投資者希望奧地利銀行能夠救市,但很快發現大小銀行都自身難保。
早在19世紀初, 拿破侖對歐洲戰争時期, 繳獲維也納國家銀行的印鈔原版。一度印發奧地利假.幣, 制造貨幣戰。
即便拿破侖已經死去五十二年,但他的幽靈似乎一直徘徊在歐陸上空。
事實上,是人性的貪欲從未更改。
在奧地利,貨幣濫發成為痼疾, 往往是當局政府直接授意,法規的制定者成為法規的違背者, 無視貨幣發行必須有足夠的貴金屬做準備。①
戰時貨幣超發,戰後還是超發。
正因為此。維也納交易所的「黑色星期五」出現後, 奧地利衆多銀行暴露出了自陷泥潭的困境。
別說找銀行救市,銀行傳出風聲, 将終止法定貨幣與白銀的兌換。那意味着大幅貨幣貶值将至。
各類報紙開始輪番大爆料。
過去一年,那些蒸蒸日上的上市公司, 所謂的優異業績究竟有多少注水編造成分。
曾經看起來漂亮的公司數據報表與宣傳語,吸引了大批投資人, 不惜抵押資産購買股票。
無形中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當股票價格被推得越高,越多人入市。越多人購買, 股價變得更高。
Advertisement
這種繁榮的地基卻是一盤散沙。一有風吹草動, 崩潰速度極快。
僅僅兩個星期, 奧地利不計其數的公司破産。
從中産精英到王室貴族, 只要參與證券交易且不曾在股價一騎絕塵的上升期反買做空,全都賠到腸子也悔青了。
很多人的資産大幅縮水。
有的一夜返貧, 有的勒緊褲腰帶過日子。
恐慌情緒開始向周邊國家蔓延。
柏林交易所與法蘭克福交易所無可避免地被影響,股市也開始暴跌。
這次金融危機看不到停止的趨勢,但是沒人能逆勢而上賺錢嗎?
有,比如那些做空投資者。
與四年前華爾街的黃金投機案不同,本次維也納交易所的全盤崩潰中,沒有聽到哪位做空者聲名大噪。
沒出現無比刺眼的超級獲利者。
即便懷疑國際游資的存在,他們也是隐蔽地分散入市,沒有出現一筆令人咋舌的超額資金。
至少大衆從公開報道中無法得知內情。
經紀人費舍爾只知道零星內部消息。
據他所知,比如他本人、交易所安保主管戴森都在這場股市危機中賺了一筆,因為遇上了金主莫倫·海勒小姐。
莫倫選擇做空交易,在6月7日前像是一則笑話,在6月7日之後變成了一則神話。
二十倍的高杠杆,讓她大賺一筆。盡管如此,因為初始交易量不夠龐大,還遠稱不上超級獲利者。
這樣悶聲發財挺好的。
費舍爾沒有炫耀。
大多數同行都在哀嚎時,他不會自爆除了傭金外,他與安保主管戴森剛剛獲得一筆額外的豐厚獎金。
為什麽兩人能得到莫倫給的獎金?
這筆錢的本質是封口費,讓他們對血腥熱氣球的去向嚴格保密,對外就說是當垃圾燒掉了。
在維也納股市崩盤之前,沒幾人在意交易所的屋頂上墜落了血腥熱氣球。
然而,金融危機地突然爆發,不只證券投資者被影響,周邊産業也遭到嚴重打擊。
經營算命炒股業務的顱相師們是在劫難逃。
股民需要找到投機失敗的借口,把損失金錢的憤怒矛頭指向顱相師,要他們給一個說法,不然就賠錢。
賠錢是不可能賠錢的。
顱相師們也找到了替罪羔羊,怪就怪那只空降在維也納交易所上方的血腥熱氣球,它破壞了許多人原有的財運軌跡。
誰放飛熱氣球,誰就是罪魁禍首。
在股市崩盤時,各種分析理論層出不窮。
比起財報數據、全球經濟産業結構變化等理論,顱相師提出的個人財運分析用到金融危機上是極其不專業的,偏偏它通俗易懂而便于傳播。
即便人們不完全相信一只血腥熱氣球能引發全國金融危機,但都關注到了這只熱氣球,它的放飛者究竟是誰?!
要查來處,肯定要問血腥熱氣球是怎麽處理的?
當時,安保主管戴森把熱氣球與牛羊腦袋賣給經紀人費舍爾,根本不在意買家是誰,對方給錢就行。
這東西從天而降,可沒有滾落人頭,只是掉出牛羊腦袋。
那麽它就是毫無威脅的垃圾。偷偷賣掉“垃圾”是賺外快,誰會蠢到把外快對交易所報賬。
此一時,彼一時。
戴森一點也不敢說實話,是把最初的謊言貫徹到底。
他說把熱氣球當成垃圾燒掉,也算是為交易所燒掉不祥之兆。
即便有人怪他沒留下調查熱氣球放飛者的證據,最多只能說他做事不嚴密,而不是群起怒罵他被錢蒙了心眼,什麽都敢賣。
*
*
仍舊是暫居多瑙河畔。
血腥熱氣球的兩位持有者,卻從維也納市內搬去了城郊。
麥考夫原本租住在證券交易所附近的旅店。
當維也納交易所的全部股票股價都一瀉千裏後,交易所一帶的氣氛從繁華忙碌變成哀嚎不休。
互毆打架、逢人就罵、極端自殺等等,這些非常影響居住體感的事時有發生,吵到人晚上睡不着覺。
麥考夫搬到人流稀少、環境空曠的城郊。
莫倫也換了地方,搬到隔壁,讓兩人做了鄰居。
說是鄰居,兩個院落相隔三四十米。
6月23日,上午十一點。
莫倫返回租借的城郊院落,沒有回自己的住處,而讓自家車夫把馬車駛向隔壁麥考夫的院子。
今天上午去交易所,完成本次做空交易的最後交割。
馬車裏,裝了重達将近一百千克的黃金,約合一萬三千英鎊。
考慮到奧地利的銀行系統備受沖擊,已經無法維持正常運作。
這時候結算股市所得利潤,直接取出黃金才能落袋為安。
如果用彙票或跨國轉賬,說不定等到提取錢款時發現銀行賬戶被凍結了,或者銀行直接破産了。
莫倫額外給了費舍爾與戴森一筆額外獎金。
感謝他們提供了熱情又專業的金融服務,祝願他們生活愉快。
這句話也就“熱情”稍微沾邊,而“專業”、“金融服務”是與事實完全不符合。
真或假,又有什麽關系呢。
重點是費舍爾與戴森拿了封口費,懂得不亂說話,他們就能在股市持續低迷的時候仍舊“生活愉快”。
從倫敦到維也納,莫倫來時各國的經濟向好,社會環境則相對穩定。
現在她即将返程,可從奧地利向外擴散的金融恐慌,已經逐漸引發各地經濟動蕩,旅途的不安定因素快速上升。
如果随身攜帶這批黃金返回倫敦,旅程的艱難度勢必翻倍。
麥考夫主動提出幫忙運輸,他可以走安全又隐秘的外交通道,把黃金轉運回英國。
他本就要為“一個朋友”,幫對方在維也納股市裏的獲利轉運回倫敦。運一份也是運,運兩份也是運,就是一件順手的事。
莫倫确信所謂的“一個朋友”,指的是福爾摩斯先生本人。
她不太清楚這個時代是否有法令,對白廳事務官在外國的證券交易做出限制。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比如借以他人名義進行交易,但不留任何憑證,事後交割錢款時只說是一筆生日禮物。
這種暗箱操作,需要足夠的信任或是利益交換,想來麥考夫不會留下授人以柄的痕跡。
“您來了。”
麥考夫與莫倫一起,分批把十箱黃金運到了地下室。
他已經提前清空了地下室大桌子,可以分散擺放十只皮箱,便于開箱驗款。
“先确認金額,再簽轉運協議。”
兩人誰都沒說不必驗款。
涉及大額資金,每一步手續辦得越穩妥,越能長久合作。
今天,莫倫為了不顯眼,用十只普通皮箱裝黃金,也就不會突兀地配備高級鎖。
每只箱子配以輕便銅鎖,鎖住兩個拉鏈頭。現在用鑰匙一轉既能打開。
麥考夫從頭到尾數了一遍,确認無誤又鎖上了箱子。
兩人離開地下室,前往書房。
莫倫收到一式兩份的轉運協議,先填寫了轉運金額。
協議寫得清楚,不收取手續費與轉運費用。今年九月一日,盡力保證她收到原裝黃金。
如果托運黃金出現了意外,當她到倫敦她取款時,能獲得1.2倍的錢款,多出來的部分是補償。
莫倫核查協議沒問題,落筆簽字。“但願一切順利。”
麥考夫也簽了字,兩人各取一份協議書保管。
麥考夫:“我無法做出100%的保證,說這筆黃金可以原封不動地送到您倫敦的住處。只能承諾,兩個月後您收到錢款金額不低于100千克的黃金。”
莫倫:“現在是不是應該開個玩笑活躍氣氛。比如問您,如果您拿不出這筆錢,準備怎麽辦?”
麥考夫:“以身抵債,為您打工直至還清錢款。這個回答有沒有令氣氛歡快起來?”
莫倫故作沉思,随後像是鄭重地做出選擇。
“我忽然覺得這筆意外之財沒了,也不過只是一樁蜻蜓點水的小事罷了。”
麥考夫煞有介事地回答:
“謝謝您。您至少沒有期盼這筆錢現在原地不翼而飛,讓我立刻淪為您的長工。”
話音落下,兩人都笑出聲。
莫倫知道轉運黃金的危險,現在是由福爾摩斯先生一人承擔。
更清楚一紙協議不是萬能的,協議只能約束願意遵守它的人。當選擇讓麥考夫負責轉運,她也就選擇相信對方的交易誠信。
莫倫真誠致謝:“謝謝您的幫忙。”
“不用客氣,這是我願意做的,也該是我向您道謝。”
麥考夫說:“您替我出面購買了血腥熱氣球,是您扛下了潛在風險。以目前的局勢,一旦這個消息外洩,您或多或少會被卷入輿論非議中。”
莫倫不在意地搖頭,“那沒什麽大不了的。當時,我已經判斷股市會崩盤,明白出面購買血腥熱氣球的利與弊。弊端是冒一定風險,但做什麽事沒風險呢?有得必有失,我得到了想要的好處。您出資,我出面,我滿足了自己對天降牛羊腦袋的好奇心。”
莫倫語氣很輕松,最後說:“好了,我們也別謝來謝去了。還有五分鐘就到中午十二點,用餐吧。午飯後,我準備離開維也納。”
“您的話很有道理。去餐廳,現在可以立即上菜。”
麥考夫輕輕抿唇,終究不再多說一句。
例如「與您可能遭遇的人身風險相比,由我轉運黃金承擔的損失是不值一提」,這樣直白的關心話語只會被他藏在眼神裏。
四目相對,眼神交彙。
莫倫捕捉到了麥考夫眼底一閃而逝的關心。
這一秒,空氣有種別樣的安靜。
莫倫仿佛低眉淺笑起來,但再細看,她的嘴角沒有任何溫柔笑容的痕跡,只是腳步不停地向外走去。
麥考夫足尖微微一頓。
可這個停頓太短,短到似乎根本不存在,他也迅速走出書房。
午餐。
兩人都沒再提血腥熱氣球或股市崩盤,只閑談了幾句從奧地利回英國能欣賞哪些風景。
過去的半個多月,莫倫已經把能做的都做了。
比如給雪莉發去電報,得知她把亡夫理查德下葬後回到了倫敦。
這就提醒雪莉,本次首發于維也納的股價暴跌,不久有極高概率蔓延至美國,是該及時處置理查德在美國時購買的一些金融資産。
有關搭載牛頭羊頭的熱氣球來自何方?
麥考夫根據熱氣球及貨物的重量、使用燃料的數量、當天維也納與周邊地區的風向風速,做了一個數學模型。計算出了大致放飛區域,它是從維也納西北側的阿爾卑斯山脈方向飛來的。
被宰殺的牛與羊是維也納的常見品種。
從熱氣球球體與吊籃的材料、樣式來看,它應是自制的,無法在市面上找到同款。
唯一的特殊點,在牛羊的口腔上颚部位有被利器刻畫的痕跡。剖開細看,六只動物腦袋的嘴巴裏都刻着字母「P I」。
麥考夫與莫倫在可疑放飛區域走了一圈。
由于當地人煙稀少,沒有找到任何目擊者,也沒能找到牛羊的軀幹部位。
究竟是誰放飛熱氣球?目的是什麽?它是否僅僅用來造成金融恐慌?「P I」是什麽意思?這些問題,無人能答。
也許将來能遇到确鑿答案,也許就此成為一則沒頭沒尾的都市傳說。
午餐後,侍者端來一盒剛送到的報紙。
不是維也納當地新聞,而是周邊國家地區的報刊。
麥考夫迅速浏覽。
十分鐘後,他停下翻動報紙的動作,目光凝視《慕尼黑早報》的內頁标題。
“海勒小姐,我不确定您還會按照原定路線返回倫敦。”
麥考夫遞出報紙,“昨天的早報,是德國慕尼黑的新聞。《驚變!慕尼黑大學學生變為藍色熒光的屍體!》”
莫倫接過《慕尼黑早報》,快速看完了整篇報道。
有關死亡事件的報道不長,事情發生在三天前6月20日。
慕尼黑大學物理系的一位大三學生被發現死在郊外。他的屍體邊放了一臺望遠鏡,疑似是在野外觀星時突發死亡。
報道沒寫他殺、自殺或意外猝死等具體死因,但寫了一個很詭異的現象。
屍體的發現者是趕早市的農夫。
當時大約淩晨四點半,天色未亮,路上沒有其他人。
農夫驅趕馬車行路,大約相隔百米,他遠遠看到前方草叢散發古怪藍色幽光。
藍光維持不到一分鐘就消失不見了。
農夫好奇,前去看個究竟。
在光源位置看到了一具屍體與一臺朝向天空的望遠鏡。沒看到明顯血跡,但附近草地是濕的,有大量清潔劑的氣味。
「根據慕尼黑警方推測,藍光來源疑似與魯米諾發光反應相關,是死亡地點的大量清潔劑與魯米諾試劑反應所致。」
報道差不多到此為止,沒有提到更多屍體細節,最後呼籲知情者提供更多消息。
麥考夫繼續查看着其他報紙,尋找是否有相關報道。
他問:“您打算去慕尼黑,了解這次死亡事件的具體情況嗎?”
距離莫倫在倫敦大學展示發光實驗,時間過去了将近兩個月。這是她第一次看到與死亡現場有關的魯米諾試劑新聞。
莫倫覺得奇怪,指出:“魯米諾試劑與血液接觸後的發光時間很短,一般是持續發光三十秒。即便優化延緩檢測過程,也只能把發光時長延長至5~10分鐘。”
如果慕尼黑郊外死亡地點,真的發生了魯米諾發光反應,而它發出的藍光又恰好能被農夫看到,說明兩種液體接觸的時間點是在農夫驅車抵達小路的幾分鐘前。
清潔劑與魯米諾試劑不會憑空發生接觸,它們自己又不會動,必是人為将其混合在了一起。
誰做的?死者本人?
如果不是的話,那位大學生是不是被謀殺?是否意味着農夫驚險地與兇手擦肩而過了?
莫倫思考片刻,決定前往慕尼黑。
“我是要改道,先去慕尼黑看一看。”
麥考夫把剩餘的報紙都翻完了,微微搖頭。
“別的報紙都沒提到這起死亡事件。如果您不着急出發,不如等我三個小時。今天下午四點半,我安排好黃金轉運,就與您一起前往慕尼黑。”
莫倫挑眉,她沒記錯的話,這位福爾摩斯先生根本不是愛多管閑事的人。
“這與您原定的行程完全不順路。”
麥考夫本來要慢悠悠地走另一條路線,取道意大利入法國,再返回倫敦。
他漫不經心地說:“公費旅游,走哪條路線都沒差別。慕尼黑的這起死亡事件有些奇怪,我去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莫倫若有所思,她很快點了點頭,似乎完全信了這種借口。
麥考夫直接取來那份《慕尼黑早報》,再仔細重讀一遍新聞報道。
他的動作很自然,雙手穩穩拿着報紙,表情嚴肅地垂眸閱讀。
沒有任何細節透露出他改變行程的真實原因——血腥熱氣球是莫倫出面買的,現在發生一起命案又牽扯上她提出的的化學試劑發光原理,兩件事會不會暗藏關聯?
這會決定同行前往慕尼黑,只是他作為血腥熱氣球的幕後購買者,選擇共同承擔風險。
沒有更多理由,他才沒有關心擔憂莫倫,那絕對是捕風捉影的錯覺。
餐桌邊,氣氛很安靜。
只能聽到兩人偶爾翻動報紙的聲音。
麥考夫又默念了一遍——有的情緒,僅僅是一種錯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