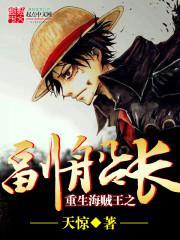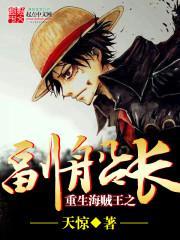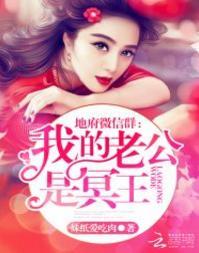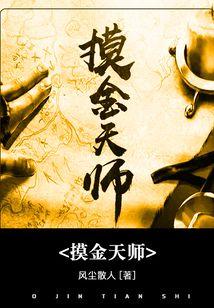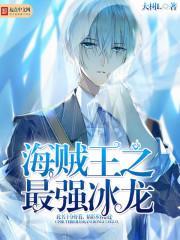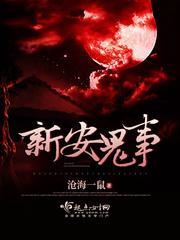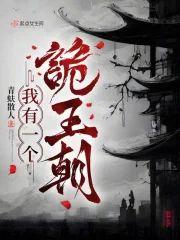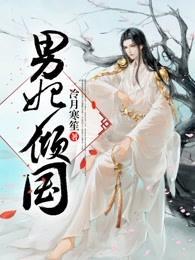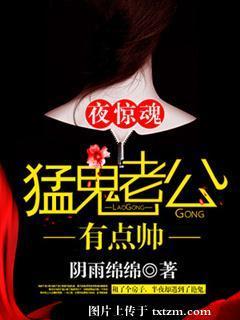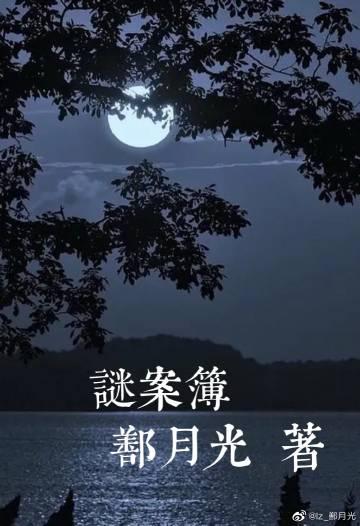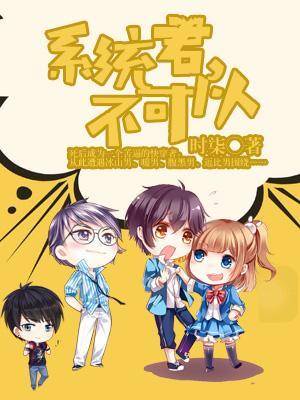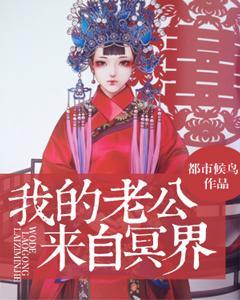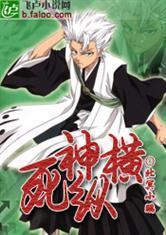第9章 記
後 記
一.關于寫作
對于我這樣的普通人而言,寫小說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三年多以前,因為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對一本“很爛”的國內同類作品大肆批判,盡情揮霍着自己的無知自大,并借楊绛先生在《洗澡》中的描述揚言:“我兩個腳指頭夾着筆,寫得還比他好些!”
朋友們對我很容忍,只是說:“好啊,那你也寫寫看。”
自作孽,不可活。
看了幾本書後旁征博引是一回事,三五死黨聚會侃侃而談是一回事,跷腳插腰對他人的作品冷嘲熱諷是一回事,自己動手寫作,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世界從來不缺陰陽怪氣戳戳點點的旁觀者,只因為腳踏實地做事真的不容易。
苦磕三年,前後兩稿,勉強有了這本書。
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只是這次,我終于明白,我沒有資格拿前人的教誨去訓斥任何人。
以上,送給我自己。
二.關于出版
我是個任性的作者,但當牽扯到出版發行,就不可能再抱着滿腦子理想去裝小孩。
其實這是個簡單到以我的智商都能想通的邏輯:出版社花錢出書——書需要賣得好——出版社能賺錢——就能繼續出更多的書——我才可能有更多的書看。
編輯只是跟我說:“你不和出版宣傳公開唱反調就好。”——真可以說是寬容到了極點。
我不懂出版,更不曉得所謂“出版宣傳”的內涵外延,但我相信,我的編輯不會做出令我反感的宣傳。
Advertisement
人可以任性,但不能因為自己的任性去傷害別人。
我更相信每一位尊敬的讀者,他們都擁有完全獨立的思考能力與鑒別水平,我寫的東西是好是壞還是不好不壞,讀者自有考量,不會僅憑宣傳造勢就把我踹進陰溝或捧上天。
實話實說,我希望這本書賣得別太糟,至少,別讓出版社賠錢。至于版稅收入,還好,我有正當職業謀生,不指着這個吃飯。
三.關于普通人
因為我是普通人,所以我寫的,也只是普通人。
我不是反天才主義者,但那群方外高人離我實在太遠。不錯,也許這個世界注定需要由一小部分精英去領導,但我更願意相信,是無數普通人在維持地球的正常運轉。
不過普通人和天才之間有一個無法改變的共同點,就是情感。無論精英或笨蛋,好人或壞人,都在共同演繹着人類的悲歡離合、愛恨情仇。
同為冷硬派風格的犯罪小說,我寫的不是什麽給精英階層收藏的高級貨,只是一個普通人寫給普通讀者看的一群普通人的故事。如果有人覺得我筆下的人物并不普通,煩請先不要急于給我扣“僞草根”的帽子,因為我一直篤信:執著與努力的普通人,同樣會創造奇跡。
四.關于北京
就像我在故事一開始寫到的,這個城市于我而言,既熟悉,又陌生。
不久前我回到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大學家屬院,順着林園區向北走,林園1號樓、2號樓、3號樓,牌號已脫落的4號樓……
然後,我就看到了被拆成一片廢墟的幼兒園。
幼兒園的西側,本來是只有一條馬路之隔的人大附小,業已搬遷多年。
還有靜林商店、修車的劉叔叔、賣漫畫書的老奶奶、自行車棚裏居住的外地夫婦、四棟平房院裏的那排桑樹……
沒有了,全都不見了。
這種體驗,許多和我一樣在北京生長的同齡人大概都有過。我早已過了悲春傷秋的矯情年齡,倒沒什麽特別的反應,只是覺得取而代之的那些高大雄偉的現代化辦公建築,實在是不甚好看。
五.關于故事與人物
很多人都問過我類似的問題:你寫的故事中,虛實各占幾分?
我沒學過統計學,歸納不出一個确切的百分比,只能粗略地說:大體上,都有原型。
因為我是個很不擅長創造的作者,讓我僅憑想象寫一部來自外平行空間的賞金獵手從黑洞穿越到南北朝擊敗楊大眼然後和韋睿拜了把兄弟娶了變性後的陳慶之最後剿滅北魏勢力統一華夏進軍歐羅巴的長篇史詩,我實在是沒這能力。
所以我只能把看過的、聽過的、經歷過的稍加彙編整理,再以此為基礎進行有限的發散性思維,就有了這麽個故事。牽扯到專業知識方面,我盡可能做到能親手核實的不親眼核實,能親眼核實的不親耳核實,親耳都核實不了的就別亂寫了。盡管如此,其間謬誤依舊難免,還請讀者多多包涵指正。
至于人物,則簡單得多——
走進花園北路35號“指紋”咖啡屋,您将有機會見到這個故事中幾乎所有的過客,馨誠、彬、老何、雪晶、白局、周所、韓教授、瞳、阿禹、石瞻、蔡瑩、小楊、姍姍、梁枭、黃鋒、阿江、彤哥、時天、小金、馬莉,也許還有陳娟……所幸,與故事中不同的是,他們的生活都很普通,只是各自承載着人生的喜怒哀樂。
我祈禱他們都能一生平安。
六.關于主題
去年的11月11日,也就是“光棍節”那天,我在某大型購物中心四層的一家小店裏買東西,突然沖進來一個女孩,盡管她衣着華美,容顏俏麗,卻盡被哭喊抓狂的姿态所代替。
後面追進來一個瘦高的小夥子,對那女孩連哄帶拽,大概是情侶之間鬧了點兒小矛盾。
店內很窄小,這兩人的手臂又頻頻揮舞,我後退回避不及,被那女孩留了長長的、鮮紅指甲的手指打了一下臉。不算很疼,但我還是本能地擡手護了一下面部,只希望能擋住下一波攻擊。
不想,引來了麻煩。
瘦高的小夥子在她身後沒看清,以為是我在動手打人,沖到前面來拽住我衣領大聲質問,口水飛濺到我臉上,還撕裂了我的圍巾。我極力解釋,同時向店主——一位四十多歲的大姐求助,希望她能證實我的無辜。
店主大概誤會了這裏面是不是包含着什麽你我他仨的三角關系,只驚恐地一遍遍重複:“你們出去鬧,你們出去鬧……”
我突然覺得很窩火,就掰開小夥子的手腕,一腳把他踹倒在地。
結果那女孩攔在我面前,改為那個替她出頭,卻又被打了回去的小夥子站腳助威,對我破口大罵。
最後,購物中心的四名安保人員趕來,把我們帶到外面,問清事實後,保安經理告訴我:“沒事了,你走吧。”
離開的時候,那個女孩昂首俏立在圍觀的人群中心,惡狠狠地死盯着我,眼神中充滿了怨恨與委屈——那眼神,我至今難忘。
啰唆了這許多,我想說的是:其實,這就是我寫的故事主題。這種無厘頭的生活橋段,每天都在發生,發生在我們每個人身邊,可以理解,又令人費解。我沒有看透任何事,恰恰相反的是,我越來越看不明白這一切。
七. 關于主旋律
我寫的,是一部主旋律小說。
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的話,這也等于提供給某些人用以诟病的話柄:這就是給某某政權某某體制某某政黨唱頌歌的谄媚詩篇,是完全背離了貧苦人民艱難生活的無病呻吟,是脫離現實的假大空悖論文集……
對此,我不知該從何說起。因為今天的我有飯吃,有房子住,有正常的生計;半個多世紀以前,我的爺爺奶奶為求一飽從老家山東遠赴關外,又因戰事所困,一路爬到北平,才終于告別了流離失所的日子。從祖上到現今,我們和許許多多家庭一樣,是某個意識形态代表取得勝利的受益者,讓我做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白眼狼,抱歉,父親打小兒就沒這麽教過我。有願意據此謾罵的,敬請随意。
社會的陰暗面我不是沒有見過,我也極其反感,我只是不喜歡寫我反感的東西而已。何況我就覺得,解決問題不是靠喊,或至少,不能僅僅靠吶喊。
雖然是破案推理,但又絕不僅僅是情節推動。就像勞倫斯布洛克的故事裏永遠有紐約的城市氣息一樣,《刀鋒上的救贖》裏,到處彌漫着北京城的味道:我們熟悉的地點、食物、哥們兒聊天的語言方式、透着真誠的不正經。如果一本小說能夠讓人感受到一座城市,那麽作者的全情投入就不難被體會了。驚喜之三。
「小2」言盡于此,多說無益。
希望罵客們在吶喊之餘,也奉獻一下自己的愛心。不多,一元錢人民幣——不曉得是不是也算“主旋律”?但這絕不是在做慈善,只是力所能及。
最後,感謝每一位讀者,您能花費時間來讀我寫的東西,我很榮幸,更是感激。希望您能開卷有益。高羅佩先生在《大唐狄公案》的前言中曾說過:“書中能使讀者滿意的方面應歸功于當初創作這些精彩故事的中國古代作家,而一切缺點都應算在我一個人的身上。”同樣,如果我的作品能夠讓您滿意,那完全是拜這個精彩的世界所賜,作者不過是一介過客,斷不敢妄肆掠美;如果您覺得很不滿意,我只能在此向您誠懇地致歉,因為斑斓的生活就在身邊,只是我拙于轉述而已。
2011年1月24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