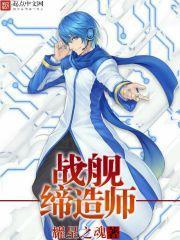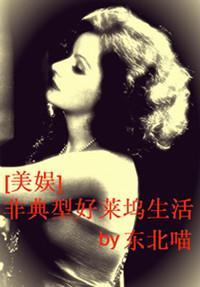第41章 《與武後靈魂互換後,李治發現了新大陸》7
第41章 《與武後靈魂互換後,李治發現了新大陸》7
【好在, 武後很體貼李治,知道他到底心理上是個男人,完全沒法接受給女兒哺乳, 所以一直是讓宮中奶娘照顧孩子。
盡管如此,有些自然反應還是無法避免。
比如嬰兒一哭, 母親就會自動分泌乳汁, 這一種神奇的自然反應一直到現代也是存在的。
所以李治還是身不得已感受了一下。】
李治要裂開了。
太平公主同情地看向父皇,現在都不敢開玩笑, 怕父皇真的崩潰。
還是假裝沒聽到吧。
【還有孕婦的坐月子,男人都以為是休息一個月, 卻不知道, 這也是排惡露一整個月。
在李治看來, 這跟來一整個月的月事沒什麽區別。
而且最可怕的是生育的後遺症,內髒、盆骨,在經歷過子宮的膨脹和胎兒的擠壓後,都變形了。胎兒誕生後并不會立即複原,需要漫長的恢複期。
這個恢複期其實并不是一個月就好了。比如想要二胎,在現代會要求順産母親至少間隔一年,剖腹産母親至少間隔三年。
也就是說, 至少一年,生産時的擠壓變形才能恢複,而且這還是現代有産後恢複輔助的前提下, 孕婦也都吃得好營養好, 在古代孕婦本就營養不足,生完孩子虧空更大。
李治感受着産後的各種不便, 疼痛比懷孕時更甚,非常崩潰。
可他不知道, 因為是貴族有奶娘和下人幫忙哺乳照顧嬰兒,已經讓他少受了許多罪。
要是在民間,産婦自己都還沒恢複好,還需要親自照顧孩子。自己身上還在不斷地流血,還要白天黑夜的哺乳嬰孩,是多麽痛苦。
Advertisement
男人不會經歷哺乳時胸被嬰孩咬到流血的痛苦,也不懂為了給嬰孩哺乳如同奶牛一般天天吃各種油膩的下奶湯多麽惡心,更不會體驗做了母親之後不管嬰孩生病還是哭是因為什麽都被責罵是母親的問題是多麽委屈。】
天幕上各種講述女人懷孕生産的艱難,越說越多,已經把不少女人吓到了。
而男人則是抗議聲越來越大:“女人不都是這麽過來的?”
“生兒育女本就是女子本分,這點苦算什麽,我養家糊口難道不辛苦嗎?”
“我服徭役不辛苦嗎?上戰場被打斷腿還不是得回來養家!”
雖然他們從來沒生過,也沒機會感受生孩子的痛苦,但是他們也不喜歡女人說出自己的痛苦。
女人,要溫順,溫柔,順從,聽從丈夫和公婆的話,做到他們的要求,所有苦難吞到肚子裏,忍受着各種苦痛成全家人孩子,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女人”。
天幕卻打破了這一切,什麽都說出來,還大聲說得天下人皆知,說得婦人共情地哭泣,說得少女們搖頭拒絕嫁人,說得他們哄着女娘與自己私奔再也不起作用——生孩子這麽痛苦,私奔了還沒娘家人幫助,豈不是自找苦吃!
男人們忿忿不平,大聲斥責,甚至有得直接要求自家女眷不許再看天幕,要把她們趕回屋內。
“你服徭役苦是女人帶給你的嗎?苛捐雜稅是女人要求的嗎?”鄰居家潑辣的婦人不客氣地大聲嚷嚷,“但是生孩子是男人要求的!”
有人出頭,其他婦人也開始大膽起來,指着那自稱養家糊口的男人嘲諷:“做工掙幾個錢就去買酒,天天喝的爛醉,這就是你說的養家糊口?”
“有本事的人家中婆娘過得好得很,孩子也聽話,男人沒本事家裏才亂成一鍋粥!”
“誰說老子沒本事!再說老子打斷你的腿!”
“外面沒本事,家裏橫得很。”
……
越是争執,吵鬧,甚至動手,醜陋的真面目越是暴露無遺。
男人的妻子沉默地在家門口看着這一切,只覺得丈夫怎麽婚後與婚前面目全非。
曾經,他雖然出身不高也能甜言蜜語哄得她那麽開心,現在才發現,那些甜言蜜語原來如此不值錢……
【李治在坐月子時,看了許多書,也有了許多思考。
他想到了武後和自己女兒從小接受的教育條件,想到了武後能接觸的夫子、能看到的書籍、能從長輩那邊得到的經驗傳授遠遠不如自己,卻依然如此優秀,越發感受到了武後的天賦和難得。
武家父母再大度,即使是允許女兒看男子的書籍,也不會像皇室皇子一樣,有條件請來天下的大儒為她講課,更不會給她講述朝堂上的為官之道,因為武家本身就有男丁,能繼承爵位、參加科舉的也只會是武家的男丁。
誰能想到,最後能站在權力巅峰、能讓整個武家輝煌的,會是武後這個女兒?
不止是武後,當他當過女人,體驗過女人的不易和各種不公平,李治再去看史書上記載的呂後、鄧太後等權勢女性,再也不像往日那樣,因為男兒身,以批判的角度去看。
想想那些從小被偏愛、得到更多教育、更多經驗傳授,以及更多父輩、家族、師門、鄉黨幫助的男人們,竟然鬥不過從小學女工學相夫教子的女人,不更顯得無能嗎?】
呂雉聽到這話,輕輕笑了。
她淡淡地看向朝堂之下那些大臣們難看的表情,笑得更開心了。
天幕這一段劇情,大概是把朝中所有男人都給罵了。
但是再回憶一番自己童年,呂雉又覺得沒說錯。
父親哪怕自诩開明,也未曾給她請夫子教學,見到劉季覺得對方有前途時,第一反應也不過是把她嫁過去聯姻。
父親不會在意當時的劉季已經跟寡婦有了私生子,也不會在意劉季比她大許多許多,更不會在意母親的哭泣和自己的不願意,因為父親對自己的定位就是嫁人聯姻、相夫教子。
呂雉又忍不住想到已經去世的前夫。
劉太公當年嫌棄劉季不如老大勤懇,整天游手好閑,劉季當皇帝後還特意設宴問自己父親,還覺不覺得自己不如老大有出息?
現在呂雉想到了早就去世的父親呂公,不知道呂公知道自己不但臨朝稱制,還追封呂氏家族其他人、讓諸呂因為自己強大榮耀,會作何感想?
【《三字經》裏說“子不教,父之過”,然而現實中,從孩子還在腹中時,無論孩子是身體健康問題還是事業成就有問題,家人和父親首先會責備的就是母親。要麽說“慈母多敗兒”,要麽說“女人頭發長見識短,都怪你帶壞了孩子”。
他們習慣性的忽視,孩子的種子是父親播下的,幼苗長歪許多情況是種子就有問題,壞種,劣種。也習慣性的忘記,女人見識短是因為在教育上從來得不到公平對待。
誰是生而知之?教育分家庭教育,社會教育,校園教育。
盡管古代許多平民的确沒機會進學校,可是家庭和社會的教育依然沒有女性的分。
比如家中種田的經驗,父親會告訴女兒嗎?不會,自小父母就是只把謀生大計和祖輩經驗傳授給兒子。
再比如在社會上如何謀生,如何做買賣,如何為人處世,父親會告訴女兒嗎?依然不會,甚至根本不允許女兒出社會社交。
就算家中有條件去上學,優先有機會上學的依然是家中的男丁。
古代書生都說明智要“讀萬卷書,行萬裏路”,但是女性有幾個能有這樣的條件?
把你困在後院中,只允許紡織刺繡,還要責備你沒見識,這就是男人。】
“子不教,父之過。”李世民輕聲一嘆,想到了自己不省心的兒子們,又想到了自己跟自己兄弟的鬥争,懷疑是自己帶了這個不好的頭。
他反複吟誦幾遍:“這《三字經》不知道是何人所寫,真想看看全文。”
“家庭教育,社會教育,校園教育。”喜愛書籍的長孫皇後也受到啓發,吟誦着,思考着。
等聽到“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眼神發亮。
貞觀朝的武将也有許多出身世家,文臣更不用說,受到這幾句經典的啓發,念誦都不夠,甚至快速要來紙筆記錄下來。
.
宋朝王應麟看到“子不教,父之過”,哈哈大笑:“是我的《三字經》!是我寫得!”
他本身寫《三字經》就是為了族學啓蒙,看到後世的女子都能随口念誦,頓時感到沒白寫。
“後世的女子都會,想必這本啓蒙書也傳遍天下。”王氏族人佩服地看着長輩。
王家自己族學中,女子年幼時的啓蒙也是會讀一樣的啓蒙書,只是“男女7歲不同席”。啓蒙過後,男子會繼續深造,女子就要去學習女工女學,世家女子也會學琴棋書畫等,家中大度的也允許學學詩詞。但是與男子深造的方向完全不同,自然也不會學治世經學等。
所以對于後世女子知道啓蒙書籍,王家人并不覺得意外,宋朝不少世家千金也善詩詞。
“讀萬卷書,行萬裏路,頗為大氣,不知道這又是何人所寫?”王應麟出于文人喜好,對這兩句頗為喜愛。
.
明朝,董其昌對此頗為淡定。
他本是書畫家,這一句“讀萬裏書,行萬裏路”出自他的《畫禪室随筆——卷二》。
已然年邁的董其昌正在練字,聽到天幕提及自己的字,當下大筆一揮,把這八個字寫了下來。
夫人誇贊道:“外人都說你的字是‘顏骨趙姿’,果然是寫得好。”
董其昌哈哈一笑,沒有自得,而是說起年輕時的往事:
“昔日,我十七歲參加松江府會考時,寫得八股文自以為非常優秀可以奪魁,誰知發榜之日才發現自己屈居堂侄董原正之下。
既是我堂侄,我豈能不知道他什麽水平?
我很不服,甚至去質問松江府知府,結果得知真相,竟然是知府衷貞吉嫌棄我的字太醜。因此即便我文章好,也只能屈居第二。”
董夫人掩唇輕笑:“所以後來你就開始臨摹顏真卿的《多寶塔帖》反複練習?”
“是,我學過許多人,無論是書法,還是繪畫。也走過很多地方。”董其昌看向自己的書架,上面滿滿當當的王羲之、王獻之、謝安、桓溫、趙估、米芾諸名家書法,有的是高價購買,有的是找人借來臨摹。還有董源、巨然、黃公望、倪瓒等畫家的畫卷,也是從臨摹開始學習。
而他也不是閉門造車的類型,等臨摹學會技法後,就開始行走天下,與人當面較量,走過大江南北不少地方。
“這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就是我能有現在成就的八字真言!”
.
明朝,李贽笑罵:“那些酸儒老喜歡說女子頭發長見識短,我看他們說得是自己。讀了那麽多聖賢書,不也一樣見識短。”
說完,他看向自己講臺下的學子,裏面不僅有常見的男性學子,也有不少婦人、少女。
他在麻城廣開學堂,招收學子不論性別,也不歧視女子,會為女子受歧視鳴不平。
當聽到天幕也談到女子的教育不公平,李贽頓時感到自己的學術理念得到支持,對學子們說道:“人們的見識是由人們所處的環境決定的,并不是先天帶來的,也不是由性別決定的。大家看,天幕也是支持這個理論。”
臺下的女學子倍感鼓舞。
而對與好友理念不合分道揚镳、與官場格格不入辭官、與這時期更普遍的儒學理學顯得異類的李贽來說,這樣的鼓舞,讓他有了面對冷眼的勇氣。
哪怕再次被污辱,被誣陷,為了自己的學說,他也堅決要走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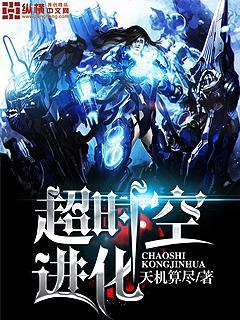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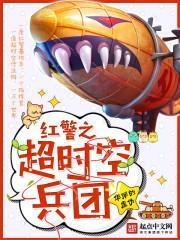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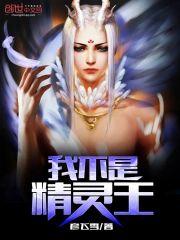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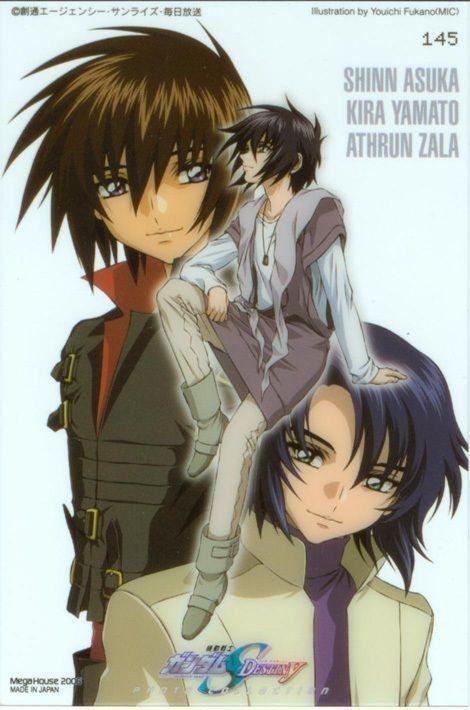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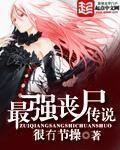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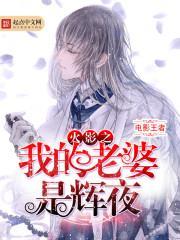
![[神夏+HP]以探案之名](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32779.jpg)

![[綜武俠]俠客們的反穿日常](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2907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