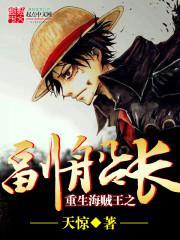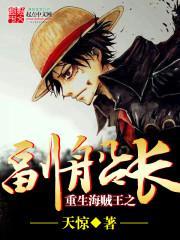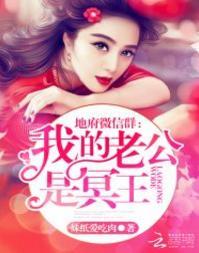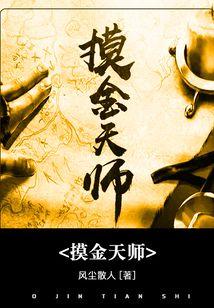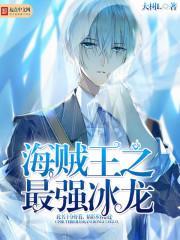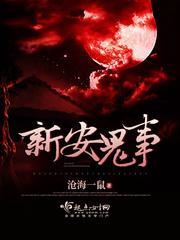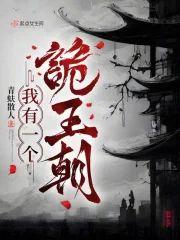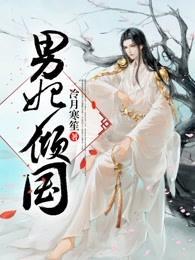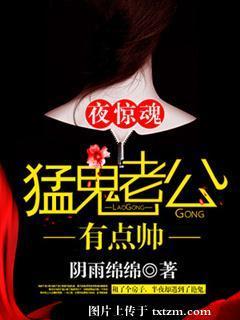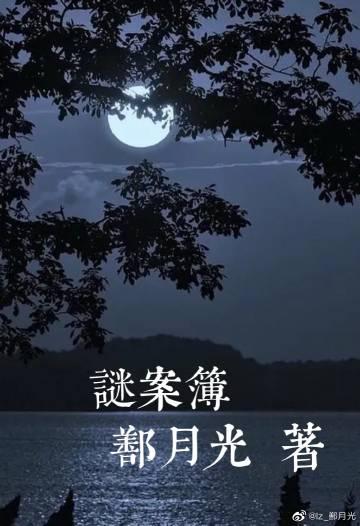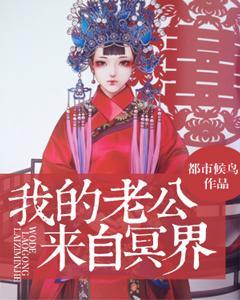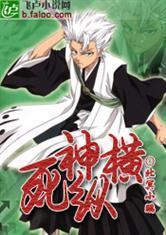第14章 人體腦組織
人體腦組織
當天晚上的小組會議,法醫王隊列席,并率先發言。
“六零一餐桌上有人體腦組織,具體地說,是腦脊液混合血液,及少量食物殘渣,啤酒瓶底部最多,桌角附近地板上也有,另外,椅背、牆上、電視上,有飛濺的血液點漬,經檢驗證實,血型與現場女受害人不符——但與金榮相符,進一步确認是否是金榮,還需是要等待DNA比對。”
除了廖俊傑和範立青現場知悉,其他人都很意外,一個個張口結舌。
“什麽?那玩意兒是人腦漿子?我還以為是蝦腦!”
馬提子扼喉慘叫,惡心的直反胃。
王隊落井下石。
“蝦腦不是小龍蝦的腦漿哈,是胰腺,性腺。”
惡趣味蓬勃而出,“我看你不挺愛吃的嗎?”
“嘔——”
馬提子想起範立青狂吐噴射的畫面,金榮破布娃娃一樣稀爛的腦袋,以及王隊斂房垃圾桶裏油污污的一次性手套,背面大口吸氣,使勁兒掐人中。
廖俊傑端坐在長條桌頂端。
“DNA确認的話,六零一,很可能就是第一案發現場。”
這話擲地有聲,衆人的目光頓時變得意味深長。
也就是說,此刻滞留醫院,等待觀察期的衛蔚,從家暴受害人搖身一變,成了命案的主要嫌疑人,而蔣森的不在場證明,也顯得十分刻意了。
“哇!範姐,你真行!”
Advertisement
斯文最先反應過來,喜氣洋洋推範立青的肩膀。
大家七嘴八舌,“要沒有範姐,這兩個案子就不相幹啊!”
“那種飛濺的油印子,随便收拾收拾就看不出來,除非做魯米諾。”
“一般入戶詢問,誰做魯米諾啊?!是不是範姐?”
“等我們查一大圈兒,發現蔣森原來就住在這兒,那他在樓下打電話報警就合情合理了,這反而解除了他的嫌疑,說不定最後把金榮定成自殺。”
王隊不樂意了,翹起大拇指指自己,“自不自殺,我定,啊!”
“一樣啊!”
十二法學專業,比法醫還嚴謹。
“等您過好幾天才确定金榮不是自殺,我們就算沖進去,把每家每戶翻個底朝天,全屋做魯米諾,也晚了,人家早全屋刮膩子刷漆,破壞完。”
王隊翻白眼,“我攔着你現在沖進去了?”
“沒證據,檢察院開不出《入屋搜查令》啊!”
“找個借口嘛,你看人家小範,不就誤打誤撞,撞上了嗎?”
“別吵!衛蔚我來審,提子!”
廖俊傑拍手叫大家靜靜,目光掃過去,馬提子剛漱了口溜回來。
“通知醫院,轉進監管病房。”
這邊範立青問,“酒瓶上采集到指紋了嗎?”
“有,瓶頸上采集到三枚,拇指、食指、中指各一,食指印沾血,但沒有蔣森的指紋做比對,還不能确認或者排除他。”
範立青問,“确認指紋是不是就能确定兇手?”
“不不不。”
王隊高深莫測地搖手指。
“目前我還不能确定究竟是擊打致死,還是墜樓致死,更加不能确定,這支酒瓶就是唯一的擊打兇器,因為酒瓶的形狀與受害人腦部的凹陷,并不是完全吻合,不過這個不吻合,也可能是姿勢造成的,我要看看有沒有其他方便握住酒瓶敲擊的姿勢——”
“吶,指紋方向是右手正握瓶,基本上就是對瓶吹的姿勢吧。”
廖俊傑說,“兩人喝酒的時候突然出手襲擊,站着的人砸坐着的?”
“我只提供手部姿勢啊,場景環境你自己推理。”
辦公室沒有啤酒瓶,王隊拿礦泉水瓶子比劃。
“正手這麽揮,反手這麽揮,行兇者如果比金榮高,或者在他背身彎腰時偷襲,是這麽個軌跡,而且指紋也可能是事後握上去的,總之——”
剩下的話斯文替他說完了,“什麽都有可能。”
“對對!”
王隊壓根兒沒聽出他是諷刺,反而豎起大拇指誇。
“985就是智商高!”
一片低低的嗤笑,王隊無辜地睜大眼。
“廢話少說。”
廖俊傑主持正義。
“關鍵是找不到蔣森,昨晚的監控就是最後線索。”
馬提子打完電話回來,站在範立青邊上撓頭。
“小賣部老板,沿街流動商販,周邊居民,當時注意力都放在墜樓上,沒人留意蔣森離開小賣部去了哪裏。人際關系排查方面,根據平臺司機反應,他微信聯系人一千多個,司機群二十來個,最愛約飯約酒,熟人裏沒什麽仇家,大家對他的印象都是熱情,愛管閑事,別人有矛盾,他擺酒平事兒。”
“平臺怎麽說?”
“‘無憂快跑’說,昨天下午快四點鐘,蔣森那輛車的定位掉線了,掉之前在梅溪鎮,這種情況不稀奇,有些司機跑的太累,會故意拔掉定位器,系統就不能強制派單,所以平臺沒當回事兒。”
“難道好端端一個大活人,說失蹤就失蹤了?”
廖俊傑拍案四顧,“還有什麽線索?”
馬提子像個提線木偶,本來癱着,被他一扥,馬上挺直身體。
“三零一是378廠的老會計,據他反應,舊廠街七十年代建造,十九棟都是宿舍,蔣森的奶奶,是378廠第一位總工程師,因公受傷後退居二線,蔣森的父親子承母業,當過最後一任廠長,他們家居住在六零一超過五十年。”
“這陳皮爛谷子上三代就你當寶!”
廖俊傑大聲吐槽,“斯文?”
斯文調出人物關系圖譜,正中間金榮的大照片,四面伸出幾根紅線。
廖俊傑點燃一根煙,望住投屏幕布。
照片上的金榮,懷裏攬着太太,太太挽着名牌包,小腹微微隆起,一個男人最志得意滿的瞬間,可他的情緒卻很緊繃,努力咧嘴,但眼睛根本笑不出來。
他現在有點同意範立青的直覺了。
金榮在害怕某個人。
照片右上方的紅線指向太太趙小琴。
斯文說,“趙小琴對金榮的人際關系一無所知,沒見過公婆和任何親友。”
右下方紅線指向金大昌和岳梅的合影。
“停産前的1995年,金榮入讀蜀都小學,這個學校現在在兩江新區,但老校區離舊廠街只有兩公裏,合理推測,金大昌一家停産後仍然居住在舊廠街,我嘗試通過學校确認金榮的具體住址,但學校沒有保留老校區的檔案。”
左上方紅線指向神秘人A,沒有照片,小字标識‘金錢交易未果’。
“A仍無頭緒,崩牙做了人臉拼圖,不好用。”
一張假臉飛上投屏,五官俱全但缺乏實感,更像漫畫或熒幕角色。
“這種圖片,對面我也認不出來,不過總之,确實不是蔣森。”
斯文晃動鼠标,手動添上第四根紅線,指向蔣森。
“蔣森出生于1991年,比金榮小三歲,也畢業于蜀都小學。”
廖俊傑很意外,“這麽巧?”
“确實很巧,他倆小學,初中、高中都是校友,初中叫觀音橋中學,高中叫五寸灘中學。”
廖俊傑來了精神,撮根煙滿懷期待地問,“中學檔案不會也沒了罷?”
“檔案在的,但沒什麽記錄,金榮高中成績突出,考一本算正常發揮。”
想到那天顧老的提示,斯文悻悻然。
“他到大三成績都不錯,大二勤工儉學在貿易公司實習,畢業轉正,有過幾次曠課,補考,大四有打架,但沒有發展到團夥暴力犯罪程度。可惜的是,這家公司是日企,前幾年就結業了,我只能找到法人代表和高管的身份信息,聯系不上,更找不到員工,目前不清楚金榮為什麽離開上海回到重慶。”
“蔣森呢?”
“蔣森考了個大專,沒去念,不過老教師反應,大部分378廠子弟成績都一般,很多家長寄望孩子頂班進廠,從小對學習就不太重視。”
“差三歲!小學還有重疊期,初中高中剛好錯開,打個照面都難。”
廖俊傑抓揉頭發,緩解疲倦麻痹的刺痛。
“我小時候,畢業班老師下來就從初一接新班,兩批學生剛好差三屆。”
斯文工作做的到位,回答底氣十足。
“我查了班主任和科任老師,全部錯開,一絲重疊都沒有。”
馬提子思忖,“那會不會父母認識?”
“不太可能。”
王隊突然插嘴,他是老重慶了,“我爸也是這種國營廠的。”
“诶,好巧,範姐她爸也是。”
馬提子笑指範立青,後者皺眉思索,聽見他叫名字怔怔嗯了聲。
王隊刮着頭皮問,“剛才你說,他們廠光宿舍就蓋了十九棟?”
“對,除了這棟幹部樓一個單元,其他十八棟都是六個單元,一個單元十二戶,總計一千多戶。”
“那比我爸廠大多了!當年啊,我們都是上子弟學校,就是工廠辦校,有些工廠種種原因沒辦學校,就跟周邊學校結對子,我的同學,從幼兒園到高中,一直是同一撥,像蔣森和金榮,父母一個廠的,校友很正常。”
馬提子說,“那還是通過父母認識的咯?”
“不是,我肯定不會跟我爸同事的孩子打交道,反而我爸對我同學的家長就很熟,沒事兒就找人打聽,看人家孩子怎麽說我的。”
馬提子代入想了下,“這倒也是——爸媽朋友的娃,我也不來往。”
眼皮子一眨,又提出一個假設。
“那再不然,金榮家也是幹部?也住蔣森家這棟?”
廖俊傑眼前一亮,這個方向未必多靠譜,但是好查。
老國營廠宿舍早期沒有産權,後來轉為商品房性質,落實産權,需要個人掏幾萬塊錢,涉及到交錢,廠裏肯定有登記,就算廠子的檔案沒了,政府産權部門也有登記,之後再易主,資料還是留存的。
但馬上又被斯文否決了。
“這個我也想過,查過了,金大昌夫婦沒有持有過這棟樓的房産。”
廖俊傑問,“其他十八棟呢?”
“我是以房查人,其他十八棟早拆了,産權登記部門的資料已經銷毀。”
“那反過來!以人查房?”廖俊傑锲而不舍。
“查不了。”
範立青插嘴,指指斯文的電腦,“沒法确定是哪個金大昌。”
斯文跟範立青飛快交換了個‘看他們刑偵這都不懂’的鄙夷眼神。
“金大昌這個名字,匹配戶口和年齡,重慶有二十五個,但沒有人的配偶叫岳梅,假設金大昌從外地調入重慶時沒有遷移戶口,把搜索範圍放大到全國,結果有數千人,比對工作太困難了,一些低線城市的戶籍資料,還沒有完成數據庫化管理,無從下手。”
線索到這兒卡了殼。
也就是說,雖然青少年時期生活半徑重疊,但金榮和蔣森可能并無交集,擦肩而過,直到修車才認識,彼此之間沒有比合作騙保更深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