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第21章
福壽堂位于鬧市中心,是座兩層的酒樓,四下開闊,二樓座位的風景極好,整個市集往來的行人盡收眼底。因此也成為京中貴人消遣的首選之地。
今日的福壽堂張燈結彩,格外熱鬧,卻不接收外客。只因京城最有名的富商方總萬将在這擺壽宴。
提起方總萬,自然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人人都知道他極富有,生意遍布全國,幾乎各行各業都有他的買賣。但了解他過往的人卻鳳毛麟角。
好在錢善武就是這鳳毛麟角中的一員,身為捕頭,如果連京城第一富豪的背景都不了解,無疑是一種失職。在結伴赴壽宴的路上,他給白逢春講述了方總萬的發家史。
方總萬不是京城人士,三十歲左右到京城來販貨,最開始做的是木材、漆器生意。後來靠這個發了財,積累了第一筆財富,之後又開始轉做其他生意。
自此他仿佛得到神仙指點一般,做什麽生意都能成功,每一樁買賣都賺了大錢。沒過幾年,就成了京城裏有名號的商人。
接着他聯合其他幾家富商,創立了自己的票號“和聯”,在全國各地設有分號。又聯系了不少部院裏的官老爺到“和聯”存銀。有了這層半官方的支持,大家自然對“和聯”刮目相看。
沒過多久他又開辦了一項新的生意:一些京官長期在清水衙門任職,熬上十幾年,終于有機會外放,到外地做一任知府、學政。可赴任需要錢,官老爺的師爺、随從都要開支,這些京官往往拿不出。
方總萬敏銳的盯上了這個機會,低息或者免費借錢給官老爺們,保他們風風光光的赴任。借出去的錢過上幾年也許歸還,也許幹脆就不要了。但是方總萬在各省的生意,官老爺們是一定要照顧的。
江南的茶葉、巴蜀的鹽井、中原的瓷器、晉北的瑪瑙,每一樁生意他的商號都有所涉及。背後都是巨大的利益。
憑着這般鑽營,方總萬很快就成了京城裏炙手可熱的紅人。商人做生意要找他,官老爺借錢要找他,甚至工部開辦一些些大工程都要找他通融。
他用賺來的錢在京城買了不少田地房産,開辦了很多酒樓和煙花場所。請碧寥來的憐花院就有他的股份,他也因此得了個“方半城”的外號。
但不少窮苦百姓卻對他恨之入骨,他買地後興建豪宅,讓不少附近的百姓流離失所,所以人們在背後送了他一個“方扒皮”的綽號。
白逢春之前并不了解方總萬的背景,聽了這些,白逢春打定了主意,撿一段喜慶的書趕快說完,看情形早點離席。
方總萬的管家早在門口守候,他泛着油光的臉上堆出滿面的笑容,不停的和到場的來賓點頭示意。
Advertisement
一旦來賓的身份讓他覺的有必要招呼,他會熱情的寒暄上幾句,親自帶客人入場。
他見了白逢春、冬青與錢善武,含蓄的點了點頭,又遙遙的拱了拱手,随即吩咐手下的仆從引二人入座。
錢善武職責在身,不能久坐,進了酒樓便去四下查看。酒樓一樓坐的是一般客人,有身份的客人都到二樓就座。白逢春因為要為客人說書,也被安排上了二樓。
他和冬青在二樓角落裏坐下,掃視四周。二樓共擺放了十幾張八仙桌,最北側有個臨時搭起的半米高的臺子,裝飾的花團錦簇。
最靠近高臺的桌子應該就是正席,正中的位置坐了位面色精黃、臉頰削瘦的中年人。看氣色有些灰敗,眼睛下有深黑色的眼袋。這人應該就是這次壽宴的主角方總萬了。
方總萬周圍坐着幾個官員和富商,有幾人白逢春似乎在哪裏見過,卻叫不出名字。
方總萬看起來很疲倦,但為了自己的壽宴強打精神支撐着,陪同桌的客人閑聊。
白逢春又看了看大堂中的其他人,卻發現了張熟悉的面孔。王之問也在席間,身邊圍着幾個文士打扮的人,正在高談闊論。
王之問也恰巧看到了白逢春,忙走過來問候:
“白先生,早聽說今天您也要登臺獻藝,我們又有耳福了。”
接着他壓低聲音道:
“上次的事情多謝您,莊明我己經教訓過了,他也保證絕不再犯。”
白逢春拱了拱手:“好說,沒想到王夫子也是方員外的貴客,看來我們真是有緣。”
王之問應該也聽過關于方總萬的非議,顯的有幾分尴尬,解釋道:
“我也是應他人之邀。方員外的一個遠房侄兒在我書院裏讀書,奉叔父t之命特地邀我一起來,我實在不好回絕,其實這種應酬的場合我是很少來的……”
看來方總萬為了舉辦這次壽宴下足了本錢,力求将京城各界名流一網打盡,盡數請到。這次恐怕不只是祝壽那麽簡單,他是要借着這次機會,要疏通平時不熟悉的關系,結識新的人脈。
白逢春暗自感嘆,到了方總萬這個位置,連過生日都是一場關乎生意的算計,實在太累。也難怪他顯的如此憔悴。
王之問指了指正席後面的一張桌子:“喏,那位巫女大人也在,這方員外真夠有面子的。”
白逢春順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霍英素和那高個子孔九也在席間。霍英素并未注意到二人,她一直盯着方總萬,似乎在思考什麽。
“想必是方員外為了感謝治病之恩,也借機邀請她了。”
白逢春想起了管家之前在茶館的話,以及祝祭那一夜他擡來的禮物。
“應該是這樣”,這時樓下傳來一陣騷動,随着“噔噔”的腳步聲,一個小厮快步上樓,向樓上的人禀告:“碧寥小姐到了”,不少人聞言沖下了樓,為了提前一睹芳容。
就連留在席間的人臉上也露出了期盼之情。白逢春與王之問對視一眼,心中都在驚訝碧寥竟有如此魔力。
霍英素此時看到了二人,起身遠遠的做了一揖,二人連忙起身還禮。以為司儀模樣的人走上高臺,宣布壽宴正式開始。
方總萬起身,對賓客的到來表示感謝,接着先舉杯自飲,随後賓客們紛紛前來敬酒。一時間觥籌交錯,熱鬧非凡。
酒過三巡,開始了助興的節目。白逢春先登臺,說了一段寓意吉祥的書話,他看出臺下的賓客有些意興闌珊,帶着期盼的眼神交頭接耳。
他明白,這些人的心思都在碧寥身上,此刻只怕自己說的天花亂墜也沒人理會。于是匆匆講完歸席。
又坐了片刻,終于該碧寥登臺了。她人還未見,伴奏的樂師先出場,古筝、短笛、三弦琴一應俱全,樂師先調了調樂器,調整好後就靜靜坐着,等待主角上場。
臺下衆人也都翹首以盼,敬酒、交談的聲音也都停了,整個二樓鴉雀無聲。白逢春無意間望了霍英素一眼,發現她沒有像其他人一樣看着臺上,反而阖上了眼,臉上顯出了有些神秘的微笑。
先是一聲清脆的古筝,接着笛聲與琴聲跟進,一起奏響宏大的樂章。麗人就在這樂章中緩緩出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碧寥竟是一身男子的打扮。
她穿着一身青布長衫,頭上戴着文士方巾,踱着方步,俨然一位飽學的書生。臉上不施粉黛,但天生麗質,膚色潔白,臉頰上自帶兩朵紅暈。
更難得的是,她穿着書生的衣服,身上就完全是書生的氣質,沒有半點風塵之氣。
她輕啓朱唇,歌聲卻不是婉約一流,灑脫中帶着一絲深情。白逢春仔細辨認,她唱的竟是蘇學士的《定風波》詞,唱至“莫聽穿林打葉聲”一句時,歌聲低沉悠揚,随即又變的高亢起來。
她的歌聲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白逢春不禁想起文人對蘇詞的評價: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公為之絕倒。”
說的是柳三變的詞适合女子清唱,而蘇學士的詞,适合壯士鐵板高歌。話雖誇張,卻很有道理。
碧寥唱蘇詞,竟也能唱出其中真意,除了自己氣質非凡,中氣足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般悠遠、灑脫的意境,唱歌的時候沒有一口悠長的中氣支持,是難以體現的。
一曲唱罷,回味悠長,不知那個冒失的公子扯着嗓子喊了聲:“好!”,随即潮水般的掌聲響起。
冬青眨眨眼,轉頭問白逢春:
“我聽這位姐姐的聲音也不見得多美,為什麽這麽多人喜歡?”
白逢春一時語塞,其中道理還真不好向她解釋。就像自己說書一樣,要有“扣子”才能吸引人,碧寥的裝扮、出人意料的選詞都是引人入勝的“扣子”,一步一步将觀衆引入了這出劇的高潮。
他只能含糊着答道:“她唱的詞大大有名,能唱好的人極少,所以大家才為她喝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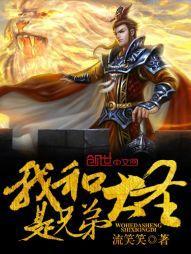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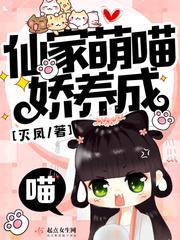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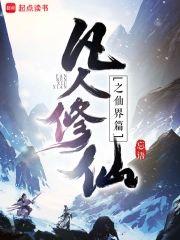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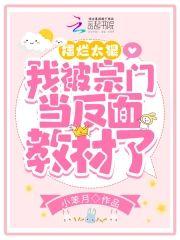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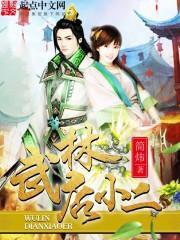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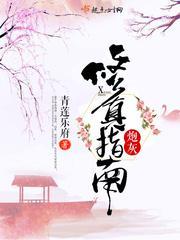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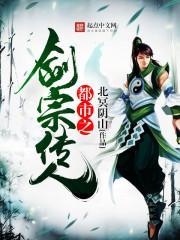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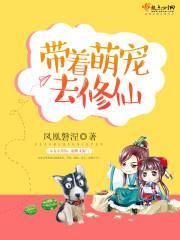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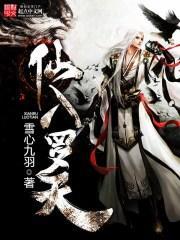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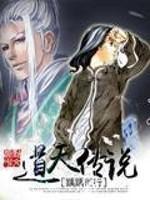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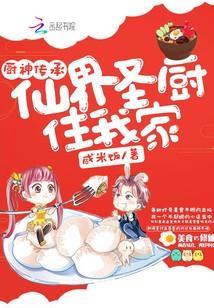



![[綜武俠]魚櫻同游](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36527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