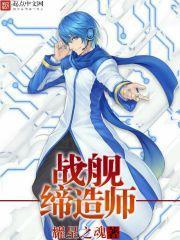第35章 致特蕾莎
致特蕾莎
“早!”吉宗清脆而雀躍的聲音從聽筒響起,讓老人幾乎被恐吓的挂掉電話。明明來電顯示的是下屬的名字,等接起來卻換了一個人,讓人想要刻意躲避都沒有這個機會。
北歐與日本的時差約有八九個小時。
吉宗特地選擇了這個時間打來了電話,恰巧是老人所處位置的早上六點,也就是他剛剛起床的時間。
在這種時候詢問對方是怎麽找到自己的,是一種愚蠢的行為。
吉宗總是有辦法,從旁人預料不到的地方串聯線索,縫縫補補的拼接出謎底。
這是恐吓,老人很清楚,這也是吉宗給他的下馬威。是我掌握了你的習慣,掌握了你的位置的威脅。
他已經老了,沒有精力去為這種冒犯而生氣。在吉宗看不到的地方,老人的笑容帶着些意味不明,像是把縱容掩藏在了笑意之下……
“God on。”
他沒有用日語作為對吉宗的回複,而是用瑞典語,不緊不慢的,把話語的主動權無形的拉了回來。
雖然吉宗這麽早找到了自己,并不在他的預料範圍內,但是還沒有超出他的掌控範圍。老人的手指在實木的桌面輕輕敲擊,迎合着他的大腦進行思考。
“北歐的分部出事了,boss現在很生氣。”吉宗不情願的把言語切換成瑞典語,語氣平鋪直敘,就像是琴酒通知他的一樣,只是簡單的進行了重複。
聽着吉宗向他彙報情報一樣,說着過時的消息。似乎是無聊,老人随手拿出了放在旁邊的黑膠唱片,放到了唱片機上。
随後撥動唱針。
回憶中,那個遞給他這個唱片的人壓低了帽檐,遮擋了大部分臉,只有下巴和嘴唇露在外面。
木質的底座因為歲月的浸潤,比原先的色澤變得更深了,那是時間沖刷下的沉澱,是無法複制的韻味。
它是19世紀90年代被生産出來的,這個時間剛好是留聲機被發明出來沒有多久。
作為一件足以被珍藏進博物館的老物件,難得的是,它此時還被保養的很好的依舊可以發揮它的作用。
随着手柄的搖動,輕柔舒緩的樂曲被重現了出來,讓吉宗原本來勢洶洶的氣勢,都削減了不少威脅性。
“我聽到那個消息了。”
老人有些漫不經心的回應着。
“可我怎麽順着線索找到了,你手下的人的動向呢?”笑意徹底掩藏了起來,圖窮匕見,吉宗展現了他的真實意圖。
“局勢動蕩的時候,總要有人借着這種勢頭擴張勢力的,我只是恰巧有這種勇氣和拼勁兒。再說,我和boss可是合作關系。盟友變得更強豈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他的回答滴水不漏,繞過了吉宗對他拐彎抹角的指控,只字不提他可能在混亂中拿到的利益,原本屬于的是組織。
吉宗有點煩躁,老人的回答像是已經知道了他的底線。确實,他查到了老人勢力的動向,但是線索斷的徹底,根本無法把他,和侵吞組織北歐勢力的那個神秘人聯系在一起。
有什麽脫離掌控的感覺出現在了心頭,那是他許久未曾經歷過的了。
于是不安愈甚……
但随後,心中某種荒誕的想法破土而出,探頭探腦的彰顯存在感。
又被他親手掐死在萌芽期。
手中所有的線索,似乎都已經被查到了盡頭,沒有了繼續推進的可能。坐在電腦前的吉宗閉上了眼睛,雙手無意識的在眼前搭在了一起,眉頭蹙起。
最近因為習慣性的皺眉,他的眉心已經形成了肌肉記憶。即使沒有生出皺紋,也會在無意識的時候團起來,像是在引導周圍的人将他的眉頭撫平。
可惜琴酒不會做出這種親密的舉動,而吉宗本人也根本不在意這點小事。
大腦如同檢索一般掃過了全部的線索,每一個都被他确認過推到了盡頭。
沒什麽迷題是找不到答案的,他很确信這件事情,此時的困惑,只是有什麽地方被他漏下了。
愈在這種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時候,大腦就會開始想些別的東西。剛才老人随手播放的樂曲就開始在腦海裏回映。
随後記憶流轉。
【阿爾】:你猜我收到了什麽?
【小羽毛】:什麽?
他總是很捧場,從不感到厭煩。
在現實中,是吉宗圍着阿爾轉圈,像是環繞在地球周圍的月亮。
可在兩人獨有的空間裏,是阿爾經常去給吉宗分享些有趣的東西。
他們很會尋找平衡,因為他們不想也不會讓任何一個自己吃虧。
【阿爾】:貝多芬的手稿,原版。
他強調了一遍。
【小羽毛】:嚯,那可是相當珍貴了,是哪一首?
吉宗明顯來了興趣。
兩人在上一世還沒有被分開的時候,就很喜歡貝多芬的樂曲。
貝多芬拓寬了鋼琴力度的對比,頻繁運用極強與極弱音。因此,他在鋼琴音樂作品中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激烈沖突,增加了極具戲劇性的音響效果。
而戲劇性,正是他們畢生追求的東西,在上輩子沒有成功達成的,只能憑借音樂以及文學作品滿足的屬于自己的訴求。
而在這一生,終于算是憑借接連的作死 ,如願以償。
但是喜歡戲劇性的沖突所擁有的,或許可以稱為後遺症的結果是,他們無法忍受無聊的人生。就像是煙花,經歷漫長的準備過程,厚積薄發後,在天空絢爛了一瞬,妝點漆黑的夜空,随後就消失了。
【阿爾】:落款寫的是致特蕾莎,沒有備注什麽我們聽過的名字,難道是這個世界的限定?
阿爾拿着手稿,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産應該被玻璃保護起來,而不是被他用手拿着,任由手上可能存在的油脂,損害着脆弱的紙張。可他不願意表現出對手稿的珍重,那會讓坐在他對面,仔細盯着他表情細微變化的人坐地起價,得寸進尺。
當然,【冷靜】的特質不會給對方這個找到阿爾破綻的機會,他的感情從來只有在需要的時候,才會外露。
“獻給特雷莎,1810年4月27日,為了紀念。”他輕輕念出了手稿上的字樣,把那個手稿放回了原來的盒子裏,随後就不再分給它眼光。從頭到尾,都表現的像是感受不到它的價值一般。
心裏卻并非如此。
誠然,這份手稿現在還不屬于他,但他已經對它勢在必得。無論用什麽方式,他都會得到這份手稿。
阿爾在等待着對方,為自己進一步的介紹,對方當然會這樣做,因為這是一個絕佳的增加砝碼的機會。
不出他所料,“其實這個就是《致愛麗絲》的原稿”,那人喝了口水,為阿爾講述了這段故事。
在1808-1810年間,貝多芬教了一個名叫特蕾莎·瑪爾法蒂的女學生,并對她産生了好感,有一次在心情非常愉快舒暢的情況下,就寫了一首《a小調巴加泰勒》的小曲贈給她,并在樂譜上題寫了“獻給特雷莎,1810年4月27日,為了紀念”的字樣。
之後,這份樂譜就一直留在了特蕾莎那裏,而貝多芬沒有自留底稿。因此,他去世後在其作品目錄裏都沒有這首曲子。
直到19世紀60年代,德國音樂家諾爾為貝多芬寫傳記,在特雷莎·瑪爾法蒂的遺物中才發現了這首樂曲的手稿。
1867年,諾爾在德國西南部的城市斯圖加特出版這首曲子的樂譜時,把原名《致特蕾莎》錯寫成《致愛麗絲》。
從此,該鋼琴作品開始以《致愛麗絲》的名稱在世界上廣泛流傳,而原本可能的命名——《致特蕾莎》卻被人們忘記了。
聽那人講話确實很無聊,于是阿爾在頻道裏給吉宗科普,一心二用的順便和那人談判。
【小羽毛】:如果沒有這個手稿,特雷莎的名字會消失吧,被愛麗絲這個大家廣為流傳取代,真可悲。
【阿爾】:就像我們,只有吉宗和光以及阿爾布雷克特的名字留存在世,卻沒人知道我們之前的名字。
【小羽毛】:但這兩個名字是我們努力經營的,畢竟名字從來只有在別人那裏被使用,才有了意義。
看似是在對話,卻是自我的和解。
在此刻,吉宗和阿爾徹底放下了對前世姓名的求索,專心的沉浸在了這場戲劇之中。
樂譜受了一番波折,最終還是到了阿爾的手裏,它被裝裱在玻璃櫃裏面,陳列在他的珍藏室中。
之前提到的,“愈在這種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時候,大腦就會開始想些別的東西。”
真的是這樣嗎?
吉宗的大腦可不是如此,它是精細的,被馴養的很好的,違反常理的。
他猛的睜開了眼睛,天色已經暗沉,而因為長時間的閉眼思索,房間裏并沒有開燈,但是如果房間裏有人,就會發現吉宗的眼睛,幾乎成了唯一的光源。
那個音樂有問題……
在發現這點之後,解密游戲就像是獲得了提示,得以繼續推進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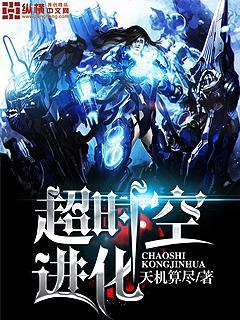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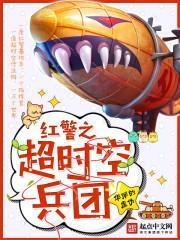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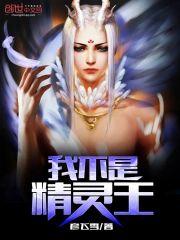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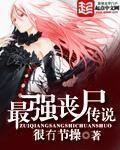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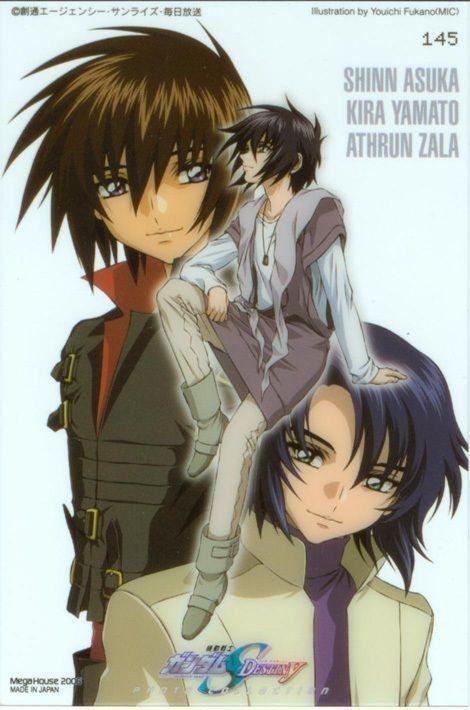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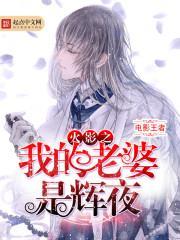

![[神夏+HP]以探案之名](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32779.jpg)
![[綜武俠]俠客們的反穿日常](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2907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