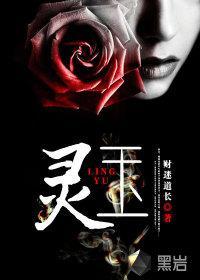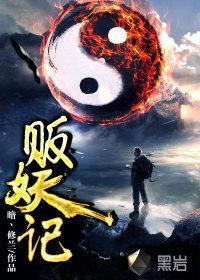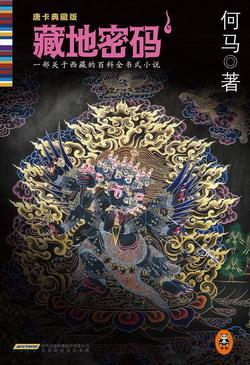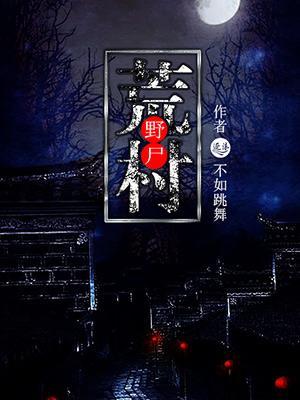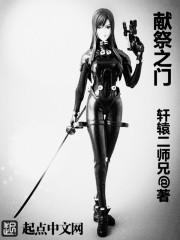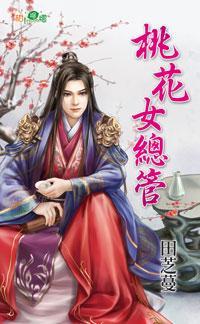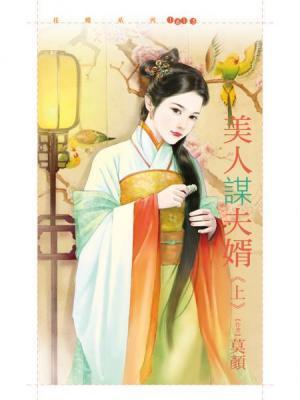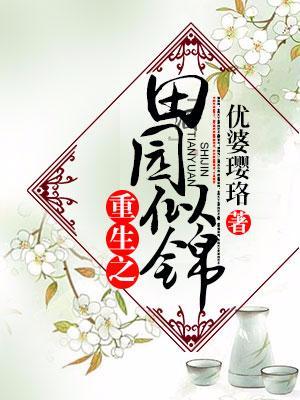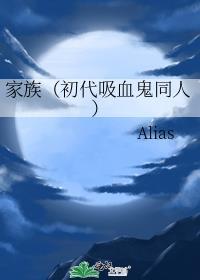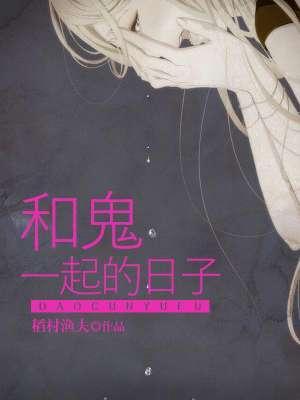第12章 十二
十二
劉恒将最後一塊山桃放進鐵釜中,動作又輕又小心,一點水也沒濺出來。
我憶着雙成的話,不甚娴熟地生火。火苗随指尖而雀躍,在劉恒的注視下,推過去的釜一寸一寸蓋住火焰,好似正逐漸蠶食一輪鮮紅的月亮。
水還未沸騰,濕潤的熱風熏得人昏昏欲睡,衣衫也逐漸泛潮意。我面上更甚,身前不像是靜水,倒像一鼎正蒸餅的甑,不得已用手背貼貼面頰,借此獲一些涼意。
庖廚的門敞着,我攥了攥劉恒的衣袖,與他往外走。皂绨觸感溫厚,這個人難得為我出一次雲室,或許他的手也不冰了。
側院不如正室,堂屋更小,僅擺了一張矮案。
劉恒沒管衣衫的褶,他随意落座,仰頭注視我,頗有些認真地問:“樊少子,山桃煮至最後,會像鹽菜一樣嗎?”
其實按常理,旁人在劉恒面前侍立答話是禮法,不算稀奇。可能他求知的心太熱烈,我還是頭一次這樣看他,不得不停步,垂目答道:“不會王上,是甜的。”
他不罷休,“若照五味羹來做,你什麽也不放嗎?”
和劉恒對坐是來不及了,我吸一口氣擺脫輕微的眩暈,在他身側緩緩坐下,“我記着呢,王上。饴蜜、姜、鹽……這裏全都有。”
他沉默了片刻,像被我說服了,再不含一絲疑惑,“……我以後也不會忘了。”
我命女使照看羹湯之時,劉恒的視線越過我,飄飄落到一處。待堂屋重回寂靜,他喚我名字,“樊少子。
“上個歲首,辎車上那卷簡牍,讀得如何?”
我心頭一跳,雙腿瞬間泛麻,忙端正坐姿。
完了,劉恒還挺盡責,他的查問不會比太子的正學之臣還嚴吧……
他或許知曉了,我半心虛半猶豫地應道:“王上,我看完了那一卷。就在這裏。”
Advertisement
“這裏……”他的指尖摩挲着案邊,像撫過歡欣鼓舞的粟谷穗,“是你身後那卷?”
代王素來喜靜,即使偶爾在雲室召見職官、開小朝會,也是悄悄的,不驚動任何不相幹之人。
與之相比,北院有時就吵吵鬧鬧。
後來,我也不下令勸了,幹脆自己躲出去,尋一個偏僻地方讀書。一來二去,我常常将許多木簡放于此,方便省事。
可讀完劉恒的書,有一段時間內,我瞧見簡牍就頭暈,甚至連卷合都嫌麻煩,滿心盡是快回北院,索性擱置了幾乎無人問津的書室。
我從他身側站起,精準地抽出一卷,“是這個,王上瞧得沒錯。”
“那卷系得更緊,似模仿我的法子……跟其他的也不同。”劉恒無聲笑了笑,眼中閃着螢火一樣零星的欣喜,“乏味嗎?”
我半分沒猶豫,輕輕點頭,垂下眼睫遞給他。他該知道我的,為了看完,真不知用了多少決心。
“春秋左氏傳。”劉恒念着,木簡被他一攥,碰撞聲泠泠作響,忽而遠逝。他繼續道,“你錯了,樊少子。”
我睜大眼睛,差點俯身行禮告罪一氣呵成,“唉,王上,我已盡力在讀……”
劉恒這回真的笑出聲了,好像他往日的自持、莊重全化作雲煙。有一刻,我忽然很想碰碰他的唇角。
或許他适合更輕盈放松的場景,話題離了書,離了隐晦的立場,而後再談及他的往事,談長樂宮的雪。
“你我拿錯書了。”他仰着臉,自如地卷起簡牍,言語中是綿密無間的贊揚之意,“春秋左氏傳,我不過也一知半解而已……樊少子,你記述了哪處?”
原來,辎車上我拾起的這卷左氏,是劉恒的書。他似要與我細談,我思索着,恍若在厚重的疑難集裏尋最獨特的一題。
我坐回他身邊,道:“王上,我初讀時,觀共叔段逃入鄢,再入共國,常驚嘆莊公先許封地、再平叛的作為,也為他除患而欣喜。
“而後,讀到晉侯封桓叔于曲沃。二位君王皆先封地,原本很相似。可數十年相伐,桓叔之後武公攻克晉都翼城,遂并晉國。王上,我......不由為莊公喜悅,為晉侯惋惜,為何呢?”
劉恒靜了片刻,反問我:“樊少子,你認可鄭國君的所為?”
我不假思索地點點頭。
莊公少時不受喜愛,而後繼承君位,我将左氏當寓言來讀,總希望他往後能順利些,不再與至親汲取同一段生命。
觀其在位之期,他尤擅治理內政,又與別國修好。即使劉恒似有己見,我依然堅定。
身旁人放下簡牍,細微聲響牽起我近乎靜谧的呼吸。我蜷縮起指尖。
“春秋卻說,段行事不像兄弟,故不言弟。莊公失教,故稱鄭伯。”劉恒的嗓音平穩,“二人勢同兩國之君,所以用克字。”
我一口氣松下來,趴在木案上,偏過臉看他,含含糊糊地回道:“王上啊,你怎麽這樣想......”
本來不願與劉恒因分歧争執,可真一遇到,我這氣息就再喘不勻了。往日他的眉眼、發絲,與裝束,此刻望着,愈發不順眼起來,我的心緒也漂泊不定。
“我理解你讀書時的情緒,樊少子。”他似安撫,我雀躍地敲敲桌面,立刻坐直身子,将長發攏至耳後。
劉恒本沒有笑的,可他的目光跟随我的指尖,一點一點揚起唇角。
“魯國史官為正名分、名實,借春秋喚回崩壞的‘禮’。”他說,“莊公定社稷,執政以寬,極利于後嗣。他又富有才能,繼位時,情勢宜徐圖之,于是順應而為。
“而無論晉侯有意,亦或避西戎,他封出曲沃,目的最終落空。晉國內長年戰亂,武公繼位,更違背周禮的繼承制。不怪你惋惜。”
“......王上,那你呢,你會有此心緒嗎?”我開口。
盡管聲音很輕,但身旁人卻敏銳地捕捉住。劉恒平視我的眼睛,就好像他動搖了,他答道:“或許我.......但真有一日,我不會逼反......”
“大王,樊少子!”
女使急匆匆跑入堂屋。她行禮,額發上沾幾滴汗水,“桃羹已備好,是否此刻就用呢?”
劉恒的話好似風吹即散的白絮,朦朦胧胧地蓋了我滿身。他未說完,這回,我卻什麽都猜不出來了。
我擡手制止女使,匆忙側過身,額頭差點抵上劉恒的左肩,悄聲求他繼續講,“王上......王上?”
他搖頭,将書卷一推,漫天不明不白的絨絮頃刻消散。
劉恒從容不迫地起身,牽過我的手,恍若我們從沒有提過左氏,“以後吧。寡人不想錯過你的桃羹。”
我順着他的步伐,極力縮短這段距離,左手摸出一塊素淨的薄配巾,欲遞給女使擦拭汗水。
經過時,我刻意放慢腳步。她應該望見我的動作了,輕輕擡一點頭,碎發随之搖晃,卻并未做出任何反應,像杳無回音的信約。
女使發絲下的面頰微紅,走出三步,我才驟然想起那非禮勿視的名目來。
劉恒不像以前了,這一刻,他的指腹柔軟地握住我,卻無論如何也抽不回來。我走在他身邊,如跌入一灣蓬松的夢裏。
他輕巧地填滿我掌心空白,位置并不正,也不自在,指尖織就了一張歪歪斜斜的網。灼熱光浪本該如影随形,可我在泛白的日光裏盜了些涼,心緒浸于一層潮濕的霧氣。
劉恒将我領在身側,行至正案前,我卻挑了他的對面落座。
案上擺一對青釉罐,罐口很小,我垂頭直直地向內望。淺色羹湯沒有倒影,桃諸浮在表面,晶瑩剔透,依稀可見些許未化的鹽。
身前人将它平推給我。我還未動,劉恒就已然舀了一勺,平靜而迅速地咽下。
我忽憶起禮記所書,與國君同進食有揖讓、周旋之禮。但自河東郡的雪夜,劉恒注視我咬第一口餌餅而始,他就從未細究過這些。
劉恒未作評價,他的瓷勺只是一次再一次地起伏。在周遭流淌的沉默裏,像很喜歡我的羹湯般,一刻也舍不得停箸。
我嘗第三塊桃諸時,身後有人踏進正室,他行禮的聲音隔很遠傳來。
“大王,邸報到了。”
聲線虛虛浮浮的,原本流利的話語乍然斷了,好似一瞬的窒息。這聲音着實耳熟,我轉身仔細瞧,卻只望見他飛快低頭時柔順的缁巾。
劉恒的袍服從我身側掠過,像一陣凜冽的山風。他的動作不留一絲餘裕,我回頭與空席對坐,繼續執起勺。
他低語幾句,命令快而明了,最後道:“……下次不要了,你明白什麽。”
侍從不敢應聲般沉默。片刻後,腳步聲也一同消失了。
邸報橫在案上,囊笥外以繩結捆紮。不牢固的縫隙處,全用膠泥加封,看着就極難拆。
我深深吸一口氣,邊識官印,邊對面前人緩慢道:“王上你……你都親自去接了。還訓人。”
“自作聰明的人。”劉恒注視着我,視線像穿透湖底的筆直日光,“若非有需,早就不想用了。”
有需.......?
他又帶了些寬縱,“不過樊少子,你的羹湯我也會接。”
劉恒念我的名字,像在喉頭滾過千萬遍。
我勉強對他扯出一個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