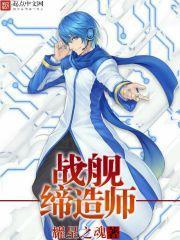第120章 公元前587年
果然, 米底國王阿斯提阿格斯經過提醒,想起了那個關于“滅國”的預言,煩惱頓生。
安善王國的小王子庫羅什, 是米底國王的親外孫。但是米底國王迷信神谕, 為了他的王國最終不會亡于“公主的兒子”手中,他派遣心腹前往安善, 打算密謀暗害這個孩子。
誰知安善人卻将小王子保護得很好。
沒過多久,甚至連阿斯提阿格斯排出的心腹都被策反了,背棄了主人的“亂命”,直接留在了安善,保護年幼的王子。
年幼而天真的小王子問那些來到他身邊, 默默保護着他的陌生人們:“你們從哪裏來?又為什麽總是跟着我?”
來人只回答:“雖然您的外祖父不希望您順順利利地長大,但是您有一位極為和善的姑外祖母。她想讓您知道, 這個世界上不僅有惡意與仇恨, 也一樣存在善意與寬容。她希望您長大後,也一樣以這樣的态度對待世界。”
小王子懵懵懂懂地點頭,默默記下:惡意與仇恨,應該敵不過善意與寬容。
安善國的小王子既然平平安安的, 米底國王的心思就此被牽制在別處, 暫時顧不上鄰居巴比倫王國。
利用這一段短暫的和平時期, 伊南在巴比倫王國國內, 将長達一百公裏的米底長城迅速地建起。
這座長城和巴比倫城牆的建築技術完全相同,但是本着盡量減少非必要勞力的原則,整個城牆的風格非常樸實, 沒有使用任何花哨的裝飾。
城牆極厚, 頂部寬敞, 牆體內甚至可供巴比倫士兵駐紮。城牆的最高處達到10層樓高, 簡直可以算是提供絕佳守禦和瞭望的要塞。
城牆接近完工的時候,巴比倫代攝朝政的王後伊南親臨工地視察。
當時曾經有無數的工匠,滿懷對巴比倫的忠誠和對王室的崇敬之情,匍匐在地,想要親吻王後的鞋子。
伊南卻讓人把他們全都叫起來,親自與他們一個個握手。令這些工匠感動涕零。
在長城建成之後,所有工匠都領取到了巴比倫王室承諾給他們的豐厚薪水。巴比倫官員轉述王後的意思:希望他們精明地使用這筆錢,不要讓金錢從此躺在櫃子裏,而是讓金錢作為投入資金,多辦一些産業,讓自己和周圍的人都能夠因此獲益。
巴比倫人本就繼承了始于蘇美爾人的商業頭腦,一點就透。
這些來自巴比倫王國各處的工匠,在工程結束回到自己的家鄉之時,都按照王後的意見,撸起袖子加油幹,将從修築長城時得來的金錢用于投入各種實業。
巴比倫因此再次經歷了一段農業與工商業快速發展的時期:
谷倉全部被堆滿,人們着手新建更大更透氣的新式谷倉;
幼發拉底河上和腓尼基岸邊的港口裏成天堆滿了等待出港的貨物,等待被運往南亞次大陸和地中海沿岸。
而各地上繳的稅金源源不斷地彙總到巴比倫。
古爾溫十分驚訝:“王後啊,怎麽好像您為修築長城而付出的那些錢,現在已經全變成稅金回來了?”
伊南微笑不語。
她這一招就是後世的大力發展基建項目來刺激經濟,從而促進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發展。
只不過,修築長城的經費,是從她自己的財産中支出;而作為稅金回到巴比倫的錢,則成為國家的公共財富。
與此同時,伊南着手用日益增長的稅金來建設巴比倫王國的騎兵。
巴比倫王國此前沒有蓄養大規模的騎兵——主要原因其實是沒有适合大規模養馬的草場。
馴養駿馬,需要合适的氣溫、足夠的草料,和适合駿馬奔馳的草原。
但是,巴比倫王國卻擁有別國沒有的優勢:技術。
馬蹄鐵為馬匹提供了保護,使它們擁有更好的耐力,并減少了受傷的幾率。
于是,巴比倫的商人們再次出發。這次,他們奔向小亞細亞半島上,在那裏,他們與牧人簽訂了購買駿馬的協議。從此馬匹被一船一船地運到腓尼基的港口,一下碼頭就被染料标上編碼,然後立即分組,輪流釘上馬掌,就交付軍方,開始作為軍馬進行訓練。
除此之外,伊南還下令改良了戰車,将原先極其颠簸的兩輪馬車改為四輪馬車,并在馬車上增加了用于防禦的隔板。
富有經驗的希臘雇傭兵來到巴比倫,開始向巴比倫的将士們傳授在馬背上作戰的經驗。
他們教會士兵如何操控馬匹,如何在馬背上使用長矛與弓箭,如何居高臨下地攻擊步兵,以及如何應付同樣在馬背上的對手。
而巴比倫軍中的将領們則紛紛聚在巴比倫王庭,由古爾溫講解各種宏觀戰術,如何應用騎兵突襲對方的步兵、營地,又在何時應當将騎兵收回,派遣步兵上前清掃戰場,等等。
“樞密大臣,原來您也對兵法和戰陣如此有研究——”
“是呀,将您留在王庭處理政務,實在是屈才了啊!”
軍方對古爾溫的能力大加贊賞。
古爾溫卻只好笑笑,偷偷地伸袖子抹抹額頭上的汗。
要知道,這些戰術與戰陣,全都是他與王後讨論過之後才拿出來與軍方分享的。在這其中古爾溫的貢獻不足十分之一,他自己有幾斤幾兩自己清楚。
王後才是屈才了呢!——古爾溫偷偷地想,如果她出生在巴比倫王庭,可能王都不是她的對手。
王後,應該是一位女王才對!
不止古爾溫一個,好多人,都這麽偷偷地想。
米底國王阿斯提阿格斯,奈何不了自己的外孫,轉過頭拿“妹妹”和“妹夫”的國度撒氣。
米底大軍終于壓至兩國國境線上。
米底王國在巴比倫的間諜早就将巴比倫的王遠航的消息告知了米底國內。王後主政的消息讓米底軍方覺得十分膨脹。
“一個女人,還不是一打就怕了?”
“算了,還是留點兒口德吧,畢竟也是咱們米底自己嫁出去的公主,雖然王好像不太待見。”
“你說,咱們的國王,下令攻打自己的妹妹。這事兒傳出去,鄰國是不是要嘲笑我們米底人不道德?”
“得了吧,你真以為王庭養育那些‘公主’是當做自己的親人嗎?那些都是用來聯姻的工具。公主嫁出去之後,她們的死活你見王真正關心過嗎?”
“唉,這麽一說,其實咱們也都只是戰争工具而已……”
雖然米底的将領們越說越喪,但是他們對于戰勝還是很有信心的——他們認為,最多是打到哪裏的問題:究竟是在邊境上劫掠大小城市和村莊,還是一路打到巴比倫去。
誰知雙方甫一交手,米底人就開始覺得不對:巴比倫人什麽時候有騎兵了?
關鍵是,這騎兵還所向披靡,在戰陣之中來回沖擊,專撿米底大軍的薄弱環節沖擊。沖了幾次,米底的步兵部分已經先潰不成軍,退回去了。
米底騎兵還在堅持。
但他們發現,對手坐騎的損傷率要比自己這邊小很多。戰馬們在戰場上撒開四蹄飛奔,卻從來不會出現馬蹄磨損的情況——他們的戰馬,仿佛完全不用休息。
這難道是因為巴比倫人對神明更加虔誠,所以神明更青睐對手嗎?
這時米底大軍派出去的探子已經從前方趕了回來,告訴大軍:散了吧,散了吧。前面巴比倫人已經築起了一道根本看不到頭的城牆,從幼發拉底河到底格裏斯河。根本找不到突破口。
消息一出,米底大軍的士氣頓時低落——他們竟還肖想着打進巴比倫,這是誰給的勇氣喲!
原本以為巴比倫王國由一個女人攝政,誰知這女人卻比誰都精明。
米底大軍只能改變方略,準備劫掠幾個邊境上的城市和村莊,然後就打道回府。
誰知就在他們傳令下去,大軍準備轉向的時候,巴比倫的新型騎兵再次自後殺到,這次直接将對方殺得潰不成軍。進入巴比倫國境的米底大軍大敗虧輸,狼狽不堪地退回米底邊境。
米底國王聞訊暴跳如雷,在自己的王庭裏大聲咒罵,指責巴比倫人出爾反爾,不守信義,竟然攻擊盟友。
米底的大臣們都十分無語:畢竟這是米底自己先動的手。
終于有臣子看不下去了,規勸米底國王:“我國這次還算是幸運,巴比倫國王撒爾不在國內,由王後主政。王後不願意多動刀兵,所以守住原有邊界就算了,如果是撒爾國王在……”
米底國王怔住了,他差點兒忘了撒爾是一個多麽恐怖的将領。巴比倫原本只是亞述的一個小小行省,現在亞述都沒有了,整個兩河流域都歸于撒爾治下。
想到這裏,米底國王忍不住十分陰險地詛咒:“現在距離撒爾出海,已經很久了吧?聽說巴比倫人自己也很久沒有得到他們的王的消息了?”
“撒爾這個家夥,要是這一輩子都回不來才好!”
确實,連巴比倫人自己都沒有得到過他們的王的消息。
随着時間推移,巴比倫的朝臣越來越擔心。開始有人向伊南上書,請求王後再派遣船隊,沿着王出海的路線尋找。
伊南拒絕了這個請求:在大海裏尋找撒爾的蹤跡是真正的“大海撈針”。再說,巴比倫現在也沒辦法再派出一支和撒爾當年一樣實力的遠洋航隊了。在這個時代的遠航,如果不能做好充分準備,那麽出海就是送死。
但是伊南的态度很快被別人曲解了。
有臣子跳出來指責伊南罔顧王的安慰,定然是戀棧手中的權力,巴不得王在海外失蹤。
伊南看着這些人在朝堂上上蹿下跳的醜态,忍不住冷笑:當我不知道你們背後是什麽人嗎?
撒爾的弟弟們,他們都認為自己是比伊南更合适的攝政人選。他們背後議論起巴比倫的王庭,總是說:憑什麽,一個女人……
伊南并沒有動怒,她命人把出面倡議的臣子送去了腓尼基,給他兩條船,委任他出海尋人。
這名臣子只出了一次海,遇上了小小的一丁點兒風浪,有那麽一點點暈船。但這個大臣立即下令掉頭回港,并且在碼頭上當衆抱着柱子痛哭流涕,說他絕對不再提派人出海這事了。
但朝堂上因此而起的風波并未因此而馬上停息。
由于撒爾長期不歸,開始有人對伊南“攝政”的合理性提出異議。
最先提出的是巴別塔神廟的大祭司們:他們仿佛已經忘記了,這座通天巨塔正是伊南帶領工匠們建設起來的。祭司們以神明的名義,要求伊南為她“攝政”給出一個理由。
此前撒爾将王國交給伊南打理的時候,祭司們都沒有提出異議,因為王權在撒爾手裏。
但現在撒爾常年不歸,伊南依舊統攬巴比倫的權力,祭司們就覺得不妥了。
于是,伊南與大祭司們開了一次閉門會議,會議結束之後,所有的祭司對伊南的主政暫時再無意見。
在此之後,伊南順水推舟地重提“長老院”和“國民大會”制度,用公共決策來替代她一人主政的局面。朝野之間,争議的聲音終于漸漸小了下去,
但所有人都心生疑惑:撒爾,他們的王,他究竟在哪裏。
今生,他還能平安地回到巴比倫嗎?
當伊南的腕表指向公元前588年的時候,從埃及傳來了一些消息。
這時距離撒爾出海已經有三年。鄰國多數認為:撒爾,這位自視甚高,目空一切的王,一定是在征服茫茫海域的時候被海洋給征服了。連巴比倫人自己也不太确定,王究竟還能不能回到巴比倫王庭。
但是,從埃及傳回消息,說是有船只在紅海靠岸,聲稱他們是當年随撒爾出海的遠洋船隊之一。
消息不太切實,而且沒有提供任何關于撒爾的消息。
巴比倫在埃及的商人們立即行動起來,從埃及當政者手裏,悄悄将這些人解救出來,護送回巴比倫,送到伊南面前。
伊南第一時間見到了這些筋疲力盡的水手。
水手們見到伊南,紛紛跪下,嗚咽着說:“我們……我們弄丢了王。”
聽聞此言,連一向矜持板正的女官多麗都失聲驚呼,不慎将手上捧着的陶罐摔在地面上。
伊南卻很冷靜:“先別急着哭,把你們遇到的情況說一遍。”
這副場面充分證明了:一個鎮定的領導者,能迅速讓所有人都迅速從不良情緒中掙脫出來。
水手們見到王後如此鎮定,而且并沒有責怪他們的意思,倒也不好意思就這麽跪着爆哭了。他們之中一個說話清楚的巴比倫人,便慢慢将撒爾出海之後的經歷一一說了出來。
他們抵達迦太基的時候,船隊擁有三十八條船,絕大多數人身體康健,船上的補給十分充裕,大家精神抖擻地從此起航,繼續向西。
确實如撒爾信上所描述的那樣,他們穿過了一條狹窄的海峽,海峽北面矗立着高聳入雲的石柱。
撒爾決定沿着左面的大陸(也就是非洲大陸)的邊緣航行。他們時而向西南,時而向東南,總之一直向南行進。
在這期間,三十八條船中,有九條船因為遇上了暗礁,沉沒或是無法修理,水手們棄船逃生。
船上的人員密度開始大幅增加,補給減少,疾病開始流行。
撒爾當機立斷,在岸邊找到了一個避風的自然良港,所有人上岸休整。
他們在岸上重新獲得了淡水,食物則依靠在海岸附近捕獵和采集解決。
船隊中的工匠們利用所攜帶的工具修補部分受損的船只,按照他們與風浪搏鬥的經驗将船的結構補強。其餘的水手們則負責解決食水問題,他們甚至快手快腳地在海岸邊的土地上種了一茬豌豆。
這次逗留是遠洋船隊在陸上逗留時間最長的一次,最終船隊出發的時候,只有二十條船,兩千人不到——有一部分人決定留在當地,不願再踏入波濤中涉險。
撒爾尊重了他們的選擇,給他們留下了一部分武器和工具,帶餘下的人一起,繼續踏上征程。
在那之後,撒爾的船隊遇到了強勁的西風。海面上終日是狂風巨浪——那根本不是海,海上的浪仿佛是一道又一道的牆。就連最優秀的水手也沒辦法在這樣的天氣條件下,穩當地操控船只。
船只和人員的損傷自然是免不了的。最絕望的時候,人們連能靠岸的地方都找不到。岸邊全是怪石嶙峋的懸崖峭壁,在狂暴的風雨中露着可怖的面目。
這時幾乎所有人都絕望了,都認為他們已經遠離了神明的眷顧,來到了被抛棄的世界。
唯有撒爾一人,依舊抱有信念,在風浪中無畏地指揮,終于帶領餘下的船只和人員,繞過了一座高聳的海岬。
從此,船隊不再向南行駛,開始轉而向北,或者向東。
這時整個遠航隊已經損失了一半的船只和人手,最後十條船上彙總了意志力最堅定,同時也是最強悍的人。
接下來的這段旅程則要相對平和得多——最險惡的海域已經被他們抛在身後。他們所經過的地方,開始出現茂盛的植被。陸地上的土著居民雖然與他們語言不通,但是要溫和得多,指點他們捕獵取食,并且給他們提供了不少幫助。
他們一路向北,經過大大小小的島嶼,眼看着陸地上的地貌和植被與巴比倫的越來越接近,氣候也越來越溫暖。所有人都覺得:他們應當已經重新得到了神明的庇佑,距離回家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誰知在這時,船隊又遭遇了一次大風暴。在風暴中,僅剩十條船的船隊被打散。等到風浪平靜之後,水手們再也找不到王船的蹤跡。水面上也沒有船只的遺骸。
用水手們的話來說,撒爾的船,要麽是被“神明帶走”,要麽就是完全傾覆在海底。
喪失了領袖的水手們失魂落魄,但也別無選擇,只能繼續按照昔日領袖指點的方向,沿着“左手邊的大陸”的邊緣繼續行駛。
終于,他們發現岸上的人口音漸漸能聽懂了。僅剩的一個的埃及水手聽出了他的鄉音,因而激動萬分。
接下來,他們就被陸地上的埃及人扣押起來,直到巴比倫在埃及的商會想辦法将他們救出。
伊南聽完了水手的陳述,托着腮靜靜思考:撒爾所選擇的航路正是環繞非洲的航路,最危險的那一段海岬正是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處在西風帶上,常年驚濤駭浪。
而這些回到埃及的水手和船只,事實上是沿着非洲大陸行進,一直進入紅海,因此出現在埃及附近。
至于撒爾,伊南又仔細問了水手們,最後一場風暴究竟是在何處發生的,發生之後,他們又停留了多少天,行進了多少天,才抵達的埃及。
到這時,她終于确定了救援的方向:命人從幼發拉底河出發,駕船駛入波斯灣,在從波斯灣兩側的海域反複搜尋,尋找王的下落。
王後終于派人出海,尋找王的下落——
這個消息立即傳遍了整個巴比倫王國,令整個國家為之轟動。
但回歸的水手帶給人們的,不只是希望,也有失望。
雖然遠洋船隊裏有人成功回歸,但他們講述的故事證實了:王确實是失蹤了。有人回歸,王卻沒有——這不正是說明了王早已兇多吉少?
巴比倫王國上下暗流洶湧,想要從王後手中奪取權力的王子們,籌謀得越發急切。
原本一直按兵不動的大祭司,這時也有些坐不住了,開始準備他們的“後手”——萬一關于王的壞消息被證實,神廟應當站在怎樣的立場上。
從各處來的視線都集中在巴比倫王庭,集中在伊南身上。
伊南卻表現得一如尋常。
她很确信撒爾還活着——畢竟是經歷了好望角狂暴風浪的男人,要說他會在一場普通風暴中沒有任何痕跡地消失,伊南認為這可能性很小。
最大的可能是,撒爾和他的船隊因為風暴而失散了。而撒爾也因為這一場風浪,錯過了紅海的入口,而是将阿拉伯半島誤認為是非洲大陸的一部分。他秉承着“左手邊大陸”的原則,選擇了繼續沿着這一片陸地的邊緣繼續向東。
如果她的推論屬實,那麽,撒爾将會沿着阿拉伯半島,一直行駛至波斯灣——而那裏,正是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裏斯河的入海口。
巴比倫的大都市埃利都,如今已經是一個內陸城市。幼發拉底河在埃利都之外沖積出了大片大片的土地。饒是如此,埃利都作為“王權天降”的第一個地點,依舊在巴比倫各大城市之中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埃利都數十裏之外的港口,一個衣衫褴褛的男人踉踉跄跄地走上棧橋。從他虛浮的腳步來看,應當是常年的海上生涯,令他已經完全不習慣在堅實的陸地上行走了。
這個男人的容貌幾乎讓人沒法兒看清,因為他的頭發茂密且打結,厚厚地披在腦後。他一臉從未經過修飾打理的絡腮胡子幾乎蓋住了整張面孔。
但這個男人擁有強健的體魄。他手臂上結實的肌肉讓所有水手見了都無比羨慕;
而只有被他直視過的人才能了解到這是擁有領袖氣質的人。他那對琥珀色的眼睛裏,透露出的每一個眼神,似乎都是來自王者的嚴令。
這個男人踉踉跄跄地從棧橋登上了巴比倫的土地。他腳步虛浮,沒走多遠,竟不小心腳下一軟,雙膝跪在地面上。
他雙手扶住地面,一個忍不住,竟然哈哈哈地大笑出聲。
周圍的人避之猶恐不及,大約都覺這人是不是有什麽毛病。
卻見此人深情地親吻了面前的地面:
故土啊,還有故人們……我,撒爾,回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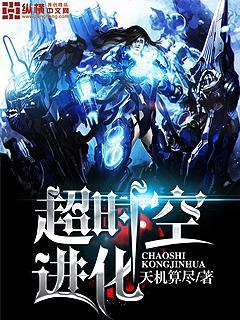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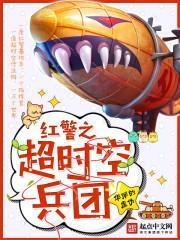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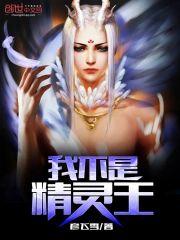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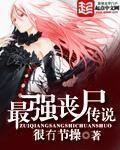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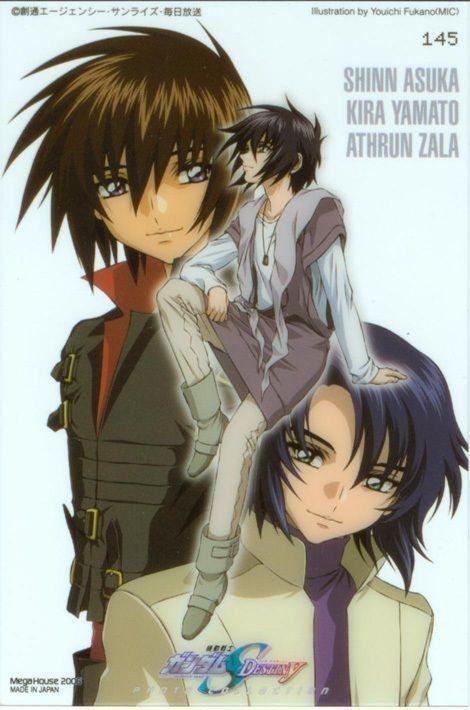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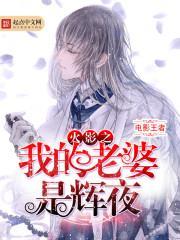

![[神夏+HP]以探案之名](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32779.jpg)
![[綜武俠]俠客們的反穿日常](https://yudongyun.com/book/thumbnail/2907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