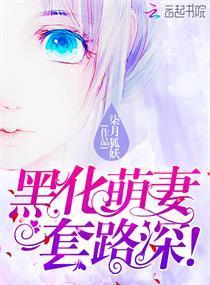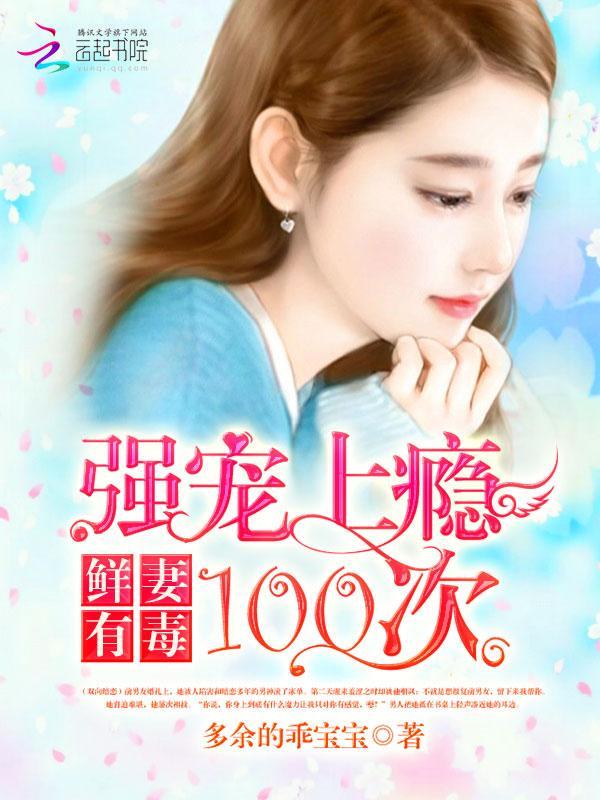第2章
一
“競聘?”例會上,蜜月歸來的林秋被網站主編朱長江嘴裏的詞驚了一下。
這不是老朱的一貫作風。
“你的機會來了。”同事大卓湊過頭來,神秘兮兮地對林秋說。
林秋沖大卓笑笑,沒說話。她的好意,林秋心領。
年近30歲還屈居采訪一線的女性,大概是媒體圈裏最尴尬的生物了吧。
提升吧,空間有限;拼搏吧,拼不過年輕人;論姿**,長時間奔波勞碌哪比得上小青年年輕貌美;憑經驗吧,人家又會說你倚老賣老。每天和一群比自己小6、7歲的年輕人一起賽跑,既不合群,又怕自己跟不上。
真是心力交瘁。
林秋對此深有感觸。
兩年前,林秋和年輕的新聞部主任杜梅去采訪音樂節。在媒體區等待時,幾個大學生志願者看見他們挂着媒體牌,少見多怪地過來打招呼,杜梅驕傲地遞出名片,林秋則尴尬地站在她身後。
那些大學生興奮地圍着杜梅,叽叽喳喳地問,你畢業不到一年就做到新聞部主任,這麽厲害。演出單位的經紀人以及媒體同行,根據名片上的頭銜也對杜梅格外禮遇,有時,他們也會奇怪地看下林秋。
他們的神色顯然在傳遞一個信息:他們也不明白,這個畢業沒多久的年輕女孩憑什麽做到新聞部主任,而旁邊那位明顯更有閱歷和經驗的林秋卻只是一名普通記者。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高下。這是一個連續四天的大型全天候的采訪活動。杜梅第一天穿大紅連衣裙、第二天換鮮綠連衣裙,日日腳踩8厘米高跟鞋,大多數時間都靜候媒體區,一頭飄柔長發紋絲不亂。而林秋日日平底鞋、休閑褲,由于要搶發報道,經常小跑往返媒體區和演出現場及後臺,一跑就一身臭汗,頭發濕了後,粘成一绺绺。
事實上,音樂節的所有重磅報道都出自林秋之手。杜梅一字未動,只是出鏡問了幾個大家早已讨論好的問題。
但是,又怎麽樣?林秋音樂節報道寫得再多、再好,最後朱長江表揚的還是杜梅。
美麗的花骨朵,誰不願意多看兩眼?
Advertisement
兩會報道,杜梅一篇人物稿寫了一個下午加晚上,淩晨兩點完成。朱長江心疼不已,大會小會表揚。他早就忘了,當天晚上林秋出了四篇采訪稿,最後一篇稿子碼好發出的時候,已經是淩晨四點。
朱長江從來不提。
其實行家略一打眼便知,杜梅所謂加班出來的稿件,跟通訊員提供的通稿差別不大,而林秋的四篇稿子全是當天下午的現場采訪稿。
這就是資深記者的悲哀。幹活的時候,人人懂得吆喝一聲“林秋”;論功行賞時,無人提。
朱長江向總部申請通報表揚的,依然是杜梅。
“今天杜梅挨批了吧,她那稿子有問題。”閨蜜張大暖一向替林秋不值,說。
“老朱什麽也沒說。”林秋說。
“為什麽?”大暖驚呼。
“她長得美。”林秋一勺子下去,把一個四喜丸子一劈兩半,利索地結束了這個話題。
林秋心想,哪有什麽“為什麽”。每個領導都有自己用着順手的人,這個人不一定能力有多高,品德有多好,但是一定會幹活,而且會把活幹到領導心裏去。朱長江偏愛杜梅不是沒有道理。最起碼,不管他有什麽決定,杜梅都是最擁護、執行最徹底的。其實,領導最在乎的,也就是這個。
林秋自問沒那個本事,也不坐那個靈霄殿。
話雖如此,朱長江終究傷透了林秋的心。
被涼水潑透了的心,反生出一種境界:平靜。
同事閑聊時,也會不經意地扯一句:世上哪有完全公平的事兒,小秋姐。
林秋微笑。
大家心照不宣。
其實林秋內心也不是沒有掙紮過。
但當時她剛轉崗做記者,新鮮感和成就感勝過一切。
她告訴自己,我愛的是這份工作本身。同行給我認可,讀者給我反饋,至于領導如何分蛋糕,與我無關。
但是,林秋還是覺得憋屈。她知道,杜梅沒有錯,錯在朱長江給她的帽子遠遠超過了她的腦袋。但是,只要有了帽子,誰還愁腦袋?
時光就像臨江漁民們出海打漁撒出去的網,一網上來,時間嘩啦啦地溜走。一晃,林秋已經29歲了,在黃海網臨江站工作了3年多,任首席記者,但杜梅已經是內容總監。兩人職位已有天地之別。
競聘是不是朱長江的心血來潮?
一向低調慣了的林秋有點拿不定主意。這幾年,說憋屈,還真憋屈。所以林秋婚假才特地多請了半個月,湊成一個月,就是想眼不見為淨。
但沒想到這才一個月的時間,網站就天翻地覆、換了人間。原新聞部主任老馬出走,招兵買馬另建了一個網站,做了站長。采編部群龍無首,編輯鄭琳暫時管理日常事物。由于重要管理崗位職務空置,不久前在總部再次競崗成功的朱長江索性要求網站所有中層崗位都要競争上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