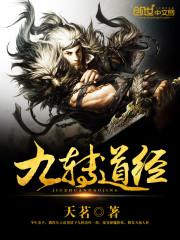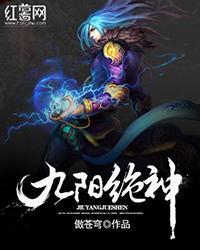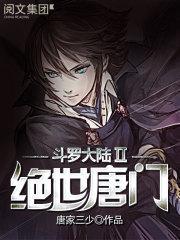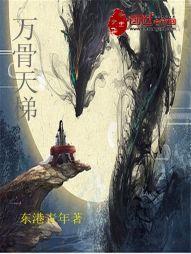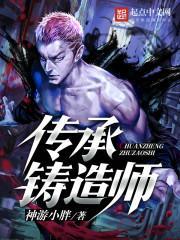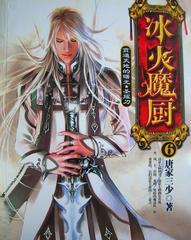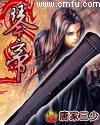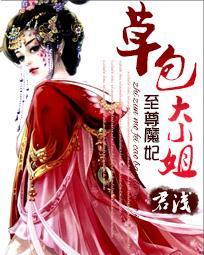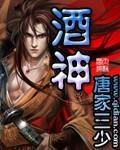第13章 (1)
因為王贲所率的大軍還停駐在楚國邊境,王贲只是帶了一小隊親兵回鹹陽領虎符,之後便立刻回返軍中,帶着大隊北上伐魏。
王離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随軍出征,但自小就在軍營長大的他對這樣艱苦的條件早就習以為常,只是手中的常勝戟過于沉重,從鹹陽出來,穿過函谷關到達大軍駐地的一路疾馳,就累壞了三匹戰馬。所以在與大軍會合之後,他索性和普通步兵一樣步行前進。
那位甘上卿還真是給他出了個難題,若非名駒,還真無法支持他使用那柄常勝戟進行長時間的戰役。
而且難題還不止一個。
王離下意識地摸了摸左胸,這裏還有一個更棘手的難題。(左胸→_→最靠近心髒的位置)
只是,現在還未到非用不可的時候。
秦軍一路北上,挾着之前一舉攻下楚國十餘城的氣勢,勢如破竹地攻入了魏地,在冬季還未過去之時,就已經遙遙地看到了大梁都城的城池。
至此,秦軍的好運氣就像是用光了一樣,大梁都城城池堅固,即使秦軍把大梁都圍了個嚴嚴實實,連一只鳥都飛不出來,但城中糧草充足,一個月內組織了十幾次攻城,都未見任何成效。
一種微妙的騷動不安在秦軍中默默地傳遞着,雖然在他們的身後,楚國的戰場上不斷傳來李信和蒙恬領軍得勝的戰報,但齊國方面卻詭異得一點動靜都沒有。
誰都不信齊國真能冷眼旁觀魏國和楚國被秦軍打得落花流水,還一直按兵不動。雖然至今潛伏在齊國的細作傳回來的消息都是一切安好,但齊國就像是一只枕卧在側的龐然大物,因為不知道它何時會起身攻擊,從而帶來了難以估量的巨大壓力。
王離遠眺着東方,心想着也許某一天在那邊的地平線上就會出現遮天蓋地的軍隊。
因為攻城戰最為殘酷危險,一不小心就會永遠地留在那城磚之下,所以誰也不敢讓王離沖過去當先鋒,後者就只能憋悶在軍營之中,獨自徘徊。
他父親王贲帶兵,恪守着一切從他爺爺那處學來的東西。駐營都是按照着《孫子兵法》中的《行軍篇》,選擇的是生地,居高向陽,盡量遠離江河水澤。只是大梁城的地勢低窪,離城數裏之處就有一條大河洶湧而過,河床的高度甚至都遠遠高于大梁城池。
王離站在軍營的栅欄前,看着那條奔騰流過的河水,耳邊聽着那呼嘯咆哮的水聲,心中贊嘆着江河險峻。若不是親眼所見,根本不敢相信居然還有此奇景。
從鹹陽城外流淌而過的渭水,在桃林塞彙入了北方的河流,形成眼前這一條浩浩蕩蕩的大河。也不知那少年上卿是不是在高泉宮,遙望着那滾滾而過的渭水時,想到的那個攻城妙計。
又在栅欄前踱步了許久,王離終于放棄了掙紮,鼓起勇氣朝自己父親的主帳走去。
Advertisement
他中規中矩地站在主帳外等親兵通報,得到允許之後才掀開帳簾而入。因為主帳內要進行軍隊高層的議事,所以也就非常寬敞。只是此時并不是議事之時,只有他父親一人在,正背對着他站着,在研究挂在帳中的羊皮地圖。
“不進則退,不喜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爾怎麽不去練武?”沒等自家兒子見禮,王贲連頭都沒回就開口斥道。他想收拾這渾小子很久了,每天無所事事地在軍營裏閑逛,別人礙着他的面子不說什麽,但心裏肯定不知道怎麽嘀咕呢!
王離暗暗叫苦,他這些天怎麽可能是毫無目的地閑逛?少年上卿所寫的錦囊妙計,只是一個大概的計策而已,絕對不可能把所有的情況都寫明。更何況對方從來沒有來過大梁,不知此間實際情況,所以他即使知道這是一個絕頂妙計,也要觀察數日才能确定是否可行。
他父親因為是武将,生怕和那些文官們交談時有什麽典故聽不懂,所以在閑暇之餘孜孜不倦地讀書,說話便一向喜歡引經據典。王離小時候就聽不懂他父親七彎八拐的說話方式,想辯論又無從辯起,所以養成了說話直接的性格,才會無形之中得罪了許多人。
想起年少時的遭遇,王離無聲地談了口氣,當然他要是說話不那麽刻薄,也許那位甘上卿也不會被人在半步堂暗算受傷。這件憾事也無形之中改變了王離的性格,每當他感到暴躁的時候,這件事都會浮現在他腦海。按下想要和父親争辯的沖動,王離心平氣和地敘述道:“将軍,在下有事容禀。”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其下攻城……為不得已啊!”王贲壓根兒就沒覺得自家兒子能有什麽正經事要說,收回了因王離進賬而分的心思,繼續在羊皮地圖前喃喃自語起來。
這段王離倒是聽懂了,因為他曾經被父親按着背了很多兵法,這句是出自《孫子兵法》的《謀攻篇》。
當時背的時候還不解其意,此時聽來,細細咀嚼,卻覺得那位不動一兵一就取得趙國十幾座城池的甘上卿,簡直是絕世天才。
上等的用兵之策是以謀略取勝,其次是以外交手段挫敵,再次是出動軍隊攻敵取勝,最下策才是攻城。攻城才是下下策,只有萬不得已之時才使用。他父親這是在懊惱現今的局勢,秦軍看似占盡上風,可是綜合周遭形勢,實乃是步入了困局之中。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順,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王離輕聲地繼續往下說着,往日被父親逼着死記硬背塞進腦袋裏的文字,現如今說出來,卻字字珠玑。謀攻謀攻,少年上卿果然是謀攻高手。
王贲很少見自家兒子主動背書,見狀詫異地轉過身來,雖然心情不佳,但還是欣慰地點了點頭道:“我這兒有兵書,你若不願去練武,背書也可。”
王離聞言翻了個白眼,從衣襟裏掏出一個小小的錦囊,本想連錦囊一起交給自家父親的。不過他想了想,還是抽出了寫滿字的布帛遞了過去,把空了的錦囊重新放回衣襟揣好。迎着父親疑惑的目光,王離氣定神閑地解釋道:“這是走之前,甘上卿給我的錦囊妙計。”
本想嫌棄的王贲一聽到甘上卿的名字,立刻把手中的布帛打開,認真地看着上面的文字,越看呼吸就越發急促,等他來來回回看了幾遍之後,怒氣也飙到了極點,揮舞着帛書朝王離呵斥道:“此等妙計為何不早點告訴我?!”
“上卿所書之計,也直言一切要以實地為主。”王離早就知道父親會暴怒,不慌不忙地解釋着,“我這些時日觀察水量後,直到今日我才确認此計确有可行之處。”
王贲的怒火沒有消弭,但總算是知道兒子不是刻意延誤軍機。可還是越想越氣忍不住操起桌上的竹簡抽了王離幾下:“蠢材!叫你讀書不讀,傻子才不知道‘春汛’二字!”
王離硬撐着扛了幾下,總算讓自家老爹消了氣,不過還是忍不住辯解了兩句:“我不是怕萬一計謀不成,也不用承對方的情嗎。爹你不是別想站隊嗎?”
“哼!人家都設好局了,就等我們鑽套呢,就是算到了我們不得不用。”王贲早就想得很開了,最壞的結果就是久攻大梁未果,反而被齊楚聯軍前後圍攻。現在有妙策可輕松奪城,甚至連秦軍的傷亡都能下降到最低點,簡直是求之不得的結果。至于政治上的事情,王贲很理直氣壯地說道,“反正有事你爺爺擔着!”
王離聽得簡直羨慕嫉妒恨!他也想說有什麽事他爹幫他擔着!而不是拿竹簡抽他!
王贲也沒空再考慮這些事,他打王離那幾下,也是懲罰後者把這麽好的計策偷藏着不拿出來。若是早些時候,攻城損傷的士兵就能少一些,而且還可以提早觀察河水的情況,提前做好準備。
不過再仔細想想,就算王離提前拿出計策,攻城戰也是要打的,否則魏軍就要懷疑他們的真實意圖,弄不好還會直接沖出來和他們做平原戰,那樣傷亡會更大。好吧,就算是讓他這個做父親的焦躁心急,也值得挨這麽幾下,天知道這些日子他掉了多少頭發!
王離自然是不知道自己挨的這幾下抽打究竟是為的什麽,還沒等他在抱怨兩句,就被王贲使喚着去找衆位軍官開會了。
王贲對着那片帛書看了看,趁帳中無人,便把後面一截果斷撕掉。
因為對大梁久攻不下,軍官們心底也浮躁不安,一聽王大将軍召集,便紛紛以最快的速度趕來主帳,本來不怎麽抱希望立刻能有解決方案的他們,在看過帛書之後,立刻群情鼎沸。
沒有人會懷疑這條計策不成功。
在中原,能稱得上“河”的就只有眼前這條,而另一條可以與之媲美的就是流經楚國境內的那條江。其餘都是分別冠以名稱的水,例如渭水、洛水。由此可見,這河有多寬廣。
王離越聽越覺得慚愧,他果然是讀書讀得太少了,居然最開始還懷疑少年上卿的計策是否能行得通。在營帳中大家越說越熱烈,坐不住的軍官們站起身奔向營外,看着那條奔騰的河水指點江山。
不明真相的其他士兵還以為這些軍官們看的是遠處的大梁城,在研究攻城方略。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王贲感慨萬分地說着,他只注意到了紮營是需要遠離河水,卻并沒有意識到可以利用這條河。他與那位甘上卿的差距可見一斑。更何況,那位甘上卿連來都沒來,僅憑一些水文、地理的資料就判斷出了這點。
“咦?為何這帛書後面缺了一條?将軍,可是寫了些什麽?”一名拿着帛書的軍官,細心地發現了端倪。王贲并沒有說這是誰獻的計策,就有人開始懷疑後面是不是有落款,卻不方便被外人看到而特意撕去。
“非要緊事。”王贲瞪了一臉無辜的王離一眼,輕咳了一聲,轉移了話題,開始分配衆人去做事。畢竟定下計策,現在還未到春汛之時,但先要做的事情也要開始準備了。
王離摸了摸頭,覺得自己被父親怪責的莫名其妙。少年上卿也只叮囑他錦囊不得輕易離身而已,有什麽見不得人的,非要特意撕掉?
※·※
看着汩汩流過的鄭國渠和兩旁綠油油的農田,扶蘇忍不住感慨道:“鄭國本想用此渠阻我大秦統一中原,卻不承想反助之矣。”
與他同乘一車的綠袍少年放下手中的書簡,順着他的視線看去,果然見春暖花開,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鄭國渠是韓國人鄭國為了拖延秦朝大軍東進的腳步,想出的消耗秦國國力的一個笨方法。開鑿鄭國渠是一項巨大的工程,即使以秦國的實力,沒有十數年都是完不成的。結果二十多年過去,西引泾水東注洛水,長達三百餘裏的鄭國渠也已經灌溉了這片平原十多年了,造就了超過四萬頃的良田,令秦國的糧倉足夠支撐秦軍開啓多路戰線。若沒有此鄭國渠,秦國所在的關中平原,定會貧瘠不堪,絕沒有富餘的糧草挑起戰火。
一個士兵一個月的口糧差不多要合八十斤,而秦國若是想要滅楚,至少要兩年的戰期,依着王翦老将軍的謀劃,六十萬人的軍隊,再加上後勤儲備,所需的口糧簡直難以計算。完全可以說,鄭國渠是秦國一統平原的基石。
“鄭先生大才。”綠袍少年頗為仰慕地贊嘆道。鄭國在修建鄭國渠之時,就被人揭露了其心思,秦王政大怒,本想斬他的首級,結果鄭國自嘆之語,讓秦王政平息了怒火。那句話頗為出名,綠袍少年銘記在心,此時不禁低語複述道:“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
“萬世之功……”扶蘇嘴邊的笑意更深了一些,車隊沿着那潺潺流過的鄭國渠前行,讓他聯想到月前之事,不由得深有感觸。“水能活人,亦能死人。”
綠袍少年知道他所指的,是一個月前水淹大梁之事。
王贲引河、溝水灌大梁城,導致城內死傷無數,魏王假出城投降,至此魏國滅亡。
誰也想不到這條看起來最艱難的伐魏戰線,居然會如此幹淨利落地解決而且秦軍的傷亡也降到了最低點。反而是出兵前信誓旦旦二十萬兵就能拿下楚國的李信,最初雖然打了幾場勝仗,但随後卻被楚國的項燕将軍尾随三天三夜追擊,最後秦軍的兩個軍營都被攻破,七名都尉被殺,李信大敗而逃。
秦王政得知了軍報之後震怒,親自去頻陽請王翦老将軍重新出山,這才有了他們今日之行。只是不知為何秦王政要帶着大公子扶蘇和他一起,也許是讓大公子說些他不好說的軟話,畢竟大公子年紀還輕,沒什麽抹不開臉的。
綠袍少年把視線從車外的渠水農田上收了回來,這些天來因為一直忙着處理伐楚戰線的殘局,還有準備再次出兵的糧草武器,他們也沒有找到時間來談論最近發生的事情,所以他也不知道大公子扶蘇對水淹大梁一事,究竟是持何種态度。
動了動唇,綠袍少年覺得此時還不是談這種話的時候,周圍的侍衛離得都太近了,只好按下心思。
一直沿着鄭國渠往南,就到了頻山。此處有一座秦厲公所建的宮室,因在頻山之南,故名之頻陽宮。而圍着這座頻陽宮發展起來的郡縣,便謂之為頻陽。
這裏便是王翦老将軍的家鄉。頻陽在幾十年前還是屬于比較貧瘠的郡縣,左右都沒有河流而過,直到鄭國渠修到此處,才改善頗多。又因為王翦成為上将軍之後,出資為族中置辦了不少田産,在頻陽也形成了一片王氏宗族的聚集地。頻陽縣鄉民們今日一早就得到了秦王駕臨的通知,故在道路兩邊列隊迎接。
車隊直接就開到了王翦所居的府邸前,王翦帶着全家老小在門口迎接秦王政。等扶蘇和綠袍少年下了車駕,秦王政就迫不及待地拉着王翦往書房議事去了。
王家派出王翦的族弟接待扶蘇,也不算怠慢這位大公子殿下。安排他們到偏廳休息,上了點心和湯羹,就體貼地離去。扶蘇估摸着自家父王在王翦面前的低姿态,也不好讓別人看見,就算是兒子也一樣。
若是一切順利,說不定就沒他什麽事了,如果不順利才輪到他出場。不過扶蘇覺得自家父王真是多慮了,王翦老将軍一心為國,理應不會推拒的。
所以扶蘇心安理得地吃着點心喝着溫熱香甜的湯羹,還不忘問自家小侍讀:“王離那家夥呢?怎麽剛才在門口沒看到?不是說被王老将軍帶回頻陽操練了嗎?”
“他随王大将軍去伐魏了。”綠袍少年解釋道,初臨戰場的王離其實并無軍職,秦國的一切軍功都是需要在戰場上拼殺出來的。所以扶蘇不知道一個小兵的去向也是很正常的,綠袍少年也覺得特意跟他彙報有些奇怪,索性也就一直沒講。
扶蘇聞言失笑,放下手中的湯碗:“那他也不知道是慶幸還是失望了,大梁城這種情況他的軍功也無從賺起。”
“他說他已經去與駐紮在楚地的蒙恬将軍會合,等王老将軍出戰後一起參加伐楚之戰。”綠袍少年想起在信中王離所說的沒參加真正戰争的抱怨,臉上不禁帶了些許笑容。他平日裏臉上挂着的笑容都是經過無數次微調的,就像是在臉上覆了一層面具,此時的笑容倒是難得帶出了幾分真心。旁人也許分不清楚,但與之朝夕相處好幾年的扶蘇一眼就看出來了,不由自主地眯了眯那雙遺傳自秦王政的鷹目。他用手指摩挲着面前的湯碗邊緣,拉長了聲音意味深長地問道:“哦?你們互通書信?”
“同戰報一起送到的。”綠袍少年倒是不甚在意,只是一張帛書而已,這點特權王家還是有的。
“連王離都篤定自己爺爺會出山伐楚,王上今日不會白來一趟?”
扶蘇略微挑了挑眉,他倒是沒想到自家小侍讀和王家的嫡孫居然私下還有書信往來?他們不是從一開始見面就勢如水火嗎?
綠袍少年沒想到自家殿下關注的重點完全跑偏,不過見周圍沒有外人在,就想旁敲側擊一下扶蘇關于水淹大梁之計的看法。他一直沒跟扶蘇坦白此事是他所獻的計策,也是因為怕被對方呵斥手段殘忍。但此事雖然他想得透徹,可實際上卻一直糾結在心間,讓他輾轉反側,如果政見不同,以後的矛盾肯定會越來越多,他做事也會束手束腳。而此事正好是試探對方底線的一塊敲門磚。
扶蘇也是想要好好問問自家小侍讀何時與王家小子關系那麽好了,只是兩人都還未開口,外面就來人敲門說王老将軍有請。
居然還真來請人了?秦王沒有說服王老将軍嗎?為何怎麽快?不多努力努力嗎?綠袍少年本想留在偏廳等候,可來人卻說老将軍有請甘上卿也同去。
兩人對視了一眼,滿腹疑問地進了正廳。一見廳內一君一臣臉上的表情,就知道正事肯定是都談妥了。坐在主位上的秦王政帶着一臉輕松的笑意,卸下了在鹹陽宮時的威嚴,看起來倒是比實際年齡要年輕不少。這世間已經很少能有人讓他如此放下戒心,而王翦正是少有的幾人之一。
秦國年邁的上将軍陪坐在客位,王家都是正宗的西秦子弟,身材高大魁梧,王翦雖然已過花甲之年,但依舊精神矍铄,坐姿挺拔,随時都能披挂上陣。果然說什麽謝病而歸,都只是借口罷了。
扶蘇恭恭敬敬地朝父王和王老将軍見禮,才剛直起身,就聽秦王政跟王翦笑問道:“将軍知寡人來,便說要見甘上卿,如今已經見矣,可否為寡人解惑?”
扶蘇這才知道他實際上是沾了自家小侍讀的光,訝異地擡起頭。
而站在他身後的少年上卿卻直覺事情不妙,王翦和他有什麽交集?絕對就是那條錦囊妙計!
果然,王翦氣定神閑地開口道:“禀王上,伐魏的功勞還有甘上卿一份,那水淹大梁之計,正是他送與孫兒王離的。”
不敢擡起頭的少年上卿,立刻就感覺身側扶蘇投射過來的目光,但他已經無暇顧及。
王翦真不愧是老謀深算,他心底的那些小心思,在對方面前簡直就是形同透明。他本想讓王家不動聲色地欠他一個天大的人情,等到需要的時候再連本帶利地讨回來,結果反而弄巧成拙。王翦輕飄飄的一句話,便在秦王面前把這件事坦坦蕩蕩地攤開來,既掃除了未來的後患,也繼續贏得了秦王的信任。
“哦?”秦王意味不明地發出了一個單音,卻讓人聽不出來他的喜怒。
少年上卿倒是不怎麽擔心秦王政多心,反正他就是扶蘇的侍讀,不為扶蘇着想又為誰呢?當初秦王政派他到扶蘇身邊,不也就是為了如此嗎?令他忐忑不安的,是扶蘇的想法。
這簡直就是最壞的情況了。
若是如此,還不如早就和扶蘇說此事,也總比他從別人口中知道要好。
只是現今他卻無暇顧及扶蘇的反應,連忙應對秦王的疑問,恭敬而又謹慎地措辭道:“只是閑時看書所思,不敢直接勞煩王大将軍。”
其實他說得客氣,若是他把這計策當時就遞給王贲,後者肯定會嗤之以鼻。最後這個結果,也是因為各方博弈,王贲無奈之下最好的選擇。
王翦也知曉此點,他的目的不過就是把雙方私底下的交往給擺到臺面上,是做給秦王看的。他也不願平白得罪這位少年上卿,所以當下和煦地笑道:“有功就要行賞,老夫這是不想上卿一片苦心被埋沒。”
少年上卿的唇角抽搐了兩下,王翦說的理由太冠冕堂皇了,他實在是無從指責,只能做謙遜狀,和這位王老将軍互相客氣地吹捧了兩句。
這王老将軍圓滑至極,他甚至可以推測得到,王翦這回做足了姿态,下一步肯定是要自污以求秦王絕對的信任了。
直到秦王政随口下了封賞的旨意,才允兩人離開,想必還有什麽話需要和王翦私下說。
※·※
一出了正廳,少年上卿就覺得不好,大公子在前面走的飛快,他甚至需要小跑才能跟得上。此時他也不管丢不丢人了,直接抓住了扶蘇的袍袖,糾結地解釋道:“不是我不想說,是……是實在……總是開不了口。”
扶蘇并沒有說什麽,拽回了袍角,但腳步卻放慢了許多。
綠袍少年一路心煩意亂地跟着扶蘇走回偏廳,腦海裏推衍了各種可能的後果,越想臉色越難看。雖然他以前還想着離開扶蘇,另投明主。但這幾年相處下來,他也不得不承認,眼前這位大公子,實際上就是他最好的選擇。這也是他肯費盡一切心思的原因,他是真的想要輔佐扶蘇登上那尊王座。
眉頭越鎖越緊,卻忽然感到一點溫熱按在了他的眉心,綠袍少年訝然擡頭,發現扶蘇正伸出手指撫平了他眉間的褶皺,面上全是複雜難辨的表情。
“該生氣的不應該是我才對嗎?”扶蘇看着自家小侍讀難得皺起來的臉,收起了眼中一閃而過的笑意,肅容道,“畢之,我感謝你為我所做的一切。”
聽了感謝之語,綠袍少年的表情卻并未輕松,反而越發凝重了。這是在總結陳詞?馬上就要他收拾走人?又或者怕他去別的兄弟那,直接派他到其他地方,不得接觸機要事物?
畢竟沒有人能忍受屬下自作主張,而且……而且據說水淹大梁之時,大梁城中也有許多百姓傷亡,這些殺孽,多少也會算在他的身上……
“然而……”
看吧,果然有轉折。綠袍少年的神情已經落寞了下去,一雙明亮的眼瞳也黯淡了許多,幾乎就想掩耳不聽。
一雙大手按住了他的雙肩,強迫他不要逃避,只聽着扶蘇一字一頓地沉聲道:“畢之,不許再瞞着我做任何事,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怕你會做出一些寧可損害自己也要成就我的事。”
綠袍少年聞言一怔,這些話不是他能猜想到的。他擡起頭,對上扶蘇的雙眼,看出對方認真的态度,不禁疑惑道:“這……好像與此事無關吧。”
“好,你想說此事,那就說此事。”扶蘇幾乎都要被自家小侍讀氣笑了,放開後者,“為何不跟我說?是覺得我會呵斥你草菅人命?”
綠袍少年咬了咬下唇,并沒有說話,但實際上心底就是這樣認為的。
他沒有上過戰場,也沒有真正地面對生死一瞬的殘酷,在想出水淹大梁的計策後,也是憑着少年意氣,才沒細想就給王離遞了绫錦囊。
前線戰報傳來時,他整夜整夜都睡不好,覺得肩頭胸口壓着的,全是鮮血和人命,讓他幾乎喘不過氣來。
“昭王十三年,白起遷任左更,出兵伊闕,攻韓、魏二國,斬獲首級二十四萬。”
“昭王二十九年,攻楚于鄢決水灌城,死數十萬。”
“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将,斬首三十萬。與趙将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于河中。”
“昭互四十三年,白起攻韓國,破陉城,攻陷五城,斬首五萬。”
“昭王四十七年,長平之戰,趙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乃挾詐而盡坑殺之……前後斬首俘虜四十五萬人……”
綠袍少年眨了眨眼,沒明白扶蘇為何在此時忽然提起武安君白起。但聽着扶蘇一句一句吐出一串串冰冷的數字,綠袍少年也覺得心寒。白起是秦國的戰神,但對于其他六國來說那就是死神一般的存在。更何況扶蘇所說的這些數字,還都是不完全統計。整個戰國時期橫跨兩百多年,戰死的人數共兩百萬餘人,而其中有一半幾乎都要記在武安君白起的名下。
真可謂是白骨堆積而成的功勳。
歷朝歷代國之能安邦勝敵者均號“武安”,近五十年中,武将得此武安君稱號者,前有白起,中有李牧,後有項燕,皆是名将,但還是白起威名最盛。
“武安君功過無人可評,長平之戰,趙軍斷糧四十六天,士兵們相互殘殺為食。降秦也是為了一時活命,武安君坑殺之亦是不得已而為之。”扶蘇的語氣沉重,卻說的異常認真。
綠袍少年也知道這段歷史,甚至之前他和扶蘇也曾談過此事。但觀點卻與今天完全相反,原本的不贊同,也因為之後的各種查證而漸漸扭轉,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外面不遠處正潺潺流過的鄭國渠。
白起若是不坑殺這四十萬人,也養不起這麽多的降卒,畢竟三十多年前的秦國,還沒有鄭國渠,糧草養活自己的軍隊都很吃力。那麽這四十萬人養不活,又還能放回趙國去嗎?等他們吃飽了之後重振旗鼓,再殺回來?那麽這場戰争就只是一場兒戲,所以只能殺之。
“至此以後,趙人深恨秦人。”
綠袍少年也知此事,秦王政正好是在長平之戰之後的第二年在趙國的首都邯鄲出生,所以童年過得極為凄慘。幼時的遭遇讓秦王政在邯鄲被攻破時都親自去處理當年的仇人,其中隐含的兩國仇怨可見一斑。
扶蘇走到半開的牗窗邊,眺望着不遠處的青山綠水,沉默了半響,才緩緩道:“在趙人看來,秦人殘暴。但秦人卻覺得相比自己的子弟損傷,敵國士兵的傷亡更好。”
“我是一名秦人。”
他邊說,邊回過頭。其實他的相貌有六分神似秦王政,另外的四分中和了他母妃的溫柔,再加之他整個人的氣質非常儒雅,倒是讓人感受不到迫人的氣勢。只是在他沉下臉,收起笑容之後,卻給人以難以形容的淩厲和威嚴之感。
“我的仁慈,只對我的臣民。想要我的仁慈,那麽就成為我的臣民吧。”
扶蘇如晨鐘般的聲音回蕩在耳畔,綠袍少年被震得一剎那間頭暈目眩。
他順從于自己的本能,向前走了幾步,直直地跪了下去,趴伏在對方的腳邊,拈起對方的袍角放在嘴邊親吻,獻上自己的忠誠。
“如您所願,我的陛下。”
※·※
扶蘇好笑地扶起跪在自己腳邊的小侍讀,話題好像被帶得有點偏,但應該很好地開導了自家的小侍讀,今天晚上不會再睡不好覺了吧?
這位少年上卿是聰明人,但有時候聰明人反而容易想得太多。
扶蘇親自伸手拍了拍對方身上所沾染的塵土,笑着嘆氣道:“我生氣,是怕你自作主張害了自己,哪怕是做對我有利之事,也不行。”
綠袍少年表面上順從地應了,但心底卻有些不以為意。以博棋比喻,犧牲散棋來成就枭棋,這是很正常的。以弈棋比喻,為了大片的地盤,而犧牲一些棋子也是值得的。(奴性?)
扶蘇知道這些根深蒂固的觀念不是一兩句話就能扭轉過來的,只能在心裏嘆了口氣,記得以後多加注意,口中已是換了話題道:“王老将軍定是會出山伐楚,你可擔心王離否?”
“不擔心。”綠袍少年想都不想地回答道。
扶蘇有些嫉妒地眯了眯雙目,羨慕那姓王的小子居然能得到自家小侍讀毫無保留的信任。而且他還無從知道這種深厚的情誼,究竟是什麽時候開始培養起來的。縱使知道對方與王離交好,十有八九是為了他扶蘇,但依舊有種莫名的不舒服。
綠袍少年沒注意到自家大公子的情緒,猶自心底腹诽着。他都送了王離戰無不克的常勝戟,必敗楚國,而且還有防身的绫錦囊,性命無憂。
都做到這樣全副武裝了,還有什麽可擔心的?
※公元前224年※
王翦在馬車上揉了揉酸痛的老腰。真是不服老不行了,若是當初他在敵軍中殺個三進三出都沒問題,現今只是坐在軍帳中主持大局,頂多騎上戰馬壓壓陣,時間長了都有些承受不住。
看來伐楚之後,他也必須要告老還鄉了。其實若李信能力足夠,他才不願出山伐楚呢,在家裏含饴弄孫豈不樂哉?
王贲在魏地安撫魏國國民,一旦魏地安穩,就要帶兵北上伐燕。魏國一戰,證明他也能獨當一面了。
只是一家兩代人都手持重兵,氣勢簡直比趙國的李牧還盛,這樣太容易遭受君主忌諱了。即使他走之前特意管秦王要良田照顧子孫,自污形象,但也遠遠不夠。所以在伐楚時,他特意帶上了蒙武,就是為了分功用的。
正思索間,就見自家孫兒掀了簾子跳上馬車,沉着臉跪在他身邊,動作熟練地為他捏着酸痛的腰。
王翦滿意地看着王離,經受了一年多戰場的磨練,已經像是被千錘百煉的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