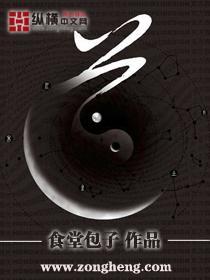第31章 《中國的政府機構》說:
“我自己親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這次公開調查的審查官們所做的決定……”
“我說看到,是因為所涉及的被判決的人的名單刊為單行本發行全國”“雖然我們已經說過中國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從前面所述應該已經很明顯,而且下面還要說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貴族政體,……如果沒有與大臣磋商或考慮他們的意見,皇帝本人對國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後的決定……所有的文件都必須由大臣審閱呈交皇帝”“我已做過徹底的調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況是确鑿無疑的,除非根據某個大臣提出的要求,否則皇帝無權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大其權力。當然皇帝可以對和他家族有關的人進行賞賜,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但這筆賞賜不能列為公家贈款,皇帝所做的贈禮也不能從公款中提取。”
“他們(引者注:指明代都察院所屬的十三道監察禦史)在某些方面相當于我們要稱之為公衆良心的保衛者的人,……即使是最高的官員,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們也直言無忌,……他們如此恪盡職守,真使外國人驚奇,并且是模仿的好榜樣。無論皇上還是大臣都逃不過他們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時他們觸怒了皇上到了皇上對他們震怒的地步,他們也不停止進谏和批評,直到對他們猛烈加以抨擊的惡行采取某種補救的措施為止。”
“事實上,當冤情特別嚴重的時候,他們控訴的就一定很尖銳刺骨,即使設涉及皇上和朝廷也剛直不阿……所有這些呈送給皇上的書面文件和對他們的答複,都要複制很多份,這樣在朝廷發生的事情就迅速傳遞到全國每個角落。這種文件編輯成書,如果內容被認為值得留給後代,就載入本朝的編年史”“幾年前,當今皇上想冊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長子為儲君,因為這個幼子受到他和皇後的寵愛,這一更易違反了國法,皇上收到了大量指責他的陳情書,……最後皇上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在大臣們以集體辭職為威脅的條件下,不得不表示在立儲這件事情上改變了主意”甲申國難,華夏文明由世界文明的頂峰跌入萬丈深淵,那些在西人筆下熱情開放、極愛幹淨、富有教養的明朝人不見了,那個深沉大氣、雍容典雅、氣勢磅礴的華夏,那個曾今被四方蠻夷尊稱為禮儀之邦、信義之鄉的華夏,那個曾今創造了無數輝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領跑了兩千餘年的華夏,如今只能和古希臘、古羅馬一樣,湮沒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之中。今天的華夏後裔,在嚴重夷化的社會中,已經無法感受古代文明的先進與文雅,也并不知道,我國地理位置的不幸,導致先進文明屢屢亡于落後民族的事實。
在17世紀中葉的1636年,從中國返回歐洲的曾德昭記載的那個“相當的富裕繁榮,在各方面都令人贊嘆”的明朝已經于1644年滅亡了,取而代之的是號稱初期“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朝。在這期間,外國人的記錄有力的駁斥了這種虛假的“盛世”經“康乾盛世”的“勵精圖治、文治武功”最終使中國落後貧窮到什麽程度,引用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一句話一目了然:“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褴褛甚至**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着吃”詩人唐甄在山西做過知縣,親眼目睹了滿清統治之下的痛苦生活,他著有《潛書》裏面提到:“清興五十年來,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
他親眼看到山西婦女多無褲可穿,而“吳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可見所謂的“康雍乾”其實都是被拔高的侏儒,在後金的統治下,老百姓的實際生活是相當痛苦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所謂“人們衣衫褴褛甚至l**體”這與唐甄的記載完全吻合,可見确實是實情。
《愛丁堡評論》文章提到,雖然“乾隆可汗”曾指示:“俟該貢使到時,必須整列隊伍,以肅觀瞻。”
但馬戛爾尼還發現清國的武裝部隊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擊。馬戛爾尼發現社會上普遍的貧窮和不安定——這跟陳弘歷可汗希望他發現清國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為沿途他看見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蕪了的建築,以及大多數清國人過着低水準的生活。馬戛爾尼認為,這個"半野蠻的"帝國"聲譽掃地",清國人生活"在最為卑鄙的***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之中",所以人們"膽怯、肮髒并且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