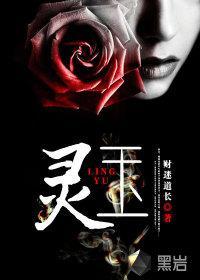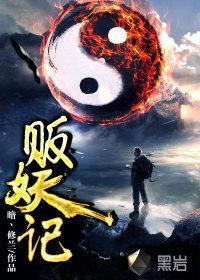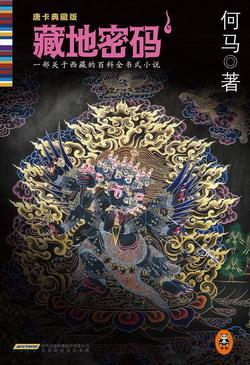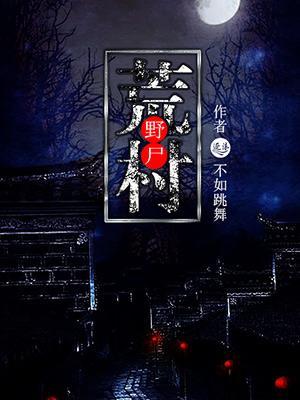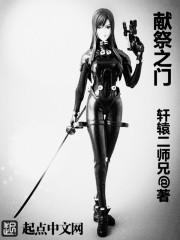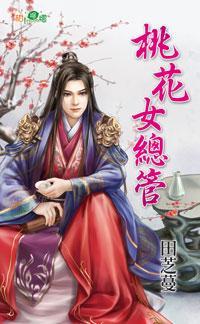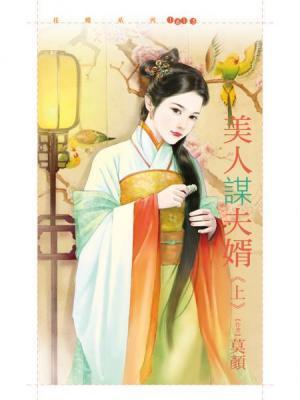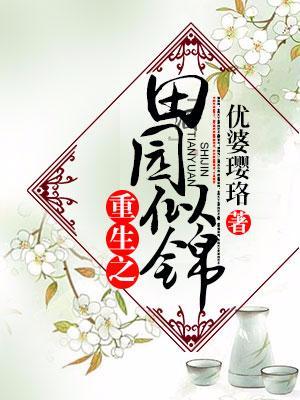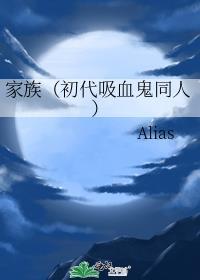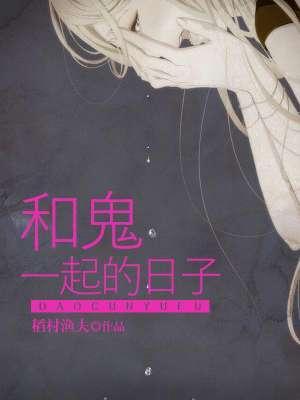第16章 十六
十六
诏令......這回輪到皇帝親自下诏令了。他不僅論功行賞,許諾免除邊關的田稅,更為散去四起的軍中流言,在诏書最後添了句話。
想必诏令一出,再無人敢牽連我分毫。
次日晨起,聽雙成這麽講,我不禁驚嘆劉盈得知消息之快。或者......流言已久,他早有了這想法?
平心而論,當日靈君的話,我只當做玩鬧。太子與我血脈相近,因那段差錯的過往,待我确實比旁人親厚些。
可僅僅止于親厚而已。劉盈是君王,獲保宗廟,即使想求西山經裏的水玉,洛水也得招神而問之,任他撷取。
何苦執着于舊時廢棄的婚約,本就荒唐。
細細思索下來,還是因血脈之故。
呂氏封王已違盟誓,平日謹慎地避退流言最好。
劉恒不讓我出北院,僅留下雙成一人。她低頭端朝食,小心翼翼道:“庖廚儲物還夠。樊少子......安香不在,婢子可以在你身旁等嗎。”
我眼眶泛熱,深吸一口氣道:“好,好。等她回來了,我們再一起吃飯。”
雖然等到天子诏令,可劉恒依舊要查,不追根溯源不罷休。
薄太後該醒了,藥方是她的囑托。其實,劉恒距離真相只有一步之遙。
因為不是我。他需查密信,查謠言之源,才能給朝廷一個合理的禀奏。
我依靠苦藥與換麻布的次數,數着時刻捱日子。
整整七日,代邸悄然沉寂,好似中庭隔絕了任何動靜,留一處院子蘇世獨立。
Advertisement
雙手傷口泛癢的清晨,薄太後将安香帶來了。
我是最猶豫的人。關在北院的前幾日,每每晨起,我倚在帷帳邊,閉着眼睛琢磨。
要是薄姬來了,該不該讓她看見傷痕?我不去想劉恒。這個人的結解不開,他來了,我也不讓他進。
因經歷的等待向來愉悅,向來完滿,我這樣的人,只會期盼自己終能等來合襯心意的結尾。
可餘下日子,北院依舊冷清。
我逐漸不為此糾結了,緩慢地學起換藥,按時與雙成一同吃飯。
安香随太後而行,她原先分明是薄姬的女使,目光望過來,步伐卻逐漸向我偏轉。
我刻意拆下麻布,衣裙攜風,鞋履踏過之處軟而綿,以手背撫她緊繃的肩頸。
“還好還好,沒事了。”我悄悄貼近她,一時間竟手足無措,“回來就沒事了。”
安香似乎欲跪,我連傷也來不及避了,勉力牽制住她,“我擔心你。他說的那些,我全都沒信。你快進去找雙成。”
我知道薄姬還在近前,身影交錯的瞬息,恍若隔一道天塹。
我轉過身,向前邁了一步。薄太後看着比以往好些了,只是唇色蒼白如雪,讓人憶起冰涼的青銅劍刃。
腳步聲漸遠,薄姬的身子仿佛在輕微顫抖,她自管自地說:“桑兒,代邸本該任你随意進出,我得知此事就趕來了。是我的過錯。
“都是我的緣故......你受苦了。”
我搖搖頭,恭敬地行禮。
“我當日就責了子恒。你留下來,他實在不應疑你。子恒與你......”薄姬嗓音愈低,“過幾天是上辛日,讓他送你些什麽,好不好?你不是喜歡......”
她低微的咳起來,目光輕輕軟軟的,有些可憐。
換作劉恒,大概也猜不中我的喜好,她無需進退維谷。
“謝過太後。我的女使已歸,便足以了。”我不由答道,“只願王上查明事實,服衆心安。他的一言一行,我銘記在心。
“太後的舊病未愈,請回南院吧。慢一些走。”
寒風蕭索,薄姬的發絲绾成垂髻,周身素淡,幾乎無一飾物,惟有翹起竹絲的長簪子。我忽覺自己很不近人情,将她拒之門外似的。
恍惚間,我慌忙垂眼,思緒不禁落至回心轉意的地步。
她仍舊在咳,壓抑着不發出聲響。我伸手欲扶,指尖差一點距離,忽被握住了。
侍從攙過太後。
此一別,這樣的距離下,劉恒身上熟稔的蘭草香消散殆盡,惟剩跨越遙遠風雪的寒意。
掌心刺痛,手腕似一瞬懸浮。我沒費什麽力就掙開了。
劉恒平和地開口道:“母親,聽樊少子的吧。天太冷了,你受不得寒。”
又來了,他這若無其事的語氣,像失去漲潮的、寂靜的死海。
我心底蒸騰起惶惑。薄姬咳得狠了,萬一旁人看來,我僅僅淡漠地旁觀,那劉恒這層猜疑的屏障,不知又加固到何處去。
“大王,你終于......”薄太後回首,透出些許不安,“你給桑兒說,快些......去何處了,怎麽查的。”
自登車的那日,我初次見她,她似乎就希望劉恒與我好好的,和睦又相扶持。
倒是從一而終。好可惜。
我蜷縮起五指,肩頸緊繃,背過身的一刻輕輕松了口氣。
“樊少子。傷好些了嗎,你別藏。”他跟過來,亦步亦趨,“先走吧。”
他說一同走,我繃着臉,立刻想停步了。
這算什麽呢?我與你的争執又算什麽?哪怕是不值一提的事,難道說放下,彼此就立刻放下嗎?
我不得不敷衍,“我與太後說過了,何須再擾王上。北院久未進出人,王上等明日吧。”
他平日洞悉隐意,得心應手。現在卻字字較真,扯出虛無之事,話語都難纏起來。
“樊少子,你要如陛下诏書中所言那般......回長安去嗎。”
我不答話,徑直往前面走。短短幾步路,已快到扇門了,大不了......大不了就關他在外面。
劉恒沒再攔我了,他沉靜的表象碎了一半。冬風蕭索,他好似不畏冷,将褪下的鐵質甲胄托在臂彎,緊随我的步伐,“樊少子,那日匈奴雖退,卻整軍至雲中郡觀望,我只得回去。
“你放心,他們最終走了。赈災很順利,我上書朝廷免去百姓部分田稅,陛下也準許。
“我已知道......細作與你無關。”
我停步,偏頭注視劉恒。
失了鐵甲遮掩,他頸間露出一線血痕,突兀得像割破新雪的枯枝。血色淺淺,濡紅了素衣交領。
他從北地連夜趕來,這刀傷,亦或是青銅矛的刮刺,恍若湖面剛凍結的浮冰,一碰就碎裂。血珠似游魚般隐現,終被衣衫吸盡。
征戰沙場,哪有不受傷的。他的話......我該關注他話中諸事。
歸根究底,百姓受了場無妄之禍。若能得代邸與朝廷的赈濟,也算些許寬慰。劉恒做事倒挺迅速,不出七日,竟已安撫好了民情。
我讀過劉恒做注解的木簡。只願他用那質古溫醇的執筆之風,為百姓多減點田稅。
心緒塌陷了一角,所以不由自主地移開目光。
“王上......看着點門,我來推。”我維持着聲線,“密信一事可有着落?安香......我的女使回來了,她與我交談後,我或許也能幫你。”
劉恒先一步碰扇門。他未說什麽,随意将甲胄擱在門邊,甩脫沉重的負擔般揉手腕。我抿着唇,有意挪正這些冷鐵,卻被他制止。
他垂下眼睫,“塵土味重,就在你正堂外擺着,正好。”
劉恒輕巧地漫應過去。其實不止塵土,還有血腥味。
屋內,雙成端上茶湯。我雙手雖冷,可暫且做不到平實地握耳杯,習以為常用指尖拎起它。劉恒的目光如影随形,他說————
“是我的過錯,樊少子。是我疑你,才致使你受傷。”
想來他查出真相,才能如此幹脆地說些軟話。
劉恒一貫如此,他氣上頭的時候,總将事情控制在微妙的界限內,似堪堪挽回,卻因不細察而傷人。
“王上,不提你與我之間,那封信的原委呢。”我問。
“你記得代邸前長史......其實未免職,我原先在用。”劉恒坐于我身側,平鋪直敘,“當日與你路過東廚,他竟直言長安的事,又與陳豨牽連。”
“他欺負過你。欺負過你的人,我都記着。”他的頸間又滲出血珠來,“我将他下了廷尉,樊少子......那人得了懲戒,我只偶爾召見。”
他仍要講,我忽然道:“現在人在哪?”
劉恒摩挲着杯壁,淡寫輕描地接話,“三日前,得知我發現密信的源頭,絕食自盡了。”
陳豨原是代相,後反叛,高帝親征誅滅。哪知還有人以此名號作亂,膽量也小,籌謀許久的要事,居然自己甘願餓死。
劉恒......誰知他是否推波助瀾。
我正思索的人繼續說,語調帶了點熱茶的溫度:“母親送到你身邊的女使,原先管筆墨。那長史抄去了字跡,傳書給同謀,在軍營裏傳。傳你是細作,潛伏許久,擾亂軍心。”
“不對啊,王上。他怎知我為太後煎藥。”
“你又未刻意掩飾。”劉恒移開目光,像是有些悔,字句停頓地說,“代邸人不多,旁人不覺。他混入徭役,日入時做工,成天看你往來。”
我咽下一口茶湯。事情并不複雜,長史誤以為自己有機可乘,大概是......大概他發現了代王防備外人,只放心自己或親信侍藥。
真是氣不打一處來。
我推開耳杯,背轉身去,“不要再說了。你走吧,劉恒,快治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