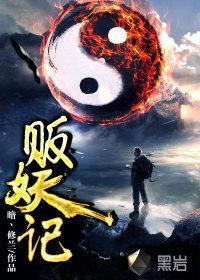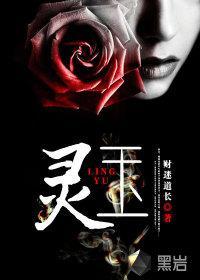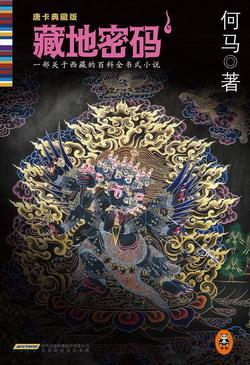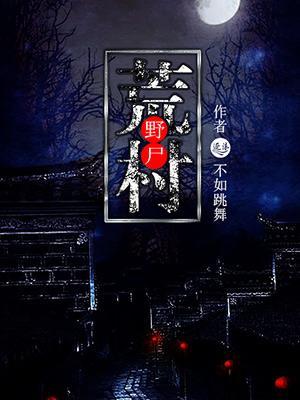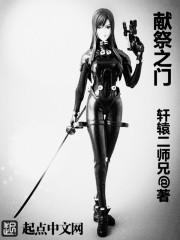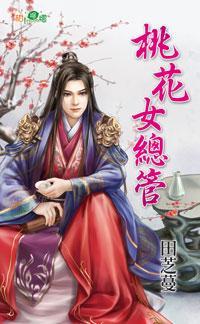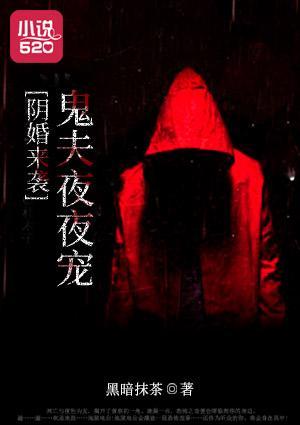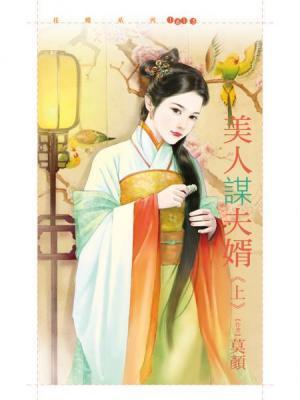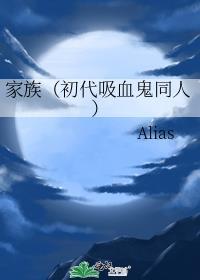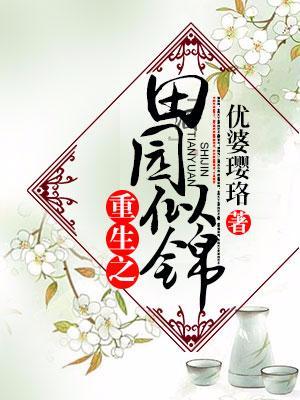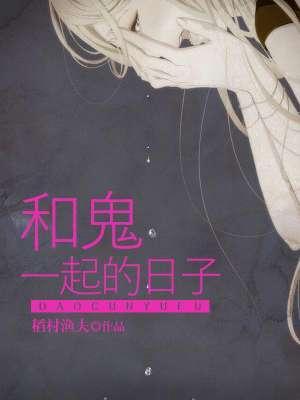第59章 Nature的一角
第五十五章 Nature的一角
**沂州叛亂,烏臺詩案**
元豐二年(1079)正月,沂州 (今山東臨沂)盜賊何九郎謀劃打劫利國監,與此同時,阚溫、秦平等奸猾之人與何九郎遙相呼應,轉戰于沂、兖(今山東曲阜東南)二州之間。官軍對此無可奈何,徐州(今江蘇徐州)知州蘇轼大膽起用犯人家屬程棐。原來,程棐的弟弟程岳豪俠勇健,精通武藝,因與李逢一道謀反,被配隸桂州(今廣西桂林)牢城。程棐極願立功受獎,以使程岳早日被釋放。蘇轼了解這一情況後,迅速派人将程棐接來,告訴他為國效力;并許願說如果捕獲了何九郎、郭進等人,其弟程岳即可釋放。七月,程朵派人給蘇轼報信說捕獲妖賊郭進等人,為此蘇轼專門給宋神宗上了兩道奏折,建議獎勵程棐,釋放其弟程岳。蘇轼以為在徐、沂等地,象程棐、程岳這樣勇敢善戰的人頗多,官府如果不安撫他們,讓他們去捕捉盜賊,恐怕這些人會铤而走險,起來反抗官府的統治,同時建議宋神宗将京東路地區的土豪組織起來,防禦盜賊等等。宋神宗采納了蘇轼的建議,提拔沂州承縣(今山東棗莊東南)縣尉師谔為左班殿直,賞錢一千貫,沂州民程棐、傅晖為右班殿直,其他一些人也給了不同程度的獎賞。
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初,梅司回到杭州錢塘。三月,在曾子固的推薦下,出任湖州文字從議郎(這是我編的,有時間修訂的時候再改吧)。同年,蘇轼由徐州知州調任湖州知州,四月二十日到任。時官員到任地方,都要給皇帝上表表示感謝。
按慣例都要寫一篇到任謝表給皇帝。蘇轼的謝表到達朝廷後一個月,權監察禦史裏行何正臣首先發難,上書謂蘇轼謝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之辭,并聲稱蘇轼的這些文字已在全國傳閱,自己是從已刊印後在市上賣的蘇轼文稿中摘錄遞呈宋神宗的。其後禦史舒亶也上書攻擊蘇轼,謂蘇轼的謝表是譏諷時政之作,士大夫争相傳誦,并進一步指出蘇轼在謝表中诽謗宋神宗,牽強附會将蘇轼的謝表加以修改,于是蘇轼诽謗君主便是人贓俱在了,從而激怒了宋神宗,達到了陷害蘇轼,“大不敬”的罪名的目的,緊接着權禦史中丞李定上書蓋棺定論,攻擊蘇轼不學無術,浪得虛名,其實是一個陰險的家夥,他還列出應該罷黜蘇轼的四條理由。于是宋神宗下令将這些人的意見下達禦吏臺,審理後迅速上報皇帝。
于是宋神宗委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捉拿蘇轼歸案。皇甫遵雖然日夜兼程,但由于兒子生病,仍被耽誤了半天。此時驸馬都都尉、蘇轍的好友得到消息,寫信交給蘇轍。蘇轍從南京任上快馬加鞭,先到達了湖州傳信。蘇轼告假不許,一時之間,一州知州,被驅如同雞犬。
同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轼被押到開封。負責審理此案的禦史臺首先是搜集整理蘇轼的文稿,然後加以驗證。但蘇轼認為自己的所有文稿都不涉及時政。蘇轼在杭州(浙江杭州市)任職期間觀錢塘潮時寫過一首詩“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禦史臺官員認為蘇轼是在譏諷農田水利法。審理近兩個月,禦史臺将審案記錄上呈宋神宗批示。
蘇轼下獄後,他的弟弟蘇轍首先上書宋神宗救援其兄,範鎮,張方平等上書力救蘇轼,王安禮、宰相吳充也曾委婉勸谏宋神宗不能因文字而殺士大夫,宋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後曹氏對宋神宗說:“以詩系獄,得非受了小人中傷”。為蘇轼說情。
大理寺依律給蘇轼判處了二年徒刑,但因曹太後患病,因而被赦免無罪。由于李定等人的竭力反對,宋神宗重新委派馮宗道前往禦史臺複審此案。
經判決,蘇轼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附馬都尉王诜追奪二官、勒停,蘇轍貶監筠州(今江西高安)鹽酒稅,王鞏貶賓州(今廣西賓陽)鹽酒務,其他與此案有關的官員被判處以罰銅的處分,其中張方平、李清臣三十斤,司馬光、範缜、錢藻、陳襄、劉邠、李常、孫覺、王汾、劉摯、黃庭堅、王安上、吳琯、戚秉道、周邠、盛僑、杜子方、顏複、錢世雄各二十斤。
******
經歷了此案,蘇轼的文風和人格追求漸漸轉變。才華橫溢又嫉惡如仇的詩人,他原來的生活态度,是見到不平之事“如蠅在臺,不吐不快”,他滿含熱情地為牢獄中的犯人□□,為衣食無着的老人哽咽;他譏诮地看着煊赫鼎沸的官場:“我本麋鹿性,諒非優轅姿。”;他描寫春光村釀的美好,也寫出鹽鐵專賣對百姓生活造成的不便“豈是聞韶解忘味,迩來三月食無鹽”。
率真的天性和語言的天賦,讓詩句像月光那樣自然地流淌出來,他的歌詩成就成為個時代的一座高峰,前人和後人都很難企及和追上。
——可是這次人生的遭遇讓他的态度徹底轉變了。
他開始受困于人生苦厄的來源。
他縱然率真,但未必就像世人給他的那個評價一樣“豁達”,他有着和市井小民一樣對死亡共同的畏懼之心。詩案給他的不僅是□□的折磨,精神上的打擊更是不容小視,他在牢獄之中也随時懼怕着死亡,因為消息的誤傳還寫下絕命之詩。
Advertisement
總是有歌頌苦難的後人說,苦難使他的靈魂得到了沉澱和升華,他後期的思想開始向着“更寬廣的人生苦難”轉向,向“儒釋道”思想深挖。——其實他并沒有完全解脫,他只是,也只能向“命運”低頭。
因為他并不明白,即使是這樣充滿靈性和才華的上天的寵兒,即使經歷了如此大風波還活下來,被家人(弟弟)太後全力憐惜和保護能夠全身而退的人類社會中的寵兒,也還是不明白。
人性。Nature。
因言獲罪。他的言論有罪嗎?僅僅是因為冒犯了君主的權威?怕不是吧。禦史臺的那些非要治他于死地的,掌握了“發言權”的人,為什麽非要将沸反的輿論炒揚到天上呢?畢竟,即使他真的在等級制度的社會結構下,犯了“犯上”的罪名,按照法律機構大理寺的判決,也只不過是“徒二年”的刑期。是什麽,讓一個輿論監察機構,可以把一個原本三年有期徒刑的罪,非要推到“死刑立即執行”的程度呢?
這就是複雜的Nature。當平常沒有撕破臉,處于利維坦彈壓的暫時的“和平”時期之時,人為了維持損失最小,保持和平。可是和平的狀态一旦打破,進入“仇恨”的狀态,那就是非要置對方于死地不可了,因為仇恨的種子一旦播下,就很難消弭,你無法将安全的希望押在對方熱愛和平而“主動放棄”複仇,人會更傾向與選擇讓對手“無力”向你複仇。
戰争為什麽和這種單方面的打擊不同呢?因為這種借由輿論的迫害行為,是借由國家機器進行的,并不動用發起者很大的精力。而戰争是兩個國家機器對等的較量,很快,卷入其中的所有個體都會體會到國家層面的“精疲力盡”,當雙方都“無力複仇”時,戰争就到了轉折或終結的時刻。
人性中的陰影,戰争和迫害、仇恨和破壞的魔鬼永遠不會消失,只能等待它們把人和人類社會折騰得精疲力竭,在傷痛和短缺中,度過短暫的和平區。
權力。Power。
蘇轼還有一個他不能說出口,也無法擺脫的枷鎖,那就是宋神宗自己下場參與了這場撕逼。無論宋神宗的動機是什麽,□□的權威被冒犯、出于對蘇轼的繼父式嫉妒(坊間有傳蘇轼和太後的緋聞)、出于一個掌握權力者想要探知自己權力界限的試探(從宋神宗的政治志向看,他是個不安份的),他是下場撕了的,而且明顯有親自下場踩的現象。
但是從那時的社會道德來說,蘇轼不能反抗。因為“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在等級制度下,當上位者對下位者行使權威,下位者只能像承受自然災害一樣接受,因為在道義上和法律上都沒有反抗的餘地。——可誰的心中沒有反抗的念頭?誰在心中沒有不平的吶喊?偏偏叫你生在這個社會體系之中,才華還是如此奪目,如果你不服從它,沒有這麽大的成就和前途;如果你服從它,也不過是屈膝折股的“雲淡風輕”。
人類,沒有誰的天性可以發展的很好。沒有一株樹可以保住它所有的枝條。
可是那傾軋的種子已經種下了,這只是一個縮影,宋亡于黨政,此言不假。
******
梅司因為跟随司馬光上書求情,而被罰熟銅十斤。
他的仕途仍然不順,但是這一次,他的內心卻感到了無比的清明——這與民無利于國無功的幾句詩歌的争論,居然掀起如此軒然大波,集中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不說本來這幾句詩原就沒有那麽深的政治意圖,只不過是随性而發,随見聞而錄;即便是真的抨擊了青苗法,那又怎麽樣?改革必有争議,圍繞着一件事,必有無數的口舌,還不準別人說兩句了是怎麽着?
整個朝堂沸反盈天,沒有一個人真正關注,青苗法是不是有所說的問題,它的發起者沒有修訂它的弊端,反而所有的輿論都被調集,來打擊假想中反對自己的“朋黨”。
這與他在後宮中經歷的争鬥,不過是換了一個場合、換了一個社會背景,發生同構的人類內部傾軋争鬥的手性模型罷了——內耗競争是人類的本性(nature),和被扔在輿論中央的這件事情到底有利有弊、是非對錯甚至都沒有關系,就像一個充滿鬥魚的池塘,那件事情不過是一塊投入其中的石頭,只要一個動蕩,人類就發揮陰影裏撕咬的本性,你死我活起來。
越發地回望歷史,就越發發現,人類從來不能從任何錯誤中吸取教訓。人類的愚蠢,從來只是重複,從未有改進。梅司自嘲地笑笑,發出和克軍曾經一樣的感嘆:“你們陸猿,真好玩。”
對于這樣的人類,他能做什麽呢?
做我能做的。
既然來到了湖州,他于是探訪當年為真宗時丞相王旦兒子種痘的名醫,繼續改良精進種痘技術,開始在平民中推廣人痘術。立下了從醫不從相的家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