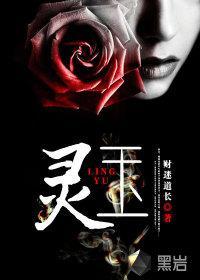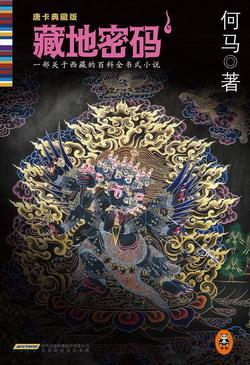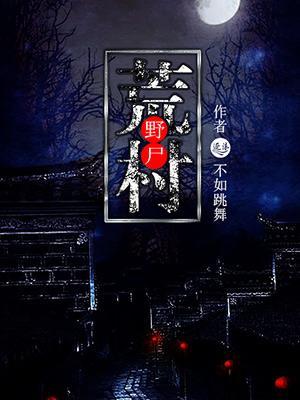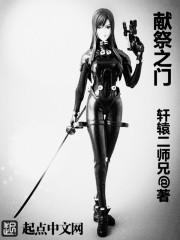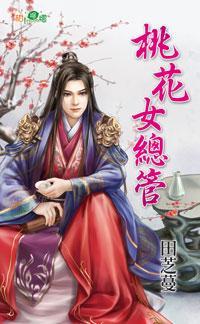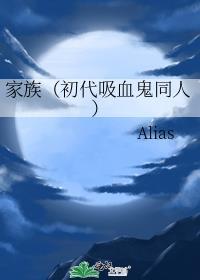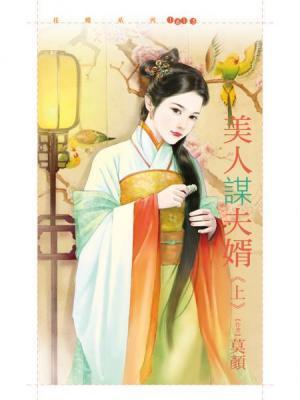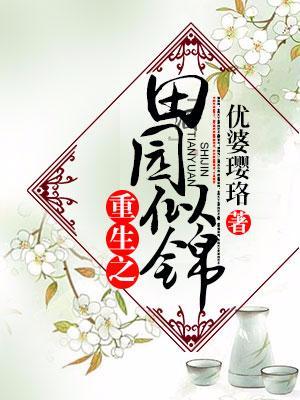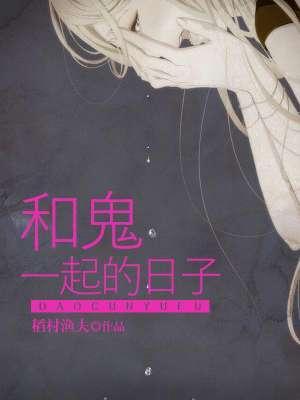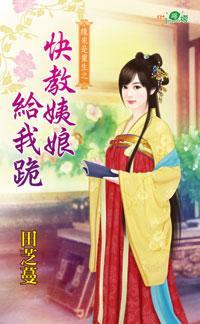第27章
第二十七章
這時王鶴站了出來:“北蠻小兒,有何懼?你們怕,我可不怕,明日我就出征,将這些蠻夷趕回老巢。”
郭玮欣喜異常,大贊王鶴忠勇,當即授予兵符,命他兩日後出發。
王鶴出征當日,郭玮親自到城外壯行,兩人對酒而飲,郭玮不由想起當年同在軍營的日子。随後大軍開拔,看着王鶴遠去的背影,郭玮心裏十分複雜。
沒想到,幾日之後,大軍行了不足百裏,卻傳來王鶴謀反的消息。與消息一同來的,是提着王鶴頭顱的李彥明。
據李彥明講,王鶴出開封幾十裏之後,說什麽也不肯向北,而是秘密聚集心腹,商議謀反之事,被李彥明察覺,混亂之中割下王鶴首級,這才及時制止。
郭玮不願相信,一面對着王鶴的首級痛哭不止,一面要綁了李彥明。在衆臣子的極力勸說下,才同意派人到王鶴家中搜查。
幾個時辰後,搜查的人回禀,王鶴家中金銀財寶、歌姬美妾不計其數,府中地庫還藏有利刃兵器,更是在其書房的暗格中,查找出了前朝的傳國玉玺。
面對鐵一般的事實,郭玮的哀恸大于憤怒,當即暈了過去,随行侍從又是掐人中又是灌湯藥、宣禦醫,好一陣忙亂,人才清醒過來。
在場的大臣很是為郭玮鳴不平,上年災禍四起、國庫空虛,郭玮作為皇帝,尚且卑宮菲食,可恨王鶴中飽私囊,大肆搜刮,全然置萬民、國體于不顧,最後更是以怨報德,罔顧天恩,實在是狼子野心。
群情激憤之下,紛紛要求郭玮定要嚴辦,肅風正氣、以振朝綱。
郭玮剛剛經歷了大恸,此刻身心俱疲,面對衆臣的極力要求,還是下不定決心,王鶴雖然可惡,但是禍不及妻兒,最後他力排衆議,下令王鶴府中沒有生養的妾室各自放還,有子女的随子女回到老家,終身不得返回開封。
消息傳出去,有人說郭玮心軟,有人誇他仁義,對王鶴,毫無例外都是唾棄。
經歷了這一番折騰,郭玮很是疲累,但也是第一次,在這皇城中睡了個安穩覺。
柴桑接到開封的來信,心中一塊巨石終于落了地。
今年光照充足、雨水充沛,澶州迎來了大豐收,百姓們還掉借來的種子糧,不用交租,雖不能一下子翻身,但總算有餘糧養活自己,日子好過了不少。
Advertisement
先前籌辦的學堂也漸漸成型,沒有了生計的壓迫,農忙之後,很多百姓也樂意将自家孩子送過去讀書識字。
眼下的澶州,雖然離柴桑的目标還有很遠,但他心裏明白,取得當下的成效已是很不容易,很多事情要慢慢來。
然而有喜必有憂,玉娘在外一個不慎摔倒在臺階上,七個多月的身孕就要生産,王府上下頓時亂作一團。
柴桑在外面一會兒聽見玉娘聲嘶力竭的嘶喊,一會兒又沒了聲響,又幫不上忙,只能幹着急。
九歌聽了消息也趕了過來,本來想進屋幫幫忙,卻被方嬸兒擋在門外,她還未出閣,方嬸兒怕屋裏的陣勢吓着她。
沒辦法,她只能在門外暗自祈禱,她雖未親眼所見,但聽着裏面一陣陣的動靜,看着一盆盆的血水端出來,十足駭人,難怪人都說婦人生子,猶如過了趟鬼門關。
情形雖然兇險,但好歹最後母子平安。
柴桑趕緊寫信給郭玮和褚良辰報喜,還特意提出,讓郭玮為孩子取名,郭玮倒是不在意這些,只是賜下了不少東西,名字卻讓柴桑自己取。
柴桑又問王樸的意見,論學識,他身邊沒人比得上王樸。王樸攤開一張紙,寫下了八個大字“青春受謝,白日昭之。”
柴桑不由得稱好,寓意好,又合了當下情境。于是給孩子取名為“昭”,昭,日明也,希望天地間終能撥雲見日,一片光亮。
轉眼又是一年,這一年像之前的每一年,不比以往艱難,也不比以往好過。
九歌有時候一個人坐着,會時常想起樂安谷中的事,那時她隐約知道世道不清明,谷外的人日子難捱,但也僅是來源于父親和偶爾得見的其他人的口述,或是來源于前人的詩書,終是隔着一層。
可這兩年,她眼前所見,卻一一證實,耳中所聞、書中所寫都是真的。
她見過路邊的森森白骨,見過拖家帶口的逃荒人、見過賣兒鬻女,見過大雪天在山上挖野菜的幼童,見過無數的普通人辛勞一年才勉強家有餘糧……
對于很多人而言,人生在世,僅是活着就耗費了全部的力氣,所謂金榜登科、錦衣玉食、花前月下、紅袖添香,都是無暇念及的奢望。
她很幸運,于萬千人之中,都算得上幸運,和生存比起來,她的那些傷心、難過、哀思、愁苦,不值一提。
她感覺她正在從自己的世界走出來,走向真正的世界。再看柴桑時,也不一樣了,以前看他是一腔孤勇,現在看他是目擊道存。
她開始真正走向他,無論是心中的橋,還是腳下的路。
父親去世一年,她才有勇氣翻開父親留下的那些書稿。父親留下的書稿不多,這很大程度上還得歸功于她。
現在所存,都是父親那年從洪水中逃生後,一點一點寫就的。當時父親在義舍,衣衫褴褛,張家在提供吃食外,還肯遞上紙和筆,真是大義。
而父親,在那樣的變故和身體狀況下,依舊提起筆,将所知所得見諸筆端,其中的堅韌和毅力,也絕非常人。
這些書稿,她整整看了兩日。
過去了這麽久,她依然為父親的才華驚嘆,這種才華,不是文人墨客的風雅,而是于故紙堆和平生所歷的淬煉,父親離京十年,字裏行間,從未放下。
九歌心中明白,依目前她的水平,這些書稿她很難完全吃透。要讓它真正熠熠生輝,她想到了兩個人,柴桑和王樸,思來想去,最後她還是給了王樸。
柴桑要回開封了,郭玮寫信催了幾回,他一直拖着,直到秋後看着澶州今年又豐收,他才放心。也是因為不能再拖了,郭玮的身體狀況,貌似不太好。
動身的那天,一行人起了個大早,天剛蒙蒙亮就準備出發。然而王府門口已經圍滿了百姓,更有人直接上前牽住柴桑的馬,拉着不讓走。平日裏與柴桑時常打交道的幾個人,把他團團圍住,為首的就是張勤。
“王爺,能不能不走啊。”張勤拉着柴桑的手,緊緊握住。
柴桑拍了拍他的手背,卻不知該說什麽。這樣的場面,他哪裏見過,更沒有想過。
“我今年四十多歲了,大半截身子都入土了,從沒見過你這樣的父母官。”張勤說着,有些哽咽,他與柴桑來往的最多,對他的人品本事最為信服。
“你走了,我們可怎麽辦啊。”一任任的刺史上馬,來來回回,誰把他們真正放心上了。
“我家才剛吃飽飯……”
“澶州好不容易度過了這個災……”
“我們向皇上請願,讓王爺留下來……”
“留下來吧王爺……”
一群人七嘴八舌,柴桑看着他們的眼睛,有種說不出來的難受,如果可以,他也不想走,他在澶州兩年多,走遍了大大小小的鄉縣,踏遍了多少的山川河流,和全澶州的百姓耗盡心血與災難抗争,親眼見着他們日子一點點好過起來。
兩年多了,他對這個地方太熟悉了,甚至對院子裏的一塊石頭、一棵樹,都有了感情。他也不想走,可他不能不走。
有人在抽泣,孩子還小,什麽都不懂,上了年紀的人才最傷心,一輩子了,他們在澶州活了一輩子,深知每一個新官的赴任,對他們而言都像是一場賭,十賭九輸。
“大家回去吧。”良久,柴桑才說出了這麽一句話。
悲傷的情緒依舊在無盡的蔓延和渲染,沒有人挪動腳步。
“大家回去吧。”圍在柴桑周圍的人,一點點散開,給柴桑留出了縫隙。
“回去吧。”柴桑揮揮手,上了馬。
依舊有人哭泣着,卻漸漸讓開一條路。
柴桑坐在馬上,拽着缰繩的手卻無論如何都使不上力。
他被眼前的場面感動,也被當下的情緒感染,他邁不出步。不是他對澶州有多重要,他做的很有限,百姓的挽留讓他心酸。他第一次當地方官,沒有絲毫經驗,只是做了分內之事,然而他,何德何能。
他又下了馬,分不同的方向,朝着四周的百姓深深行了幾個禮,之後對着百姓說:“會好的,都會好的。”
此去,願他能不負深恩。
城裏的百姓一直跟随着柴桑的隊伍,一路送到城外的十裏長亭,像送一位遠行的親友。
長亭裏,有人置了酒,杯酒下肚,柴桑望着澶州百姓,道了一聲珍重,而後踏上新的征程。
此後,他這一生縱馬行舟,走過無數的地方,卻從沒忘記過澶州。
九歌騎在馬上,領略過一路的風景。此去前路,不可預知,只朝前走,莫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