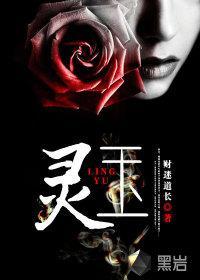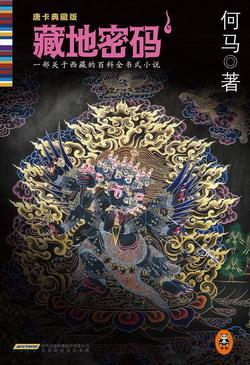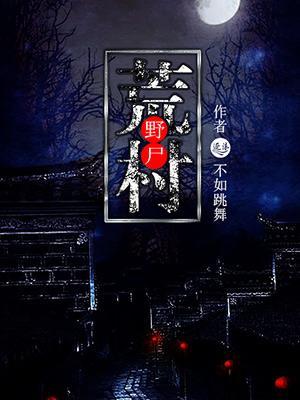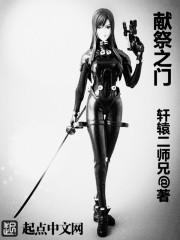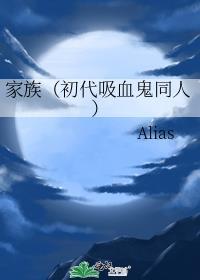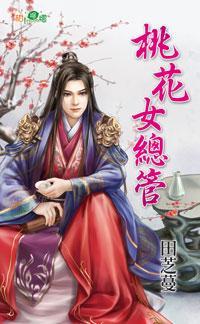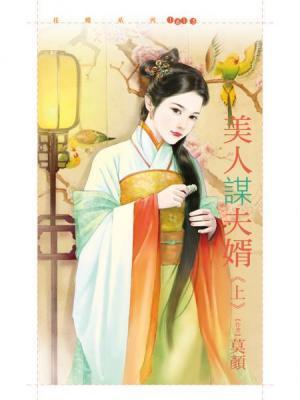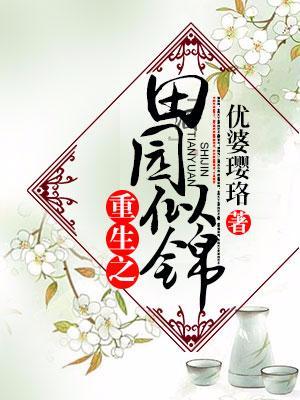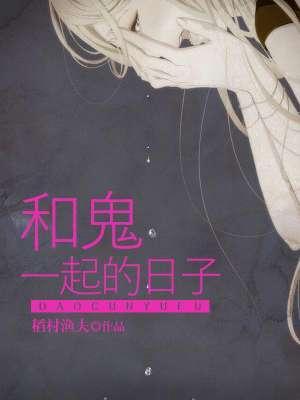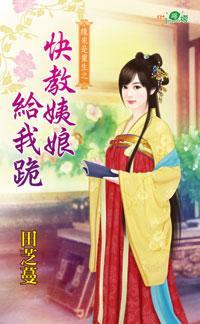第5章 (5)
未知世界居然是如此的可怕,而且自那件事情之後,我始終堅信,無論是追溯之前還是展望其後,都沒有什麽比它更能讓我感到毛骨悚然的了!
事情發生的時候,我正處在有生以來最不如意的一段時期,所以這件事情的發生,真實地讓我感受到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人生窘況。
我曾經供職的單位,位于上海遠郊的淮陰路,這裏有一座被稱做“七號公館”的九層紅色小樓。如此偏僻的地理位置,似乎也彰顯着七號公館的與衆不同,而事實上,它的确是個非常特殊的機構,特殊得有些詭異!
這個機構在國內獨一無二,我蒙祖上之蔭進入了這一機構,并在這裏度過了七年的時光。但是,七號公館成立于何時?因何而存在?究竟是何背景?我一無所知。這棟九層紅色小樓,就像是天外來物,很突兀地出現在世界上,随時又可能很突兀地消失,似乎與這個世界不存在一點點的聯系。
作為七號公館的第三代成員,我有編制,有職稱,甚至有某些擠破腦袋才能争取到的特權。于是很多人認為,我所在的機構既然如此的特殊和詭秘,所從事的工作必定是充滿刺激和挑戰,而我們這批人,定然也是掌握着某些高度機密,享受着某種特殊待遇的。
每每聽到這,我只能作一聲嘆息,實話說,我們這些人只能算是集體神經質,沒有目标、沒有方向、神經緊繃如行屍走肉般的職業生涯,才是我們這些人生活的真實寫照。
我始終相信高度機密定然是存在的,只是因為我們是屬于奮戰在前線的,所以真正的高度機密絕對不容許我們窺視。即便如此,我在七號公館的七年生涯中,受到的最正統的教育總結起來只有兩個字:保密!
正如預想的那樣,某一天終會來臨!2002年夏的一天,我們的機構在沒有任何征兆的情況下,突然宣布撤銷,所有人員盡數遣散。這一切來得極其迅速,一夜之間,原本神秘莫測的七號公館便人去樓空。面對七年的職業生涯就此結束,當時我的心情既不是留戀,也沒有解脫感,七年的時間培養出的那份敏感告訴我:有事情要發生!
我們這些人被遣散後,随即各奔東西,有不少人就此便斷了聯系。我本有機會再次進入事業單位,但此時的我已經厭倦了按部就班的生活,于是選擇了下海。本以為這樣,我必定是和之前的生活來個徹底的告別,但命運的轉盤是神奇的,不經意間,它就會調動着你的人生走向,進而使得你被動地回歸到一切的起點。
2004年夏天,我承包了市郊一棟爛尾樓的拆遷工程,附帶新樓盤二號樓和中心綠化帶的建設項目。那時候,國內的房地産業蓬勃興旺,大量的郊區被城市化,但由于種種原因,我這幾年一直在慘淡經營。屋漏偏逢連夜雨,我承包的上一撥工程出了質量問題,急需回籠資金,而這筆業務是個肥差事,我只得拆東牆補西牆,竭盡全力通過以前在單位的老關系搞來這個工程,也虧得有了這層關系,才使得我這樣一個本來最不可能競标成功的小建築商順利奪标。
一切就好像是安排好了似的,跟我有關的東西,終究無法逃避。也許我注定和七號公館有不解之緣,我所負責的項目恰巧正是我再熟悉不過的七號公館辦公樓,自從我們部門撤銷之後,這棟九層小樓便人去樓空,如今剛到兩年時間,就淪落到了必須強行拆除的境地了。
而就在一切工作就緒後不久,技術人員突然帶來一個消息:此樓地下多處出現不規則的空洞,而且分布極其不均勻,所以不适宜施行爆破!
聽到這樣的消息時我大吃一驚,倒不是顧慮無法爆破會給我增加多少拆遷的成本,而是我很明白這種不規則的空洞意味着什麽,那正是說明,這棟樓的底下分布着很多的地下室。
我在七號公館整整工作了七年,或多或少地也接觸了一些被別人稱做機密的東西,可我從未聽說過七號公館有地下室。我雖然明白,在七號公館,很多機密不僅僅是針對外人,對內部人員也是一視同仁,但那時的我尚未從人生的低谷中徹底走出來,心理狀态很差,所以得知這個消息的一剎那,我頓時有種被蒙騙的感覺,這種感覺就如你死心塌地地為某個人賣命,他卻像防賊一樣地防着你。
于是,我毫不猶豫地下了決心:必須進去一窺其究竟。雖然當時的我并不知道這樣的決定是否正确,但至少現在看來,我從未對當年的這個決定感到過後悔。
正如爆破人員所說的那樣,地下室的分布很不均勻,入口的位置也十分的隐秘,在一樓根本找不見任何地下室的入口。無奈,我只得借助工程人員的力量,在地下空洞的一樓某處強行打孔進入。
Advertisement
一樓的地面極其厚實,比尋常有地下室的房屋足足厚了一倍多,中間還包裹有尺餘厚的隔音材料。待整層地表被完全洞穿時我才發現,地下室的房高遠遠高于一樓,為了安全起見,我們不得不借助繩索才得以進入。
當時我的心裏很明白,有些東西之所以如此慎重地做着保密的工作,自然有它的道理,而我也從未嘗試過窺探,但事已至此,內心的那種悸動和好奇是無法阻擋的,帶着這種複雜的心情,我和兩個夥計的腳順利地踩到了地下室的地板上。
從開鑿的洞口下來,剛好是地下室的走廊位置,這棟樓已經閑置兩年了,所有的電路系統已經廢棄,我們只能借着幾只手電向裏摸索。走廊裏顯得平淡無奇,地面是水磨石,頂面石膏天花,牆面的石膏粉都已經崩落,給人一種老舊的感覺,牆面零星地懸挂着幾幅人物肖像畫,畫框的玻璃大多已經碎裂,和一些文件資料一起散落在地面上,很多儀器、桌椅等物也橫七豎八地倒在一旁,現場淩亂不堪,就好像這裏的人遭遇了什麽突然變故緊急撤離了一般。
走廊并不是筆直的,而是呈弧形,由此可見整個地下區域的格局和地上九層是完全不同的,地下一層完全是獨立體。每隔一小段,走廊兩側的牆壁上便會出現一扇塗了綠漆的鐵門,有上了鎖的,有虛掩着的,也有大門洞開的,從敞開門的那些房間看,這裏分明是被隔成了一個個小房間,房間內桌椅、書架、書報夾等辦公設備一應俱全,顯然正是用于辦公的場所。
看到這我更是一頭霧水,我可以肯定,在七號公館這麽長時間,從來沒聽人說過這地下居然還有如此像模像樣的辦公場所,而且七號公館工作人員這麽多,不可能保密工作做得這麽好,此時我甚至懷疑所有人中只有我一個還蒙在鼓裏!
這樣的想法越加刺激了我的窺探欲望,繼續向前,直到走廊的盡頭,前方是一堵封閉的水泥牆,再便是兩扇朱紅色的鐵門。鐵門從裏面反鎖,且相當厚實,蠻力根本無法打開。我當時決心已定,再加上這已經是确定拆除的項目了,我更是無所顧忌,馬上讓人取來了氩弧焊切割機,強行破門而入。
鐵門一打開,一股怪異的氣味便撲鼻而來,夾雜着嗆人的金屬焦味,極為難聞,我緩了好大一會兒才勉強适應。
這是個相當大的封閉石室,足有一個籃球場那麽大,站在鐵門前,手電的光還無法照到對面的牆。放眼望去,隐約可見一張張長方形的長桌整齊地排列着,我疑心這裏是地下的會議室,但沒走兩步,當我慢慢地靠近那些長桌時,一種異樣緊跟着撲面而來,接着我就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這些長方體根本不是什麽長桌,分明是一口口棺材!我簡單掃了一眼,數了一下,這些棺材共十七口,圍繞着石室中心的一座石臺,呈菱形的方陣排列着,而石臺的上方,赫然矗立着一個更為巨大的方形物體,用厚實的帆布掩蓋着,看不清面目。
我當即一怔,伴随着恐懼湧上心頭的,是極度的困惑。說實話,我在七號公館的七年,可以說過的是一種難以言表的渾渾噩噩的生活,我根本不知道七號公館為何種目的而成立,也不知道自己每天究竟在做些什麽。雖說我們也接受一些考古研究的項目,但那對業內人士向來都是公開的,而眼前我所見的一切顯然是瞞天過海而進行的!
這裏怎麽會出現這種東西?我帶着滿腹狐疑,再次掃了一眼四周。昏暗的地下密室中,十多口棺木齊整地排列着,這情形原本就足以讓人吓破膽了,更駭人的是,這些棺木雖然擺放得極其整齊,但有幾口呈現半掩的狀态,就好像後來有什麽力量使得棺蓋被啓開了一般。
“我說沈工!我覺得這裏瘆得慌,咱還是別折騰了!”随我同行的一個叫阿廣的夥計見此情形當即道,另一個夥計立刻表示響應。
而我當時的想法稱得上固執了,我有種很清晰的預感:自己正在接近一件巨大秘密的核心部分。這種力量使得我當時無法就此收手。
兩個夥計在我的壓力下只得硬着頭皮上了,我心裏樂道跟着我做事也夠慘的,拖欠工資不說,還得幹這些趕鴨子上架的事情。
我們小心地繞過那些密集的棺木,直接來到中心石臺上。這裏顯然已經廢棄了很久了,甚至可能遠遠超過我在七號公館的生涯,帆布上積了厚厚的一層灰,而且脆弱不堪,輕輕一扯便支離破碎,帆布扯下後,一個巨大的金屬箱子赫然顯現在眼前。
我無法具體形容我看到的東西,只能說這是一個箱子,黑色的金屬箱子。箱子近似正方體,長寬估計兩米左右,高約一米半,周身漆黑光滑,觸之冰涼異常。将耳朵貼到箱體上,隐隐約約地,似乎能聽到箱子內有響動,那聲音若有若無的,但卻能清晰地感覺到聲音正是來自于箱子內部。
箱子是密閉的,合上之後便上了鎖,但因為年代久遠,鎖眼已經鏽堵了。從敲擊的聲響判斷,這箱子異常的厚實,我們現在的工具是沒法強行切開它的,而且我當時還有着那一點點覺悟,對于這種隐秘的未知之物,我想做的僅僅是窺探而并不是破壞。
箱子表面并沒有任何紋路,只在靠邊的一個角上,發現有一行用漆筆寫的紅色小字:1982年5月13日,南陵,8號檔案。再便是一個封條,封條上的日期是1989年。看到這我便知道我猜測得沒錯,我是1995年進入七號公館工作的,原來這裏早在我來六年前就已廢棄不用了,也難怪我一點也不知情。
“沈工,有發現!”我正在那兒納悶沉思,我的夥計忽然叫了一聲,一個勁地朝我招手示意。我一怔,趕忙上前順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發現石臺上赫然有一個像小門一樣的入口。
放置鐵箱子的石臺相當的大,高度也超過一米,那入口開在離北牆最近的一面上,那是一個不到一米高的窄小門洞,虛掩着一扇鐵制栅欄門,栅欄門的門鎖已經鏽壞脫落,形同虛設,被我們幾人合力一拉便打開了。
打開鐵栅欄門,裏面是一個一次僅供一人通過的窄小通道,當時的我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探求欲望了,當下咬着手電,小心地順着那通道探了下去。通道在底下一人深的地方便到了底,進而便轉變了方向,由原本的縱向變成了橫向,徑直通向七號公館北牆的方向。
但通道的大小卻并沒有多大改變,依舊窄小,通行起來十分的困難,就連轉身也是件比較吃力的事情。好在這一段路程并不遠,我們貓着腰很快就抵達了盡頭。這時候,通道又變成了縱向,寬度也陡然增加了好幾倍,呈現在眼前的,是一條條鋼筋鑄成的爬梯。那些爬梯一直通向頂端,手電光都無法照到盡頭,而我們所在的地方,正是最底端的位置。毫無疑問,這裏是條秘密通道,而且極可能是地下室與上層連通的唯一通道。
我簡單地回憶了一下地下室的布局,腦子漸漸清晰起來,這裏應該已經處在七號公館北面最外牆的位置了。我記得七號公館裏有位老前輩和我說過,這棟樓剛建成的時候,正北面中心位置本來留有一個凹形的角,為了放置排水管道的,後來因為各層的領導辦公室都處在這裏,排水管道又被改到了其他地方,而這個凹形角也因為風水的問題最後被堵上了,使得整個北牆一馬平川。
這樣的說法顯然是為了麻痹無知的人,那個年代的人們狂熱地信仰着我們的主義,何況是我們這樣嚴肅的部門,堂而皇之地談論風水幾乎不可能。而現在看來,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就十分的明顯了,顯然就是為了制造出這樣一條不為人知的密道。
望着黑黝黝深不見底的通道盡頭,我微微遲疑了一下,但很快地,我便轉頭示意我的兩個夥計就在這裏等候,接着我戴上工程帽,咬着手電便就着那些爬梯往上攀。我的夥計不放心我,見我态度如此堅決,當下堅持和我一起上去。
爬梯的确很長時間沒有使用了,手一握緊就扒下來一把鐵鏽,爬九層高的爬梯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一不小心摔下來就足以喪命,我一邊爬一邊還得檢查着四周有無出口。
等出口找到的時候,我已經爬到了最頂端,當下已經累得氣喘籲籲,幸好底下漆黑一片,否則讓我在沒有任何安全措施的狀況下,在如此高的地方俯視地面,足以将我吓壞了。抵達最頂端的時候,通道再次變成橫向,只不過這次不再是磚石結構,而是變成了金屬板,扁平扁平的,就像是室內中央空調的通風管道。
順着通道再穿出去,第一眼見到的又是一扇木質的子母門,門是虛掩着的,我毫不猶豫地推門而入,進入了一個房間內。
這間房相當的寬敞,卻沒有窗戶,是一間完全封閉的房間,房間四周的牆壁用的都是軟包,做了很好的隔音處理,正中間位置,擺放着一張可容二十人開會的會議桌,四周圍繞的是一圈轉角椅,會議桌的正中位置擺着一臺膠片放映機,桌上整齊地擺放着一套套杯盞、碳素筆、紙質文件等物,就好像剛剛有人在這裏開會才散會一般。
上前一看,只見桌子上已經蒙了厚厚一層灰,杯盞中的茶水早已幹涸,茶葉凝結成了一團黴塊,紙張也被老鼠啃咬得不成樣子,軟塌塌的一抖就散。
靠北的一面牆上整齊地碼着幾個檔案櫃,其中一個檔案櫃的櫃門敞開着,地上淩亂地散落着一些文件資料。而敞開櫃門的檔案櫃裏,碼放的是一堆堆包裝完好的鐵皮箱子,這些鐵皮箱子塞滿了整個櫃子,上面都被做上了記號,分別标記着1997年2月、1997年3月、1997年4月……這些箱子就被用這些不間斷的日期标記下去,很容易看出這是某種檔案,用日期進行标記的。
而且再仔細一看,房中所有的檔案櫃子裏都裝滿了這種東西,清一色地都用日期進行了标記,我掃了一眼,這些标記從1995年一直到2002年,每個月份幾乎都有。但我看着那些東西,越看越覺得奇怪,總覺得哪兒有些不對勁,再理了一下才猛然發現,這些東西缺少了1998年的,而按着這些東西的排列規律,我發現1998年的那十二箱就放在那個被打開門的檔案櫃裏,很明顯,有人特意拿走了1998年的這套東西。
就在這時,屋內的日光燈突然忽閃了兩下,接着“撲哧”一聲爆了。這樣的情形着實讓我吓了一大跳,但随即便聽到一旁的阿廣驚愕地道:“沒想到這裏居然還有電!不過這兒太長時間沒用,電路早就老化了,剛才那一下就短路了!”
七號公館已經廢棄兩年,電路系統也早已經廢棄,這裏能通電,肯定走的是獨立的電路系統,或者就是為了防止電路故障而設置的應急備用電源。
我試探地摸索着尋找電源開關,試圖再打開光源,但光源控制開關實在太多了,剛才的一下造成了短路,整個光源系統已經盡數崩潰了。而就在我按下最後一個開關時候,突然一陣“嗤嗤”聲響起,屋內騰起了一道微弱的亮光,而我很快辨別出這亮光并非來自于頂面,而是來自會議桌的方向。
亮光正是放映機的指示燈,我大感驚愕,沒想到這廢棄多年的放映機居然還能夠使用。而到了這個時候,我相信任何人都沒法去阻止自己的下一步行動的,所以我當時直接省略了猶豫這個過程。
我在入七號公館之前,曾做過很短一段時間的林場放映員,這種東西對我來說再熟悉不過了,我熟練地上手調試了幾下,先簡單往回倒了倒,确定膠片沒有粘接在一起後,當即按下播放鈕。
放映機的轉盤微微晃蕩起來,接着順利地被啓動,對面的幕布上出現了清晰的影像。
畫面黑白,從拍攝的角度來看,是居高臨下俯視拍攝的那種,而且不住地抖動着,不難看出拍攝者是乘坐飛機在進行航拍。影像沒有聲音,只有畫面的底端配着字幕,但字幕的文字都是日文,我們在場幾人都無法識別。
畫面的主要場景是大片的叢林,飛機拍攝時進行的是低空飛行,一旁不時還有飛機呼嘯而過,地下濃煙四起。我當即明白,這很可能是在進行着轟炸,這架飛機的航拍就是為了觀測這種轟炸效果。我放慢了鏡頭,捕捉定格住了幾個飛機的畫面。
我受家庭環境的影響,自小對軍事武器之類的頗感興趣,多年的軍事常識積累,使得我一眼便認出了畫面中的飛機類型,這分明是綽號為“飛行雪茄”的日本三菱G4M一式陸上輕型轟炸機。
一式陸上轟炸機是二戰期間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使用率最高的一種俯沖轟炸機,在日本一系列侵略戰争中,可謂立下汗馬功勞。二戰期間,這種戰機憑借着優良的性能和龐大的載彈量,在中國和東南亞諸國制造了一系列的血腥恐怖,可謂臭名昭著。
畫面上的幾架一式轟炸機對一片茂密的叢林進行了輪番轟炸,原本郁郁蔥蔥的廣闊密林被強行撕開了一個大口子,一塊塊隐藏在密林中的巨石顯現了出來。與此同時,航拍的飛機繞着那些巨石的上方盤旋了幾圈,徐徐地向目标靠近,使得此時的畫面顯得越加清晰了。
從高空俯視,那些巨石排列得十分緊湊整齊,像是一塊塊矗立的墓碑,由于被炸開的地方是一個圓形區域,在叢林的反襯下,灰白色的巨石組合起來,形成一道白色的圓形地帶,像極了一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上空。尤其是航拍的飛機向目标靠近,畫面被拉得越來越近的時候,那東西看起來就越像是一只人眼。
而我此刻盯着這些畫面,直感到一陣詭異從裏面透出來,但我又不知道裏面的東西究竟哪裏不對勁,只是這種畫面看着讓我糾結,有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轟炸産生的煙柱像蟲子在蠕動,飛機在上空盤桓了幾下,仍在向那眼球狀巨石陣接近。這時,畫面突然出現了幹擾波,接着劇烈地抖動起來,充斥着許多雪花點,原本清晰的畫面開始變得模糊不清。
就在這時,我突然發現畫面上的那眼球狀巨石陣有了些變化,和之前的不一樣了,但我還沒來得及辨清那是何種變化,畫面迅速模糊起來,根本無法再辨清了。很快地,畫面上滿布雪花點,就此定格住了。
我迅速将帶子倒回去,從出現幹擾波那時候再重新看,無奈這種老式放映機的性能實在太差,卡鏡頭的緩沖帶太強,我來回折騰了好幾次,都沒有卡到我想要看到的鏡頭。我也知道即使卡準了位置也會因為畫面的原因無法看清,于是失去了興趣,接着又迅速地快進,将這些無聊的內容跳了過去。
跳到後面,畫面忽然又變成了彩色的,同樣是以俯視的角度航拍,但這次的不但有了色彩,而且比之前的黑白畫面清晰了很多,而當畫面上又出現了那叢林巨石陣的時候,我很快就明白了。
這顯然是兩次不同時期的拍攝,從後面拍攝的那些彩色高清畫面來看,兩次的拍攝時間至少間隔四十年。但它們的拍攝角度和方法都是一樣的,更奇怪的是它們的拍攝目标也是一致的,也許這才是它們被剪輯到了一起的原因。想到這我頓時又疑惑叢生了:是什麽人整理剪輯這些相差數十年的錄影帶?他們究竟在研究什麽?
就在我疑惑的時候,畫面又轉移到了那巨石陣的上方,随着飛機的緩慢挪動調整角度,最終拍攝角度停留在了巨石陣的正上方。從畫面的顯示不難看出,這次運用的是直升機定位拍攝。
那些巨石陣已經不再是掩藏在密林中了,從上方一看便已經暴露無遺,顯然為了這次的拍攝,掩蓋着那些巨石的樹木被砍伐殆盡,而且這次暴露的巨石範圍比之前那次不知道大了多少。
而畫面中的直升機似乎很忌憚那些巨石,一直沒有靠近拍攝,随着拍攝角度從巨石陣的邊緣掃過,直升機便開始緩緩上升,遠離巨石陣,不一會兒,整個巨石陣便盡收眼底。
我們幾人看到那東西的第一眼,止不住一陣驚呼,一種怪異的感覺從後背襲上來,直讓我渾身一陣哆嗦。畫面就此又定格住了,只見高空俯視之下,那些巨石排成的方陣,形成了一個極其複雜而規則的圖案,那居然是一張人臉!
這的确是一張人臉,而且還稱得上清晰,由碎石組成的人臉,就像是一張人臉照片被撕成了無數片,再拼湊組合起來一般,看起來極不舒服,而且此刻我總覺得畫面上的人臉呈現出一種難以言表的異樣,有一種妖異感。
我一扭頭,只見兩個夥計都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副十分困惑的模樣。見我一扭頭,阿廣即道:“沈工,我覺得這張臉很……我好像在哪兒見過!”他的話剛說完,一旁的另一個夥計也接過道:“對!沈工你不覺得嗎?”
他們說着,目光在幕布和我的臉之間來回跳動,好像在比對着什麽!我腦門一熱,很快意識到了什麽。再仔細一看,當即驚愕得差點沒站穩腳跟:畫面上的巨石陣人臉,極其逼真傳神,無論從臉形還是面部表情來看,都像是從一個模板上複制出來的,那居然是我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