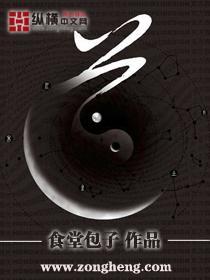第1章 作品相關
《明末之偉大舵手》 - 作者:英聯邦
番外篇1:紅丸案
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萬歷帝病死。
太子朱常洛繼位,改年號為泰昌,史稱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沖粹無病容”,就是行走、儀态正常,沒有疾病的症象。
泰昌帝在萬歷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發銀100萬兩犒勞遼東等處邊防将士,罷免礦稅、榷稅,撤回礦稅使,增補閣臣,運轉中樞,“朝野感動”。
本來泰昌帝以為新君繼位,會有一番作為,不想登基大典後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
第二天的萬壽節,也取消了慶典。
內閣首輔方從哲是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資格入閣的,他在萬歷朝擔任了七年首輔,很能處理君臣間的關系。萬歷皇帝對于方從哲替他草诏的各項谕旨,幾乎沒有受到過駁斥,那是由于方從哲設法結交了萬歷最寵愛的妃子鄭貴妃的緣故。
方從哲剛來到朝房,內廷就送來了一道緊急公函。原來是泰昌帝有病亂投醫,昨天竟擅自斥退太醫院醫官,而請內侍崔文升給他看病。崔文升開了一個方子,皇帝吃後大瀉不止,一夜之間如廁三四十次,現已昏迷不醒,急請內閣處置。
當方從哲帶着閣臣們趕到太和門時,內廷已經亂成了一團,皇帝昏迷不醒,太醫們束手無策。
天近中午了,幾位禦醫才從宮中出來。領班的禦醫已經七十多歲了,平日與方從哲交往很深,一見面就壓低了聲音說:“上頭的病不妙。”
方從哲有些疑惑:“剛剛四十出頭,怎會病成這個樣子。”
老太醫搖了搖頭:“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皇上精損過重,所以太醫們一向使用固精建中之類的藥物。這類藥物本是慢工,豈能神仙一把抓?皇上埋怨服之無效,而濫用瀉藥,以致我們數月調治之功毀于一旦。”
方從哲脫口問道:“莫非不好辦了?”
老太醫嘆了口氣說:“如果不再亂用庸醫,只以充血生精之藥調理,還是有望的,只怕……”
方從哲趕緊說:“我當進宮勸谏,請皇上按太醫院的醫案調養。”
Advertisement
送走老太醫,已經過了午時,方從哲匆匆用了一點午餐,正準備寫勸谏皇帝相信太醫院的劄子,卻聽到太和門裏一疊聲的傳呼:“皇上急召首輔入宮。”
方從哲又火速進了乾清宮。
泰昌帝伸出有些顫抖的手握住方從哲,說:“朕這幾日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臨朝,一切大事都煩先生操勞了。”
方從哲趕緊道:“萬歲天恩浩蕩,從哲敢不竭盡全力報效國家?”
泰昌帝說:“朝中政事先生可代朕朱批,太子生性懦弱,也望先生扶持,後宮妻妾尚未來得及冊封,先生可依舊例拟定名分。”
這幾句話無疑是交代後事了,方從哲忙安慰說:“萬歲春秋正富,偶染小疾,原無大礙,望安心調養,千萬不要誤信流言,作踐龍體。”
泰昌帝搖了搖頭突然問道:“壽宮可曾齊備?”
方從哲感到十分為難,思索了一陣才說:“萬歲放心,大行皇帝已安葬完畢,天壽山地宮于前天開始複土……”
沒等他說完,泰昌帝打斷說:“朕問的是朕之壽宮。”
方從哲慌忙顫聲勸道:“太醫院禦醫已禀報,萬歲目前不過是體質虛弱而已,哪裏會有天崩地裂的事?”
泰昌帝厭煩地說:“太醫院一幫庸醫,朕信不過。”
方從哲說道:“萬歲若信不過太醫院,臣當傳檄天下,廣召名醫。”
聽到廣召名醫幾個字,泰昌帝就問:“聽說鴻胪寺有官員來進藥,如今為何還不送來?”
方從哲說:“鴻胪寺丞李可灼曾上本說他有仙方可治萬歲病症,但臣與內閣諸臣計議,以為不可輕信,所以已将李可灼斥退了。”
泰昌帝面露嗔色:“太醫無用,仙方又不可信,難道叫朕束手待斃?”
方從哲吓得連連叩頭說:“微臣怎敢?只是李可灼之言實不可信,皇上三思。”
泰昌帝揮了一下手說:“你傳旨下去,朕要試試這個仙方。”
方從哲知道,從萬歷帝的爺爺嘉靖帝起,就信奉道教,求煉長生不老的仙丹,這股風氣由來已久。看來泰昌帝也迷信“仙方”,只好推托道:“待臣與六部九卿商議後,再來禀明皇上。”
泰昌帝揮了揮手,示意方從哲不要再說。
方從哲匆匆退了出去。
接連三天,後宮裏不斷來人催問:“李可灼的仙丹是否送來了。”
方從哲只是推托,到了第三天下午,皇帝的親随太監來到體仁閣,說皇上降旨,着李可灼速帶仙丹進宮。方從哲無奈,只得與閣臣韓爌議定,由他二人陪同鴻胪寺丞李可灼帶所進之藥進宮見機行事。
鴻胪寺丞李可灼是個五十開外的老人,他舉止飄逸,确有點道骨仙風。所進的“仙丹”盛在一個十分古樸的錦匣內。據李可灼講:此仙丹乃是他年輕時在峨眉山采藥時得遇一位仙長所贈,所用藥料均采自神府仙境,能治百病。
泰昌帝顯得比前幾天更消瘦了,體質虛弱。但他的神志十分清楚,見方從哲進來就問:“仙丹可曾帶來?”
方從哲跪着奏道:“李可灼已攜仙藥進宮,究竟能否治病,臣尚不敢妄言,請皇上明斷。”
這時,李可灼也捧着“仙丹”跪在後面。泰昌帝示意把藥呈上來。李可灼見周圍大臣有疑慮神色,先自服一丸,大臣們方才放心。
而泰昌帝一見仙藥,于是命人取水來,急匆匆地把藥吞下去了。
過了會兒,泰昌帝睜開雙眼,坐了起來,好像一下子健康了許多,臉上露出了笑容,連誇:“果然是仙藥,仙藥!”又稱贊道:“李可灼是個大忠臣。”說罷探出身來叫道:“李可灼!”李可灼伏地輕應:“微臣在。”
泰昌帝說:“朕服仙丹果然奏效,請你明天再進一丸來,大概就可痊愈了。”
李可灼答道:“臣家中尚有一丸仙丹,但仙長曾指點過,需在第一丸後三天再進第二丸,臣當于三天後再獻靈藥。”
泰昌帝說:“朕病好後,一定給你加官晉爵。”
自吃了李可灼的“仙丹”後,泰昌帝的病好似一下子被驅走了一半。
兩天來,他除了時常坐在龍案前養神外,居然還有兩次走出了殿門。誰知當夜競暴卒。
方從哲想來想去,覺得只有利用拟遺诏的機會,申明服用紅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見,把責任一股腦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
果不出方從哲所料,泰昌帝的暴卒引起了整個朝廷的注意,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兩天之內就達數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經公開指出,給泰昌帝服瀉藥的內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鄭貴妃屬下任職,後來才由鄭貴妃轉薦給泰昌帝。崔文升竟敢用瀉藥摧殘先皇,其背後必有人指使。
于是方從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閣臣同意,頒布了由他親筆起草的遺诏。遺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誇獎李可灼,并诏賜銀幣。遺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們都知道遺诏出自首輔之手,無形中更把方從哲與紅丸案緊密聯系在一起了。
十月中旬,追查“紅丸案”的呼聲達到最高潮,禮部尚書孫慎行和左都禦史鄒元标上了兩道令人矚目的奏疏,孫慎行指出:“從哲縱無弑君之心,卻有弑君之罪。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這給追查“紅丸案”元兇定了基調。
方從哲思來想去,他寫了一道很長的奏本,一面仔細為自己辯解,一面十分誠懇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
方從哲奏本遞上去不到十天,天啓皇帝的批準谕旨就下來了。十一月初,這位執政八年的老臣,離開了京城。
泰昌帝的猝逝,使得禦史鄭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與多年前的“梃擊案”出于同一“奸謀”,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與鄭氏、光宗寵妃李氏等陰謀奪權有關。
後續
朝臣之争
泰昌帝繼位一個月即駕崩,加之朝廷內黨派紛争激烈,使得關于此案的議論甚嚣塵上,并且多少帶着東林黨借機伐異的意味。
這些議論圍繞着泰昌帝的死因展開,方從哲、李可灼、崔文升等皆成為衆矢之的。
吏部尚書張問達、戶部尚書汪應蛟、禮部尚書孫慎行、左都禦史鄒元标,以及衆多言官紛紛彈劾崔、李二人用藥、進藥錯誤之罪。
其中禦史王安舜認為:“先帝之脈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紫赤,滿面升火,食粥煩躁。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疹,幾何不速亡逝乎!”
由于泰昌帝是服下紅丸後死的,而首輔方從哲卻在泰昌帝死去的當天,拟遺旨賞了進獻紅丸的李可灼,引起了一些人的懷疑,禦史王安彈劾方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以自掩”。
禦史郭如楚彈劾方從哲不應該賞賜進藥的李可灼。
方從哲在衆人攻擊下,拟太子令旨,罰了可灼一年的奉祿。
十月,禮部尚書孫慎行和左都禦史鄒元标上了兩道令人矚目的奏疏,孫慎行指出:“從哲縱無弑君之心,卻有弑君之罪。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方從哲上奏辯解并請辭,于11月初卸任離京
陰謀加害
禦史鄭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與多年前的“梃擊案”出于同一“奸謀”,即有人必置泰昌帝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與鄭氏、光宗寵妃李氏等陰謀奪權有關。
最終判罰
方從哲離京後,還是無法脫淨幹系,要求嚴查紅丸案的奏折不斷。
一天,天啓帝收到了方從哲從老家寄來的奏疏,疏中說: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進藥,罪不容誅。為表示謝罪,願乞削去官階,以耄耋之身遠流邊疆,以平朝臣之怨。果然,許多大臣為他開脫,天啓帝亦被方從哲的誠懇打動,但苦于真相未明,一時難以決斷。
這時,一直緘默無言的閣臣韓爌終于站出來說話了。他把當時目睹的一切事實都詳細地說清楚了。特別是方從哲當時左右為難的情景,被描繪得十分具體。最後,韓爌提出,“紅丸”一案糾纏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現在也沒有處置,這兩人雖然亂用藥物,但也确實是奉旨進藥,可以适當懲處,紅丸一案則不宜繼續深究。
韓爌在萬歷年間就是個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餘年處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閣後又一直陪伴方從哲料理進紅丸之事,說出的話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報上後,很快地使一場風波平息了下來。
不久,天啓帝下旨問崔、李二人罪。1622年(天啓二年),明廷将崔文升發遣南京,李可灼遣戍邊疆。“紅丸”一案由于各派的争鬥總算草草了解,但其中的疑點并沒有弄清楚。
後人為此曾進行過一系列的考證和争論,但最後也都沒有結果。泰昌帝的死是否與紅丸有關依然是一個千古之謎。
案件餘波
天啓年間,宦官魏忠賢當權,他要為“紅丸案”翻案。于是,聲讨方從哲的禮部尚書孫慎行被開除了官籍,奪去所有官階封號,定了流戍。
抨擊崔文升的東林黨人也受了追罰,高攀龍投池而死。崇祯年間,懲辦了魏忠賢,又将此案翻了回來。
崇祯帝死後,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為題材挑起黨争,直到明王朝徹底滅亡。
争議
關于泰昌帝的死因,有人說是服紅丸而死,也有人說與紅丸無關;有人說舊病未愈,有人說是勞累所致;有人說是惑于女寵,是鄭貴妃有意加害;有人說是用藥差誤。有的大臣因李可灼進紅丸功,議“賞錢”;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誅”,議“罰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醫官,且非知藥知脈者”議上,将其遣戍;直到天啓五年(1625年),魏忠賢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這個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為天啓朝黨争的題目之一。
紅丸到底是什麽,這也是一個引起争議的問題。有人認為,李可灼進的“紅色丸藥”就是紅鉛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藥。
春藥屬于熱藥,皇帝陰寒大洩,以火制水,是對症下藥。李可灼把春藥當補藥進上,只是想步陶仲文後塵而已,只不過他時運不佳……有人認為,那紅色丸藥是道家所煉金丹。用救命金丹來對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則名利雙收,死了算是病重難救,李可灼很可能是這樣想這樣做的。
三百餘年來,史學家設想了種種答案,但沒有一種令人信服,因此紅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謎。
番外篇2:薊州兵變
1595年,明朝北方九大邊鎮薊鎮發生了一件事,在歷史上很不起眼。
這一年正是萬歷朝鮮戰争的第三年,由于前線戰事趨緩,明軍将第一階段在入朝的部分士兵調回國內,駐紮在山海關,石門等地。他們的人數約3700人。
這支部隊被稱為“南兵”,都是從義烏,處州等地招募,按戚繼光兵法訓練和作戰的軍隊。主将是跟随戚繼光數十年的老将吳惟忠,也就是說這是不折不扣的戚家軍。
戚家軍在朝鮮的表現非常出色,在平壤戰役中他們奮勇登先,連吳惟忠本人都被鳥铳射穿肚腸,但戚家軍還是第一批登上了城牆,一天一夜就拿下了被日軍占領了多日的平壤城。
按說遠赴異國,定一國之都的功勞可以載入史冊,但等候他們的卻讓人意想不到的事:
新任的上司薊鎮總兵官王保,把他們叫到演武場上,
戚家軍發現自己被已經武裝好的友軍包圍,屠殺,最終死亡人數最有根據的說法是1700人。
然後他們被冠以兵變的罪名,草草上報了事,雖然有熱血禦史為之鳴不平,但是在當時兵部尚書石星的擔保下,總兵王保不但無罪,甚至還因“平等變難”得賞。
史稱“萬歷二十三年薊州兵變”。
戚家軍被冠以的罪名之一是趁亂搶劫殺戮附近的商戶居民,但且看看朝鮮君臣對這支部隊的評價“功最廉操”,“一路皆立碑頌之”來看,這支部隊軍紀極佳,在朝鮮時是少有的不搶劫不擾民的軍隊,朝鮮當年所立碑到兩百年後還看得見。
在國外戰區尚且如此,到國內反而會搶劫商戶殺戮自己人民?明顯不合理。
那原因是什麽呢?
他們因何被殺戮?
為什麽在日軍的火繩槍下他們不過犧牲數百,回國後反而倒在友軍刀下?
戚家軍是一支高薪酬的職業士兵。
雖然戚家軍很強調愛國保民教育,但士兵們确确實實是為了高報酬而來,戚繼光也并不諱言這一點,他只是教育士兵們:養貓是為了抓老鼠,養狗是為了看家,你拿着朝廷和百姓的銀子,出力殺賊乃是本分。
在朝鮮期間他們更是雙饷待遇,一名普通士兵的年薪達到約43兩,遠遠超過國內一般水平。更何況在平壤之戰中,明軍李如松曾經許諾:先登上城牆的賞賜300兩。
但平壤之戰過了接近2年了,不但先登賞銀沒有兌現,連應該拿的雙饷也有拖欠!(當時冒死和他們一起登城的吳惟忠副總兵得了個可笑的20兩賞銀。)忍無可忍的士兵們鼓噪着要讨個說法,這樣本來就和他們有宿怨的北軍軍官們就趁機發難,用兵變的名義殺人,從而為大明節省了這筆費用。
一個袁崇煥之死被人記了數百年,到今天還是網絡熱點,因為他是文官。那1700名欠饷士兵之死的事情卻傳不了一年,甚至明史裏也覺得沒必要專門記錄。只是在某些奏章裏有記載,本來對邊塞從軍應募踴躍的浙江兵,在這件事後逐漸減少。
表面的原因,主要就是“要賞結聚”“挾增月饷”,就是說索要欠饷,聚衆鬧事。
明朝中期的軍饷,募兵制一般是每年十八兩。但是東征援朝是出國作戰,有所不同。
當時經略軍務的宋應昌将南軍的軍饷提高了一倍,達到了一年43兩左右。宋應昌在職的時候,都是按此标準執行,問題是他在第二次抗倭援朝戰争前被解職,截止被解職時,軍饷并未全部按期發放,這成為了隐患。
南兵鬧事的原因,并非全部是軍饷,還有第一次入朝作戰時該得的賞金,大家都是提着腦袋拼命去的,仗打贏了,事先答應的賞金卻遲遲沒有,這當然讓人寒心。
宋英昌優待入朝士兵,這是好的,能提高士氣,激發戰鬥力。但他離職時沒有做好善後,宋英昌自己也在給內閣首輔王錫爵的書信中說:平壤首級大功未賞,各軍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
兵變主要內因
欠饷本是軍中常事,士兵不滿乃至鬧事也并不鮮見,為何立下汗馬功勞的南兵會被屠戮?這牽涉到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軍中的南北之争。
南兵都是戚繼光從浙江招募的子弟兵,前後共有二萬餘人。
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戰争中,吳惟忠率領薊鎮3700多南兵參戰,表現出色,有目共睹。
朝鮮人在《朝鮮宣祖實錄》中如此評價南兵:
“南兵不顧生死,一向直前,吳惟忠之功最高。”“游擊吳惟忠領南兵進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軍力戰,死傷尤多。”
但是,軍隊的統帥李如松,是北軍的靈魂人物,他在戰後的軍功分配上,明顯偏向北軍,把原來南軍的戰功按到北軍頭上,比如平壤的“首敘”之功,是吳惟忠奮勇先登,結果到了最後,被歸到了北軍将領楊元頭上。
不得不說,李如松這手做得不地道。南兵将領王必迪甚至直斥李如松“不智不信不仁”,下級當面斥責上級,可想而知南兵的憤怒。
南兵沒有得到公正對待,事先許諾的獎賞也不到位,明軍內部北兵與南兵之争愈演愈烈,碧蹄館之戰後,李如松戰意消沉,沒有進一步的軍事動作,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戚繼光為何特意要将南兵調到薊鎮,就是想以此作為垂範,整頓北兵的風氣,籍此來練兵,戚家軍的軍紀有目共睹,即使在之後出國的遠征中也同樣如此。但這樣做,必然會傷害部分人的利益,同時也造成南北兵之間的矛盾,戚繼光在的時候,還不至于表現得很明顯,等戚繼光去世以後,裂縫就越來越大。
南北的争端,并不局限于軍中,朝堂之上,也是如此。張居正、戚繼光去世後,繼任者多是北方人,多少會偏向老鄉。等支持南兵的宋英昌被罷官後,南兵更加勢單力孤,無人為他們說話,前面答應的饷銀,更是不知找誰去要。
薊鎮總兵王保,當然就是北方人。
所以,薊鎮兵變的爆發,就是南北矛盾的爆發,在這次兵變中,缺少支持的南兵被心懷怨恨北方軍官誘殺,随後扣上個謀反的罪名,這才是事實的真相。
兵變深層原因
不過如果再往深層次探究,這就反映出明朝軍隊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弊端。
明朝軍事,從起初的軍戶制到随後的募兵制,發展到萬歷晚期,已經運行得越來越艱難,從根源上,又與財政息息相關。仰賴張居正改革十年間,國庫得以充實,不過三大征一打,就再也沒有恢複。
“皇帝不差餓兵”這個說法,估計深居皇宮的萬歷沒有聽說過,崇祯應該也沒有聽說過,正是他們不斷的差“餓兵”,“餓兵”都變成了“賊兵”,最後,大明終于亡于“餓兵”手裏。
薊鎮之變,其實可以看做是對萬歷,對明帝國的一個警告。身為九邊重鎮之首的薊鎮出了這樣的事,一定是哪些制度、哪些環節上出了問題,這樣繼續下去,大明帝國很危險!
可惜,萬歷和群臣選擇性忽略了。
這件事的罪魁禍首薊鎮總兵王保,事後受到了什麽追究?
什麽都沒有,王保随後替代董一元鎮守遼東,卒于任上,死後贈左都督。
南兵将士們半年前剛剛為國家遠征歸來,在異國土地上揚名立萬,在戰争中奮勇當先。可是,這些軍人,沒有在戰場上死于日軍槍林彈雨,卻在駐地被自己長官誘殺。國家就是這麽對待功臣的?這是人幹的事嗎?
薊鎮之變後,戚繼光花費十六年,苦心積慮構築的防線很快失去了作用。三十多年後,皇太極指揮清軍長驅直入,大明的北邊各重鎮不堪一擊。在清軍面前,它們仿佛已失去了屏障作用,只剩一道道邊牆。
這是萬歷二十三年,也就是1595年的事情,再過49年,明朝滅亡。